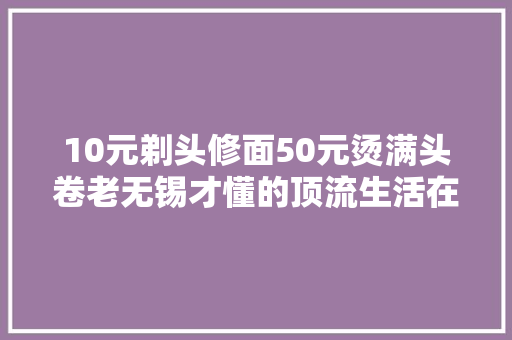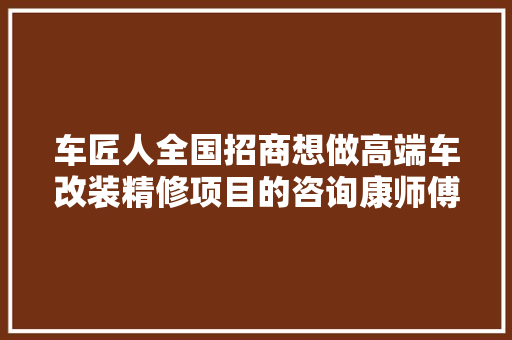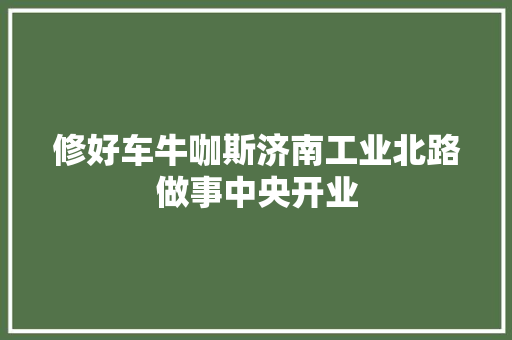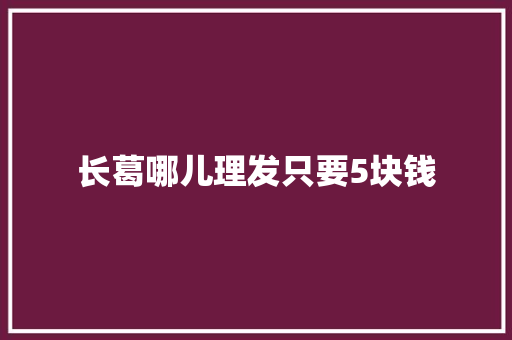不过,随着韶光的推移,过去司空见惯的老行当儿,如今只能在影象和笔墨里找寻。作为一位隧道的“老北京”,孟繁强年复一年地写下自己的影象,讲述着他经历的岁月和变革。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看看他笔下老北京的做事行当儿是什么样的。
以下内容选自《老北京故人往事》,较原文有删节,已得到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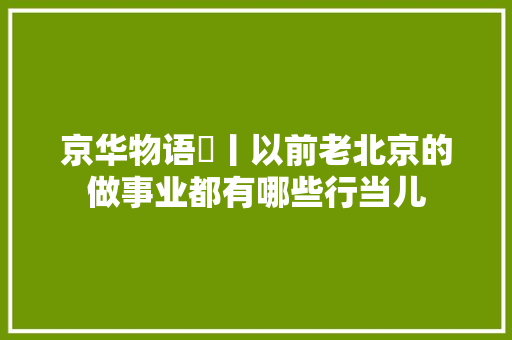
《老北京故人往事》,孟繁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版。
原文作者丨孟繁强
摘编丨安也
绱鞋铺
老北京有句口头禅:“脚底下没鞋,穷半截!
”说的是人们日常穿着打扮,脚下必须配一双适宜的好鞋,才能衬托出全身的衣着衣饰更加靓丽精神。如果全身穿着时髦阔气,可是脚下却穿一双平庸破旧的鞋子,整体看来就显得高下两截,不伦不类,引人讥笑。想想很有道理,这就好有一比:家家都有陶泥花盆,单独看一眼很不好看,如果您把破花盆放在花梨紫檀的架子上,破花盆急速就像代价连城的古董,以是脚上的鞋便是这花梨紫檀的盆架!
我小时候,街上有修旧鞋的摊子,也有“绱(shàng)鞋”的店铺,当然“绱鞋铺”也管修理旧鞋,但是他们紧张的业务还是“绱鞋”。所谓“绱鞋”,说白了便是“来料加工”——顾客在家里按自己的喜好,做好鞋面纳好鞋底,然后送到“绱鞋铺”加工完成一双俊秀的布鞋。诚然,过去的“绱鞋铺”是与百姓生活中息息相关必不可缺的做事行业。
旧时,除了一些“摩登人物”穿皮鞋高跟鞋,一样平常人还是穿家里自己做的布鞋。家里女人从十七八岁姑娘时就开始学做布鞋,直到出嫁变成白发老妪,一辈子都在为百口人制作各式冬夏单棉布鞋——做鞋是女人们炫耀自己勤俭持家和机动双手最好的展示。布鞋一样平常都是泰西入口的玄色纯毛“崇福呢”或“礼服呢”做面料。
这种面料色紧紧固,光亮细腻,是做高等服装和鞋面的上好质料。自己做鞋,工序繁杂,每道工序仔细制作,缺一不可。首先要打“袼褙”,家里的旧衣裳和各色旧布头便是打“袼褙”的上好质料,先打半锅稀糨糊,找一块大些的木板子,把布铺在板子上,用手掌蘸着糨糊均匀抹在布上,布就贴贴实实粘到木板上。再拿另一块布与刚才的布,对缝仍是如此操作,整块木板糊完了一层布再糊一层布,直至糊了四五层,层层糨糊层层布就可以了,糊了布的木板子立在院子里风吹晒干,过两三天干透了,顺木板的边缘逐步揭下来,便是一张完全的“袼褙”。
开始做鞋了,女人拿出早已画好的纸样,在袼褙上剪出了鞋面粗坯,再把粗坯粘到鞋面面料上顺边剪下,另一壁再粘好白色鞋里布,用细细的针线把鞋面鞋里与“袼褙”缝在一起,把边缘修剪整洁,然后用玄色斜纹布条延缝鞋口,一双鞋面就做好了。
比较之下做鞋底就比较费时。剪好鞋底形的袼褙两层粘在一起,用白布包边糨糊粘牢,这算一个“单元”,七八个这样大小同等的“单元”再全部叠粘在一起就成了名副实在的“千层底”,放在重物下压实,过四五天鞋底就全部干透压平,粘好后的“鞋底”大约1.5厘米厚,白白的鞋底整洁规范,但这还不是真正的“鞋底”,还须要用麻绳千针万线紧密纳实才能成为一双结实的鞋底。
《城南往事》剧照。
“纳鞋底”是最需功夫技巧又费韶光的工序,坚实的“纳鞋底”须要结实的麻绳。
女人们去“麻刀铺”买来“麻皮”,耐心用梳头发的篦子把麻皮劈成细细的麻筋,再用专门打麻绳的工具——“拨槌”把三四根麻筋续在一起,打成单股麻绳,再两根拧在一起成为真正能用的麻绳。用这样啰嗦辛劳劳作打好的麻绳,再一针针纳鞋底。鞋底纳一针挨一针,瓷瓷实实板板整整,纳好的鞋底再用铁锤砸实,就可以和鞋面一同送到“绱鞋铺子”去加工布鞋了。
“绱鞋铺”的师傅都是男人,别看男人五大三粗,做起这样精细的活计就须要技巧和力气。绱鞋分“正绱”和“反绱”,所谓“正绱”,便是鞋面弯进去,与鞋底联合处整洁不露痕迹。我们现在一样平常的皮鞋都属于“正绱”;所谓“反绱”,便是鞋面平铺与鞋底联合在一起,俗称“飞边儿”。冬天的棉鞋鞋面很厚,不能翻转,就必须反绱。
“绱鞋”的工序更加繁芜,用一个木质脚形“鞋楦”先把鞋底翻过去,用钉子钉在鞋楦上,再把鞋面打湿,鞋里朝外包在鞋楦上,用麻绳收口,鞋的各处都平均平实了,就开始了真正的“绱鞋”。待一针一线把鞋面与鞋底完备缝合完毕,鞋就绱好了。启出钉子,拔出鞋楦,但这时的鞋面鞋底都是反的,这就须要更强大的技能——翻鞋!
鞋匠把整只鞋泡到水盆里,待鞋底吃透了水分,变得优柔,就从鞋跟开始逐步用力翻转,翻转的同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能破坏鞋面任何一部分。全体鞋翻好了,再把鞋面浸湿,放进两半截的鞋楦,加进“木楔子”,使鞋楦前后牢牢把布鞋“撑”实。这样要经由五六天的韶光,等布鞋完备干燥了,拔出鞋楦,便是一只都雅像样的布鞋。
为了使布鞋的黑鞋面白鞋底更加精神耐看,还要用一种“白膏子”均匀抹在鞋底边缘,再用钢质“压子”划压白膏子,压过的鞋底边缘就发出了白亮闪耀的光芒!
等到顾客前来取鞋,鞋匠从架子上拿下新鞋,用刷子刷去浮土,一双漂俊秀亮干干净净的新鞋就交到顾客的手里。费工费时费力,要眼要脑要力!
工序这么繁芜啰嗦,技能这么高超,可是当年绱一双鞋的加工费也只够买六七斤玉米面!
从前,人们穿家做的布鞋,小孩穿“老虎”鞋,老人穿“老头乐”鞋,老太太穿黑缎尖口鞋,女人穿皮底缎面绣花鞋,男人穿圆口“便鞋”,姑娘穿“扣袢”鞋,学生穿“五眼”鞋,卖力气的穿“洒鞋”……这统统都是女人们一针一线劳动所得,都是“绱鞋铺”的鞋匠至高的技能所得!
思想起来中国民间的“布鞋”“绱鞋”真是凑集了劳动人民深情厚意与无穷聪慧,可是这伟大的聪慧却都在短短几十年间里,随时期大潮逐渐被社会无情地淹没和遗忘!
磨刀老头
“磨剪子嘞——抢菜刀——!
”
这高亢的吆喝声您一定听到过,歌手刘欢还有一首歌《磨刀老头》,歌里就有磨刀人的吆喝声。
如今,大家都把这磨刀的吆喝当作老北京的韵味欣赏,当作老北京的民俗尽情回顾。磨刀人大部分是老年,有谁能知道当年那些磨刀老人事情的艰辛与生活的苦难?
他们在屯子勤恳耕种劳作,强挺着欲折的老腰,为自己也为儿孙拼着老命,挣得一碗还算咽得下去的粗饭;为自己也为百口,盖得一间还能遮风避雨的土房。
农闲时农夫不闲,不愿在家里给儿女造成拖累,就在自己已经枯瘦的肩膀上扛起那干硬的板凳来到城里,去做那自己还能撑得起的活计,由于城里人须要他们,他们也从城里人那里,换回一点强拼苦挣得来的一点响当当的零散碎银。
人们提到磨剪子磨刀,只想到他们大声吆喝,实在这一行当有两个派别。
一个派别是:吆喝带打响板;一个派别是:肩扛板凳嘴吹小铜号。
现在一样平常见到的便是吆喝带打响板的一派,和从前不同的是,现在吆喝远远不如从前的吆喝字正腔圆味道纯洁,手里的响板也是破铁皮,做得粗糙不堪。从前的响板做工很讲究,三扇铁页,上窄下宽,每片顶端有两个洞孔,用红布等间隔片片串起,最上边是一个铜铁环,手拿圆环前后一晃,铁片碰铁片,发出“哗哗”的声音。
每当在家里听到街上的响板,我就知道一定是磨剪子磨刀的来了。再听他们那抑扬抑扬的吆喝,声音悠扬,就像七月暑热吃了一个冰冻的凉柿子一样舒畅顺畅!
那另一派吹号的不知是什么时候天生的,那黄铜制成的小号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也不大随意马虎考证,他们为什么要用吹号作为叫卖也不明白,反正,这一派磨剪子磨刀的叫卖工具是吹号。他们肩扛板凳,板凳上绑着磨刀石,手拿一个黄铜的小号,和现在铜管乐队里的千篇一律边走边吹,吹出的声音也没有音符和旋律,只有一声长鸣溘然一响震得吓人!
在年节前,尤其进了尾月,家家买肉做菜更须要利刀利刃,磨剪子磨刀的买卖就格外火热。不管是打响板的还是吹号的,不管是推着独轮车还是肩扛大板凳,有了买卖就把家什靠近墙边,骑上板凳把菜刀卡在磨板上,磨刀石淋上净水开始磨刀。有时家里菜刀用久了还须要“抢”,“抢刀”铁杆一尺多长,两头有小木把手,中间一个四五厘米长非常锋利的“抢刀”,把菜刀立起来,用“抢刀”顺着菜刀的刃口用劲地切刮,生生把菜刀两面多余的钢铁给刮下来,使菜刀薄而轻利而刃。
一把菜刀磨好了,撤除了锈痕,发出了亮白的寒光!
手艺更奇的是还可以“吹发立断”,不过我只听说却没有见过,不知真假不能胡说!
磨剪子,磨刀,修理刀剪,花不了多少很多多少银钱!
请巧厨师,快刀生花,煎炒烹炸;
让妙裁缝,飞剪云霞,衣衫袍褂!
各行匠人在北京的大小胡同走街串巷,五行八作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修理雨伞
冬天恨寒冷,大雪压青松。
秋来落叶怨,哀树孤雁鸣。
春暖多刮风,浑天地也蒙。
只把夏季盼,又怕蚊虫叮。
早晚湿闷气,暑天热蒸腾。
晴天一身汗,阴天云雾浓。
还要天落雨,倾盆江河生。
欲往东门去,涉水不轻松。
擎支大雨伞,衣服洇湿烘。
举头一看:噫!
雨伞漏了一个大窟窿!
北京的雨水只是“阵雨”,绝没有南方那样的连绵不断令民气烦的“梅雨”。阵雨过后,乌云散去,阳光复出,树显油绿,花更浓喷鼻香!
湛蓝的天空就像纯美的宝石,天边一弯七色彩虹。地上统统清新干净,院子里瓦灰的墙壁,火红的榴花,淡粉的初荷,艳紫的莲瓣,翠绿的新叶,石青的苔藓,闪白的猫儿……这统统展现出一幅清美的水彩图画!
“修理——雨伞!
”胡同里传来修理雨伞的吆喝声!
下雨之前,人们想不起来雨伞。大雨来临才拿出屋门背后的雨伞,打开一看,却早已被该死的耗子咬了一个破洞!
过去的雨伞是油纸雨伞,竹子的伞杆,竹子的伞骨,只有伞面是桐色的“油纸”,虽然有些笨重,但是利用起来还是得心应手。
“修理——雨伞!
”修伞匠人的叫卖没有“响器”,单凭一副咽喉似叫似吼,声音前高后低干艮倔闷,嗓音洪亮穿墙透户。修伞匠人肩背一副“褡裢”,前面口袋装动手钻、刀铲、桐油、刷子;后边的口袋是竹管、竹签、铅丝、麻绳和“高丽纸”。
打开大门叫学习伞匠人,他就在门道里摆开架势修理雨伞。支开雨伞展现破洞,匠人逐步拿出质料工具,先在伞面高下破洞周围刷了桐油。待桐油微干,又拿出高丽纸用手撕下一块,带着毛边贴在破洞之上,再用刷子蘸着桐油刷一遍。白色的高丽纸便牢牢粘住了破洞,同时也由白色变成了与伞面完备同等的桐黄色!
听说那桐油里掺进了猪血,变得既有黏性又不怕水浸,棉质的高丽纸也极具韧性,耐折耐磨耐久不坏。
如此这般再贴一块高丽纸,再刷一次桐油,上边的刷完,反过来再刷伞里边的,如此三四次,那雨伞里外修理得平平整整,破洞不见了,俨然是一把整旧如新的雨伞!
连续去经风雨见世面了。
修理雨伞还可以换伞骨,换伞把,换全体伞面。价钱要比买一把新雨伞便宜不知多少。
夏天是修理雨伞的时令,而且匠人只修竹制雨伞,修理其他的伞便是其他的行当了。
锔碗匠人
老北京不管贫富,居家过日子谁家有东西坏了旧了都要修理,可不像本日,不管什么东西坏了一扔了之,随便扔东西在当年一定被算作败家子儿,遭人讥笑!
过去人们对那些修理业者,每天见面也就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司空见惯天经地义。如今这些过去的民间技艺都变成了社会的民俗,变成了纪念的过去,变成了传承的知识,变成了本日的回顾!
六十多年前,我家老少四代人口浩瀚,上至七十多岁的“老祖”(爷爷的母亲),下到比我小两岁的堂弟,房多院深,日常用品自然也多。平时人多手杂,免不了什么东西碰了、摔了,或是什么东西日久天长须要修理。奶奶房里案上摆了一对乾隆年间群桃祝寿珐琅彩大瓷盒,天青的底色,上面画了许多翠粉色鲜鲜大桃,蟠枝绿叶陪衬煞是好看,放在案上是持重实用又清心文雅的摆设。平时搁些时新糕点,不管存放多久不霉不干。
《茶馆》剧照。
瓷盒又大又重,又亮又滑,一次,奶奶去给老祖取点心,稍欠妥心抱在怀中的瓷盒盖子溘然滑落,“嘭”的一声!
我们跑去一看,地上已是粉碎一片!
奶奶神色吓得惨白,不知所措,匆忙蹲下身子,心疼地捡起残片,老祖听见声响走出房间,见这不堪景象,心里极不高兴,也只好看在奶奶已是有了孙子的人的份上“哼”了一声讪讪说道:“碎碎(岁岁)安然吧!
”沉着脸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家人拿来扫帚,奶奶亲自归扫碎片,边扫边说:“听着街上锔盆锔碗的来了,千万叫进来!
”我们小孩子就跑到门道里去等那“打小锣的”锔碗匠人。
以前谁家有的瓷器陶器摔了,小从酒盅小碟,大到洗衣盆大水缸,不管裂成多少瓣,在锔盆锔碗匠人手里不算回事,都能把碎片用铜锔子修睦。样子虽然不大好看,但照常利用。锔盆锔碗的行头是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一个带抽屉的小木柜,抽屉里放着质料和工具。木柜上面有一个木头的提梁,提梁的中间挂着一壁锃亮的小铜锣,铜锣的两旁又分别用细线绳挂着两个小铜球,作为锣锤。匠人挑起担子一走,那小铜锣摇来晃去,碰到小铜球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以是也叫“打小锣的”,那也便是“叫卖”的声音。担子的另一头是个小木凳及其他零星的用品。
胡同那头传来了“丁零当啷”小铜锣的声音!
我跑出门道瞥见那边真的来了锔盆锔碗的,挑着担子一摇一晃逐步走近。我大声喊叫把那匠人领进门,在门道里放下担子。又跑进内院叫奶奶,奶奶知道“修理职员”来了,从屋子里拿出用包袱皮兜着的瓷盒子碎片放在匠人面前,匠人拿起往一起对碴,见不缺不少,便先和奶奶讲起价钱——大约用多少个锔子、得钻几个眼、一共须要多少钱,等等。经双方讲好价钱,匠人就开始了修理事情。
身为小孩子的我好奇,蹲在一旁呆呆地看。他在腿上铺上了一块厚厚的大布,从身后的架子上拿下了一副“金刚钻”,又把瓷片用两个膝盖夹住,左手拿一个白瓷小酒盅,扣在“金刚钻”轴的上端,右手拉弓子。那弓子的皮绳绕在轴的中间,一推一拉,就像拉胡琴,开始在瓷片的边缘钻眼。
三下两下,瓷片上就涌现了一个小洞,洞的周围还钻出许多白色粉末。等把两块瓷片的小眼都钻好了,又从抽屉里拿出了小铜锔子。铜锔子大约是一厘米,中间宽两头窄,两头各有小钩,把两头的小钩按在两块瓷片钻出的小眼里,再用小锤子轻轻地敲击两下,锔子便牢牢地锔住了分裂的瓷片。然后在另一个小盒子里,用手指挖出白色的腻子,抹在锔子周围固定好了,一个锔子便完成了,接着再锔其他的锔子。
天都擦黑了,大汉还是那么负责仔细地事情着……快吃晚饭了,大汉叫奶奶:“老太太,您看看,锔好啦!
”奶奶闻声过去,从匠人手中接过锔好的瓷盒盖子仔细不雅观看,已经摔碎了不知多少片的残物居然被匠人一点不落地全都锔在一起,成为一个整物,数了数一百多个锔子,用手轻轻晃了一下丝毫不松,奶奶不由得赞了一声:“妙手艺!
”
大汉站在一边用毛巾擦着脸咧着嘴笑,接过奶奶递过去的工钱就要走了,奶奶看太阳已落,忙叫家人从厨房拿来两张烙饼、一碗大米粥、一碟咸菜送到大汉面前,大汉先是推辞,后来大概确实饿了,千恩万谢后蹲在地上吃了起来。
后来,那对大瓷盒一贯摆在奶奶房里的案子上,盒子上一个个铜锔子就像闪烁的金星,看起来更有无限的韵味!
多年往后,乌云满天,狂风雨降临,臂膀上戴袖标的“红卫兵”来了,他们横眉立目、气势汹汹拿着皮鞭和木棍,不由分辨理直气壮!
家里的东西被砸碎了,乾隆年的群桃祝寿珐琅彩大瓷盒被砸碎了——彻底地碎了,碎得无影无踪!
从此往后,再也没有人去锔盆锔碗。锔盆锔碗的匠人不见了,锔盆锔碗的手艺或许失落传了,锔盆锔碗这一行当或许消逝了,留下的只有残余在头脑中的影象!
剃头挑子
农历仲春,男人们可以剃头理发了。
有一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
”是形容“一厢宁愿”。古老的“剃头挑子”已经消逝良久了,年轻人没见过剃头挑子,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剃头挑子”是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木制的下大上小的矩形柜子,设有两个或三个抽屉内装各种剃头理发工具,又可以当作顾客理发的坐凳;另一头是一个木架,当中安装了一个小火炉,炉子上坐有黄铜洗脸盆供顾客热水洗头润发。与木架相连又安装了镜子和可以搭毛巾的装置。顶端还挂了“杠”刀用的磨刀牛皮条,洗脸盆旁预备了“喷鼻香番笕(喷鼻香皂)”,以是歇后语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剃头匠人挑起担子走街串巷,手拿钢制“唤头”沿街拨响,声音悠远震颤,四合院里须要剃头的老少爷们只要听见“唤头”的分外金属颤音,就知道是剃头的来了!
《剃头匠》剧照。
民间流传“正月剃头去世舅舅”这样的民俗传统,一贯延续到本日恪守不变。难道真的在正月里剃头会去世去舅舅?原来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误传。
汉族自古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论调,对自己的头发更是保护有加,不能胆大妄为,如果损伤了头发切实其实便是剔命,是对父母极不尊重的背叛!
以是明朝以古人们一贯束发于头顶表示先人父母的至尊。
清朝顺治初年,原来明朝的文人墨客市井百姓仍旧怀念大明王朝多年的旧制,对付清朝天子敕令所有汉人一律剃发束辫的命令反感非常。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的杀无赦令,使汉人陷入极度惶恐。但是汉人仍旧思念旧的礼数,虽然已经被清人统治,但是汉人认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用正月一整月不睬发的形式思念旧的章法,以抗议清朝强行剃发的专治行为,当时谓之“正月不剃发,以示‘思旧’”。但是韶光久了,流传得广了,不免涌现偏差,传来传去就逐步就变成了“正月不剃发,剃发去世舅!
”这一可笑又奇怪的民间习俗。
“正月不剃发”的民俗既然已经被广大民间所承认,以是人们就规规矩矩遵守这一荒谬的民俗,头发长了就等待正月过了,到了农历仲春初再踏踏实实地舆发理发,这就派生出了“仲春二,理发日”这一清爽的日期!
一副担子唤吆喝,铜盆清汤偎热火,去辫留头满清起,精神抖擞又发达。白布围巾似呆鹅,街边坐稳迷眼佛,快刀斩去烦恼丝,白亮油光如弥陀。
《剃头匠》剧照。
老北京有传统的剃头挑子、廉价的剃头铺和当时很新潮的“理发馆”。新式的“理发馆”一样平常都是新派人物、学生、职员等人的去处,而老派守旧的人绝不会去门前。那些转着红蓝白三色“走马灯”的外来户,认为从理发馆出来的人都是油头粉面妖艳无比,且世风日下全不像年夜大好人,归根到底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剃头”家什最好不过!
剃头匠人挑起担子稳稳走街串巷,左手拿一个像大夹子一样的钢制“唤头”,右手拿了比筷子稍粗的铁棍,插在唤头中间往前一拨,“唤头”就发出分外的“嗡嗡”声。那声音似钟似罄,远处听声音悠远悠扬,悦耳动听;近处听却是耳根发麻,浑身鸡皮!
北京电视台曾经请了一位“讲古”的人在节目里信口说“唤头”别称“惊闺”,这就十分欠妥。“唤头”就叫“唤头”!
以是讲说过去的事情要准确无误才是正理,不然修改历史歪评胡说,就有不懂装懂贻误后代的嫌疑!
清代以前没有“剃头”,只有“梳头(篦头)”行业,梳头的匠人穿着干净利索,腋下夹一蓝布小包袱,装着刀、剪、梳、篦、头绳、辫梢及“刨花”。
《剃头匠》剧照。
满族人统治下的中国,男人脑后都梳一条大辫,哪家的男人叫来了梳头匠人,先用剃刀把脑袋前半部的发茬剃光,再推拿通脉,打开拓辫洗净,用细竹篦仔细通发梳理,梳掉碎发往后,抹上“刨花水”,再次用竹篦梳光理顺,编好发辫,续上辫梢,接好流苏。编完的辫子看上去油光水滑,一拖落地,全体人也增加了无限风骚倜傥!
清朝灭亡往后,袁世凯做了大总统。“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人们被逼迫剪去辫子。可是辫子没有了更觉丢脸至极,脑袋前半部寸草不生,右半部齐肩短发,走起路来一飘一摇,这便是人们戏称发型为“马子盖”的典故!
张勋复辟失落败,“发型革命”又来“二茬”,这才生出了“剃头挑子”行当,直至后来的几十年,剃头挑子已经蔚然成风,遍布全国各地。剃头匠人为客人剃头,围好大布,先用热水闷湿头发,拿出锋利的剃刀在“杠刀皮”上翻飞两面“啪啪啪”背完快刀,左手扶住头皮,右手准确下刀,手稳,刀快。只见:头顶寒光闪闪,烦恼顿时全完。
顶上光秃无垠,脚下生出毛毡。值得一说的是,这样分外的剃刀现在已经彻底不见。刀子用精髓精辟锋钢打制,大约1.5寸宽,2.5寸长,有可折叠的竹管刀柄,拿在剃头匠手里利用自若锋利无比,真可说吹毛断发!
剃头匠为客人剃净头发收了刀具,再拿出“耳挖勺”,依次把客人的耳屎挖得干干净净,客人闭起眼睛舒畅得龇牙咧嘴。这时铜盆的水也热了,客人在盆边低了头,匠人手撩热水,仔细给客人洗净擦干,客人直起身子,匠人又使出十八般身手在客人的头、颈、耳、肩、背、臂,尽情地推、捏、拿、揉、打、掐、摁、摇,利用各种推拿推拿功夫。此时再看那位客人,像是散了架子腾云驾雾了。到此,剃头的全部过程就完结了,客人晕晕乎乎给了钱钞,道声“辛劳!
”站起身摸着秃顶走了。
《剃头匠》剧照。
有一句俚语:“饱沐浴,饿剃头!
”剃过了秃顶肚子真是饿了,晃着亮亮的“电灯泡”去饭店叫了一盘炒菜、二两烧酒开荤去了!
还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便是所有的剃头匠人身怀一件别人不会的技能——捏骨接伤!
谁家有摔伤、脱臼,只要伤者咬牙禁得住“疼”,则请来剃头匠人,三下两下就能治愈。剃头匠人沉住心气,稳拿稳推,捏罹病人吱哇喊叫,满头大汗!
剃头匠捏准部位猛地一下,病人大叫一声昏去世过去。家人赶忙手掐“人中”,头蒙凉水毛巾,不一会儿伤者缓过气来,逐步活动,就可以运动自若了。剃头行业捏骨的规矩是一钱不受,只要病家谢过转身就走。这也彰显过去与人为善的社会良好风气!
如今,剃头挑子早已不见。大街小巷尽是当代的超新式的“美发”“发廊”“发屋”,做出的头发也是新潮时尚,年轻人尽做潮流时尚的“先驱”。
剃头挑子再见了!
你将永久留在我的影象里,留在浩瀚历史记录的史册中!
原文作者丨孟繁强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校正丨危卓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