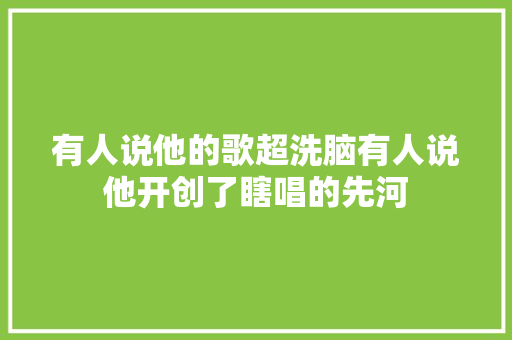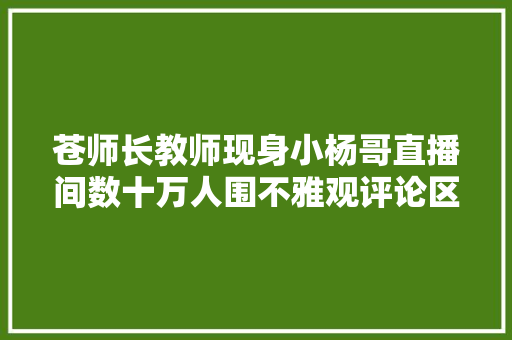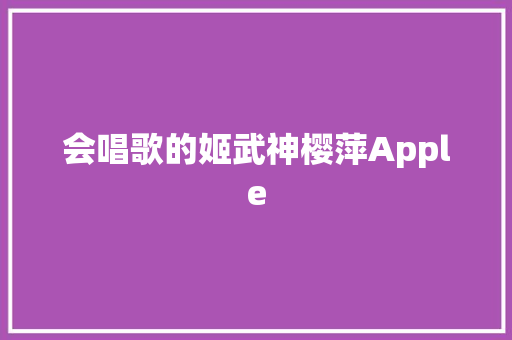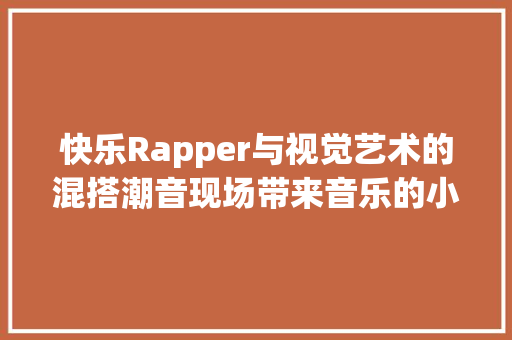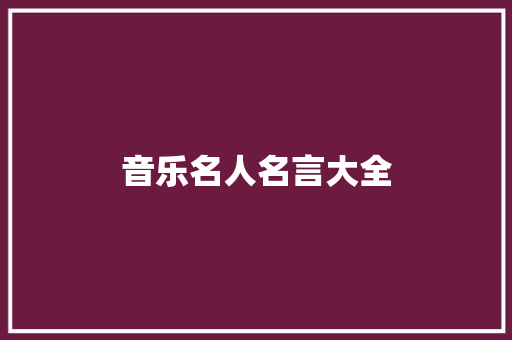汪曾祺曾提出疑问:“样板戏”是否蕴含可借鉴的履历?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样板戏”在考试测验办理当代生活与戏曲传统演出程式之间的抵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显著造诣,使得京剧表现当代生活成为可能。
最初的“样板戏”,如《沙家浜》和《红灯记》,其创作者仍试图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行。他们创作了贴近口语的唱词,希望唱词能充满生活气息,展现人物性情。部分唱词还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例如《沙家浜》中的“人一走,茶就凉”,以及《红灯记》中的“穷汉的孩子早当家”。然而,后来的“样板戏”唱词却逐渐被空洞的“豪言壮语”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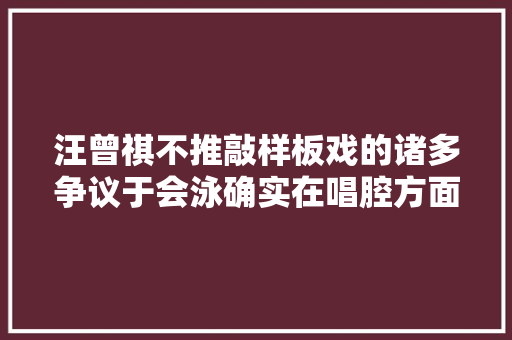
只管“样板戏”的某些唱腔存在不敷,乃至有一位老演员在听过一出“样板戏”后戏谑道:“这出戏的唱腔是顺姐的妹妹——别妞(别扭)。”指出其行腔高低不合规律,多数“样板戏”都方向于利用高腔,险些所有大段唱的结尾都是高八度。
汪曾祺说: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个中有些唱腔确实悦耳动听。于会泳在音乐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成功地将地方戏、曲艺的旋律融入京戏中,他所总结的慢板大腔的“三送”(同一旋律,三度移位重复)理论,极具洞察力。他设计的《杜鹃山》中的“家住安源”唱段,哀婉动人,深受不雅观众喜好。在《海港》中,“喜读了全会的公报”的“二黄宽板”唱段,更是对京剧唱腔的一次重大打破。不考虑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于会泳确实在唱腔方面贡献很大。
对付京剧加入泰西音乐和配器,有人持反对见地。但许多从事京剧音乐工作的同道都深感,传统的“四大件”(京胡、二胡、月琴、三弦)实在过于单调,加入配器势在必行。在这方面,于会泳做出了主要贡献。他设计的幕间音乐与了局的唱腔相折衷,使得音乐能够自然地引出下一场戏,不显突兀。《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幕间曲便是其精彩代表。
1964年全国京剧当代戏不雅观摩大会之后,于会泳于1965年3月28日在《文申报请示》上揭橥了《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做事》的文章,高度概括了京剧《红灯记》的音乐成就。从60年代开始,于会泳当选中参与“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是他充分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艺术上显露头角并施展才华的主要机遇。
他把多年来对民间音乐的研究与理解、在学院中学到的泰西音乐知识及新的创作理念、技法以及中国民间音乐创作手腕都利用到了“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当中。他的创作与实践代表了一个期间中国音乐尤其是京剧当代戏音乐的创作风格,其所展现的时期风尚也得到了中国广大公民群众的认可。
由于于会泳全面的艺术教化和技能功底,使得他在唱腔音乐创作上更加得心应手。他首先冲破了行当界线,在旦腔中融入了生腔成分,使得旦角唱腔既展现出奇丽之美,又透露出刚健之毅。他打破了传统唱腔程式,融入了西方音乐创作思维,并借鉴西方音乐的各种手段来创制新唱腔,使得戏剧所表现的人物性情及音乐形象更加光鲜统一。
他还在传统根本上创建了许多新的板式,为西皮、二黄板式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的探索。从《海港》的初步实践到《龙江颂》和《杜鹃山》的逐步成熟,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高峰,创造出了一大批既有传统神韵又具有时期风采的京剧唱腔音乐,成为中国京剧当代戏音告成长的主要标志。
京剧“样板戏”中第一个利用中西稠浊乐队体例的剧目《智取威虎山》也是由于会泳等人共同完成的。于会泳不仅在唱腔创作上发挥着重要的浸染,而且从唱词、舞台调度及整体艺术上都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并起着主导浸染。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龙江颂》和《奇袭白虎团》等剧目和电影的紧张音乐灵魂,均出自于会泳之手。他奥妙地将泰西作曲技法与演奏色彩,与中国民歌素材和京剧韵味相领悟,首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其横溢的才华令各界人士为之折服。
在过去,京剧唱段的设计紧张由演员与琴师通过磨合来完成,因此,唱段每每有着明确的曲牌或套路,强调传承而缺少创新。然而,于会泳所创建的“音乐布局”则险些参与到了整体的编剧和构造体系中,类似于西方歌剧的音乐为先的创作样式。
这种创作办法所带动的音响设计每每带有承前启后的气候,除了局部唱腔的活灵巧现,更有成套的设计思路和主题腔调贯穿全剧。他提出了“广度、深度、层次地表现人物详细情态的三种办法”,这种立体化的创作思维和能力,将当时的主旋律文化推向了历史的顶峰。以下是对几个于会泳作品案例的解读:
案例1: 在《海港》中,方海珍的“喜读了全会的公报”唱段,按照程派唱腔进行设计,却完备采取了泰西化的作曲和演奏风格,这一唱段乃至被大量改编成小提琴钢琴演奏曲,广受欢迎。
案例2: 在《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这段唱段,于会泳奥妙地将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憨实的圆号交织在一起,将杨子荣策马扬鞭的场景与英雄气概刻画得维妙维肖,令人印象深刻。
案例3: 在《杜鹃山》中,柯湘的唱段如“家住安源”、“乱云飞”等,都将当代京剧创作推向了新的经典层次。电影上映后,杨春霞也因此成为了大众的至尊偶像。
案例4: 《沙家浜》中著名的“智斗”一段,更是将三个人物的性情和生理活动进行了交叉叠加的设计,这种新颖的手腕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群众性文艺的艺术高度。
除此之外,《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作品也都有大量的亮点。
同时,于会泳的作品也触及了传统的审都雅。在京剧唱腔的片段中,其韵腔表示着京剧音乐特有的旋律感。落在强拍上的任何字都会得到适当的修饰,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气。如果在原作上进行调度,很可能会削弱唱腔原有的戏曲风格。然而,于会泳却敢于寻衅传统,对多处经典唱段进行了修正。
例如,他重新修正了昆曲《永生殿》、《小宴》(斗鹌鹑)以及《思凡》(山坡羊)等唱段的唱腔,使唱起来更加顺溜、不那么拗口。然而,这些昆曲唱腔已经唱了几百年,没有人去质疑过。他通过调度和编曲,将原来的风格表现从普通易唱的角度进行了优化,降落了唱腔难度。
他还提出了修君子们心目中的经典唱段《空城计》中的西皮慢板的建议。他引用了余叔岩《空城计》中的“散淡的人”一句,认为原腔中的“的”字没有弱化处理,该当进行重新修正。他在“散淡的”中“的”的节奏上利用了次强拍的修正方法,这是一种对腔词关系处理的探究。虽然修正后的音乐线条显得顺畅,但却不如原唱腔有韵味。至今也没有哪个流派按照他的思路进行调度。
当然,经典传统唱腔的改变不能与新剧目唱腔设计相提并论。书中提到的其他经典唱段的修正,对照原唱段的意见意义,或多或少地都削弱了传统的韵味。文中大量存在对传统唱腔细节问题的鞭笞,这也触及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然而,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唱段,经由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常年的演出实践,个别字上的行腔处理已经历过无数次的演出实践,音乐处理达到了饱和状态。若从和声效果方面考虑旋律走向的改变,将会更具意义,并且拥有成功的履历作为支撑。音乐的历史已经证明,留在人们影象中的是于会泳创作的京剧当代戏唱腔,这类统一于音乐思维的“程式”之作。
就传统唱腔的修正而言,京剧各个流派至今无人采纳利用,坚守着自己的风格。在“的”字上进行韵腔处理,在传统京剧的唱腔和念白中较为常见。正好是这些分外的运腔让人影象犹新,在传统剧目中显得别出心裁,为程式化的音乐注入了活力。或许旋律不那么普通,但古人在个别字、词的利用上,完备能够游刃有余。至于音乐篇章的安排,则是另一番考量了。
透过对上述唱腔的深入剖析,以于会泳的判断为准,纵然是精良的传统唱腔,只要他认为不得当,不符合他的音乐不雅观念,他依然会绝不犹豫地进行修正。书中涉及的大量经典唱段都被他改动……在他的评价系统中,没有禁忌,名腔名段都可以再改,只要能为他的音乐创作所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改革创腔的思路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腔词关系》的思维在于会泳的当代戏音乐创作中得到了印证,展现了他对戏曲音乐创新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地。
在戏曲舞台的演出中,音乐贯穿始终,正所谓“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戏曲强烈的音乐性哀求戏曲剧本措辞也具备音乐性,地方剧种的声腔每每从舞台措辞的韵律中衍生而出。剧本措辞的音乐性是戏曲唱腔音乐性的根本,只有将剧本措辞的音乐性根本打牢,才能更好地展现戏曲唱腔的音乐美。
一个剧种须要将舞台措辞韵律与音乐性相结合并将其充分发挥,才能光鲜地表示自己独特的声腔特点,邵武三角戏便是如此。邵武三角戏非常看重以字行腔,在戏曲演出的过程中,通过押韵合辙、句式、节奏等办法,奥妙地领悟措辞、内容、唱腔,使三角戏的唱词节奏与音乐的节奏紧密相连,形成统一的整体。如《卖花线》中的唱词:
“一要鸳鸯枕哪,二要绉巾哪,三要水粉呀子伊子呀,水粉就涂白脸哪,四要胭脂粉哪,五要五色线哪,六要喷鼻香包挂在妹胸前,七要七姑草,八要烟荷包,九要那个飘带,十要绣花针。”
这段唱词采用颇具音乐节奏的表述办法,具有很强的措辞张力,生动真切地展现了富有地方意蕴的戏曲艺术,使得全体戏曲演出更显灵动与意见意义,深得当地百姓的欢迎。
戏偏言话既要普通易懂,又每每哀求合辙押韵,唱词上哀求选用符合音律的语词。邵武三角戏虽为民间地方小戏,但其措辞顺口、易唱,措辞程式上以五言或七言为主,句式整洁,句型多为“二三”或“二二三”,讲究合辙押韵。以下是一些唱词的例子:
(1) “凌晨爬起来呀,把门两扇开呀,只见鲜花呀子伊子呀,鲜花就满地开。”(《卖花线》)采取怀来韵。
(2) “担子转过弯,来到糯米山。”(《卖花线》)、
这些唱词不论内容含义如何,单就演唱而言都朗朗上口、和谐悦耳、颇具音乐性。这些和谐流畅的唱词不仅符合戏曲曲律的规律,也表示了戏曲唱作者发音的巧用,易于识记,不雅观众也易于接管。
唱词句子形式的选择对戏曲唱腔的形成具有主要意义。于会泳曾指出:“由于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创腔实践中,唱腔句式的处理对付全体音乐构造的处理具有主要的根本意义。”邵武三角戏常采取传统戏曲中的非处置式“把”字句,唱来既普通易懂又和谐整洁,易于传唱。如:
(1) “凌晨爬起来呀,把门两扇开呀。”(《卖花线》)
(2) “到了渴凉亭,就把凉亭进,凉亭镇静静。”(《卖花线》)
(3) “担子放下肩,忙把礼来见。”(《卖花线》)
(4) “一步就把家门出,转身带关两扇门。”(《下南京》)
(5) “不觉到了渴凉亭,将身就把凉亭进。”(《下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