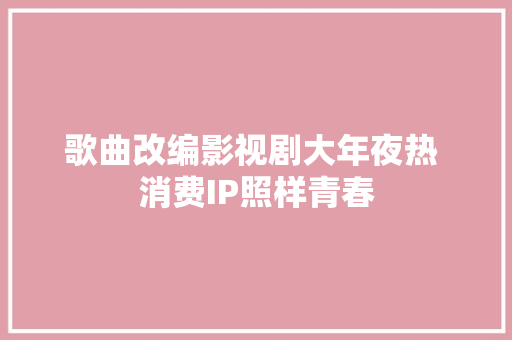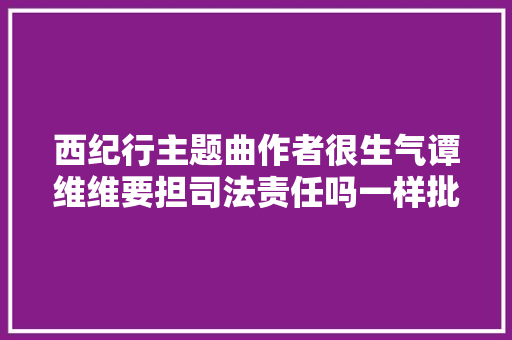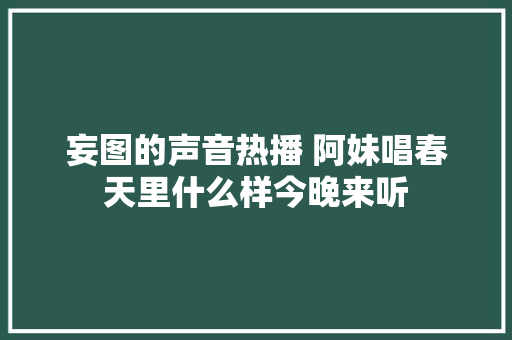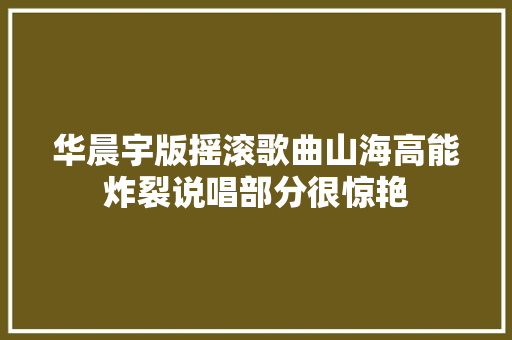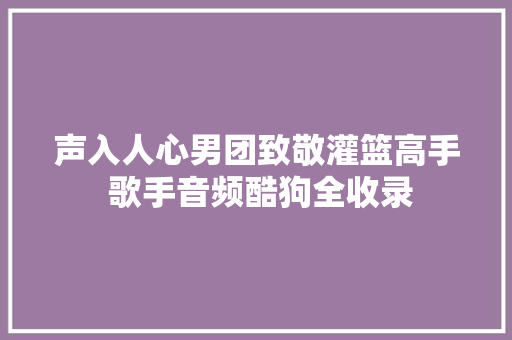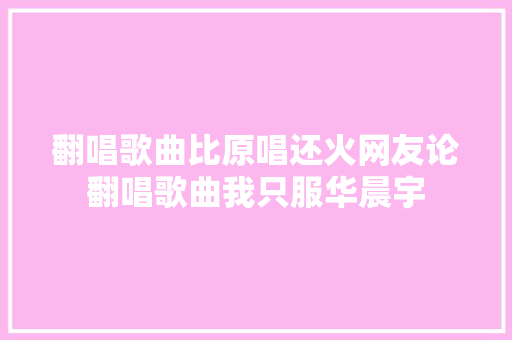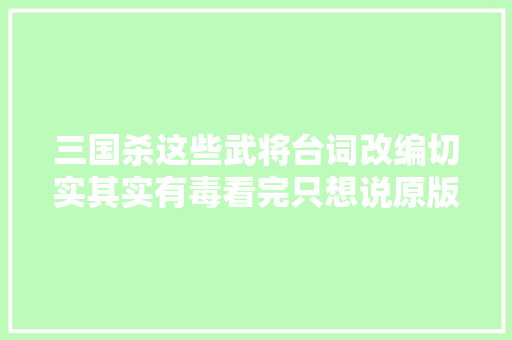作者:谷海慧(文艺评论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每当我们谈及中外话剧经典,无论出自莎士比亚还是易卜生,无论属于曹禺还是老舍,能够担当“经典”二字的,无一不是精良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因此精良案头剧本为条件的舞台创造。文学供应的精神视野和情绪代价、敏锐感想熏染与精准表达,是话剧最为名贵的艺术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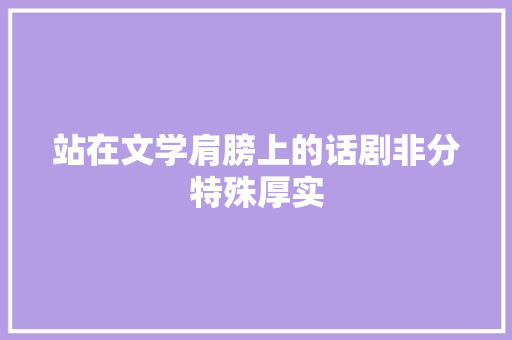
文学作品的话剧改编是近年戏剧舞台上的一个主要征象。仅就新世纪以来的本土作品改编,我们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长恨歌》《推拿》《白鹿原》《平凡的天下》《一句顶一万句》《历史的天空》《繁花》《尘埃落定》《人间间》《狂人日记》《我不是潘金莲》《俗世奇人》《主角》《钟鼓楼》《人间正道是沧桑》《红高粱》《一日三秋》《张居正》……这些赫赫有名的文学作品已成为话剧舞台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对原创话剧的有力补充。同时,文学改编也表示了话剧艺术的文体自觉,显示出话剧艺术对文学性这一自身主要属性的确认。
文学一贯是不同门类艺术的根本支撑,电影、电视剧、戏剧等领域,都不乏文学改编之作。话剧,顾名思义,是一门离不开措辞的艺术形式,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对付话剧来说,文学改编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当代话剧发展进程中,文学改编从未缺席。一些主要院团的“看家戏”很多都是来自文学改编,如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和新近排演的《正红旗下》。许多戏剧名家的代表作也都来自文学改编,例如黄定山的《我在天国等你》、方旭的《二马》,皆因此话剧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解码与重构。作为对原创的主要补充,文学改编拓宽了话剧舞台作品的来源,不断为话剧舞台供应滋养。经由文学加持的话剧作品,每每更具精神厚度和艺术深度,更能彰显出文学魅力,也让话剧舞台更具活气和活力。尤为主要的是,文学作品改编话剧让一度在话剧作品中有所欠缺的文学性复归话剧舞台,重新成为创作者和不雅观众视野中的艺术标准。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一些先锋戏剧作品的文学性便有所弱化。近年,伴随“后戏剧”时期来临,各种新的戏院要素被推向前台,代表文学高度的剧本越来越被忽略。这些关于戏剧可能性的新探索固然名贵,但其对话剧创作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轻视剧本、忽略文学的方向涌如今创作领域。这样说,并不是哀求话剧一成不变,而是哀求它有所坚守——坚守文体的纯洁,在守正根本上再进行创新。这个“正”,便是文学性。
在关于戏剧艺术本体性的研究和谈论中,我们常会听到这些答案:戏剧是综合艺术、舞台艺术、戏院艺术。戏剧确实具有综合性,也须要在舞台上和戏院中得到生命,但戏剧同时也是文学艺术。尤其话剧,将文学性视为其第一性,不算夸年夜。每当我们谈及中外话剧经典,无论出自莎士比亚还是易卜生,无论属于曹禺还是老舍,能担当“经典”二字的,无一不是精良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因此精良案头剧为条件的舞台创造。文学供应的精神视野和情绪代价、敏锐感想熏染与精准表达,是话剧最为名贵的艺术资源。在这一点上,其他戏剧类型都没有话剧的哀求急迫。
譬如歌剧,虽对歌词有文采哀求,但声乐与器乐才是表现剧情的紧张载体,舞台美术和服装也霸占主要位置。再比如舞剧,虽剧情依托于故事,但故事线索常日较大略,整体没有台词参与,肢体动作作为舞剧传情达意的主要媒介,代价高于其他要素。即便是戏曲,虽有《牡丹亭》《西厢记》等文辞典雅富丽的作品,但多数代代相传的剧目对故事、人物乃至唱词的哀求并不高,逻辑大略的故事、性情单一的人物、不甚讲究的唱词等在戏曲中并不鲜见。受众“听戏”的审美期待在于悦耳娱目,唱念做打乃至配器伴奏都非常主要,文学性则是锦上添花。唯有话剧,与文学的亲缘关系最为密切,对文学性的哀求高于其他姊妹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多于其他类型戏剧的缘故原由。
虽然戏剧不雅观念和艺术边界在不断拓展,戏剧艺术的重心经历了从剧本到舞台、从舞台到戏院的转移,话剧艺术也在强调自身的戏院性特色,但文学性作为其主要属性,依然提示创作者不断向其复归。文学改编便是这种环境下话剧创作的自觉。
对付改编者来说,站在文学肩膀的高出发点上,他/她已经具备了先天上风,接下来须要着重考虑的是若何不辜负这个条件,在与原作的对话中进行一次新创造。一个好的改编者,从不是原作的搬运工,而是长于理解与把握原作精神,同时生发新的意义。改编是另一次创作,是改编者代价不雅观念、现实敏感、审美意见意义与原作之间的碰撞领悟。只有相得益彰和相互造诣,才会有成功的改编。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两人饰演同一角色的办法表现人的两面性,玻璃走廊将舞台一分两半,既平分秋色又让人旁边难堪,男主人公对感情的不专一就这样被具象化了。北京人艺和陕西人艺的两版《白鹿原》,用的是孟冰改编的同一剧本,分别经由林兆华和胡宗琪进行二度创作,即表现出不一样的美学风格,前者高远苍茫,后者沉郁苍凉。同样依托于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丁一滕改编的《我不是潘金莲》以青花瓷盘式转台和戏曲旦角空脸做出符号化隐喻;牟森则在极简的舞台上演绎《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的孤独。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我们从中看到:文学担保了话剧作品的艺术质量;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则在彰显文学性魅力、增加舞台精神厚度的同时,完成了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与再传播。
文学改编话剧,本来便是一场文学与舞台之间的双向奔赴。当文学在舞台着花,舞台会因此流光溢彩;当舞台完成文学想象,文学便得到诗意重构。作为一种文体自觉,文学改编既是话剧的主要创作办法之一,也必将为舞台带来持续活气。由于,在这场艺术再创作中,话剧会借文学之名发展,文学则会在舞台之光下愈发明亮。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6日 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