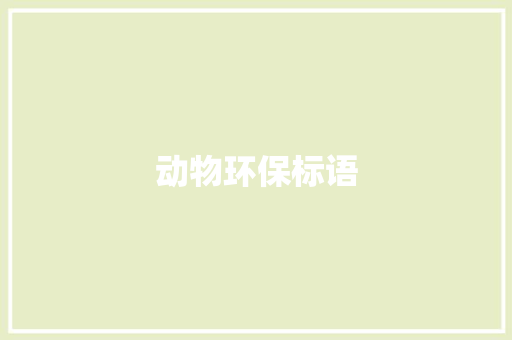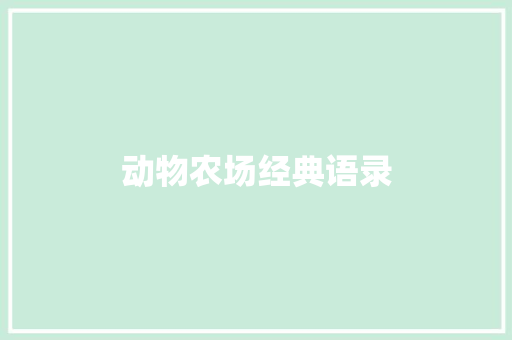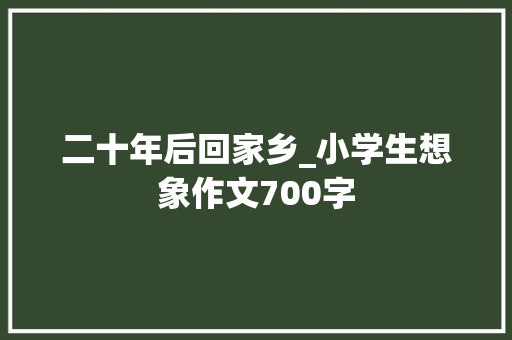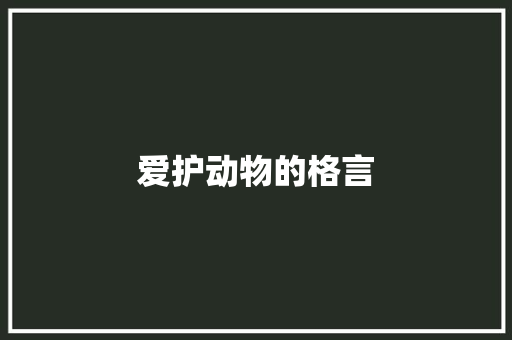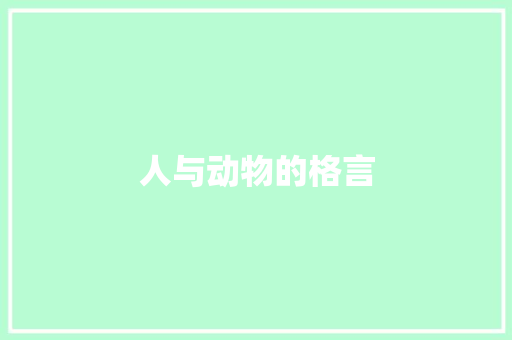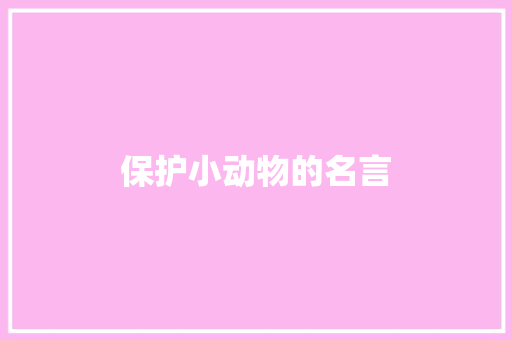动物题材与儿童文艺
西安市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火印》近日在上海巡演。火印,是一匹名叫雪儿的马儿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后被烫上的烙痕。雪儿的这一遭遇,很随意马虎使人想起电影《红樱桃》中的女孩楚楚。虽说人与动物差别巨大,却有通连之处,尤其对自然的敬畏者和艺术的崇奉者来说,身体的痛楚、精神的屈辱以及由此造成的身心分离、抗争、救赎、解脱,不独为人类所有,而是所有灵性生命体都有。只管剧中的成年人如坡娃爹、乡亲们、河野少佐多次称雪儿为“牲口”“牲口”,但少年人如坡娃及他的小伙伴并没有如此称呼,坡娃乃至还把雪儿称作“妹妹”。从中可见,该剧的主创通过不同人物对雪儿的态度,对雪儿作了有节制、有限度和分层面的处理。须要把稳的是,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全是为知足少儿不雅观众。动物题材的作品因深受孩子们的喜好,每每被纳入儿童文艺的范畴。然而动物题材同样是大量成年人所爱,其审美的边陲要广袤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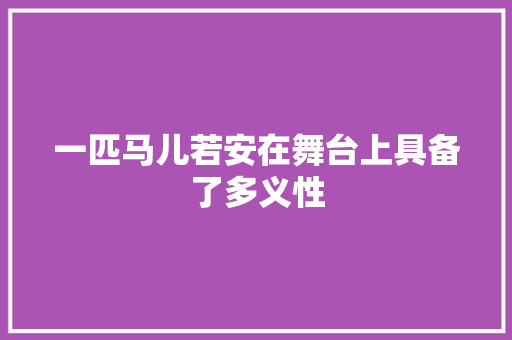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动物题材文艺创作一向不作纯客不雅观的自然摹写;近当代后也不走纯古典的寓言路子,而多将动物的自然生态与人的社会形态作领悟的处理。当动物被置于大量的、繁芜的社会话题中,便在审美创造和接管层面都涌现了一些新的课题和问题。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认为,当代中国的动物题材的文艺创作显著增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继续了赤色革命文化精神,这是好的;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涌现了大量的观点化、公式化的征象,缘故原由是仅以少儿不雅观众为唯一受众群体,为加强教养功能,不仅从生理活动到详细行为都对动物形象进行充分拟人化,更是加以道德判断乃至政治附会,从而导致动物与人、与人类社会间的爱恨情仇,直接成为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使作品扁平、僵化、呆板乏味。
笔者认为,在动物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注入社会含量、注入教养功能,是中华传统文化及美学精神的表示,并在文学史上涌现了像《聊斋志异》中《毛大福》《禽侠》《蛇人》《小猎犬》等将动物与人类、写实与志怪、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佳作,应予继续和弘扬,而条件是要同时做到尊重以动物为代表的自然、尊重以不雅观众为代表的社会,并通过奇妙的故事、独特的讲述、精美的技艺及整体的驾驭呈现出来。对此,《火印》的主创显然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作为,在对赤色文化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对中富丽学精神的坚持和弘扬两方面,都作出了符合动物题材文艺创作规律的实践。
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马的个体如白龙、赤兔即为“动物义士”,具有“龙”的属性也即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特性,对马的拟人化处理可谓顺理成章。《火印》将雪儿与坡娃的相遇、相知、相亲、相离、相聚作为主线,是从个体上对这一民族传统精神的古典性继续;同时由于这段故事被置于抗战情境中,便从群体上对这一民族传统精神作了时期性发展,并融为一体。总之,从单个的“马”到群体的“龙”,《火印》的核心题旨较为完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从个体的人与动物的自然关联,向群体的国与民族的意识觉醒的转化。同时,《火印》主创保持了创作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力求以简洁而又丰富、通透而有回味的审美感想熏染,同时知足小不雅观众和大不雅观众的须要。详细表现在并未将“雪儿”充分拟人化,而是始终保持节制,试图在同时尊重自然、尊重社会的根本上,将两者有限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并未将抗战背景完备具象化,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随时增减,降落生硬拼装之感;表现为并未将台词歌词单一化,而是按雪儿、坡娃、河野、稻叶等的不同身份、视角、想法和目的,分别予以针对性的处置;表现为并未将舞美设计纯粹自然化,而是将大山、大湖等景不雅观与人物的心态、主题的指向象征性地勾连起来……通过上述处理,当雪儿涌现了非凡的思维和令人惊异的行动时,不雅观众不仅不会反感,反会深受传染——这正是由于全剧始终确保了“雪儿是一匹马,而不是一个人”。至于对“动物通人性”的创造,对“动物有人性”的阐释,主创并没有亲自去实行,而是让不雅观众自发去完成的。
主题多义性和人物繁芜性
通过对剧中的动物、人物形象的针对性塑造,《火印》既站稳了外在特定的历史事宜背景,又延伸到内部普遍的人性抵牾冲突,使主题显得既有通透感又有多义性。
无论大小不雅观众,都能非常确定地觉得到,雪儿作为一匹马,只有感坡娃的救命之恩、视坡娃为主人的意识,对河野的虐待只有记仇、报复的意识;坡娃从狼口下救马、在日寇前护马、在战火中寻马,则出于爱马和视马为亲的意识,鲜有主动抗战的意识——最少是在最初。所谓的坡娃的“心重”,只是个性使然,他及小伙伴们的仇恨也紧张为遭受日寇的抢夺与侵害所致,指向明确但并没有无限拔高。纵然以日军小马倌稻叶而论,剧中表现的也只是他的爱马之心及重然诺、从长者等人的天性或近乎天性。与此相对,坡娃爹则显示出较强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性,河野少佐表现出野蛮的军国思想及征服欲,八路军小哥展现出武断的抗战意志及行动力。总之,主创通过对动物和人物的精准定位和鲜活塑造,产生了令人信服而又耐人寻味的效果。
当代的儿童剧创作是否须要追求主题的多义性和人物的繁芜性?笔者以为未必,但对动物题材的儿童剧创作,则应予以肯定的回答。如前所述,动物题材每每被纳入儿童文艺领域,故创作者大多会以孩子的天真心态、自然视角出发来完成作品,高度拟人、高度教养,进而又推动了动物题材归属于儿童文艺领域,这显然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在动物题材的成人文艺创作不发达的当代中国,儿童剧如何既站稳脚跟,又以动物题材为打破口和审美增长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何况当代的儿童剧审美,正呈现出“少长咸宜”的发展趋势。这不仅由于现下儿童剧不雅观众的构造大多为“二带一”“四带一”,更由于许多家长与孩子在审美生理、意见意义上涌现了某种趋近的方向,且在科幻、动物等题材,穿越、拼贴等形态上发生了汇合。当代儿童剧的创作既不能忽略孩子们无意的“老成”,又不可忽略家长们故意的“萌化”,而是要对儿童与成人审美交汇面的扩大与相似度的提升,加以必要的研究和有效的探索,更好地把握当代儿童剧的艺术规律及市场的发展态势。不过无论研究还是探索,都不虞味着将严明题材儿戏化、将童稚风格严明化。最主要的是,主创须对文学性这一创作之本做深入的挖掘和精心的提炼,并表示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艺术的呈现上,构建“少长咸宜”的高质量的认同带和平衡点。在题材的选择上,大自然无疑是一片永恒又时尚、广袤且深邃的领域,而动物题材正是个中最丰富、最诱人也最富于寻衅性的。
《火印》的主创对动物,也即对雪儿这一形象的处理,既没有走纯自然摹写的路径,也没有按纯道德教养的理念,而是将自然物象、动物天性与人类或纯或杂、或正或邪的表现,置于抗日战役背景下,由此展开对雪儿的拟人化处理,分寸拿捏较好,并兼顾了主题的指定性与象征性,接通了不雅观众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除了雪儿,全剧还有其他既具指定性、又有象征性的物象,大湖的自然和平意味、军刀的暴力抢夺意味相比拟较大略,而雪儿身上的火印则较为繁芜——有人阐释为自然天性的损伤,有人解读为民族耻辱的印记,有人以为是精神创痛的伤疤,有人认为是发展的代价……笔者认为都对,都属于全剧或规定、或延伸的题旨,也都属于不同年事不雅观众或觉得、或理解的意味;进而认为这枚火印,实为文明冲突在自然、在社会的表层,在个体、在群体的深层的烙痕,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和励志功用。这种警示和励志来于自然,来于个体,来于民族,见告不雅观众如果未经巨大磨难,不留刻骨烙痕,从一头动物到一个人、一个村落、一个民族都是无法发展、成熟并真正变得伟大起来的。
对原著的虔诚与创新
《火印》改编自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主创对原著作了虔诚与创新兼顾的舞台呈现——虔诚其思想性尤其是文学性,创新其戏剧艺术性尤其是演出艺术性。
首先,编剧从原著小心地裁取出一个故事,环绕雪儿与它的救命恩人坡娃悲欢离合的主线,精简出场人物和动物,删削次要情节和细节,加强人物塑造,凸显戏剧冲突——这是符合戏剧改编小说及儿童剧创作的规律的。其次,导演对剧情发展做了适当的跳跃性处理和散点式展现,又以旋转式舞台、多媒体影像将这些跳跃和散点加以弥合、汇拢。在这种导演理念及调度下,纵然是坡娃救马、日军抢马等原著中的核心情节,在剧中也是通过有含量的对话、有分寸的动作和有诗意的布景呈现出来的。值得把稳的是,空灵叙事、浪漫意境的营造,唯有在夯实了现实抵牾冲突的根本之上才有发挥的可能。如果说后者须要不雅观众主动作点“脑补”,那么前者则能供应不雅观众充足审美享受,不雅观众的付出与得到大致是成正比的。其三,主演以自己的禀赋、悟性和激情创造,将雪儿作为一匹“中国良驹”的天然秉性与家国属性,通过形体、歌喉、肢体动作进行了艺术的表现,与坡娃扮演者的天性流露形成一种默契,令人动容。笔者认为,两位主演基本把握了这场演出中最关键的内容,即把动物的特色、能力与灵性,与人的特点、作为和思想情绪先“分”开来,再“合”起来,从“通人性”的演出向“有人性”的不雅观感不断进取,实现了将动物“拟人化”的艺术佳境。
由此可见,《火印》对原著的改编是成功的,舞台的写实与写意并举,对应着小说的物象与意象的领悟;演出的拟物与拟人兼具,对应小说的自然描述与人性描写的融汇。由此,该剧才能在简约、豁亮清明、层次分明的构架中,蕴含了丰富、多元、层次交叠的精神,包括自然与人类、友爱与仇恨、历史与时期、战役与和平等等,犹如一块多棱的精神镜像。显然,这归功于原著拥有的文学性,也归功于主创对小说文学性的戏剧艺术转化。
《火印》温情与悲壮兼具的风格,是当代儿童剧中较为少见的。当代儿童剧风格多偏于精细和温顺,此类作品量多且成功率高,而壮丽、阳刚风格的作品量少且成功率低。调度这种态势,同样是儿童剧审美“少长咸宜”趋势的哀求。在此机遇与寻衅面前,儿童剧从业者应努力通过不雅观念创新和艺术创新,寻求当代儿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不雅观赏性的升级与新的平衡。(胡晓军)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