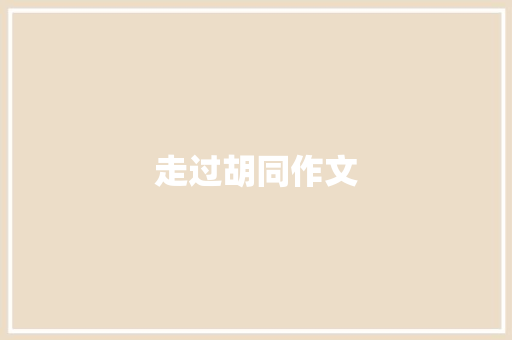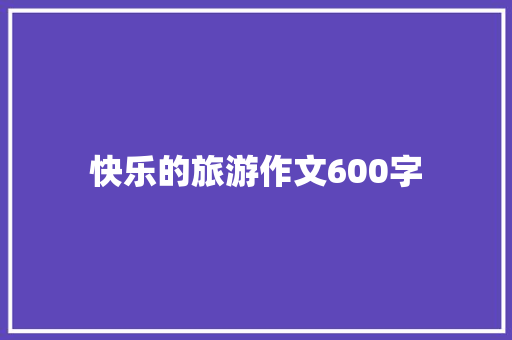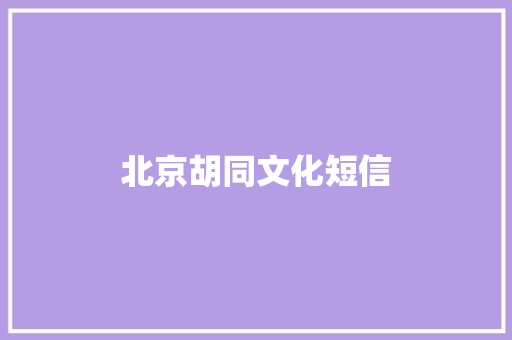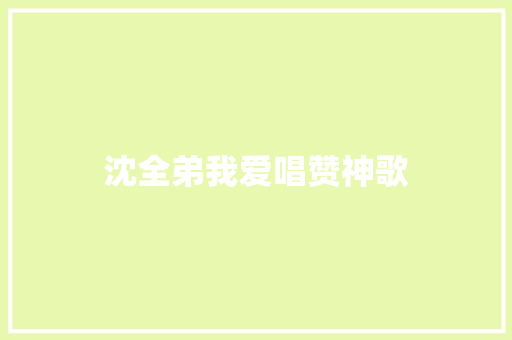人到老年思往事。和同龄朋友们谈天时,在回顾往事中大家最怀念的,险些都是童年时期的趣事。虽然有多方面缘故原由,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之以是那样留恋童年时期,大概是那时候我们可以尽情地抒发我们的感情,尽情发泄人性自然的流露。我们在回顾童年生活时,又不谋而合地谈到那唱歌的乐趣。
每个人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启动和震荡心灵的歌曲相伴,不管谁爱唱歌或不爱唱歌,基本都生活在歌声中,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儿童期间正处于人们文化娱乐生活贫乏期。回顾起童年及少年期间的歌曲,像《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虽然是我们爱唱的歌,但毕竟是在学校作为一门课程的“贯注灌注式”学唱的歌,该当说这些歌对我们康健发展起了主要浸染。而那些自然而然地就引起我们童年的好奇心和童稚乐趣的歌曲,特殊是那俏皮的近似“荒诞”的歌词儿,每每给我们带来想不到的快乐。每当回顾并唱起这些歌曲时,我们急速会变成“老顽童”,儿时情景会急速浮现在面前。

不管居住在四合院还是大杂院,总之,那时候的人们都是居住在胡同里。文化娱乐生活贫乏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唱歌既是一种娱乐享受,也引发那种充满天真和想象力的激情亲切。住在一条胡同里,如果一个孩子唱一支新歌,很快就成为这条胡同里孩子们共同唱的歌曲。而且不管是有童心未泯的成人刻意编造,还是出自具有天分的孩子的大脑,那自编的、具有诙谐感的、乃至有些“俗气”的俏皮新词儿,彷佛比歌曲原有的歌词对孩子们更有吸引力。只管对唱这类歌词儿,有时候应对听歌的孩子进行必要的思想勾引,但是童言无忌、活泼好奇等,这毕竟是孩子们天性的流露。
前不久,和几个昔日小伙伴提到那时候的一首歌曲《泼水》,听说现在有些孩子还在唱这支歌,名称统一叫《泼水歌》。记得歌词应是:“那一天我从你家门口儿过,你正提(音读di)了着水桶就往外泼,泼到了我的皮鞋上,街上的人儿都乐呵呵,你什么话儿也没有对我说,迷瞪着眼睛就看着我。”唱起这《泼水歌》,我很激动,由于那时候我也和小伙伴们唱这支歌,尤其是看胡同里那些女孩子唱时,更多乐趣儿。我记得不知是哪个天才的孩子,竟把这支歌编出五花八门或意思丝毫不连贯的歌词儿,那些歌词儿唱起来,让孩子们,也包括不少大人们听了都以为搞笑。加上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唱歌时还伴着自己编的不少活泼轻快的动作,使得歌声中又多了欢畅的笑声。记得在这支歌原有的歌词儿前,曾增加了这样一些歌词儿,但曲调还是原曲调。一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儿,花园儿里面花儿喷鼻香。感谢我们的毛主席,感谢我们的共产党。”然后接下来便是“那一天我从你家门口儿过,你正提了着水桶往外泼……”。这两段童谣词儿意思毫无联系,但是这样唱起来使歌曲韶光拉长,当然那些女孩子的舞蹈动作也增加了。一是更可笑的歌词儿,也是用这曲调唱,歌词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儿,花园儿的花儿多又多。感谢我们的共产党,感谢苏联老大哥。那一天我从你家门口儿过……”现在想起来,也琢磨不出是谁编出这样的词儿。
至于个别的孩子“瞎编”的歌词,更是五花八门,让人听了忍俊不禁。尤其是我们胡同里有个智商毛病的男孩子,外号叫“傻二子”,这也险些是那时候的孩子们对那些傻男孩子的共同“俗称”。这个“傻二子”还真有编歌的天分,他居然自己编了一套歌词儿,加上他傻呵呵地操着五音不全的嗓子站在胡同里一唱,连那途经的蹬三轮车工人都停下来“捧场”。他的歌词儿是这样:“提(读音di)了、提了着水桶就往外泼,你泼到了我的皮鞋上,什么话儿你都不说,你光知道用眼睛看着我。”结果,他刚唱完,一些孩子就喊“傻二子,看你好玩儿呀”,还真把这个傻二子气得咧着嘴大哭。这下子胡同里急速“热闹”起来!
还有一支童谣也很故意思。令我想不到的是,在一次电视台播放的联欢会上,已故著名电影演员陈强还演出过这支歌,当然,那歌词儿略有变革。我们胡同里那些孩子唱的歌词儿,说不清要表达什么意思,乃至现在看起来彷佛有点庸俗。有人说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歌,这显然不对。由于我小时候,即上世纪50年代初,不少胡同里的男孩子就唱这支歌。估计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有人利用这曲调填新词儿唱,这倒有可能。我小时候听到的歌词是:“第一次我到你家你不在,你爸爸给了我一皮带;第二次我到你家你又不在,你妈妈给了我一锅盖;第三次我到你家你还不在,你们家的狗咬了我的‘膊楞儿盖’(音似,老北京人对双腿膝盖的俗称,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记得孩子们唱完都哈哈大笑。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名儿叫“老梆子”的孩子学会了这支歌,结果回家一唱,让我母亲听见把我好一通训斥,从此我再不敢唱这类歌。
记得胡同里一些女孩子,用陕北民歌《绣金匾》的曲调编了一支歌,边唱边舞,唱歌的女孩彼此之间的动作又显得活泼,又显得亲热。那歌词是:“太阳一出来呀,我把那家门儿开,姐姐妹妹快出来,去把那花儿摘。雇主的大姐姐呀,西家的小妹妹,姐姐妹妹一起来,来把那花儿摘。”我们胡同里有个叫“大凤”的女孩子,嗓子特殊好,动作也特殊活泼、幽美。可惜我们没有说过几句话,她家就搬家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向老邻居问她的姓名,听说她后来真考上了某部队文工团,这是题外话。
这支歌的歌词儿可是一点儿也不俏皮,但唱这支歌的可笑之处,便是有些三四岁的男孩子看着那些女孩子的舞蹈动作以为新鲜。于是这些小不点儿非要当“小妹妹”,也加入那唱歌的行列。那些天真激情亲切的女孩子倒是不在乎,她们很高兴地让这些小弟弟加入行列一起唱。但是有个别的老太太却“恶作剧”,她对那些男孩子说:“你们是小子,小子不能舞蹈。你要当小妹妹,那就要抹个红嘴巴儿。”那些男孩子还真听话,争先恐后地让老奶奶给自己抹红嘴巴儿,于是那个老太太给这几个小男孩儿每人嘴巴儿上抹点儿“口红”,说这样就变成小妹妹啦,可以跟大姐姐舞蹈啦。结果,这几个“丑八怪”男孩儿边唱边跳,嘴里还唱着“雇主的大姐姐呀,西家的小妹妹”,连过往行人看了都哈哈大笑。
还有什么“大红花,开满地,小朋友拍手做游戏”、“1、2、3、4、5、6、7,我的朋友在哪里,在学校、在操场”、“新年、新年,你来了,我们一起唱歌又舞蹈”、“我是一个大苹果,又喷鼻香又甜又好吃”,等等,充满儿童天真活泼朝气的童谣和孩子们自编的各种舞蹈动作。曾给我们这些孩子,乃至胡同里的大人们带来无限乐趣!
这种类型的儿童歌曲,大概也就唱到1957年前。自1957年底开始,尤其是1958年,那些胡同里的童谣大部分都变成了紧跟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儿童歌曲”。从此,胡同里的孩子,包括我,开始唱着“黎巴嫩、约旦,大胆的公民,正义的斗争,全中国的少年儿童支持你们”、“抗击英法,反侵略,支持埃及斗争,要和平”、“打倒美帝,争取自由,我们高举小拳头”、“少先队员顶呱呱,翻身骑上小飞马,快马加鞭大跃进”、“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讲故事、学英雄,永久提高不掉队”、“我虽年纪小,没有冲过锋,但我随父亲,一起参过军,我的胆子大,统统都不怕”等中外儿童歌曲的歌词。这时候,我溘然以为我们这些孩子仿佛一下子就变成“大人”啦!
以是当那场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到来时,在青少年身上爆发的那种“狂热性”,并不使人们感到溘然!
(转悛改浪博客:老骥伏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