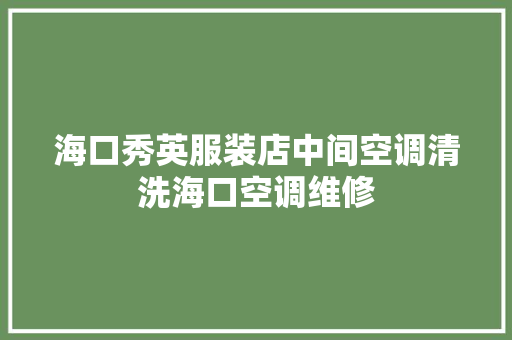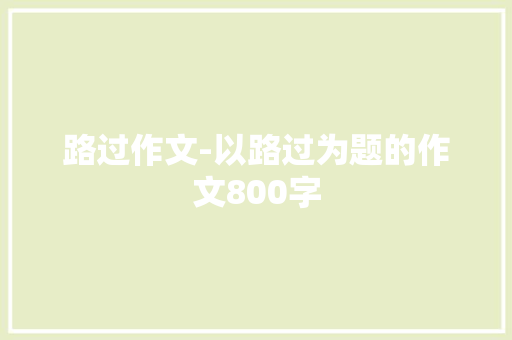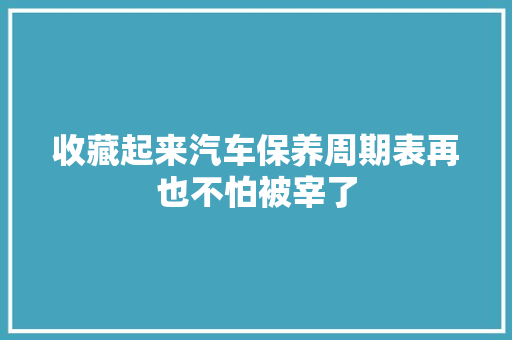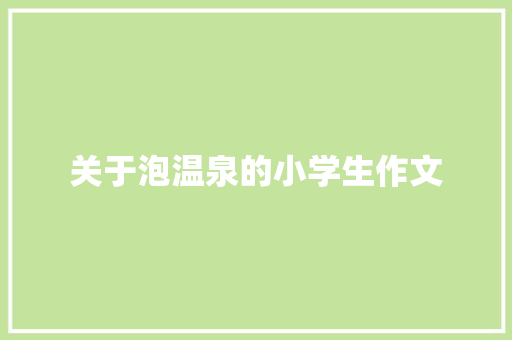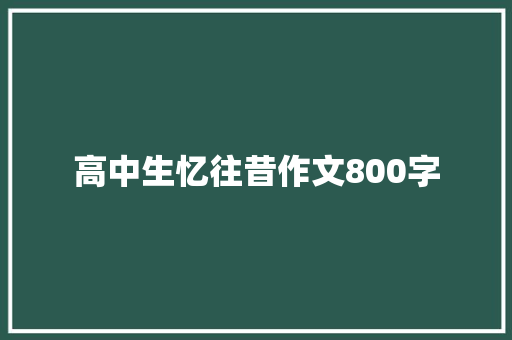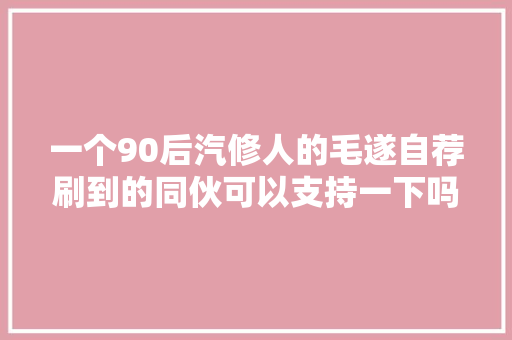讲述 王晓义 67岁 来自 河北唐山
1973年2月19日,我收到冶金工业出版社寄来的一本《矿山电铲》,大喜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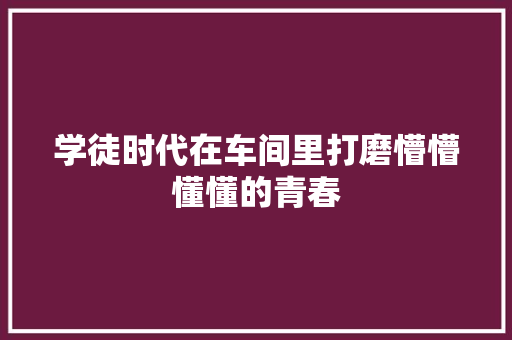
1970年,我走出校门被分配到河北迁安,在首钢水厂铁矿当了一名电铲学徒工。电铲也叫挖掘机,是采矿的“重型武器”,每天昼夜一直地吼叫着,大口大口地吞吐着矿石。为尽快节制电铲技能,我从一点一滴中领悟师傅的操作办法,逐渐学会了一样平常电器、机器常见故障的打消。那年月,整天批“白专”道路,专业知识相称匮乏,根本没人组织系统授课,只能靠师傅手把手教实际操作,从师傅嘴里零打碎敲、只言片语地学点东西。我非常渴望有一本专业技能教材,给自己系统地“充充电”。
在求知希望的使令下,我贸然提笔给冶金工业出版社写信,讯问是否有电铲方面的技能书本,想求购。没成想,一天,我竟然收到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赠阅的《矿山电铲》一书。拿到书,我如获珍宝。有了专业教科书,我明白了设备的基本事理。再加上有师傅言传身教,理论与实践结合,我的业务技能进步很快。不久,我3年学徒期满,经由考察合格,成为一名正式电铲司机。并且,我很快就当选为甲乙丙三班司机长,自己也带上徒弟。
随着电视节目学理论知识
讲述 刘保顺 65岁 来自 山东济南
1975年12月5日,高中毕业的我坐车来到莱芜钢铁公司第二铁厂生活区,卸下行李,住进20多人的大宿舍。经由集中培训,我被分配到第二铁厂质料车间,当上了一名电工。
工厂盛行一句口头语:“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对付没被分去当生产工,我非常光彩。但是,我对电工知识险些一无所知。当师傅说到“空气开关”,我无知到疑惑空气怎么也能当开关,实际因此空气作绝缘介质。干电工,我从一点一滴学起,小到接线、电机正反转掌握、爬电线杆高空作业、日常电气检修,大到高压变压器的日常掩护……逐步地,我从陌生到上手,一点点进步。业余韶光,我也试着修理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掀起学习业务的高潮,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更名为中心电视台)每天17时至18时播放科教培训节目。那时,电视机还很少。我自行到莱钢安装处,参加电视听课。虽然不是一个单位,但人家也没有撵我,我很感激。其间,我在电视上听过华罗庚教授的优选法和一名专家讲的晶体管电路根本等。
我随着师傅当了三年学徒,学徒人为每月21元,满三年后每月31.5元。6年多的电工职业生涯,培养了我敬业爱岗的品质。班组师傅看我年轻肯干,就相互推让,使我连续几年当选厂里“大干社会主义斥候”和劳模。
从师趁师傅出去,自己操作加工
讲述 赵民 63岁 来自 辽宁沈阳
1976年,我中学毕业进入沈阳旗子暗记灯厂当学徒工,每月人为19元。我师傅姓李,是个八级车工。李师傅年近六十,个头不高,面庞清瘦,不苟言笑,每天默默地事情。
一次,厂里来了一批活,精度哀求非常高。那时没有当代化数控加工设备,李师傅全凭手工操作车床加工这些零件。我在一旁看得木鸡之呆,打心眼里敬佩师傅。我也是年轻好胜,趁师傅出去办事工夫,赶紧装夹工件加工起来,结果一欠妥心把车刀崩刃了。我卸下车刀,模拟师傅的动作,在砂轮机上磨了起来。磨完后,我装上车刀又加工起来。我刚加工好一个工件,师傅回来了,用千分尺一测,不合格。师傅苦口婆心地对我说:“遇事不要急于求成,小小车刀有大学问。”然后,他戴上老花镜,在砂轮机旁精心地磨起车刀来。在师傅的耐心辅导下,我用师傅磨过的刀具再加工工件,完备达到了图纸哀求。我和师傅一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年终还得到了厂里“前辈事情者”称号。
在工厂待了将近两年后,我考上了大学。至今,我回忆起自己当初当学徒时那种卤莽和无知,还感到风趣可笑。
完美操作,让师傅扬眉吐气
讲述 王志宏 67岁 来自 湖南长沙
我1970年参加事情,当时才16岁多一点。我们厂是生产轴承的,我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做维修车工。刚下车间那段韶光,我一贯进入不了状态。一方面是自己年纪太小,面对C620车床这样的庞然大物有些不知所措;另一方面,还是自己玩心太重,总是想着本日要排练个什么节目,来日诰日要与谁打球,没把多少心思放在事情上。结果,随着师傅学了几个月下来,我还不能独立操作。别的师傅双手揣在口袋里,让徒弟操作,自己这边看看那边聊聊。看着他们一脸得意,我师傅非常恼火,乃至放言:“我不带这个徒弟了!
”听到这个,我哭得梨花带雨。假如师傅真不要我了,我回去怎么向父母交代?幸亏师傅讲的是气话,只是将我几天内打碎的十几把车刀一溜儿摆在工具柜上,让我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从此,我彷佛负责点了,但觉得还不能分开师傅的视线,害怕出废品。与我一同进厂的小L的师傅炫耀地对我说:“你瞧,小L都能车内T牙螺纹了!
”那时候,我真的认为自己很笨。
只管我们学徒期有三年,但一样平常师傅带了徒弟几个月后,就会分开操作。一次班组开会,说生产任务紧张,徒弟必须与师傅分开操作。领导说:“小L能独立操作了,小王呢,拉毛坯也拉得。”意思是,我纵然独立操作也只能车毛坯,让别人精车,为人做嫁衣裳。车间主任对我说:“零件的每个尺寸,你都留2毫米余量,但是都要按照图纸的精度车削,这样既避免出废品,也可以磨炼自己。”但真正独立操作的时候,我却没按领导哀求的做,而是直接按图纸将零件的每个尺寸车到位了,并且也没出废品。看到我进步了,我师傅也得意起来。师傅将我车得很俊秀的T形丝杆放在显眼的地方,终于可以与其他人一样扬眉吐气了!
写家书总是含着眼泪报安然
讲述 彭素君 71岁 来自 湖北荆州
1971年下半年,我是石油仪表厂机加工车间的一名仪表车床学徒工。仪表厂在湖北沙洋县,刚从大庆搬来不久,除了紧张厂房外,其他都在培植中,非常简陋。在机加工车间,夏天只有一台吼声震天的落地电风扇。体弱之人站在扇前,会被风推着走几步。但在车床上干活的人,汗水顺着头发丝往下流。冬天,车间又冷得出奇,我在单裤里套着一条旧绒裤,双腿能被冻僵。
油田对学徒工哀求极其严格。我们每天上班得提前20分钟到岗,给机床加油、试运转,等师傅一来就立即开工。上班韶光除上厕所外,我们不得擅自离开车床与人谈天,不准坐凳子上安歇。每天七八个小时站下来,两条腿彷佛灌了铅一样沉,一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再也不想动弹了。厂里住房紧张,师傅们不管家里几口人都只能分到一间土坯房,学徒工们的生活空间就可想而知了。夏天,六七人挤住在临时搭建的小铁皮房里,像住在烤箱里。冬天,薄薄的铁皮房实在是无法住了,我们搬进了风雨飘摇的土坯房里。1971年冬天特殊冷,断断续续下了半月大雪。我从家里带来的只有一床四斤重的棉被和一卷草席,只好与工友在一个被窝里挤了半个冬天。一天早上,宿舍的门被冻住了,我们怎么也推不开。眼看上班韶光快到,大伙急得团团转。末了,大家把热水瓶都拿过来,用热水顺着门缝从上到下浇了一遍又一遍。等6瓶水全用完,我们协力冲向木门。门被撞开,我们也倒进雪窝里……
面对恶劣的住宿环境、每天寡盐少油的饭菜,还有超负荷的事情,我咬牙坚持着。我每次给父母写信都不谈这些,总是眼里含着泪报着安然。由于,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星期天走走县城便是幸福
讲述 毕政 71岁 来自 湖南长沙
1969年11月,身为知青的我怀揣招工关照,与差错一起来到了地处湘西南的绥宁县荣岩水电站报到。我们挑着行李担,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才得以抵达这座正在紧张施工阶段的水电站。第二天,我们就换上工装上班,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学徒生活。
我们上班第一课是学习钳工,抡大锤、用钢锯等变成了我们的基本功。大伙儿个个都是兴致勃勃的,但只一个星期,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只管如此,我们也并没有灰心,在师傅们的带领下冒死干。尤其是每到工地要浇筑混凝土阶段,以及后来安装调试阶段,还真是磨练人的意志的时候。我们把人马分成两半轮班转换,十几个小时一班,一贯要把活干完,才能好好安歇一天。我们一年究竟上了多少个班,没有人算过。
当时我们最大的幸福,便是星期天能好好安歇一天。早饭过后,大家结伴步辇儿去十几里外的县城,看看热闹玩上半天。然后,我们去车站或正街国营饭店吃上一个客餐。要问这客餐有什么特点,便是有半斤米饭,加上一个辣椒炒油渣,还有免费的鸡蛋汤,统共开支约为5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