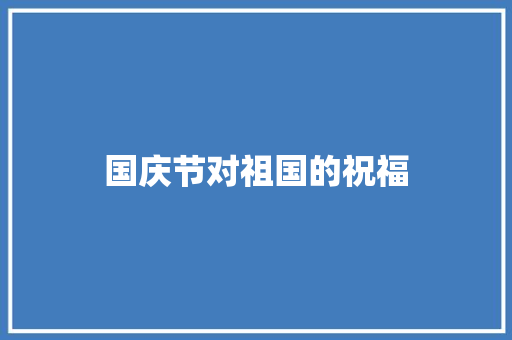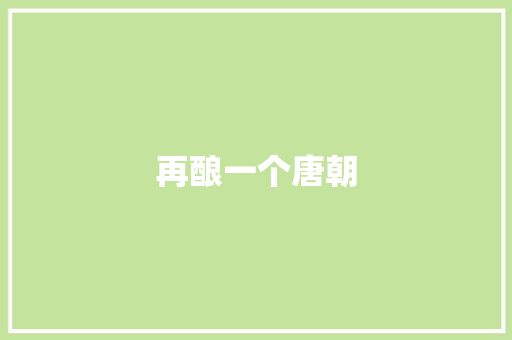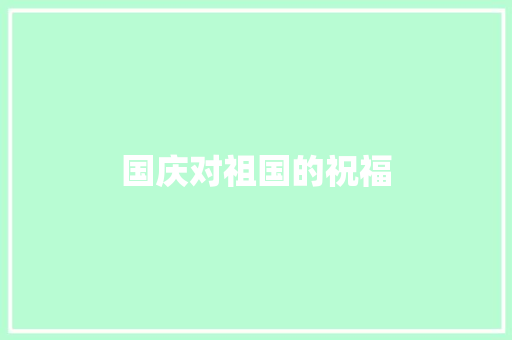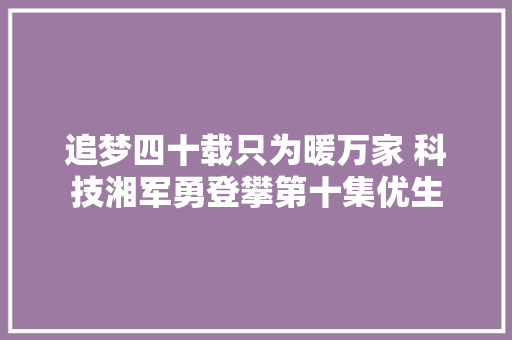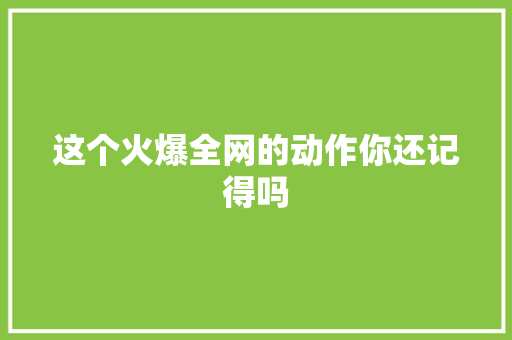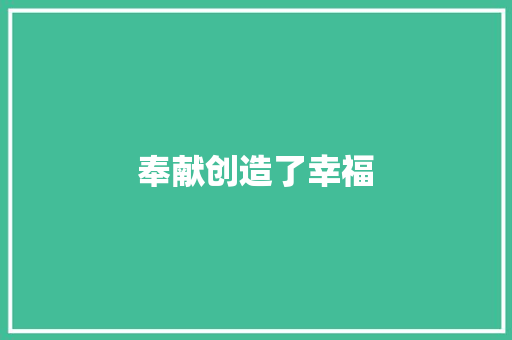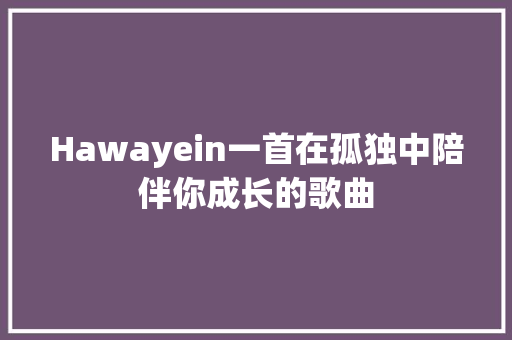中国艺术歌曲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一个世纪以来,特殊是改革开放往后,中国艺术歌曲日臻成熟。艺术歌曲发轫于德国,传入中国后,经由中国音乐艺术家的改造创新,逐步凸显了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
诗意盎然是中国艺术歌曲的显著特色。原来欧洲的艺术歌曲便是诗歌与音乐的高度领悟。那时,艺术歌曲的歌词大都采取名人诗作。中国诗蕴藉隽永,意境更胜,谱成歌曲,以声传情,以情达意,别有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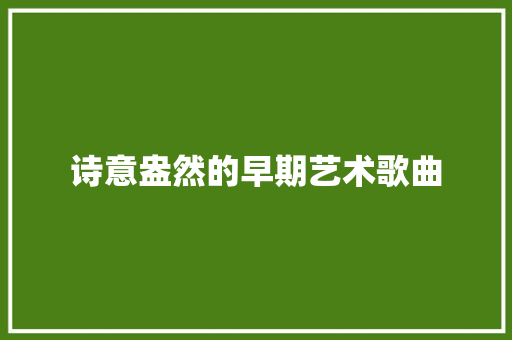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唐诗宋词,很多名篇被谱写成歌曲,或写母爱亲情,如孟郊的《游子吟》;或写思乡之情,如李白的《静夜思》;或写报国之情,如岳飞的《小重天》;或写怫郁之情,如辛弃疾的《欲说还休》;或写离去之情,如叶清臣的《留别》;或写豪迈之情,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等。这些歌曲无不以情见长。一些艺术家也用新诗谱曲,个中不乏名作,如赵元任谱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这是刘半农于1920年写的一首口语诗,1926年旅居伦敦的赵元任把它谱写成歌曲。
赵元任被誉为“汉措辞学之父”“中国近当代音乐的先行者”。在英国留学时读到刘半农的这首诗,深受触动,他把诗中的男女恋情转化为思念故国之情,为之谱曲,把自己的语文教化与音告成就倾注个中。诗共四段,用比兴写成。每段四句。末了一句都是“教我如何不想他”,节奏光鲜,朗朗上口。第一、二段,用地上、天上、玉轮、海洋等意象,描写广阔的空间,展示了恋爱的广度,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苦恋。第三、四段,用“落花流”“鱼儿游”“枯树摇”“野火烧”等意象,还有燕子传信、残霞示愁的拟人手腕,渲染悲情,表达了墨客难解乡愁、流落不定之情,展现恋爱的深度。每段都用反问句,暴露恋之深、愁之痛、爱之切、情之浓。歌曲主调建立在五声音阶根本上,点题乐句“教我如何不想他”,采取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腔调加以变革,使作品的民族风味显得格外浓郁。这首作品男声高、中、低音均可演唱,百年传唱经久不衰。
反响时期精神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又一特色。中国歌唱艺术历来有“乐教”传统,更重视“教养之义”。西方艺术歌曲则更重视“声音之美”。
中国艺术歌曲总是表示着时期精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战役风起云涌,其间呈现了不少反响抗日救亡时期精神的艺术歌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艺术歌曲渐入成熟阶段,特殊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艺术歌曲涌现了“井喷”征象,精良作品如《在希望的野外上》《啊,中国的地皮》《那便是我》《多情的地皮》《我和我的祖国》《乡音乡情》等,无不表现了中国公民斗志昂扬、昂扬向上的时期精神。
且以中国早期艺术歌曲萧友梅的《问》,来看艺术歌曲对时期精神的反响。萧友梅是中国音乐教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内忧外祸之中。时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的萧友梅,对易韦斋的词《问》产生强烈共鸣,写成歌曲《问》。全词两段,采取了屈原《天问》的风格,每段都以“你知道你是谁”发问开头,继而发问:“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悲惨的泪?”“你知道尘世的波澜有几种温良的类?”自问自答,借鉴陆游《钗头凤》的手腕,采取痛彻心扉的单字“垂!
垂!
垂!
垂!
”作结,泪滴悲痛,直抒胸臆,表达了万箭穿心、恸不忍言的伤痛之情。对应于朴实的笔墨,萧友梅谱曲,没有用华美的音乐措辞和繁芜的创作手腕,而是用极其简练的材料,以舒缓的慢板、发散的音型、蕴藉的律感,唱出了对当时国家沉沦的忧虑。歌曲末了沉吟似的尾声,使全曲余韵无穷。
伴奏与和声是中国艺术歌曲形态的主要特色。伴奏特色是艺术歌曲异于其他歌曲的固有特色。一样平常歌曲的伴奏,都是“以歌为主,以奏为辅”的陪伴关系;而艺术歌曲的伴奏,则是“歌奏相谐,结随同行”的差错关系。艺术歌曲的伴奏每每因此和声涌现的。和声最大的功能是美化旋律,或补充,或润色,或凸显。和声常常表现为歌诗与音乐细致入微的有机结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领军人物黄自的作品,伴奏与和声的特色就很突出。他谱曲的《玫瑰三愿》,词作者龙七,歌曲描述了一位不甘接管命运安排的女子憧憬美好未来,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黄自师长西席谱曲采取的是两段体的构造。前奏4小节,弱起进入,力度很小,和声织体以柱式和弦为主,重复音乐主题,表现寂静、淡雅的感情,为入歌做铺垫。第一段歌曲唱完,进入间奏,仍旧采取年夜声部柱式和弦的手腕,将柱式和弦音叠厚利用,并在低声部利用分解和弦琵音的织体形式与年夜声部比拟。由间奏自然引出了第二段唱。当歌曲进入高潮部分时,对“红颜常好不凋落”中“红颜”两字,钢琴伴奏中年夜声部一个小节仅两个柱式和弦的衬托,将音乐推向高潮。末了一句“留芳华”在柱式和弦的伴奏下推向了不协和,以极弱力度的低音结束全曲,让听者体会“美永驻人间”的美感。
《春思曲》词作者韦瀚章,阐述的是在春雨绵绵的深夜,一位女子因思念情人夜不能眠的情景。黄自谱曲采取了再现二部曲式构造。全曲旋律形态是大调的调式走向,但从和声的角度来剖析,又为小调的和声体系,如此和声表示了闺怨之情。音乐的发展部,少女看到绿柳东风,双燕嬉戏,触景生情,为了描写“更妒煞无知双燕”,音乐主旋律层层递进,利用转调手腕,将音乐转到小七和弦旋律,悄无声息地转回大调,音乐和歌词领悟为一,把女子的思念和怨恨推向高潮,迸发出摄民气魄的传染力。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1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