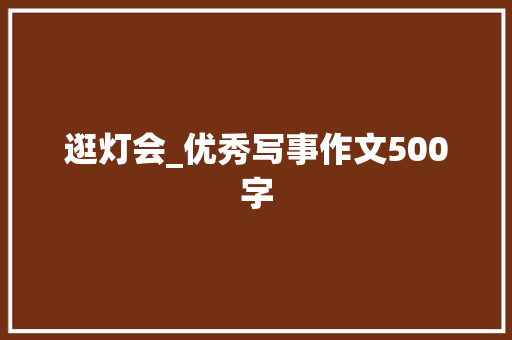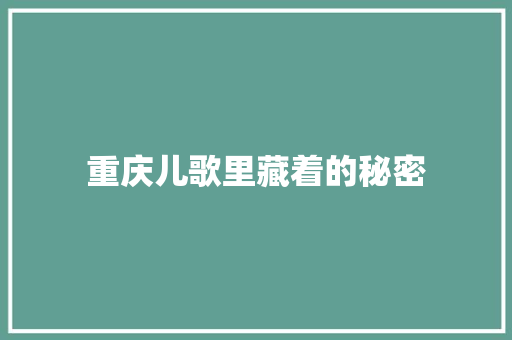上一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推举了瑞典著名汉学家喜龙仁关于北京城墙的拍照作品和笔墨考据,受到不少读者的青睐。实际上,喜龙仁当年的著作以“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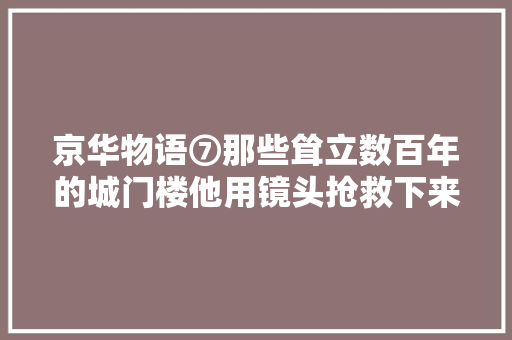
为题,城墙只占了书中的一小部分,他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建造材料、工艺更为繁复的城门楼。
他对北京的城门楼做了拍摄与丈量,并绘制了详细的正面、侧面、平面图,对城门的建造、修葺历史也做了细致稽核。同样,大部分城门楼都在后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被拆除,如今仅留下前门、德胜门等少数几座城门楼、箭楼和角楼,但当年气势恢宏的瓮城已经不再了。第七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从喜龙仁的《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摘取了关于城门的部分内容,他用颇富文采的笔触和黑白镜头,为我们留下了那些耸立了数百年的城门。文章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瑞典)喜龙仁著,沈弘、聂书江译,广东公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撰文|喜龙仁
摘编・徐学勤
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是用围墙将整座城市大约 50 多万人圈起来。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巨人,城门就彷佛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城门这张嘴。凡出入于城的万事万物,都必须经由这些狭窄通道,因此全城的生活脉搏都在城门处集中,通过这个通道的,不仅仅有浩瀚的车辆、畜生和行人,还有人们的思想和希望、希望和失落望,同时还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生老病去世。通过城门,人们不但能够感想熏染到生活的脉搏,还能够看到城市生命和意志的流动。这种流动,给予这座城市极其繁芜的生命和节奏。
当夜幕降临时,一样平常在夜晚关闭的城门就变得模糊不清。天一亮,当第一位赶着大车或小骡车的行路人赶到时,古老厚重的城门就像被唤醒的巨人一样缓缓清醒。随后,进城的人越来越多,有的颤悠悠地挑着装满农产品的扁担,有的推着小货车,各不相同。到了晌午,城门处的活动不但多,而且凌乱、繁忙。人力车和汽车殽杂在相继而来的挑夫、手推车和各种驴车之中,这种穿行于狭道的通畅节奏,是不会受任何威胁声音的侵扰的。这种节奏会随着推车、马车和人力车的繁忙程度而越来越密,但川流速率不会更快,尤其是当有相反方向的车、人同时穿过城门时,这种流动就会停滞一段韶光。到了午饭的时候,城门的流量达到最高峰;到了傍晚,流动开始放缓,随着暮色四合,人、车逐渐稀少。对付城门的关闭管理,如今的管理并不如过去那样严格。
城门处的生活场面,不仅会随着城区和郊区的分布特点而异,而且也会随着一天中时辰的变革而变革。南面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央和商业中央,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耸立着三座壮阔的城门。个中正门为正阳门,也被称为“国门”,规格上比其他两个门都要高大,古代仅供天子出入。只管由于岁月的侵蚀,它已经失落去了过去的富丽堂皇和古朴典雅,但它是北京城生活中央的所在地。在与正阳门相距不远的东面和西面,分别伫立着哈达门和顺治门——这并非是官方名称。此二门为南北通衢的入口。过去顺治门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由于送丧行列常常经由此门,故也称为“去世门”。而哈达门相反,不但天子经由此门,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常常从此门通过,故而该门也被称为“景门”,寓意光明、昌盛。南三门为管理内外城的闸门,属于二者的城门,故而不是人们进城的入口。两门的箭楼已经拆毁,一条铁路贯穿在哈达门瓮城和顺治门瓮城,二门现在的风格和外面早不如过去。
瓮城内看永定门箭楼
北城墙仅有两座歪路,而没有中门,二门的位置间隔中轴线较近,它们与南墙二门的位置并不对应。过去属于元大都一部分的城外郊区,现在还是村落庄样子容貌。由于北方一贯是受到攻击最多的地方,因此,北门历来被视为北京最主要的防御城门。时至今日,最大的营地也依然设在城市以北,北门依然是主要的军事交通要地。德胜门,顾名思义指道德美,也称“修门”
(“装饰”之门)
。安定门,又称“生门”
(丰裕之门)
,天子每年要经由此门赴地坛祈祷来年丰收。这些城门外不雅观气势雄伟,瓮城
(部分因修铁路遭毁)
和城楼由于没有屋舍、树木的掩蔽而显得兀然高耸。
东墙二门在修铁路的时候,瓮城部分被废弃,城门被改建。但是,远不雅观风景,城外依然有杨柳依依的护城河,景致十分迷人。这条大运河紧张功能是运输北京市民赖以为食的大米,运到后储藏在东墙下建筑的仓库里。东直门也被称为“商门”,天子从来不到此门,而普通老百姓却在此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的买卖活动。齐化门,常称为“杜门”,休憩之意,顾名思义,有仿照东直门取名字之意。
值得庆祝的是,西直门和平则门并未受到修建铁路的毁害,因此,这两个城门就为后来者供应了北京城门的本来面貌,这两个城门不仅仅保留有用于监视和防御的双层城楼,而且还保存着城墙围起来的可容纳小庙和小摊位的空地。在瓮城的外围,有一条通过瓮门的小路,杂粮店和餐馆依路而建。这里,城门就成为联系城市与郊区的得当纽带。城门处生动的场景,既是人们理解中国北方州里快乐生活的地方,也是知晓当代文明随着汽车逐步进入中国的平台,在清闲得意的村落庄生活中,当代生活显得极为不自傲。平则门,意为安宁和公道之门。由于附近居民常常被天子的令书惊扰,故而也被老百姓称为“惊门”。而西直门,意为开门,即晓喻之门,表达参悟天子令书的英明。
由此我们创造,各个城门的别称都具有某种含义和象征,只管别称的来源可能不可考了,但是这些别称却值得记录,由于它们是用来表明城门的浸染和特色。对付老北京人,他们还时常用这些名字,这些名字还存留在他们的影象里。内城各门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只是在大小和细微之处略有不同。最突出的特点是双重城楼。建于城台之上的门楼是一个巨大楼阁或壮丽殿堂,三檐双层,每层环有围廊,城台上还筑有可供登上城台的马道。箭楼城壁倾斜,为两层屋檐和四层箭窗组成,是非常朴素的砖砌建筑。外楼下部是凸出于瓮城弧形墙体外的壮阔的城台。
城门的全体建筑风格完备是中世纪式,与热兵器时期的建筑哀求不符合。城门虽然有改进,但是形式大体仍保留元代面貌,抵御枪炮的能力一如既往。众所周知,用薄砖建筑的城墙,木质构造的城楼,不但不能够供应防御功能,还随意马虎招致当代武器的攻击。值得光彩的是,除德胜门外的其他城门的门楼,都保存下来了。如果这些门楼被毁坏的话,全体北京的建筑群体就会失落去最有特色、最迷人的特点。从军事角度看,这些城门在当代武器面前,已经失落去了防御的功能,但作为征税的关口,却依然有代价。各城门的入市征收所,依然是北京政府最可靠的税收来源,但是城门和城墙的防御功能却不复存在了。
瓮城内看永定门城楼
西垣城门
平则门,官方名称为阜成门,是西垣南门,瓮城垣重修于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
,城 台年代较早,可能为明代建筑,均用薄砖精心砌成。城门木柱用铁丝加固,门楼第二层栏杆不可再见,下面的雕刻栏板残破而露出大洞。其下檐残缺不全,西北角完备缺失落塌落。其梁上的彩画灰尘蒙蔽、剥落不堪。从趋势上可以看到,如果那些年久的木质构件不及时予以改换,全体建筑就有可能完备坍塌。从建筑上可知,城楼可能建于明代,虽在后来有所修缮,但是间隔韶光总有三五十年以上。整体而言,该门楼给人以破败残缺、年纪过久的印象。
城楼坐落在石制台基之上,台基比城身略高一点,长为 33 米,宽 18.8 米,而楼身宽 27 米, 深 13 米,阔七间,进深三间。每面中间两根柱子的跨度较大,如此应对城楼四周的门。在城楼下面有立于方形石柱础之上的木柱,这些柱子直径大约半米。木柱的两侧由赞助的抱柱支顶上边的大柁。
城墙的框架也是木柱组成的,木柱分内外两排,木柱的四分之三被砌在墙内,中间以砖填砌。城楼的每面都有布列形式完备同等的三排柱,只有四角柱子是沿对角线排列。比较而言,这种把两排柱子部分埋于砖墙中的构造,并不是常见形式,其他城门都是内排柱独立于楼阁中的模式,这解释平则门是较早期的建筑。
金柱高约 9 米,支撑着第二层楼板梁。檐柱高 5 米,由嵌在其顶部的额枋连接。额枋止挑出三铺斗拱,支托着两根桁
(直径约 30 厘米)
,桁则承托着屋檐的两层微微翘曲的椽飞。梁的端部暴露在外,上面雕有花卉图案并施有彩绘。
第二层上的回廊与第一层上的形制相同,上面是屋顶,廊内没有容纳柱的空间,仅有嵌在砖墙内承托着斗拱的梁枋。第二层内部的长和宽均与一层相同,但墙厚仅及一层的一半,以是有余地环建回廊。廊上加筑平坐,斗拱再支托平坐,从下层檐上的梁枋挑出。第二层上的柱高约 7.2 米,由高下三层粗重的梁枋纵横连接。第三层梁与屋檐齐平,未装有天花板。
从屋顶构造可知,该门楼是由二层以上的梁枋构成。房梁是一种可获取的建筑模式,
左安门箭楼侧景
阜成门门楼剖面
紧张浸染便是构成屋檐上部的两顶端三角山墙。这种建筑风格,也被称为歇山式顶,即指带有向下延伸至屋檐一半处的山墙的有斜脊的屋顶。架在厚重额枋上面的三根承椽枋支撑着椽,脊檩则由紧贴屋脊的最上部梁上的瓜柱支撑。从构造图可知,房梁的数量繁多,后来重修的城门楼,虽然有些不同,但是一些基本的构造却变革不大。城楼高
(包括屋脊)
21.2 米,最宽处为 31.2 米。
其彩色紧张为朱赤色,但年代久远,又加上风吹日晒,色彩险些脱落无遗。但不管如何,所有砖构部分,都涂以朱赤色灰泥,门和柱皆用赤色,表面的梁枋和斗柱则是绿色和蓝色,平坐滴珠板有时用金色。凸凹相间的屋瓦,仅主干屋檐部分利用绿色琉璃瓦,别的则都是灰瓦。正脊和垂脊很高,皆采取盖脊瓦和琉璃脊筒;屋顶端部列有望兽,脊上安设着一排脊兽,喻意化险为夷。箭楼建筑风格简洁古朴,形似城堡,其墙壁用厚砖砌成,但它的构造浸染不大,仅仅是为了增加屋架的厚度。实际上,无论外表如何,箭楼的内部构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表面都会有曲线玲珑的、挑出老远的飞檐。根据碑记,厚砖墙段的年代并不比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
重修的瓮城早。
构造上,箭楼有两部分,主体正对着城门桥,建在凸向前的城台上。主体后面是规模稍小的抱厦,在瓮城墙壁之上。主体正面台基宽 40 米,楼上宽 35 米,顶部不敷 32 米,正面高 30 米,而城台高 13 米,楼高 17 米。主体的深度为 21 米,抱厦的深度为 6.8 米,二者的侧壁相连,每一侧都会有一个宽约 3.5 米的拐角。由此可知,抱厦的总宽为 25 米,高为 12 米,形成一种主屋的前厅模式。抱厦与主体墙体相连,但屋顶互异。
阜成门门楼正面
在布局构造上,箭楼屋架与门楼相同,都是梁枋连接的立柱,个中 6 根直径为 80 厘米的木柱列为一排,从楼阁中部延伸至 12 米高的屋顶,柱间相距 3.8 米。与大柱相对应的是那些较小的柱子,被埋砌在四面的砖墙中。这些独立的柱子和壁柱,都因此梁枋纵横连接,以撑持现已毁坏的城楼的主楼板。
翘曲屋顶一样平常都出檐深远,也是由依托在三铺斗拱上的桁木撑持的,斗拱则是从部分埋砌在砖墙内的坐斗枋上挑出的。墙壁很厚,基部不少于 2.5 米,而上半部分则由于外表面的收分而逐渐变薄,直至缩为 1.2 米厚。下屋檐与第三层楼板处于同一水平高度,环抱着包括抱厦的全体楼体,这个抱厦仅有一个三面暴露的歇山式屋顶,第四面则与主体相连。
箭楼屋檐的顶部无论在构造和装饰上都与城楼上层檐完备同等。同一般环境一样,上层檐之椽飞也比下层檐之椽飞略短。
箭楼正面和侧面的箭窗与大殿内部的间隔同等,即,第一层檐以下有三层箭窗,以上有一层箭窗,正面每层为 12 个箭窗,侧面每层为 4 个。箭窗的内外侧壁都呈梭形,以便使楼中弓箭手射出的间隔更大。而用枪炮防守基本就不须要了。我们疑惑是否有把重炮架设在楼上过,不过架在底层楼板上倒有可能。不过,在封闭箭窗口的木板上画上大炮口倒是很得当的,既起了装饰浸染,又大体上与想象中的城门防御功能相称。
箭楼外不雅观素朴,由于灰尘的长期附着,灰砖已呈玄色,屋瓦也变成了灰色;经由彩饰的额枋、斗拱和山花,也都完备褪色了。画在正面箭窗木板上的大炮口迄今犹在,像是向可能涌现的陵犯者发出警告。
瓮城门上有一座谯楼,比垛口略高,但没有凸出于城墙表面。它是一座正面开两层箭窗的朴素的砖造建筑。由于险些隐没于垛墙和女墙之间,故不太显眼。在城楼北面的主墙处,有一间相称破旧的哨所,还有其余两间被几棵古树掩蔽的供巡警和守城士兵居住的哨所坐落在马道前面的街道边。
在瓮城规模上,平则门并不是最大的,其宽 74 米,深 65 米。由于居民生活,其园地大部分都聚拢着煤棚和缸瓦铺,仅在东北角,在道路和城墙之间,有一个有围墙的小关帝庙似的建筑,但是,该庙彷佛不再作为人们的崇奉场所,由于里面堆积着各种瓶瓶罐罐和废弃之物。平则门瓮城的东南角,堆积着五颜六色的釉陶。如前面一样,空场后面,依然是脏乱差的煤棚。只有到了春天,靠近墙角的玄色地面上才会长出绿叶,从而呈现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尤其是一些小椿树,为这一角落增长很多绿色。当然,最积极的依然是赶驴人,一旦有行人涌现,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奉劝城外的道路适宜骑驴而不宜步辇儿,奇怪的是,对这个见地,很少有人反对。
穿过瓮城门往北是一条老式小路,路边排列着各种店铺和小吃店。在这条道路上,那些赶车的、推小车的、挑扁担的都能够悠然自得地走着。这种两边都是店铺的道路,与瓮城和城楼十全十美,成为全体建筑群的一部分,使人宛如进入几百年前的生活场景,也使人在进入深邃的城洞前熏染了一种怀旧的感情。
西直门也便是西墙北门,无论是规模还是构造都跟平则门相似。但是,它的瓮城规模较大,形状呈直角形。整体而言,西直门气度非凡,沿着宽阔的街道,人们就能够看到一座巍峨门楼,伫立在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这些排列在街道两旁的矮屋子大都是格子窗、格子门,样式老旧、新奇,规模很小,衬托得箭楼雄伟挺立。靠近此门,只见光秃秃的平地上瓮城和箭楼兀然耸立,俨然一座城堡,令人印象深刻。瓮城的前墙漫长笔直, 坚实地支撑起高耸的箭楼,比城门外
(瓮城城脚弧形处)
更显刚健壮不雅观。最能明确地表示出全体建筑群伟大规模的地方是城门侧面,特殊是南侧。箭楼略低于门楼,错落有致,笔直的线条、光鲜的轮廓、刚劲有力的造型,无不彰显著磅礴的气势。城下池塘中的倒影,更增加了别样的风情。
左安门瓮城与城楼
西直门箭楼外不雅观颇为古旧,不如门楼整修得那么精细,后面屋顶已坍塌。屋瓦显然经由更换修整,但是,砖砌墙壁依然未修。在规模、平面和正面等方面,与平则门险些一模一样。通过上面插图,可看出其全体形状。
西直门瓮城面历年夜,非常吸引人。人们一想到它就遐想到鳞次栉比的摊棚、车水马龙的集市。后面园地像平则门一样被煤棚盘踞,而在正门向南折向侧墙瓮门的道路上,则堆满了商品,到处是货棚,乃至还有一块人力车的停车场。而东北角处被一处环境幽雅的寺院的砖墙隔断,寺院里有屋舍几间、古树几株及精心照料的花园一座。里面有一座 1894 年重修的关帝庙,至今保存无缺,但已废弃不用。这座优雅的大寺院前面,曾经是羽士住所,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商业花园。盛夏时节,庙内椿树、桧树参天,绿荫落地,风凉怡人,与瓮城喧嚷的主体区截然不同。瓮城南墙的城洞上有一谯楼,从楼下穿出,便跨入一条隧道的老式街道,道旁两旁有一排排较为古老的房屋。一大批低矮的建筑包围着瓮城西南角,倚着瓮城墙而建,从城门顺着墙根一贯排列到箭楼城台处,如同一个长形市场,不过这个市场是由一长列店铺组成,店主把商品陈设在石阶上,或把食品摆在门外的桌凳上,供旅游选购。道路的另一旁,则是一长排供进城屯子人安歇的小店和堆栈。房屋模样形状千篇一律,但或为一层或为二层,高度不一,从空中望去,建筑物映在空中,参差不齐。这种独具特色的旧式街道格局,并没有考虑到任何审美的考量,而仅仅是出于风水的角度。这些房屋大多是由两根木柱、几扇大格子窗和格子门组成。这条街道,明显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设计支配,因此,在正在消逝的建筑风格中,显得特色明显。如今,那些乘着汽车前往颐和园和西山的搭客,在看到这些古老而有特色的街道时,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放慢速率,逐步经由这些街道。由于他们明白,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卧佛寺来,更能够给游客供应古老中国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
东墙城门
东边有二门——齐化门
(朝阳门)
和东直门,由于保存状况不如西垣各门,因此从建筑学不雅观点看也显得不那么吸引人。过去的环城铁路的施工对此二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有铁路从中部贯穿,瓮城险些全被拆毁——而在南垣的哈达门,因穿行而过的京沈铁路线,瓮城仅开了几个豁口。瓮城毁坏殆尽,箭楼已经没有门洞了,只有一条沿着铁道旁低矮砖墙蜿蜒而去的小道,拥有一个月台的火车站霸占了过去瓮城围栏的园地。这些铁路、火车站等,凸显出人们对古城门的美和独具一格特色的极度忽略及鉴赏力和建筑美学的匮乏。
从规模上看,齐化门可能是北京重修最大的城门。1902 年,其内外的两个楼曾经被重修。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时,齐化门被围攻北京的俄、日炮轰,破坏十分严重。城楼上的彩画开始褪色,干燥漆层也在剥落。幸运的是,城楼尚未糟朽。屋顶上的绿琉璃瓦也保存无缺,给城门增长了一抹亮色。远眺正楼全景,在绿叶青枝的陪衬下,城楼婀娜动人,甚为悦目。齐化门城楼共三层,构造比较普通,高和宽向顶部逐渐紧缩。廊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与西垣城楼对应,以是形制与平则门城楼相同,与西直门城楼和其他的重修城门相似,其构造模式也发生了某些变革。异于其他城楼的是,按比例其宽度要大得多。与平则门城楼的相应尺寸比较略大,楼宽 27.5 米,深 13 米,廊面阔 32 米,进深 17 米。在厚度上,此楼墙壁薄很多,并且只有中间一排柱子建筑于墙体之中。因此,齐化门楼与平则门楼大体相同,至于现在看到的构造不同,实际上是后来人重修的结果。
齐化门(朝阳门)门楼地盘图
这两座城门箭楼的平面和大小基本同等,因此,前面的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后者。然而,齐化门城楼保存得比较完全。城墙砖石呈浅灰色,砌缝平整,与城台残损不平的包砌砖面形成极大反差。而城台年代显然较早,但据碑文记载,一些地方也曾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整修。
从城台延伸出来的瓮城残垣,长度短,端部台阶为“之”字型,中间有数层平台隔开,台阶旁设有阶梯式扶手墙。实际上,这些看起来线条眇小的建筑,与前面古朴雄伟的城门、城墙风格大相径庭,彷佛它们受到了西方中世纪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然而这座瓮城受到的改变和代价与那些为修铁路而遭受的报酬是一样的。
在古老的瓮城中,有一座依傍在门楼城门阁下的小关帝庙。此庙内有古树数株,虽不起眼,但在以铁路占主景的单调瓮城中,却也别有韵味。城外狭窄的城濠上横有一座普通的桥,实在大煞风景,而城楼脚下破乱不堪的棚户区,更是不可语焉。
东直门,门朝东,与朝西的西直门为姊妹门,二者遥相呼应。二者制式相同,大小险些一样,这点与南边的两个歪路不同。与西直门比较,东直门保存得并不完全。瓮城城墙毁坏不堪,瓮城遭到摈弃,城楼状况亦不佳。个人觉得,这座城楼的历史可能不超过 100 年。
据墙上碑记,1803 年,即嘉庆八年重修了通向城楼的马道。东直门的墙很薄,解释年代久远一些。箭楼可能年代较早,但也不会早于乾隆末年。城台上嵌有石碑一块,但无铭文。
右安门箭楼与护城河
与西直门比较,东直门门楼平面尺寸略小。其楼宽 26.7 米,深 10.7 米,厚 1.2 米,廊面阔 31.5 米,进深 15.3 米。全体构造很是普通,柱有三排,中间一排是墙内柱,里外两排柱均有方形抱柱加固。木质材料表明年代悠久。楼台栏杆已残坏,下面滴珠板上洞孔累累。屋顶也开始朽坏、断裂,其颜色已经不是琉璃瓦的绿色,而是附着了草色的绿。柱子颜色由于受到灰尘的粉饰,已经不可辨识。整体而言,全体建筑古色古喷鼻香,有端庄秀雅之气。
东直门内外城楼间的间隔,比齐化门两楼的间距大得多。正对着其侧面看,只管两楼间的连接部分现已失落存,但是此门范围与齐化门差不多,仍能感想熏染到是瑰丽的建筑群体。瓮城的墙垣已经坍圮,仅有几段残垣堆积在箭楼城台附近,这些残垣比齐化门处的断墙要长几段。由于有植物丛生,这些残垣与主墙之间的园地并不显得空荡荡。其余,残垣倾斜的底部,也有齐化门一样的“之”字型台阶和层层平台,但建筑得更为和谐一些。之前我们讲述的城楼和城墙残垣,都是空空如也,赤裸光秃,呆板乏味,但是,东直门的残垣处,却草木葱茏,活气勃然。
只管有低矮砖墙和木栅铁道从中穿过,但是,东直门的原貌依然能够清晰可见。在这座古老瓮城的后面有几座环境秀美的小关帝庙。庙里供奉着几尊任其自生自灭的精美神仙雕像,几位当地的老人把这块地方作为居住之处。寺庙里外遍植槐树、榆树、椿树和散发着喷鼻香气的野枣树,它们的树冠在城墙顶上形成花冠。箭楼虽然很新,但是屋檐已经开始断裂,这种残破的景象恰好与周围的草木十全十美、和谐自然。
总之,瓮城遗迹中的自然景不雅观,仅仅是城外风景秀美的开端——城外的风景,是北京其他各大城门不能与之比较的。暮春或初夏时,城外柳色葱郁,河边芦苇刚嫩,此时正是赏景的最佳时节。
在这幅风景画中,宽阔城河是主体。岸坡下,幼童在芦苇中玩耍;水面上,群群白鸭浮游着,溅着水花,发出嘎嘎的声音;岸边,提着洋铁桶打水的男女,蹲在地上,悄悄地欣赏周围的田园景致。南边不远处的对面有一个小渡口,通过此处,人们就能够便捷地到火车站。偶尔,一只方形平底船,载着身穿夏装的搭客,在垂拂的柳枝中轻轻滑过。这幅活气勃勃的画面中那些又安静、又和谐的人和物,无不倒映在清澈的水中,又生发出一种新的意境美。实在,当铁路和汽车等当代化举动步伐尚未涌现时,这种田园风景,北京各城门附近是随时随处都可瞥见的。
南垣城门
南垣三门是内、外城之间的紧张交通要道。由于它们地处中央,故为人熟知。第一次到北京的游客,一定会折服于南门规模之伟大、建筑之富丽。但是,如果以历史学和建筑学的标准核阅,南门却是北京各城门中最不吸引人的。由于,此三门被毁坏得最为严重,被重修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前门,即中间正门,改建最为彻底,两边歪路改建规模也很大。
顺治门和哈达门是一对姊妹门,其规模、形状乃至保存的状况都险些一样。这两个门均是 1920—1921 年重修,实际上这种重修仅仅是修了门楼,而箭楼则一拆了事。听说是由于箭楼已残破不堪,加上有铁路从其下经由。实际上,顺治门楼上的房梁表面新而坚固,哈达门楼檐角已开始倾圯脱落,只有从门楼的里面才能够看到高耸城门的宏伟外不雅观;从表面则只能看到平淡和乏味,由于瓮城内没有一个主体建筑超过主墙的水平线,构造也无损毁或遭风沙侵蚀。
哈达门(崇文门)门楼
在规模上,哈达门的门楼比前述所有的门楼都大。其宽28.7米,深14.4米,廊面阔33.4米,进深 18.8 米,城台以上楼高 25 米,包括城台总高近 40 米。两层均面阔七间,进深五间。
有三铺作的斗拱,但其承重的浸染不大。梁枋较为宽厚,彩画也很亮丽。屋架也是三排柱构成,个中,屋中用梁枋纵横连接,并用童柱和檩共同承托。总体而言,其构造较早期的简练,屋顶梁的数目没有平则门等城楼多,但它仍是按照旧模式营造,从而使得形体巨大。
隆冬时节穿过右安门的驼队。
一条长长的街道上,坐落着高大的拱形城门和规模巨大的瓮城及箭楼。同时,人们在瓮城的侧墙挖了一条通道,一条两边砌有低矮砖墙的双轨铁路穿过个中。在这条干线上,火车频繁过往。但是由于城门常常因关闭铁路道口的围栏而中断行走,甚至引起交通拥挤。两侧有很多空地,宽阔的瓮城园地空空如也。低矮的哨所和建在对面的平顶房,是这里仅有的建筑。寺庙早已毁坏,仅余几株树。瓮城的墙上和城台顶上,长满了杂草。空地里小洋槐树和野枣树很多,雨季到来后,它们就野蛮成长。
由于箭楼荡然无存,城门外景致呆板无味。城壕仅有一条混浊的溪流,甚是狭窄,桥的模样形状也稀疏平常。附近最引人把稳的建筑便是铁路旁的煤栈。只有向南连续走,才能够看到一些雕饰都雅的旧式商铺。
如果要赏不雅观城门本身,就该当从主干道的正面不雅观看,或者从顺城街上的侧面不雅观看,由于马道周围有俏丽的树木作陪。
顺治门外不雅观与哈达门别无二致。箭楼已经不在,瓮城城墙拥有大而平缓的弧形。在箭楼遗址上,人们还能够看到柱础和几根大木料。此外,在箭楼台基上,还遗留了五尊生了锈的铁炮。个中三四尊铁炮上还镌有炮主的官员姓名。只有一位是崇祯时官员,别的为康熙时官员。事实上,作为历史文物和法国传教士铸炮技能的证明,这些铁炮该当保存在更为妥善的地方。
由于这些门楼重修一新,大小与哈达门基本相同,仅比后者略窄、略低些。因此,对其装饰和构造,不再赘述。由于顺治门保存无缺,因此,顺治门和哈达门在城门上差别很大。经由此门的铁路仅沿箭楼外通过,并没有穿过瓮城。与上述保存较好的西垣城门的情形类似,一条道路穿过城楼下的门洞,陡然东折,未沿直线连续延伸,穿侧墙的瓮城门而出。由此形成一个被墙隔绝起来的颇有特色的场所。
位于主墙和道路之间的小关帝庙是这里的紧张建筑,它被高大俏丽的椿树环抱着。靠近小庙附近是几间算卦师长西席搭盖的棚子,这些算卦人,大多为一些与崇奉无关而与人们日
顺治门(宣武门)门楼地盘图
常生活干系的问题供应指示,并得到用度。在瓮城另一侧,有几间脏乱而实用的斗室子,大部分的屋子地面上堆满了日用陶器,一些陶器还有釉,在白色小屋和绿树的映衬下光彩照人。瓮城后面的煤栈,占地较小,不扎眼,基本被厚木板、大批陶器和大树所遮住,以是大体上无损于这里的柔美环境。
这种独具风格的景致一出瓮城门就急速消逝了。实际上,当代中国城市中那种喧华纷乱的场面已经取代了古瓮城中那种宁静和谐的场景——现在险些都是繁忙的街道、砖和灰泥建筑的半洋式房屋、铁路和煤栈,以及一些在骆驼队和人力车中开辟道路、嘀声不断的福特牌汽车。
前门,即正阳门,位于皇宫正前方,是北京最主要的城门。伟大的规模使其成为北京最具有历史代价的主要建筑。关于此门及与此门有关的历史事宜,险些可以成书。但本书只能简单谈谈建筑特点和近年来所进行的重修。历史上,宏伟壮阔的古城门建筑群,是帝王禁苑与城市百姓的巨大缓冲,它是皇城的紧张通道。现在存在的城门实际上仅仅是古代城门的临时替代品。
原城门建筑群内有空场,包括一个巨大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北门面向大清门
(即现在的中华门)
,开在宏伟的城楼之下,通过一道长方形围墙与之相连。北门对面是辟于箭楼城台中部的南门,门前是护城河桥和外城的紧张大街——前门大街。这是天子专用的通道,其他人等只能从东西两侧的瓮城门出入。该瓮城宽 108 米,深 85 米,基台厚 20 米。
它是皇城最表面的庭院,通过墙垣、城门与紫禁城连接。如今,这里成了市场。过去环抱 它而建的瓮城与箭楼是防守内城的要冲之地。由于此门位于北京中央的枢纽地带,因此,这座伟大建筑的最初形式,被较新式的建筑方案
(尤其是城市交通)
所替代。
彰义门(广安门)箭楼
最先是在瓮城两侧建筑火车站,城门交通量因之陡增。到了民国政府,因其急迫哀求褫夺皇室特权,结果把前门交还给民众,这就意味着这座中心大门再也不是皇家御用,而是变成了可供民众利用的通道。由于进入内城的人马车辆数量不断增加,且都要经由同一个城洞,因此,这个孔道很快就显得拥挤不堪,交通壅塞时时发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委托德国建筑师罗克格
(Rothkegel)
研究制订改建前门的设计方案,目的是改进城门及周围的交通。
1915年,使北京正中大门当代化的操持制订后开始履行,到 1916 年,城门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那些曾经亲眼看到当初带有巨大瓮城、瓮城门和瓮城园地的前门原貌的人,在看到大部分的古建筑被人为拆毁时,无不扼腕嗟叹。但是,人们也承认,古建筑无论是在卫生或是交通方面,都不能与当代的建筑比较较。鉴于那位欧洲建筑师所受到的多方责怪,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他本人的见地。他认为,中国政府并未严格实行他最初的设计方案,而是对诸多细节任意修正。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修正大多属于建筑装饰和箭楼的细节方 面,并不涉及平面方案中的要点,这从罗克格师长西席本人的设计图中可以清楚查验。经作者首肯,我们将其设计图复制于此,并将改建前的前门总平面图一并列出,有何异同供读者自己判断。这里仅就个中的主要之处略作解释。
整体上看,瓮城城墙已经完备被拆毁,原来的封闭空地变成了开放园地,箭楼孤零零耸立在这矩形园地的南端,人们在原城门两侧的主墙又各开辟了新的通道。为了方便去城门东西两侧火车站,这里重修有宽阔街道。在瓮城围墙外侧,这条街道分两岔绕过,汇于护城河大桥上。靠近瓮城主墙的小屋和店铺,一律被拆除,仅剩下不雅观音庙和关帝庙。庙墙原封未动,庙南不远立有两尊大石狮。除此之外,瓮城其他地方依然是空旷的,其间只有两条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交叉而过的宽阔铺面路,路两侧被石柱和铁链环绕,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彰义门(广安门)瓮城与城楼
此外,北面位于门楼与中华门之间的广场,经由一番改建铺以石板。原来在广场北真个哨所,用铁链围起,现移近城墙。在哨所北面前方不远处新辟一眼装饰性喷泉。广场较远的另一半一贯到中华门一带,以欧洲办法栽种着一排排树木,周围用铁链栏杆围起。新方案中指出,在城楼两旁建筑两条直贯南北的平行街道,并使之从城门两侧新辟的两个通道穿过,从而能够疏通内、外城之间的交通。为了这个目的,人们不得不捐躯全体瓮城墙垣,由此,旧瓮城园地便不复存在。
实际上,这个中心大门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给人一种令人失落望的印象。门楼仍旧保留原样,但城门马道新开了两道拱门
(拱门对城楼构造的坚固有损)
,前面广场由于过于泰西化,而与城楼的建筑风格不大折衷。从南面不雅观望,其景象令人失落望。箭楼的环境也是如此,更加严重的是,人们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截然不同的办法重修。箭楼孤零零伫立,两侧瓮城残垣所余无几。两条呈“之”字型的马道直达城台顶部,台阶中间又隔有数层平台,汉白玉栏杆和凸出的眺台建筑在平台之上。不但如此,箭楼的窗户上侧还仿照宫殿窗牖模样形状饰有弧形华盖,有点哗众取宠的觉得。在前门全体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建没有什么实际代价和情由,最令人酸心。
有些人说失落火缘故原由是由于印度军队的轻忽。而中国人害怕恶运殃及全城,急于重修两楼,这是自乾隆时期以来北京修复的唯一古迹。门楼的建筑历时近五年,场面蔚为壮不雅观,高达八层的竹制脚手架震荡了西方建筑师。不用钉、锯、锤,仅将竹竿的端部绑在一起,即可架至任何高度,同时搭建和拆除也颇为随意马虎。”
改建前的前门箭楼正面
改建前的前门箭楼侧面
前门门楼正面
这种脚手架,目前仍盛行于中国和日本。在日本,我曾亲眼看到一座搭到令人晕眩的高度的木塔的建造过程。在日本,古老的传统工艺比在中国保存得好,木建筑保留着纯粹的形式,仍很盛行。可惜的是,这种建筑在中国北方由于缺少木材,已非常罕见,这种环境在新城楼上也有反响。在新城楼上,例如,构造繁多的斗拱已损失其构造功能,变成一种纯挚的装饰物。
沙窝门(广渠门)瓮城内景
正门两侧是两座黄顶小庙,东边是不雅观音庙,西为关帝庙,是前门建筑群中最俊秀的建筑。虽然有 100 年的历史,但维修状况良好。其院内,黄顶白碑的建筑掩映在树木参差的环境中,非常都雅。
位于两条铁路线旁并与城墙相接的候车室,年夜约靠近两侧。该候车室为传统模样形状,有宽大翘曲的屋顶和外廊,把城门楼与泰西式火车站连接起来。它们中间是一片宽敞的广场,即原瓮城空地,广场上的铁链、两座孤独的石狮和几棵萎靡的小树,渲染着冷落寂寞的气氛。箭楼南边是北京最主要的交通中央之一。一座宽阔的新式石桥横跨在护城河上,狭窄的护城河里污流穿行,桥面上形成的方形园地以铁链和石柱隔成四条大道,分别向南、东、西三面延伸出去,直达外城最主要的商业区。从城楼上俯瞰前门大街,这里有北京城最俏丽、最令人愉悦的街景。街道两旁绿柳依依,旧式牌楼林立,车水马龙,大车、人力车、驮东西的骡子、骆驼队,与汽车和自行车殽杂在一起——古老的事物正在逐渐让位于机器时期的新事物。
北垣城门
在北垣两门中,安定门如今更为人熟习,也更主要。它是一条南北向大街的出口。大街南段称王府井大街,北段为安定门大街。安定门间隔孔庙和雍和宫很近,这是北京城两个最大的庙院。这里交通川流不息,紧张是运载煤和驻扎在离城门不远的士兵。有的时候能瞥见一些喇嘛,以及一些来不雅观访雍和宫的蒙古族同道。
有箭楼两侧部分弧形城墙遗存,这样从北面望去,外不雅观依旧完全无损,并引人瞩目。与周围环境最不折衷的元素是一座有抹灰的墙和波折的山形墙的两层半洋式哨所。城楼气势雄伟,城台宽阔,砖壁朴素,并辟有四层方形箭窗,重檐挑出。城楼脚下有宽阔的护城河环流而过,城楼在水中的倒影,使画面更加俏丽。瓮城墙垣,或者只能称之为残垣,与城台似均为明代中期遗物,但城楼该当是后世所建——有可能为乾隆时重修,由于很多防御性城楼都是这个年代所筑。城楼毫无疑问是经由重修的,由于 1860 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时,城楼曾被炮火轰坏。条约签订前,此门一贯为联军霸占。
安定门城楼显得更为古老、残破。垂脊和中间的平坐已开始断裂。很多柱子裂痕严重,用铁箍加固着;梁柱上面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土,原来的颜色只能显露微毫,雨季一过,杂草灌木便在松动的屋瓦之间发达地成长起来。实在,这样的城楼,比起南城见过的新城楼,更为和谐同等。
安定门的规制险些与东直门完备相同,只有在比例上略宽于东直门,楼身宽 26.4 米,深 11.5 米,回廊面阔七间
(31 米)
,进深 16 米,高 22 米。至于墙的厚度和老檐柱靠近墙外侧的构造形式,都跟东直门一样。由此看来,这两座城楼可能统一兴建于乾隆年间。由于木质构造建筑破坏得较快,后期可能重修过。然而并没有创造有关此二楼建筑年代的任何记录,甚为可惜。
瓮城墙垣大部分毁坏,又加上铁道穿过,故内景令人失落望。遗留下来的形式与东垣诸门相同,也是中间隔有平台和“之”字型台阶,其风格风雅周详,与城墙和城楼的古朴、壮丽形成明显对照。幸运的是,在瓮城后面,还有一些古建筑和树木,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箭楼脚下有一座真武庙,虽然很小但是却很清幽,包括六间各自独立的寺阁。小庙院内立着一座大喷鼻香炉和一块块大理石碑,个中椿树交错,树影婆娑。安定门一带,除了沙质平原便是土屋,环境十分冷落,以是,这个小庙实在是一个难得名贵、引人入胜的风景点。
德胜门是北垣的西门,城墙至此开始折向西南,这一带比较宁静。在通向城门的街道两旁,有一些繁盛的大树和别有特色的老式店铺。但一附近城门,却让人兴趣顿失落,面前并不是一座带有围廊和三重飞檐的雄伟城楼,而仅仅是一座平坦的城台,辟有一道拱形城洞,微高于墙身。1921 年,人们认为有倾颓的风险,故把城台上的楼拆毁。1922 年的夏天,那时候大部分建筑材料仍旧摆放在城墙上。据我所见,柱子和梁均未腐烂。其余,柱础和墙址的原样也得以保留,这样使我能够绘制已毁城楼的平面图。相较于安定门门楼,德胜门门楼更大,楼宽 27 米,深 12 米,廊面阔 31.5 米,进深 16.6 米。城洞大而高,险些达到城台上沿。又由于城楼已经不存在,因此,更显得格外高大。
沙窝门(广渠门)城楼
穿过城洞,这里的景象就更加令人把稳。与安定门瓮城一样,此处瓮城的部分地方被穿过的铁路毁坏,而铁路两侧则围有藩篱和低矮砖墙。由于它两侧残垣较长,且铁路蔽墙是沿对角线伸
向瓮城残垣的阶梯式端部,因此与其他残缺不全的瓮城比较,保留着更多的古老特色。这条路绕过瓮城和城楼,分为两岔会于北面桥上。古瓮城后部并没任何新式建筑,仍是一个封闭、荒凉的园地。有一座保存相称无缺的庙院,寺前的椿树挺立健壮,全体环境令人憧憬。“之”字型台阶和瓮城残垣的雉堞被树丛灌木掩映着,这片荫凉和遮蔽风雨的地点,也因此吸引许多食品贩、赶驴人和剃头匠及浩瀚的顾客过来。整体而言,德胜门瓮城景致奇丽、宁静怡人,是任何其他瓮城难以比肩的。这里的真武庙,比其他城门寺院都大。庙内,于正门两侧各有钟、鼓楼一座,还有几间亭阁和羽士的住房。但是,这座寺庙是否确实用于宗教目的我深表疑惑,由于我末了一次参不雅观此庙时,瞥见一两间小屋里堆满了棉花,部分地皮还种有白菜和土豆。
德胜门箭楼的规模和构造非常一样平常,是最近二三十年重修的。楼的砖墙外表蒙有一层淡灰色,与城台古朴的砖石构造比较,有碍不雅观瞻。城墙是建于嘉靖或万历年间,而城台主墙于乾隆时重修。箭楼前方的古老城门桥已开始崩坏,城壕轮廓也变得不甚清晰,但如果忽略城楼脚下褴褛不堪的哨所的话,全体楼景在这片光秃秃的地带中还是相称壮不雅观的。
德胜门瓮城内的珍品,是一座立于铁道中间的碑亭。亭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石碑,镌刻有乾隆帝六十二岁时的御制诗。这位当时的太上皇在提到德胜门的名称时,在“德胜”二字上发抒了一番豪情壮语。
本文摘自喜龙仁著《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 喜龙仁
编辑 徐伟
校正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