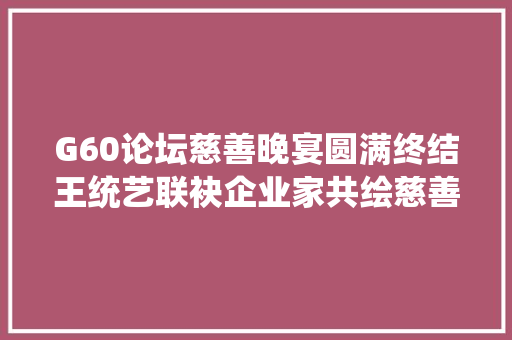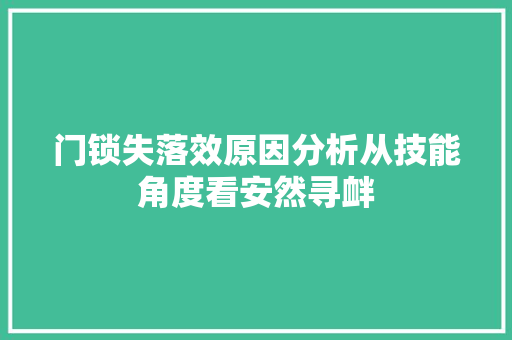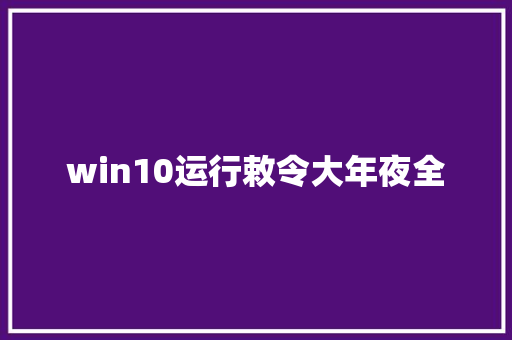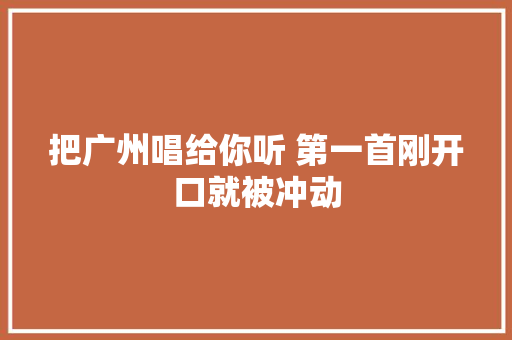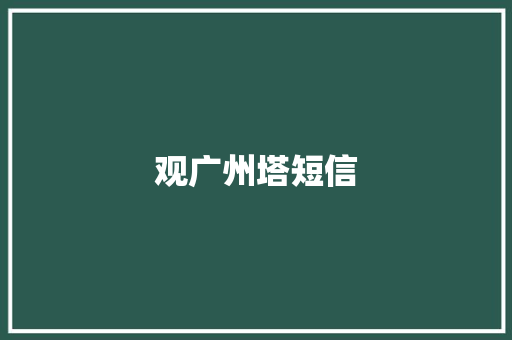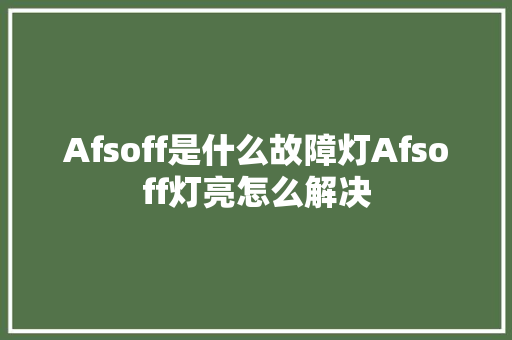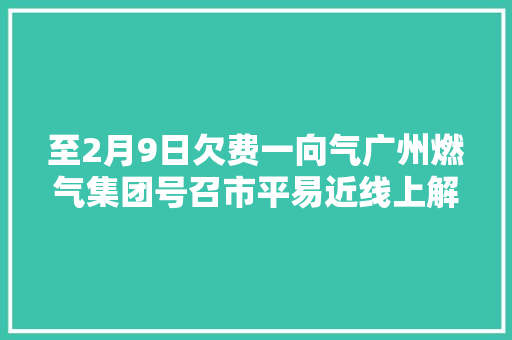大洋网讯 毁灭性的台风最高风速可达到每小时一百多千米,可轻易吹倒高楼大厦,不过在广州塔上隐蔽着一对抗台风的利器:两台各装满10万公升水的巨型水槽……9月16日,“山竹”来袭之后,在网上流传的“广州塔塔顶竟然装了20万公升水,知道为什么吗?”的一段视频不免让人惊叹。
谭平,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央教授,正是这一装置的设计者,他阐明道:网传20万公升水的说法并不严谨,实则是两个各650吨水箱,每个水箱的水约350吨,其余300吨是混凝土水箱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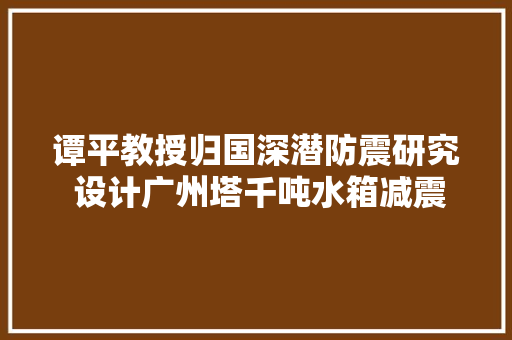
“山竹”到来确当日,他像日常一样“轻描淡写”:“只派了一名年轻的老师去塔顶采集数据”,如果放在以前,“要派一大队人上去”。
“按照我们的设计,再来两个‘山竹’也不怕”,在位于广园路28号的办公室内,谭平说话的语气武断。
位于广园路28号的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央,墙上的牌匾字迹已经斑驳发黄,谭平的办公室就在这栋老楼里。在与办公室相邻的实验室内,堆积着包括广州塔、港珠澳大桥桥墩、高铁桥墩在内的抗震实验模型。
600多米广州塔的抗震装置就出身在这栋有些年代的楼里。
因广州塔返国
谭平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人生会与广州塔联系起来。然而,2006年,正是广州塔让当时在美国做博士后的谭平下定决心返国。
2005年中,谭平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接到自己海内导师周福霖院士的电话,动员他做一点实际的工程项目。老师所说的这次机会指的便是广州塔的抗震系统。
在美国留学做理论研究多年的谭平有些动心:“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当时,谭平的学术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他的导师正是当时美国减震掌握学会的主席,凭着自身的研究实力,谭平很快就在美国学术界崭露锋芒。
在很多人看来,谭平未来之路顺其自然会留在美国发展。谭平却志不在此,“在美国这种发达国家,做理论做实验比较多,但真正用到实际工程的机会非常少”。
“像纽约、芝加哥,城市培植已经基本完成,新建建筑很少;而中国正是培植的高潮,现在环球最高的二十多栋建筑,有十几栋都是中国的。”谭平心中的天平早已倾斜。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做出点事才行。”
老师周福霖的电话就像给他点了一把火,“一着就燃”。在谭平返国前的半年韶光里,他就开始在学研之余查阅各种干系资料。他记得很清楚,2006年1月6日回到祖国。不过周末,他没有安歇,也没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而是直接去了办公室开始了预备事情。
“对那一年的春节没什么印象了”,谭平隐约记得当时已经靠近年终,人们都逐渐进入到放假模式,然而对谭平来说,“紧张的日子刚刚开始”。
谭平及早地开工,正是预见到了整件事的难度,“仅广州塔的减震方案就做了两年”。此项方案的事理提及来并不难,但在广州塔这一独特造型内详细履行时,“难题就出来了”。
“抠门”设计师不断优化方案
当时,谭平去了台北101大厦取经。一研究,他就创造难有借鉴之处。“台北101大厦给了五层楼高的空间做抗震系统,而广州塔只‘给’了两层,还不是完全空间,要与一些不雅观光游乐举动步伐共享。”谭平说,末了他拿到的“地盘”只有不到9米,水平间隔±1.2米。
“空间的高度不足,水平方向的位置也不敷,这给我们的寻衅非常大。”谭平心里有些打鼓,“基本没有先例可循。”
更让谭平以为“雪上加霜”的是,“作为不雅观光塔,哀求设备不能用混凝土弄得黑乎乎的,还要具有一定的不雅观赏性”。以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水箱造型,既要知足减震功能,又要好看,“这一项,我们花了三个月韶光来优化”。
从刚开始几个不同的方案,到末了确定一个最可行的方案,谭平说:“我们打算剖析花了一年多韶光。”末了把这一方案确定后,谭平团队又花了数年韶光来完成各细部的深化设计,试验与现场调试。
谭平满眼自满:“台北101大厦是一个被动掌握系统,而广州塔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元素,有主动掌握也有被动掌握系统。全体塔遍布传感器,能即时把数据通报到电脑,再根据内置的实时智能算法,可以下指令让减震系统始终处于最优的事情状态,把全体塔的震撼减到最小。”
还让谭平更骄傲的是,广州塔的这套减震系统还是个“抠门”的方案:把塔内原有的消防水箱的质量变成全体减震系统的组成部分。“台北101大厦减震系统的金球花了400万美元,广州塔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来做。我们用混凝土增加消防水箱的重量,通过优化形状,结果看起来也还不错。”谭平笑道,“混凝土和水都花不了什么钱。”
广州塔减震系统施工现场
逼出来的方案
这些年来,减震系统也遭遇了好几次大台风的正面“宣战”,这次的“山竹”是风力最大的一次,不过,谭平却没有2012年“韦森特”来访时那么紧张,当时塔顶风速达到35米/秒,这次的塔顶风速超过了40米/秒。
前几天“山竹”到来,谭平说:“大家都在感叹,减震系统都运行八年韶光了。”
“从2006年开始到确定减震方案,花了1年多韶光,各关键子系统模型的性能测试试验,在实验室里又花了近两年韶光;在广州塔顶的原型掌握系统的现场安装与调试,又花了两年韶光。”谭平说,直到2010年,整套减震系统才正式启用。
谭平感叹,子系统测试时,全部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事情,特殊是炎酷暑日,塔顶上也没有空调设备,常常在里面一待便是一整天。
不过,这些在谭平看来也“算不得什么”。2008年,整体方案的打算已经完成,但“设计每一个子系统,精确到每一个零部件”让他非常头疼。“我们确定采取天下创始的主被动复合质量调谐掌握技能后,要把这个理念落实到每一个子系统,包括调谐所需质量如何利用现有消防水箱达到?怎么把水箱支承起来又不能偏离中央?若何让系统运行时的摩擦最小?采取何种驱动装置来实现海内首例主动掌握。”谭平形容走的每一步都“揪心”。
比如他们最初设计的两个正交的阻尼器,在水箱下部的有限空间运行时极有可能会“斗殴”。“好在还有一丝可能性”,后来,他们把整套系统的每一寸空间都进行了优化,把空间“挤到极致”。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丁点空间的腾挪每每要对全体系统进行重新调度,这个事情量就极大了。
他拍着办公桌说:“好多个晚上就在这里,以为做不下去了。”不过,心里还是想着:绝不能放弃。“好在不是一个人,大家一起想点子,把它坚持做下来了。”谭平说,“有好的想法要去真正实现并不随意马虎。末了出来这样一个方案,完备是逼出来的。”
风再大塔都吹不倒
:广州塔的减震系统还会不断更新吗?
谭平:我们会不断地更新。由于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实在,我们已经更新过一次了。
在过去,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做造诣行了,现在则会更多考虑到它的安全可靠。譬如装了这么多传感器,万一有一个传感器失落灵,我们就会把这个传感器的信息屏蔽掉,不会由于缺点信息而误导掌握系统。
再过两年我们设计的系统就十年了,到了这个十年的阶段我们会为系统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假设有比“山竹”更猛的台风,会不会担忧广州塔的抗风能力?
谭平:没有什么担忧的。首先广州塔本身没有安全性的问题,风再大塔都是吹不倒的。
其次,系统现在的这个潜力才用了不到一半。整套系统都有±1.2米的位移,这次“山竹”台风系统的位移才40厘米旁边,即便到了80厘米,系统进入第二级事情状态,系统的阻尼会增大,减震效果稍有低落,但整套系统的安全裕度还很大。
“山竹”已经是个足够剧烈的台风了,要比“山竹”大一倍的风力才能达到我们第一级优化的极限,我以为我们(的系统)是绝对安全的(笑)。
:为什么当时下定决心返国?
谭平:我的家人都想不通。他们以为国外好一些。我跟家人说我到哪里事情都饿不去世,在美国也能过得很好,但是人不仅仅是谋生的问题,还是要做点事情。在国外可能只能做研究,但是返国后可以学甚至用。
:返国之后就一贯待在这里做工程防震研究吗?
谭平:是的,我从2000年参加事情之后就一贯待在这里。你看到的是破褴褛烂的实验室,我倒是以为这里是踏实做学问的地方。当时返国也有些学校约请我,但我还是回到了广州大学。一方面我的导师在这里,另一方面是广州大学在这一块领域做得非常好。
:现在国际互换有没有共同互助的空间和方向?
谭平:广州市给我们投了3.6亿元在大学城建立新的实验室。建好后的实验室在全天下都是一流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和更多同行互换和互助。
现在提倡“一带一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互换,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我们立时要去访问意大利减震方面天下有名企业,我们中国也有一些相称规模的企业。希望借助这种平台能把国外的前辈产品引进来,同时把海内好的产品带出去。
文、图/广报全媒体杜安娜、罗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