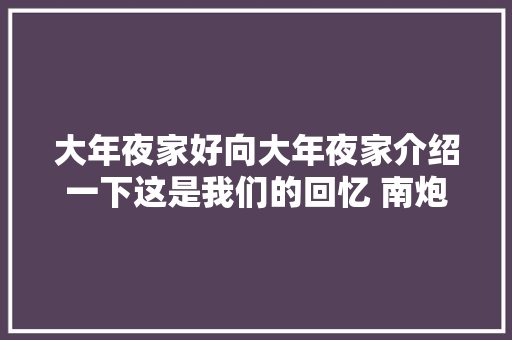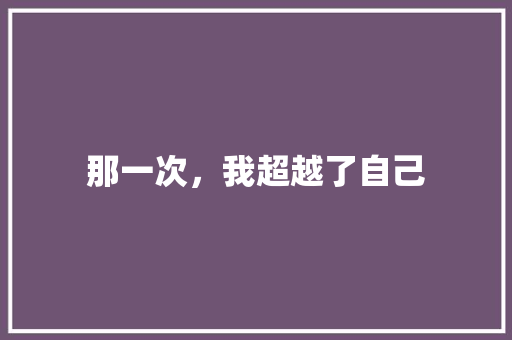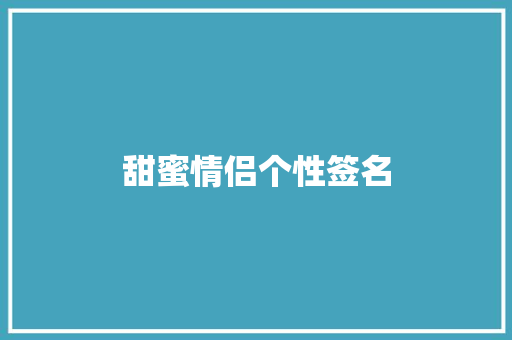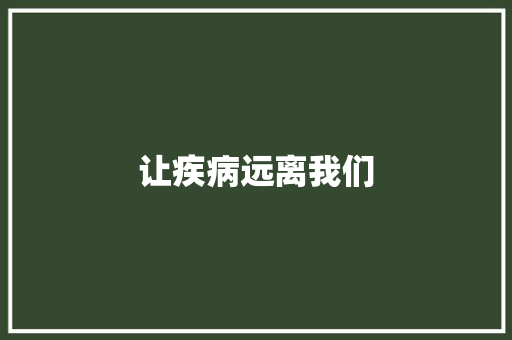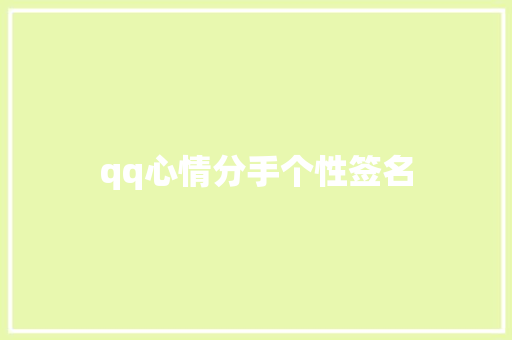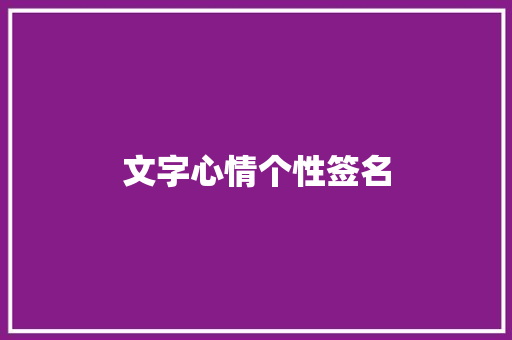个中有一首歌在当时也并不很红,却是最值得咀嚼回味的,便是这首《不来也不去》。
不来不去,何谓“不来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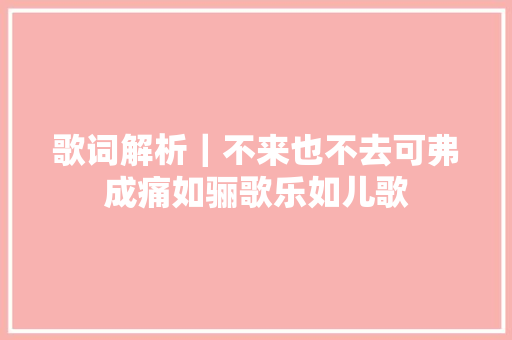
“不来不去”是一种佛学术语,谓法之本性无去来往复也。智度论曰:“即知统统法,不得不失落,不来不去。”
先不必去想为何这首歌会和佛学有所分缘。
词圣林夕去到化境的歌词,令人明白人海逐日发生的情爱,缘分使然,刚巧主角是我们,啱啱遇着刚刚,没有欠谁。
接下来,我们进入歌词。
第一段主歌部分
扬帆时 人潮没有你
我是我 和途人一起
停顿时 在你笑开的眼眉
望眼将穿之美
如果大家曾有机会独自旅行,或是一人置身于热闹的地方,会很随意马虎有这样的共鸣感——虽然周边人来人往,但是仍旧感到孤独,由于身边的人都是陌生的。
人生就像一场出海航行,漫长的旅途,起初进入这人海,我们都是独自一人,和万万千万陌生的途人一起。
但在某一次停顿安歇时,我遇见了你。望着你那笑意盈盈的眼睛,如望眼将穿之美。
秋水,秋日的雨水、湖水,古有“岁暮寒飇及,秋水落芙蕖”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日的水,也不会是很磅礴,而是那种斜阳照射下的温顺,是落花和流水的相遇、共振。
“今日箇蹙损春山,望眼将穿。” 秋水便是女孩的明眸,是爱人明澈的眼波。
这便是我们的相遇。
回程时 浪淘尽了你
任背影 长睡着不起
留下我 在粪土当中 翻检背囊
直到拾回自己
回程时,浪淘尽了你,我已没有了你。失落去恋人的时候,人们每每有一个颓废期。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事都不想理,放任背影长睡不起。
此时的我还心有怨气,从「留下我」三字便可感知一二。我「在粪土当中翻检背囊」。翻检背囊便是翻看回顾,在身边散落一地的影象碎片中找寻过往。
值得寻思的是林夕在此大胆的用词——「粪土」
林夕曾在2000年王菲演唱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中写道:「爱护自己 是地上拾到的真理」、「从泥泞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
这封大略的劝人自爱的情书,现在看来仿佛已无法拯救因损失而沉沦的失落意人,「泥泞」一词也已无法再形象地展现“沉溺、挣扎、思考、重生”的苦痛过程。于是,我已不止身处泥泞,而是身陷「粪土」之中。
在这痛楚之中,颓废地回顾过往,直到我重新将破碎散落的自己拼凑成人的样子容貌——只是样子容貌。
掌心因此多出一根刺 没有刺痛便
就当共你 有旧情没有往事
直到我拼好自己的躯壳后才创造,手掌心里已多出了一根刺,因执念而生的刺,握得越紧,刺得越痛。
既然这根刺去除不掉,那便干脆假装不知,也就当作我和你有过旧情,却没有往事。
但谁又不明白「没有刺痛便
但真正的忘倒是不须要努力的。
第二段主歌部分在解读第二段主歌之前,先分享一则耳熟能详的佛理小故事。
据《坛经》记载,一日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讲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幡动,一僧曰风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由此可知看待事物的三个层级:一是只看出幡动,这也是最表面的层级;二是看出风动,已经从表面征象不雅观察到了内在缘故原由;三是看出既非幡动也非风动,而是心动,这便看出了外物的迁转流变皆有自我心中分缘产生。
看出恋人的拜别,这是幡动。
看出恋人的来和去,这是风动。
看出恋人的拜别,太多的情歌唱出了这一层的心声,也像林夕2000年写给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写给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前者失落去恋人,渴望自强,后者失落去恋人,祈求天父怜悯。它们都讲——失落去。
看出恋人的来和去,有如林夕2002年写给陈奕迅的另一词作《人来人往》。「爱若能够永不失落去 何以你本日竟想找寻伴侣」,此时的林夕已然领悟到“来”和“去”的平衡关系——我当天会得到你,是由于你离开了他人,若没有“去”,“来”也不存在,同样正由于我本日究竟会失落去你,当初我也才会得到你。犹如落花和流水的相遇,终极流水蒸发变云,落花落地生根,曲终散席时,谁是客,又要怎么分?实在每个人都是别人的过客,人来,人往。
谁同行 仍同样结尾
血液里 才遗传悲喜
谁亦难 避过这一身客尘
但刚巧出于你
看出恋人的不来不去,这是心动。
这统统,与你是谁无关,与是不是你无关,我发觉实在无论是和谁,结尾都一样,我想明白了,便可以不再责怪你,不再有怨气,可以放下你。为什么谁同行都会是同样结尾,由于悲喜都生于我心,它流淌在血液里,不因你到来,也不因你拜别,而因我心动,若碰着的不是你,难道我就不会经历这番悲喜了吗?人生平中每次出行,总会在旅途中风尘仆仆,人生也是天下的过客,谁都难避免这一身客尘,只不过这样的情节,刚好主角是你我,这身客尘,刚好出于你。
杜牧在《赠别》中寄词:“烛炬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黄庭坚在《题阳关图》中落笔:“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
而实在我们的感伤与离愁,又关烛炬、烟柳何事?只是心中未定,才寓情于景。
正如释敬安的《流水》所言:“落花流水初无意,惹动人间尔许愁。”
同样的道理也像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所说:“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头上。”
这统统,非“幡动” “风动”,而是“心动”。
低头前 没缘分丧气
睡到醒 才站立得起
盲目过 便看到天机 反复往来
又再做回自己
【垂+目=睡】
低头颓废前,我为没缘分感到丧气,任背影长睡不起。
现在我醒了,之前只是拼出了自己的样子容貌,一具躯壳,而现在,我可以站起来了。
因我盲目过,故得以窥见天机,创造真理,便终于可「做回自己」,而不但是「拾回自己」拼接而成。
纵然生平多出一根刺 没有刺痛别要知
就当共你 有剧情没有故事
「纵然生平多出一根刺」,原来在掌心的那根刺,现已融入生命,仿佛稀释了,没有刺痛别要知。
于是,我就当与你有剧情,没有故事。“剧情”是一种设计好的情节,这样的剧情纵然换了主角,也依然会发生罢。
我看到天机,终可释然。
而作甚天机,答案在副歌中。
副歌
如开篇所说,“不来不去”是佛学术语,我们要明白,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般若”,意为“聪慧”。而这聪慧,是能够参透生命的聪明,我们对生命的认知,在佛学里就叫“知见”。
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卷七曰:
见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断。常见者,见五众常,心忍乐;断见者,见五众灭,心忍乐。统统众生,多堕此二见中。菩萨自断此二,亦能除统统众生二见,令处中道。
这便是说,世间统统众平生日有两种缺点的见地,一种叫常见,一种叫断见。
所谓常见,便是认为“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常恒不变,并且心中认可接管这种不雅观点,以此而“心乐、心喜”。
所谓断见,便是认为“五蕴”是灭后不中兴的(如持有“人去世如灯灭”的不雅观点),心中认可接管这种不雅观点,以此而“心乐、心喜”。
菩萨便可以断除这两种缺点的见地,也能够帮助和辅导统统众生断除此两种缺点见地,令众生处于中道。
作甚中道?中道是指众生本来具有的真如佛心,此心含藏万有,森罗万象许庄严,然而本性空寂,从来不熏染万法,这样本就具足中道性。
而中不雅观则是我们藉由佛法去亲证这个真如佛心时,能够现前不雅观察、体验真如佛心具足中道性、清净性、涅槃性、真如性,这样的妙不雅观察,即是中不雅观。
中道不雅观是大乘佛学的基本思想,龙树菩萨在《中论》中说:“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这便是所谓“八不中道”。
但又要如何破除“常见”“断见”——
破除常见,我们要明白事物不会常恒不变。《金刚经》有 “统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不雅观” 。“有为法”指分缘和合而生的统统事物,既然虚幻而短暂,我们便要学会接管,接管纵然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如烟 因给你递过火
如火 却也没熔掉我
回望最初 当损失是得着可不可
可痛若骊歌 乐如童谣
像你没来过 没去过
【火+因=烟】
【因+果=缘】
因我给你递过火,我们就产生了如烟的爱,烟是那么虚无缥缈。但说它虚无,却又因我递过火而如此炽热。可又不对,爱如火炽热,可无论是热恋还是一起到失落恋的冲击,却也没熔掉我,以是它又是那么微小。
因+缘,才能得果。
好似因是种子,缘是雨露农夫,此分缘和合而水果。
我们递过火,我们的相遇便是有了因,可是究竟是没有缘分,我们终不可得果。
既然如此,回望最初,可不可以就当作损失也是一种得到呢?正如“塞翁失落马,焉知非福”。
这样,就可以「痛如骊歌」,也可以「乐如童谣」,只看我怎么想,统统随我心,就彷佛你最初没有来过,本日也没有拜别过,像一场梦,我仍安好,无事发生。
但这样就参透了吗。
我们破除常见,在创造事物虽然会变的同时,实在也不变。
有幸在一位B站up主的视频里得到启示,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现在有一个新鲜无缺的苹果,常见便是我们认为这个苹果可以永久和现在一样无缺,永久属于我。而作为破除常见的一个行为便是我们吃了它一口。
我们将苹果从最初的无缺到后来的残缺用胶卷记录下来,第一帧画面是无缺的苹果,末了一帧画面则是残缺的苹果。
接着,我们分别剪下这两帧画面单独拿出来。将无缺苹果的那一帧给A看,将残缺的苹果那一帧给远方的B看,A和B二人会认为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苹果吗?
不会,他们会认为这是两个独立存在的苹果,一个无缺,一个已经破损。一个苹果,好和坏的状态,相对独立,各自存在于各自的时空。
也犹如我们平日里看到的LED滚动屏幕,看似是字幕在屏幕上滚动,实则不过是一个个小LED灯一闪一灭,它没有动,却让我们看上去以为它动了。
这也便是我们看世上的很多事物,它实在没变,可我们的错觉让我们在脑筋里认为它变了。
以是当初无缺的苹果,和现在近乎糜烂的苹果,它也是独立存在的,它并不因此前的苹果来到现在,也不是现在的苹果去到过往——它没有变。
我们有了相遇的因,却没有外在的缘,不能走到末了。但是倘若也用胶片记录下这一段旅程,那起初的我们,是不是还定格在胶片的第一帧,我们依旧存在呢。
佛学还有一个词叫“霎时”。那一帧画面,我们便可称为一霎时。那一霎时,永久定格在那,那个因产生的果永久存在,那根刺永久存在,不会消逝。走不出来的我,就像是一直地沉浸在那一霎时里。这样该怎么办——
既然每一霎时都是定格的,愉快定格在某一瞬间,不愉快也定格在某一瞬间,前一帧画面往后一帧画面并无关联,它们都存在于一个时空没有改变。以是我可以在那根刺刺痛我的霎时里「痛如骊歌」,也可以在曾经愉快快乐的霎时里「乐如童谣」,「像你没来过 没去过」,并不是强行要去忘却这段影象,而是我们走过的旅途,我们的关系,已经定格在那个时空里,不来不去。
结尾副歌
如花 超生了没有果
如果 过路能重踏过
就当最初 是碎步湖上可不可
不种下什么 摘来什么
像我没来过 没去过
我们种花,希望它结果,可超生后,终没有果。
如果过去一霎时,现在可以重新踏过……
「就当最初 是碎步湖上可不可」。过去的画面、感情,实在永久都在,那一帧画面和当下这一帧画面并非同一事物,我们只要记得有过俏丽的曾经就已足够,不用去想它后来变成什么样。
如果把掠过湖面的过程变为一帧一帧胶片,每一步都是一帧画面,这是不是就像是一霎时一碎步?那俏丽的曾经,便是碎步湖上的俏丽霎时啊。
像绽放的烟火,纵然现在已经熄灭,但是它已经永久定格在那个时空,它,不灭。
我们不须要去想那俏丽的画面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变的不是你我,而是时空。
过去种下的和将来摘得的,就像过去和将来的两帧画面,两者乃至无关。
以是不仅是过去的你没和我往未来去,实在我也没往未来去,「像我没来过 没去过」。我们仍在某个时空,在过去的某一霎时,彼此相伴,拍拖。
总结
实在,统统都是心动,外物的迁转流变皆由分缘产生,幻化不实。
林夕在他的书里写过:“只要心静,世间统统起伏变革,都不过是有为法,如露亦如电,虚幻而短暂,悲欢离合聚散的所谓感想熏染,没错,会上心,可一个人总该有能力以至修为去掌握人最自由的地方,心。”
如果我们能掌握心不为外物所动,则不会牵于世情,生出烦恼各类。但凡尘俗世内,又怎可能不惹尘埃,不熏染一身客尘。
《金刚经》云:“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心。”
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的工画师,对自身所感,对周遭的环境,既然都源于我见而生出声、色、喷鼻香、味、触、法,都没有一定的形态,为何不可随心而涂改?
若能心如流水,流到哪里是哪里,随自然环境而改变形状,心无所往而不假外求,与自然成为一体,不为拥有而拥有,内心的空间任我行,则无需向天问,于江湖笑而不傲。
这都是林夕想要表达的佛学思想。
也便是“天机”。
也不必为此反将自己禁锢、束缚,我们不必忘怀感情,也不必放下爱人,但可不为了拥有而拥有。爱若为了永不失落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
“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乃是实兴。实兴者,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护法品》
原该是参透统统有为法的成住坏空,不悲不喜,乃是佛性。但这一阙词,究竟是林夕想安慰失落恋者,让人把悲哀识破。我们也无法达到那般境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是无论能否领悟到些许佛理,只要能得到哪怕一分抚慰,也已足够。
就当我们还在一起,在某一个时空里,在那一个霎时里,还有我渴望的那一双你的眼睛,我的抱拥。
“如嫡便要阔别,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