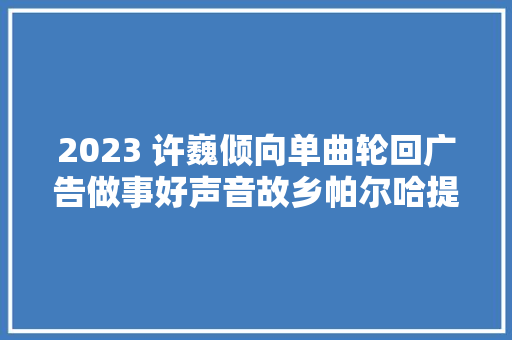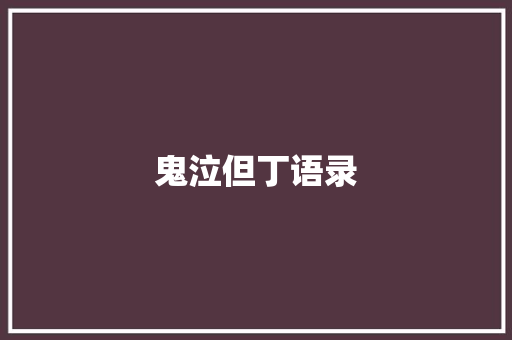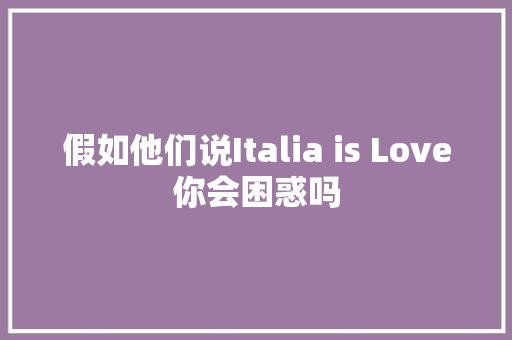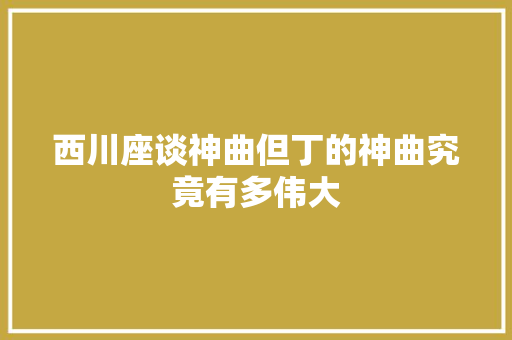英国画家亨利·霍利迪作品《存问贝雅特丽齐》 资料图片
《马可瓦尔多》封面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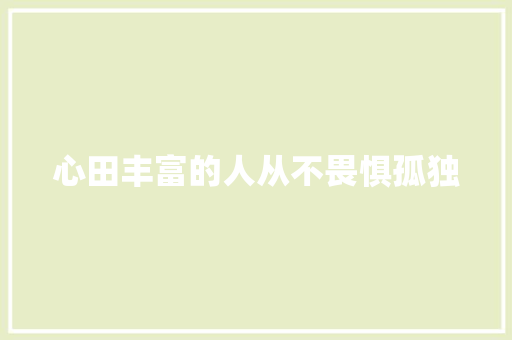
卡尔维诺漫画像 资料图片
波提切利所画但丁 资料图片
对付当代人来说,越来越便利的电子通信设备,并不能从根本上肃清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时乃至从技能上加剧了沟通的障碍。在物质生活日益改进的本日,如何面对孤独彷佛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一点上,文学已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痴迷书本的人
一个终生未能拥有自己家庭的废纸打包工人,35年来一贯置身于地下室的废纸堆中,从事着天下上最卑微的事情。但他却以此为契机,通过阅读神话、哲学、文学等著作,将自己本来可能孤独至极的人生过得分外充足。这便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1997年)的小说《过于鼓噪的孤独》中的主人公,也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人生。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曾经志愿去做钢铁厂工人,工伤病愈后又到废纸收购站成为打包工人。赫拉巴尔笔下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默默无闻,乃至“被扔到社会的垃圾堆上”。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自经历,挖掘这些人物身上的特点和措辞中的精髓,使他们成为文学星空中熠熠发光的人物。他们险些都具有同一个特点,那便是所谓“巴比代尔式”的举止言行。这是一种生活办法,也是一种使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的风格。
小说中的废纸打包工汉嘉,乃至将这种生活称为“我的爱情故事”,将他度过生命中大部分光阴的地下室视为天国,由于那里是完备属于他的天下,他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迫在眉睫地阅读被当作废纸丢弃掉的宝贵著作,就彷佛是“把俏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他的生活原来非常艰巨:老鼠成群的地下室,永久处理不完的旧书,还有成群向他进攻的苍蝇,唯一的抚慰仅仅是偶尔喝点啤酒。然而,他诙谐地说:“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能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拍浮池……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汉嘉乃至决定退休后把废纸打包机买下来,放在花园里陪伴他。他也曾说自己的生活一向是悲哀和孤独的,却也在个中倾注了所有的激情亲切,而且借此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建立起联系,尤其是那些个性光鲜又充满韵味的茨冈女人,还有一些文化人,个中就包括时常来他这里购买废纸堆里淘出的书本的美学教授和《戏剧报》评论家。汉嘉之以是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正是由于他长于从面前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又长于用诙谐来装饰自己悲惨的日子。
汉嘉对付书本的痴迷,不禁令人遐想到美国作家雷·布莱伯利(1920—2012年)的小说《华氏451度》中的消防员盖·蒙塔格。故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年代。主人公蒙塔格同样是一个痴迷于书本的人。他在实行焚书任务的时候,趁同事不把稳将勒令销毁的书本带回家偷偷阅读。实在,其他消防员也都会好奇地“偷回”一两本禁书,只不过他们会在24小时内将其销毁,以担保百口安然。蒙塔格却极为大胆,他收藏了数目可不雅观的经典书本仔细阅读,还希望与妻子谈论读书的心得,更是想辞去这份令人厌恶的事情。然而他的妻子依赖电视而对书本并不感兴趣(戳穿电视对人们阅读习气的威胁也是作者撰写这本书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终极,妻子告发了丈夫私藏禁书的行为,消防队准备用喷火器摧毁他的家。幸好蒙塔格逃到了乡间,与那些亡命的鸿儒会合,连续诵读经典。
当书本与知识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不仅是常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有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或许由于他们过着穷苦而又孤寂的生活,才对书本产生了超乎平凡的执着与痴迷,而书本也授予他们充足的生活以及活下去的勇气。
文学作品中的独行侠
意大利作家路易吉·马莱尔巴(1927—2008年)在短篇小说《蜘蛛人》中写道:“在独处的光阴中,我们的身上可能会迸发出独特的机制。没有孤独,爱因斯坦就不会提出相对论,莱奥帕尔迪也不会成为墨客。”小说的主人公在一家银行当出纳,业余韶光基本都待在家里。他本人最喜好看漫画,或者模拟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有一段韶光,他决定模拟电影里的蜘蛛人。一天晚上,他把尼龙绳系在暖气片上,从窗户跳出去,考试测验着像蜘蛛人那样翱翔。虽然他后来意外受伤,只得暂时放弃做大英雄的游戏,但有一天,一个男孩认出了他并称他为蜘蛛侠,这不啻对他这次冒险考试测验切实其实定和安慰。这是他对抗孤独的游戏,也是他浩瀚考试测验中的一个。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年)的小说集《马可瓦尔多》的主人公同样是孤单的。马可瓦尔多是意大利南方的农人,为了生活举家北迁到大城市都灵,成为一个大工厂的小搬运工。只管生活在大城市,但霓虹灯、广告牌和招贴画并不能吸引他的目光,相反,树上一片枯黄的叶子,瓦片上飘落的一片羽毛,树根泥土中钻出的蘑菇,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引发他对时令变迁、未来期许的思考。只管马可瓦尔多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但他充满天马行空般的抱负。为了给家人供应康健的食品,他会去河流的源头钓鱼;为了孩子们的康健,他会带着他们到山里去呼吸新鲜空气;为了家里有木材取暖和,他会到高速公路上砍伐广告牌……只管许多事情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但他驰骋在自己想象的王国,始终保持着乐不雅观的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神往,以此降服困境与寂寥,使本来非常沉重的生活变得轻盈了许多。这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第一章提倡的那种文学的轻盈,同样也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轻盈的态度。
制造鼓噪的人们
很多作家都曾说过:孤独是一种财富。在谈到自己的成名作《质数的孤独》时,意大利著名作家保罗·乔尔达诺(1983年—)就说过,孤独并非一件坏事,也并非总是悲观的。乔尔达诺每天将自己关在自家的地下室,只有完成当天的写作操持方能出来。孤独给予他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天下,一个完备属于他和他笔下人物的天下。一个内心天下丰富的人不会畏惧独处,由于纵然阔别外在的天下,他内在的乾坤也会自行鼓噪起来。
乔尔达诺是一位长于思考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也始终伴随着他和他对人类社会的领悟一同发展。他的第一部小说《质数的孤独》紧张描述男女主人公少年和青年时期孤单的人生,以及他们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情绪,第二部小说《人体》中的那些年轻的士兵则已经不再纠缠于青春年少的愁思,而是开始思考人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战役对人类的摧残。在第三部小说《黑与银》中,主人公已经发展为一名成熟男人,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的思考也日臻成熟,并且借助书中保姆的角色磋商生命与去世亡的命题。乔尔达诺每部作品中的主角也仿佛是些“独行侠”,永久不能被他人理解。然而,这些人物又始终在努力建立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这或许正是作家本人思想成熟的过程。与其说他们孤独,不如说他们始终用自己的眼睛核阅生活,用独立的思想阐发着社会。
墨客但丁被视为意大利文学之父,他后半生颠沛流离,始终无法返回故国。然而,他并没有在这种表面的孤寂中沉沦,而是创作出了一系列传世佳作。除了描述单恋情人贝雅特丽齐以及对她的情思的诗集《新生》以外,他的所有主要作品都是在流放期间完成的:《飨宴》《论俚语》《帝制论》,尤其是惊世宏著《神曲》。
在《神曲》中,但丁多次以预言的形式提及或者影射了自己的流放及其缘故原由,个中最主要的一处涌如今《天国》篇。但丁在那里碰着了曾曾祖父卡洽圭达。但丁首先讯问了自己家族的历史,以及昔日佛罗伦萨城的景象,接着向卡洽圭达问起自己未来的生活,特殊是在地狱和炼狱中曾多次以晦涩的办法预示的那次流放。卡洽圭达阐明了但丁被迫离开佛罗伦萨的详细情形,以及将被迫寻求各个领主的支持和保护的事实。他还说,但丁将与其他流亡者分道扬镳,而这样的做法是精确的,由于他们将在拉斯特拉战役中被击败,而但丁将逃往维罗纳避难,继而得到贵族家庭德拉斯卡拉和坎格兰德的收留。在这一点上,但丁产生了另一个疑问:如果他将被迫流放并不得不依赖这些贵族老爷的帮助,那么他是否还要冒着得罪他们的风险,讲出旅途中见到的统统呢?相反,如果他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又担心会破坏自己的荣誉,作品也无法流芳百世。卡洽圭达清楚地回答但丁:你必须讲出自己看到的现实,纵然这样做会让一些人不悦。在卡洽圭达看来,但丁的警告该当像一阵风那样吹到最高处,那将为他赢得名誉;此外,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将长诗所具有的教诲意义深深印刻在读者的脑海中。
纵然在地狱和炼狱中有精神导师维吉尔(代表着人类理智与哲学),在天国中有倾慕的情人贝雅特丽奇(代表神圣的恩典)作为引导,陪伴也仅仅是象征性的,但丁所进行的无疑是一次孤独的旅行。只管如此,但丁发挥非凡的想象力和超人的学识,创造出一个沸沸扬扬的天下,那些故事使但丁这次“孤独”的旅行充满力量与内涵。《神曲》本色上是中世纪人类所得到的所有知识的总和,是墨客毕生对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天文学等各种学科学习和思考的结晶。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年)是意大利著名的墨客、散文家、哲学家和措辞学家,也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紧张代表之一,近年来在意大利受人追捧的程度不亚于但丁。只管他生平中始终在承受家乡的闭塞、家庭的束缚以及身体的孱弱给他带来的痛楚,但莱奥帕尔迪创作出了浩瀚传世的诗歌、哲学和散文佳作,个中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田园诗《无限》、情诗《致西尔维亚》、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存问大利》以及表示他哲学思想的散文集《道德小品》和《杂文集》等等。莱奥帕尔迪的诗歌在浪漫主义中又加入了爱国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风格,而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生平中大部分光阴都在封闭和孤寂中度过有密切的关系。
莱奥帕尔迪出生在意大利非常传统和守旧的大区马切拉塔的没落贵族家庭。他在童年期间就开始学习拉丁语、神学、哲学和各种经典著作,继而开始创作诗歌作品和哲学论文,表现出惊人的天赋。14岁之后的7年中,他更是废寝忘食地独自阅读父亲的一万六千卷藏书。尤其是16岁到17岁中间有几个月,被他称为“不受打扰地学习,并对未来有明确的期望”。这种孤独而又猖獗的学习办法造就了后来博学而多产的墨客,但也严重危害了他的康健。1817年,在古典文学学者皮埃特罗·乔尔达诺(1774—1848)书信的影响下,他创作了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存问大利》。在诗中,他回顾意大利昔日的荣光,并将其称为“雍容华贵的夫人”,然后为她如今的样子容貌感到酸心,“几块乌青的肿块/多少很多多少流淌的鲜血/以及累累的伤痕……借使你的眼睛是两泓鲜活的泉水/哭泣也永久不能荡涤/你遭受的丢失与屈辱”。墨客诘问意大利沉沦腐化到如此地步的缘故原由,继而发出热切的呼喊:“啊,苍天,请让我/用我的鲜血在所故意大利人的胸膛/点燃熊熊的烈火。”写这首诗时,墨客年仅20岁。在不久之后掀起的意大利民族复兴和统一运动当中,他的这首诗勉励了无数意大利人,为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实现祖国的自由统一而斗争。
1819年,莱奥帕尔迪非常渴望摆脱家乡雷卡纳蒂镇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试图离家出走,但被父亲抓了回来,并从此被扼守起来,失落去了自由。极度的痛楚令他险些失落明。这一期间,他创作出了传世的诗篇《无限》——
这孤独的小山啊,
对我总是那么亲切,
而竹篱挡住我的视野,
使我不能望到更远的地平线。
我静坐眺望,仿佛置身于无限的空间,
周围是一片超乎尘世的岑寂,
以及无比深幽的安谧。
……
当我听到树木间风声飒飒,
我就拿这声音同无限的寂静比较,
……
就这样,我的思想
沉浸在无限的空间里,
在这个大海中遭灭顶之灾,
我也感到十分甜蜜。
故乡的风光是如此安谧和令他留恋,同时也是挡住他目光的竹篱。正是这种极度的孤寂与痛楚,这种地理和文化层面的狭隘以及人为的枷锁,引发出他的遐想,从而达到一种超然于世的升华,融入无限的自然和宇宙空间,使诗歌与哲思十全十美。
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们,用他们非凡的才能与“孤独”的耕耘,为我们创造出无数经典作品,使我们能够在独处的时候并不寂寞,而是能够乘着他们为我们打造的翅膀,在作品中层峦叠翠的山岭和鼓噪的人间上空飞越。
(作者:魏怡,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措辞学院副教授,罗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