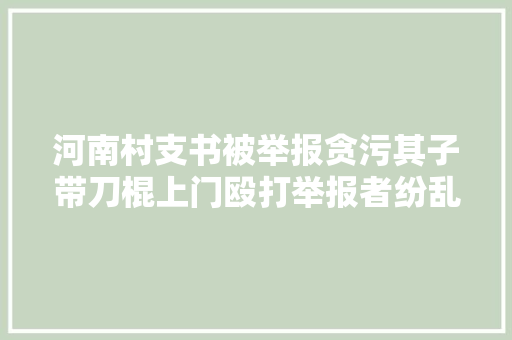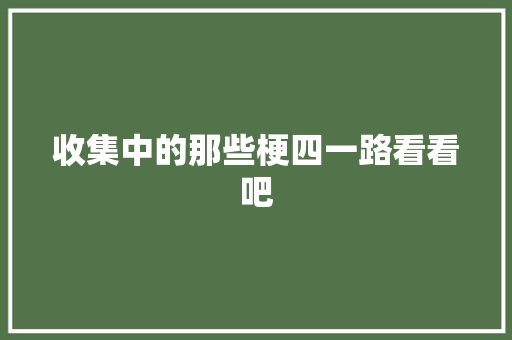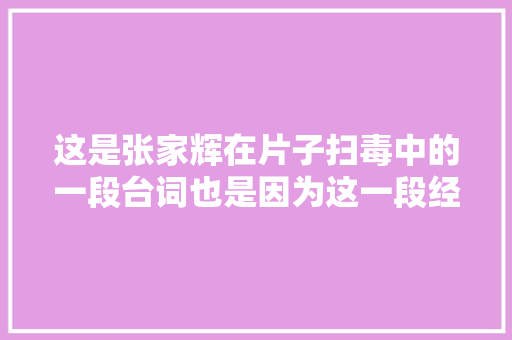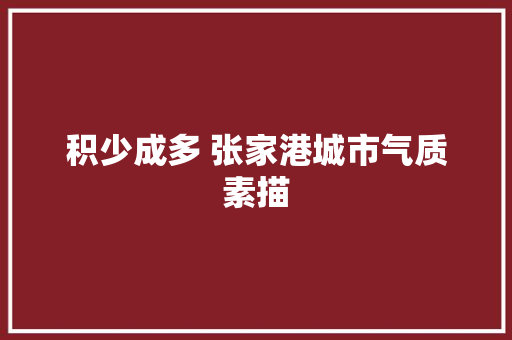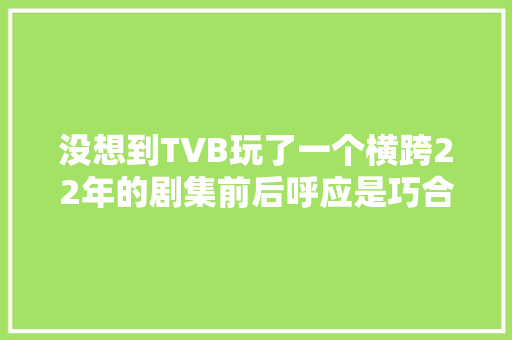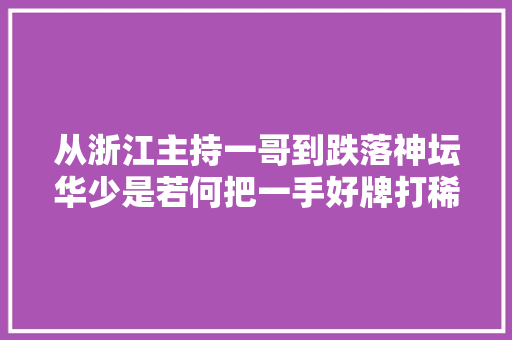赵薇演唱《六尺巷》
““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猴年春晚赵薇演唱的一曲《六尺巷》,让安徽桐城六尺巷背后的张家故事再度进入公众年夜众视野。

《大清首辅张廷玉》
提及六尺巷事宜,就不得不提到张英当年建筑的五亩园,人怕出名猪怕壮,而今的五亩园已经被十里八乡的人称作宰相府。五亩园当初仿照北京四合院建筑的,西、南两面都是城墙,靠北是吴家的老宅,靠东是阳和里巷。张英为官清廉,建宅院自然要考虑节省银子,其余他喜好田园乐趣,以是园子的外墙,除了正门靠阳和里巷的东边,筑了一道砖墙,其他三面都是用竹篱笆。考虑到周边过往行人的方便,竹篱墙与城墙都隔开了三尺,北面也与吴家老宅隔开了三尺。如此一来,从西城门出入的路人,就可以抄近路,路子宰相府与吴家老宅的夹巷,来到阳和里巷。宰相府位于桐城县城西南角,张英当初买下这块宅基地,便是以城墙墙角、阳和里巷以及阳和吴家老宅为四界的。照此说来,宰相府的三面竹篱墙外各三尺小路,也是张家的宅基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周边的人沿着张家的竹篱笆走惯了,久而久之,谁也没想到每天走过的小路,竟是张家的宅基地。
张家是桐城官宦王谢,张英离开桐城老家,曾立了家训:“门无杂宾,择友而交。”张家人服膺老爷的告诫,一贯深居简出,与外界闲杂人等并无打仗,与邻居吴家也是隔墙隔院,除了偶尔照面,险些没有什么交往。俗话说人不怕鬼,就怕三更半夜鬼拍门。张家人由于门第显赫,恐怕在地方惹出是非,以是行事低调,待人谦和。可是不成想还是牵出一桩扯犊子的麻烦事来。
起因是吴家的老宅扩建,引起吴家和张家的地界轇轕。吴家老宅是吴家各房都有份的祖业,如今长房长孙要娶媳妇,须要扩建一进房,于是拆了自家的南院墙,准备建新宅。吴家没有知会张家,竟然将自己新宅的地基挖到张家的竹篱处。
竹篱墙的三尺之地原来便是老张家的,吴家拆墙建屋,不仅越界占了张家的地基,还堵住了过路行人的通道。张府确当家人,也便是张英的哥哥张克俨,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当即带上几个仆人,来到吴家理论。谁知吴家却说巷道原来便是老宅基地,倘若张家人不信,可以挖出地下的界石来证明。
张克俨一见吴家人说得铮铮有词,难道是卖给张家地基的人骗了老张家,他半信半疑地走到刚刚开挖的地基,只见那儿横放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吴界”两个正楷大字。张克俨纳闷地说道:“我们张家有地契为证,这张地契可是我家相国老爷经手的。地契上清楚写道:北以吴氏院墙为界。”
“俗话说商不跟官斗,可是官家总得讲理!
你还是找卖地给你的上家问个究竟?我父辈先前说过宅基地埋有界碑,当时建院墙就留有三尺滴水。没想到这次扩建老宅,真的挖出了界碑,好在父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真说不过你!
你们老张家被上家给蒙骗了?”吴老太爷回嘴张克俨说。
你道张家宅基地的上家是谁?这原来是块无主的闲置空地,是张英当年从县衙买下的,并立了字据。难道县衙立的字据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张克俨越想越来气,于是一纸诉状将吴家告到了县衙。桐城钱县令一见原告竟是宰相府的人,哪敢怠慢,当即升堂,差人传张、吴两家主事人前来问话。谁知两家各自为政,张家有地契作为凭据,吴家有界碑作为证物。
钱县令可是通过科举正途走立时任的,吴家这点小伎俩,他难道还看不出来,当即斥责吴家人说:“你们吴老太爷只是听说父辈埋有界碑,没有确切证据,怎么就敢在张家的地皮上开挖地基,探求界碑呢?”
这次出庭的是吴家长房吴老爷,捐了功名的红顶贩子,他在桐城地面上,也算是个有头脸的人物。吴老爷随即阐明说:“家父亲耳听父辈提及地基埋有界碑,此事怎能有假?没有确切证据,我们开挖地基,做法诚然不对,可是我们拆墙建房,是在开挖基地,证明界碑之后的事啊,请大人明鉴!
我们也不想将此事闹大,可是张家把我们告到县衙,我们吴家虽不像张家有朝中宰相撑腰,可也是桐城地方上有头脸的乡绅,万事总得讲理,钱大人乃是地方父母官,定会秉公断案,还小民明净!
”
钱县令怎不知吴老爷这一番说辞的用意,倘若他判吴家败诉,吴老爷就会在桐城分布钱县令官官相护,欺凌百姓。可是张府有地契在手,又怎能说人家诬告呢?为了摸清详细情形,钱县令传唤为吴家拆墙挖地基的工匠,工匠们也不清楚界碑之事。原来第一个创造界碑的人是吴家的管家吴全。吴全卖力吴家拆墙建房之事,除了卖力吴家日常生活琐事,还可以为吴老太爷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据吴全交代,他确实奉了吴老太爷的指使,为了防止张家阻扰,半夜三更时分,他孤身一人在张家竹篱墙处探查,终于挖到埋在地基下面的界碑。当时在场的眼见者,只有吴全和吴老太爷和吴家长房吴老爷三人,二吴都是被告,吴全是唯一的证人。鉴于吴全的证词可信度低,钱县令只好宣辞职堂,此案暂时搁置,待日后再审。吴家老宅的扩建也只能歇工,要等县衙结案后,方可复工。吴家是这场官司的被告,此案悬而未决,恰好给他们落下口实。不到两三天韶光,桐城大街小巷便风传宰相府的人仗势欺人,不准吴家挨墙建屋。钱县令竟然恃强凌弱,将案子搁置不理,县衙如此官官相护,老百姓今后怎么过日子!
钱县令闻之,也如坐针毡。张、吴两家都有凭据,这官司实难裁断。无奈之下,钱县令只好深夜拜访相府,要求张家主事老爷张克俨高抬贵手,接管调度。钱县令对张克俨说:“眼下你们两家的官司在桐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案子搁置日子长了,我丢官事小,只怕影响老相爷的荣誉,吴家干事手脚麻利,那界碑疑点甚多,便是苦于没有反证,无法判他败诉。”
看到钱县令心急如焚的样子,张克俨也于心不忍,于是问钱县令说:“钱大人打算如何调度张、吴两家轇轕?”
“此案你们两家都有实证,错在县衙断案无能。请张老爷把地契变动一下,把墙外那三尺宅基地划归吴家所有,县衙按地价如数赔偿丢失。”钱县令也是茶壶倒饺子,有苦说不出来。他只得硬着头皮把上任县令留下的烂事给抹平了。
张克俨回忆上任县令当年坐地起价,硬是高价卖给张家这块土地,心里十分烦懑,他朝气地说道:“难道老张家就缺这几两现银吗?钱大人如此纵容吴家胡作非为,必将导致今后民风大坏,即便钱大人放任不管,我们老张家也不会受这个窝囊气!
”
“那依师长西席之见,我该如何断案?”钱县令笑着向张克俨讨饶。
“审案是衙门的活,我弟张英虽贵为当朝相国,但是张家在大人治下便是百姓。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我无需大人格外照顾,只要大人公道办事就行了。”
“张老爷此话倒是点醒了我,既然地契确当事人是老相国。咱们就该当写信征询他老人家,看老相国如何处置这桩轇轕?”钱大人如释重负,趁机把此案当作皮球,踢给了张家。
“钱大人请放心,老夫已经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写成书信,寄往京城了。我受相国之托,管理张家家当,岂能不明不白就把家产弄丢了?”
“如此甚好!
”钱县令一听张克俨如此说道,内心甭提多高兴。只要拿到老相国的手谕,这案子就好办了。你吴家在桐城再蛮横,有本事就到京城向皇上告状去吧。
没过几天,张英便收到张克俨寄来的家书。信中详说了张家与吴家的宅基地之争,还说了钱县令无法断案的缘由,末了,便是恳请老爷处置此事。
张英看过家书,立地唉声叹气地说:“大哥真是糊涂!
你怎能去打官司呢?如今我官居一品,廷瓒、廷玉都是朝廷京官,这样的家门,朝中同寅见了,怎不妒忌恨!
如今这官司一打,你再有理,人家也会说你仗势欺人!
”
张英倒不担心桐城吴家能生出多大的幺蛾子,紧张是康熙年间,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不管情形是否属实,只要听到传闻或非议,御史就可以藉此参劾朝廷命官。参劾之后,方才查证,这便是所谓的言者无罪。当时的朝廷命官只要被御史参劾,就会大触霉头,即便查无实据,没有被革职罢官,可是名誉受损,长期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上班,这种事搁谁身上,谁都感到窝心。曾经由于管理河道有功的顺天巡抚李光地,即便被康熙爷付与“能吏”的光荣称号,可还是逃不脱被御史参劾的命运。
张廷玉看到父亲眉头紧锁,于是劝解父亲张英说:“父亲也不必太担心,这分明是吴家耍地痞,咱们就认不利,接管县衙调度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话虽如此,桐城钱县令也是个厉害角色,他把烫手山芋甩给我,让我复书,他好藉此结案。我总得明确回答家里人,免得又生乱子。”说罢,张英在信尾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廷玉一见,纳闷地问道:“父亲这样就算回答了吗?”
“弗成啊,我还得另写一封书信与你大伯,免得日后又生事端。干脆把竹篱墙都拆了,全部砌成砖墙。”
钱县令切切没想到,一场险些让他丢官的诉讼案,竟然被张英的一纸书信给化解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张克俨按照张英的意思,把竹篱笆拆了,在原址砌了砖墙,如此一来,张府靠西南边就与城墙留出了一条三尺小巷,可供路人通畅。只是靠北一壁,吴家就要紧挨张府墙外建新宅,这条通道一旦没了,那么从西城门出入的路人,只能绕道来到阳和里巷。
吴家得知张家主动撤诉,并且拆了竹篱,砌起砖墙,主动让出三尺地基。吴老爷起初还以为张家得了县衙很多好处。后来仔细打听,才知道老相国肚里撑船,主动撤诉,并让出三尺土地。吴老太爷得知事情原形,钦佩老相国的高风亮节,想那吴家也是桐城王谢,不会为了三尺土地,堵了巷道,做全城百姓谩骂的恶人。
吴老太爷把各房儿孙叫到跟前,决定退出已占的三尺地基,同时还让出自家的三尺地基。吴家长房老爷遵照父亲的意思,悄悄让出自家三尺地基,也效仿张家砌了一堵青砖院墙。从此六尺巷的故事,还有张英的那首诗,便在桐城的大街小巷和酒肆茶楼流传开来。
令张英吃惊的是皇上竟然比他先知道此事的处理结果,这些年国泰民安,康熙也年近五旬,性子比先前温和了很多,没事的时候,常常与身边的老臣唠唠嗑,大概皇子的夺嫡之争,让康熙寒了心,那些寄托皇子朋党为奸的臣子更让康熙讨厌至极,眼下让皇上感到放心的,只有这些每天侍候在他身边的天子党了。某天,皇上听讲之后,正与众学士闲聊,溘然笑着对众臣说:“朕昨日听说了一件奇事,竟然是发生在当朝,朝中有一个大学士,家乡的宅基地被人侵略,家人寄来书信乞助,没想到那大学士肚里撑船,批诗相让与人,不仅平息了一场诉讼,此事还成为坊间嘉话。这位以身教养百姓的大学士,诸位爱卿可曾知晓?”
康熙话音刚落,群臣听了,却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张英刚刚处理一桩类似的诉讼,但他还未曾知道六尺巷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不敢妄加揣测,况且此事刚刚发生,断不可能传到皇上耳朵里。
正在群臣云里雾里的时候,只见皇上呵呵笑道:“那批诗写得绝妙,我念给诸位听听,‘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康熙话音刚落,众臣还在仔细品诗,却见张英惶恐地跪在地上,向皇上叩头说:“微臣该死!
因是家中小事,以是没有奏报皇上。请皇上恕罪!
”
“张爱卿莫慌!
”康熙起身,将张英扶起,转身对众臣说:“朕虽年过五旬,也不至于闭目塞听。”说罢,他拿出一封信函,交与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传阅,张英是末了一个看到的,只见信中将六尺巷事宜的前因后果逐一详述。只是信尾的署名被皇上用朱笔涂抹。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封直呈天子的密奏。张英看罢,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倘若自己对此案处理不慎,这封密函将会如何说道。张英也知道康熙为何调集天子党,把这封密函公示于诸臣,实在也是为了爱惜自己的羽毛,康熙的用意便是劝诫天子党不要在夺嫡之争上瞎参合。由于朝政稍有风吹草动,他老人家就能及时察觉。
张英放工回到府邸,桐城的家书才刚收到。张英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只见儿子张廷璐在信中详述张家接到批诗后,如何奉命让地息讼,吴家又是如何效仿张家让地,并详述六尺巷事宜在桐城是如何成了嘉话,还说了钱县令为六尺巷亲自竖匾题联,藉此教养桐城百姓。
张英看收手札,立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书信的题名日期,是在竖匾确当天寄出的,可还是比皇上收到的密函慢了两三天。作为天子近臣,他自然知道密折专奏之事。张英当年告假葬父还乡期间,也给皇上呈过密折,但他写的都是路子州县的民情吏治,可张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家人的日常生活,皇上都派出眼线监视。可见夺嫡之争已经危及皇权了。倘若自己真有仗势欺人之举,皇上怎能不知?好在自己为官谨慎,家人也知礼遵法,才不至于涌现疏忽。想想自己已经六十五岁了,张英决定奏请皇上,哀求告老返乡,以避“贪位”之嫌。
摘自广东公民出版社重点图书《大清首辅张廷玉》
王岐山低调拜访安徽桐城张家故里,倡导做官先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