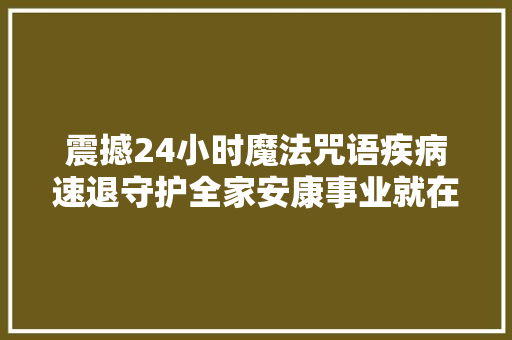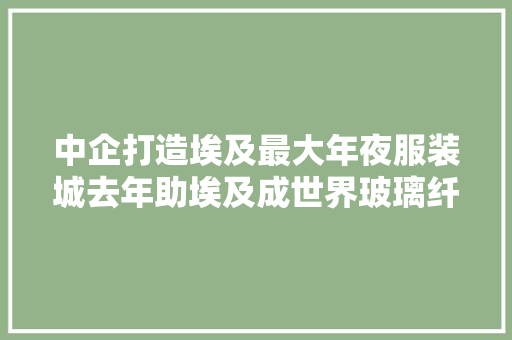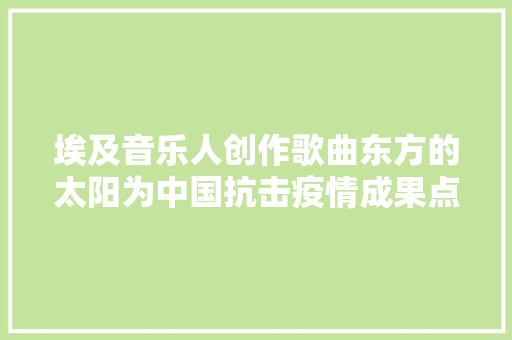文/小楚
序言
法老时期的古埃及爱情咒语现存只有一例,而在罗马期间的 “希腊邪术纸草”中却创造有大量同类咒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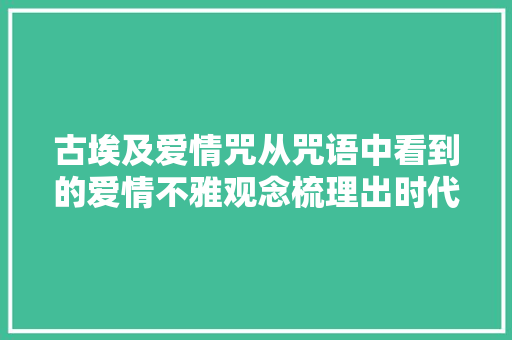
创造于埃及境内的希腊邪术 纸草,个中的咒语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着古埃及的影子,乃至法老时期爱 情咒语的孤例也可以在个中找到“嫡系后裔”。
在文本内容剖析的根本上, 以咒语中唤起的神祇、措辞中利用的动物类比手腕与为确保效果而对神祇 进行的威胁三点为线索,可以找出邪术纸草中与法老时期爱情咒语关系最为紧密的例子,继而梳理出古埃及爱情咒语在法老时期之后的变革。
可以看到,古埃及爱情咒语在后期明显受到了希腊方面的影响。
爱情咒语植根 于古埃及多样的邪术文化,历史悠久,法老时期资料的稀缺或容许以归因于咒语的日常性。
古埃及法老时期爱情咒语的资料十分罕见,早在 1941 年学者保罗 · 史密瑟(1913— 1943)在为他所翻译的一条科普特语爱情咒语探求古埃及时期的先例时便把稳到了这点— 由于仅有创造于麦地那、年代为第 20 王朝(约 公元前 1189—公元前 1077)的一例存在,即陶片 ODeM 1057 。
1978 年埃及 学家乔里斯 ·F. 伯格豪斯(1939—2018 年)在编译《古埃及邪术文本》时 收录了这条写于陶片之上的僧侣体咒语,并形容其为“罕见的”。
有关爱 情咒语最多的资料来自“希腊邪术纸草”。
“希腊邪术纸草”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献名称, 只是为当代学者所用以统称一系列记录咒语、仪式、赞颂诗等“邪术”内容的纸草。
这些纸草的出地皮点虽不尽相同但都在埃及境内,韶光跨度为公元 1 至 4 世 纪。
就内容而言,爱情咒语霸占不小的比重。
据学者统计,以《古埃及邪术文本》中的咒语类型构成比例为参照,“希腊邪术纸草”中爱情咒语的比重。至少是前者中的 20 倍。
鉴于法老时期资料的稀少,对“希腊邪术纸
草”的 解读本应成为研究古埃及爱情咒语的关键。然而关于文本性质的辩论却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先论证“邪术纸草”中的爱情咒语是否属于古埃及(文化)。
希腊邪术纸草”中的文献大部分由希腊语写成,但是鉴于希腊语是当时的通用语且文献中存在埃及世俗体以及古科普特语的文本,措辞本身并不能成为判断文本来源的唯一依据。
从措辞比重的角度而言, 有不雅观点方向于埃及语文本译自希腊语,然而文本内容反响出的宗教/文化背 景却显示出古埃及的特点。
“纵然有情由相信世俗体的文本是希腊语的翻 译,但是至少与邪术干系的原材料可能是埃及的。”
同时,从双语运用的熟 练程度来看,邪术纸草的缮写者受到过埃及传统的(祭司)书吏演习,而纸 草的利用者也同时节制两种措辞。
在罗马期间的埃及, 这样的人更可能是 (文化上的)“埃及人”而非“希腊人”。
然而,措辞之外,邪术纸草中明显的希腊元素亦是不能忽略的。
“希腊邪术纸草”的多文化特色无疑是古代晚 期地中海天下文化互换领悟的表示。
但是有关邪术纸草中文本的文化源头的辩论一贯存在争议。
从零散的干系研究中可知,整体而言, 撤除前文提到的法老时期资料罕有的特色之外,在内容上,古埃及爱情咒语 的一大特点是措辞中动物类比的利用。
在对单条爱情咒语的内容进行剖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把握作为整体的爱情咒语。
然而由于数量的悬殊,这种概括只能环绕邪术纸草即罗马期间的爱 情咒语展开。
① 在邪术纸草中, 爱情咒语在类型上与其他咒语无异, 紧张有 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史诗套话型(epic formulae)。
② 史诗套话型咒语多以 神话故事为背景,将咒语的浸染工具代着迷话中的角色。
这种咒语古已有之, 如法老时期的一些治疗蝎毒的咒语会讲述伊西 斯治愈为蝎子所伤的小荷鲁斯的故事,并将伤者代入小荷鲁斯的角色,以求 得到同样的治愈效果,较为范例的例子便是梅特涅希石碑 上的咒语。
③在希腊邪术纸草中也有同一类型的治愈魔咒,如一则治疗发热的 咒语在描述了荷鲁斯正为高热所折磨之后写道 :
爱情咒语中的看似属于这一类型,咒语以讲述伊西斯向其父图特哭诉自己为奥塞里斯与奈 芙缇丝所背叛为始 :
伊西斯 回答道 :
但是这并不是一则以挽 回(丈夫)情绪为目的的咒语,也没有任何施术工具被带着迷祇的角色。
在 接下来的咒语中,图特彷佛让伊西斯取回了某种神秘的炎火(容器),而男性施术者想要利用的正是这种炙热带来的痛楚,以此折磨女性施术工具直到她来到施术者的寓所并与之交合。
史诗套话型的爱情咒语极少,大部分爱情咒语属于第二种咒语类型,即包含仪式道具的制作、利用方法以及咒文等内容的操作指南。
咒文中常会提 及神名,但是没有角色代入,对付神话故事的背景也不做描述。
如一则杯子妙咒 :对着一个杯子重复以下内容七次,恳 请 您, 西普利斯(Cypris,阿芙洛狄特的别名,即“塞浦路斯之女”)之圣名,如 果您潜入了某某、即某某之女的内心深处,引发她的爱。’
碰触吸引咒 :取一只圣甲虫,在上好的药膏中熬煮,取出甲虫将 其与野豌豆(vetch) 一同碾碎,然后放入玻璃杯中,重复以下咒语两次 ,迫使她, 某某、即某某之女追随我, 如果我碰了她。’”
此类咒语的篇幅长短不一,视 道具制作、咒文等内容的繁芜程度而定。
但是同样,爱罗斯也被当作一样平常神明为请愿者所召唤。
回到作为爱神的哈托尔。她与爱情咒语最为直接的一次联系涌如今一则公元 3 世纪的世俗体爱情咒语中。
在形式上,这则咒语采取的是法老时期就已涌现的格式,在大篇幅的 咒文之后写有道具的制作与利用解释 :
在内容上, 从咒语中涉及的神灵(哈托尔) 以及动物类比的 运用这两点考虑, 这则爱情咒语是邪术纸草中与第 20 王朝孤例最为相似的, 可被视作法老时期古埃及爱情咒语在罗马期间的表示。
然而二者间也存在决定性不同。
第20 王朝的文本对付咒语失落效的威胁是
对付神明的恫吓在法老时期的 埃及邪术中十分常见,如一则关于吓退仇敌的咒语也“威胁”了奥塞里斯 :
此外还有威胁 宇宙秩序混乱的例子,如一条针对水中鳄鱼的咒语写道 :
与第 20 王朝爱情咒语出处(麦地那)相同的蝎毒咒 语则很好地展现了以上两种威胁的结合:
但是 世俗体咒语中更多表示的是对付施术目标的“折磨”。
这一点也表示在了同一纸草 上的另一则世俗体爱情咒语之中。
如一则涉及点火没药的爱情咒语写道 :
这种虐待性最为直不雅观地表示在了一具 罗马期间的埃及泥偶 身上。
泥偶为女性,呈跪姿,双 手被束于身后,身上统共插有 13 个钉子, 整体形象与中描述的 爱情人偶同等 。
对付施术工具的“折磨”是第 20 王朝爱情咒语中所没有的,而这一点在以勾引
咒为代表的古希腊爱情邪术中却表现得较为普遍。
从公元 3 世纪的 世俗体爱情咒语中可以看到第 20 王朝爱情咒语的影子,但是咒语本身却由于 包含对施术工具的折磨而具有光鲜的希腊文化特点。
法老时期的古埃及爱情 咒语发展至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古埃及爱情咒语的特点 在科普特邪术文献中依然清晰可见,传统的动物类比、对宇宙秩序颠倒的威 胁等元素光鲜地展现出了古埃及邪术传统。
而一则公元 11 世纪的咒语则将埃及与希腊的传统糅合—在折磨施术工具的同时还威胁了请愿工具 :
经由了两千余年,科普特爱情咒语依然保留有古埃及咒语的痕迹,可以 被视为法老时期古埃及爱情咒语的延续。
从爱情咒语中可以窥见古埃及文化的许多方面,而对付爱情咒语的考 察也不能局限于此类咒语本身。
与其他类型的咒语进行比较,剖析爱情咒语 产生的背景, 更有助于理解爱情咒语的内涵与实质。
首先,“爱情咒语/魔 法”这一分类是当代学者提出的观点。
“希腊邪术纸草”中许多被当代学者 译为“爱情吸引咒”(love spell of attraction)的咒语的希腊语原标题实在是 “agōgē”即“勾引”,指将施术工具“引至”施术者处,而这一术语的利用并 不局限于爱情咒语。
或者说爱情咒语这一分类只有在关注咒语内容与目的 的时候才故意义。
许多咒语是多功能的, 如一则世俗体咒语既可以用于将女人带给男人,也可以用于托梦 。
腊语咒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咒语的事理是相通的, 但是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
托梦、隐形与爱欲涉及的领域相去甚远, 然而也存在在目的上与爱情咒语十分靠近的类型 — 魅力咒(charitesion ), 即以得到受益性喜好(favor)为目的的咒语。
这种喜好常日与社会性认可干系,比如“给予我偏爱,口才,对世间男女的吸引力”,带着它(注:护身符),你将成为众人的宠儿,收 获友情,人见人爱”。
但是在很多情形下,这种社会性偏爱与私人爱慕间的 界线并不清晰。
如一则咒语写道 :
根据高下文, 前文中的某某之子或许是地位高于祈愿者的某人(如上司或国王),这是魅力咒中比较经典的祈求工具。
而下文中的女性某某则可能代表祈愿者的爱恋工具,由此可见魅力咒与爱情咒语的领悟。
希腊语文献中也有类似例子 :
根据奎克的不雅观点,“希腊邪术纸草”中魅 力咒的原型早在古埃及古王国期间就已经涌现,与仪式干系,而魅力咒(尤其 在希腊罗马期间)也被运用于爱情邪术,其自身的历史表示了一种“仪式—魔 法”的变迁。
爱情咒语的终极目的每每便是性结合, 而若将爱情咒语视作古埃 及情色文化的一部分,那么爱情咒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埃及中王国期间。
溯源古埃及爱情咒语的同时,现立案例的背景剖析也不容忽略。
第 20 王 朝的陶片出土于麦地那,而麦地那工匠村落是研究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资 料来源, 其所展现的古埃及人生活细节是其他遗迹无法比较的。
情绪生活 无疑也是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故爱情咒语创造于此并不令人感到 意外。虽然爱情咒语仅有一例存在,但是仍有其他可能与爱情邪术干系的创造。
比如一具女性小雕像的背面装有人类指甲碎片、头发、皮肤或布料的残留物,可能用于巫术活动,或与爱情邪术干系。
根据“希腊邪术纸草”中的 记载,将施术工具身体的一部分(如头发)用作邪术仪式中的主要素材确实 见于爱情邪术。
与爱情咒语可能干系的还有情诗/歌— “传统的邪术咒语 也潜藏在一些早期诗歌文本的形式之后”。
已知的古埃及情歌全部创造于麦 地那,在韶光上属于拉美西斯时期,与爱情咒语相同。
情歌与爱情咒语在措辞 构造上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介词 m-sA,即“随着”一词的利用),情歌的部分 内容乃至可以直接作为咒语利用(虽然是作为开门咒),乃至在情歌中“爱情” 自身便是一种保护咒,充满魔力。
邪术文本可以是情歌的灵感来源之一。
在麦地那出土的文献/文物中,爱情咒语并不是唯一孤例的存在。
此外 作为孤例的还有绘有男女交合画面的“都灵情色纸草”(PTurin 55001)。
罕见 的情爱类资料均创造于麦地那并非巧合,这些在利用目的上极具日常性的文 本并不会涌如今墓葬或是神庙等“高等”举动步伐之中,就保存下来的遗址遗迹而 言,相对付数量浩瀚的“高等”举动步伐,能够保留并展现古埃及人日常生活内容 的险些只有麦地那工匠村落,这也阐明了为什么法老时期爱情咒语的案例如此之 少。
罗马期间爱情咒语案例的丰富源于“希腊邪术纸草”的创造。
而记录大量 日常咒语的邪术纸草的涌现,却与当时埃及本土的“精英”祭司阶层的推动 有关。虽然就目的而言, 相对付繁芜的神庙仪式,爱情咒语可以归属于日 常邪术,但是它的内容来源并不是民间。
“希腊邪术纸草”中的 爱情咒语原来属于神庙仪式文本 :“埃及有名于罗马期间的、记录于大量‘魔 法’纸草的民间巫术,仅仅是官方神职职员所节制的传统仪式知识。
”在罗 马期间, 随着传统神庙体系的崩坏,埃及祭司们不得不钻营新的出路。
“一些 人将做事场所由衰退的神庙转向城镇或村落庄 ;其他人将他们的仪式演习与祭司 关系带至神庙辖区以外,成为流动的仪式专家、‘邪术师’,成为古代晚期埃及 流浪墨客、‘演出者 ’及知识分子网络的一部分,对付特定的神庙或地方仅有边 缘性的或不必要的身份认同”。
罗马期间的爱 情咒语来源于古埃及神庙中的仪式文本,其大量涌现是当时神庙体系衰落、神 职职员飘泊所引发的知识大面积分布导致的。
神庙的生命之屋中藏有的“神 秘知识”经复制、改编之后,以手册、合集的形式被出走神庙的祭司们携带至 民间,就像当时的埃及祭司一样,这些知识也不再限于神庙之内,并且更加与 祭司个人干系。
一位罗马期间埃及祭司的“知识手册”或由于陪葬墓中而被保 存了下来,并在千年之后为阿纳斯塔斯所获。
这样的“手册”成为后众人眼中的“邪术纸草”并保留了有关古埃及爱情咒语的最多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