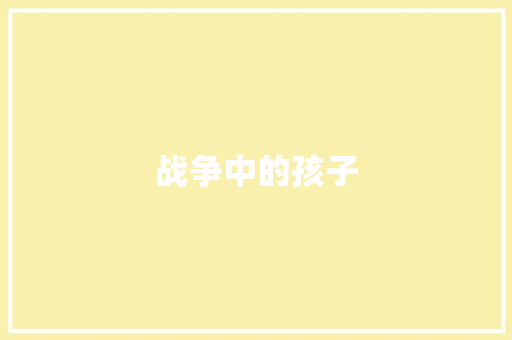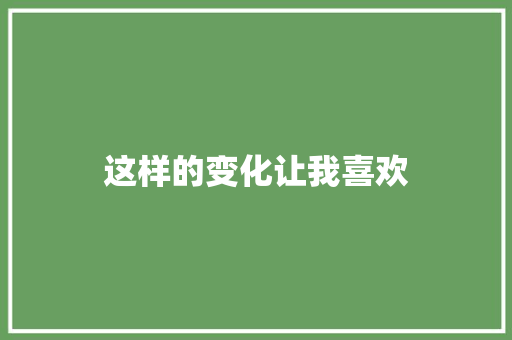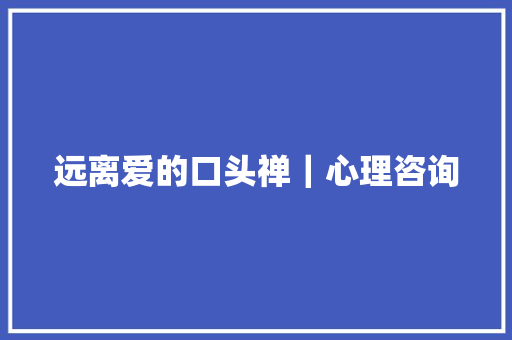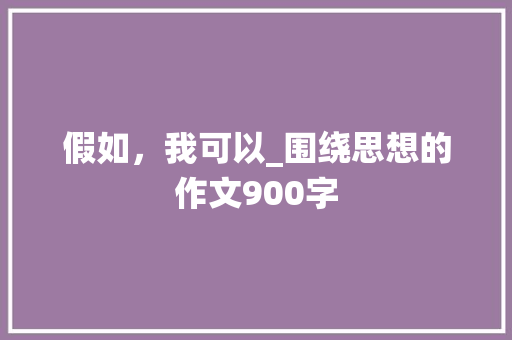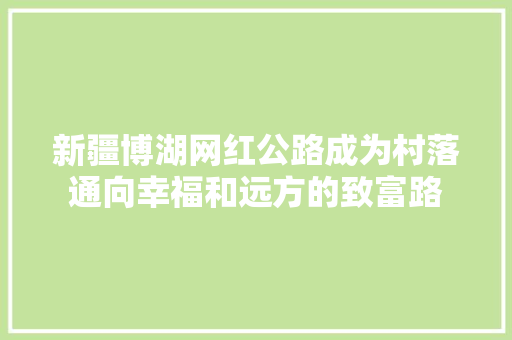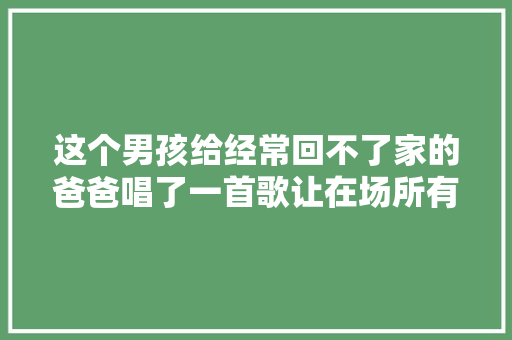红地皮上的绿帐篷在顽强“抵抗”,积蓄的雨水把它顶部压出一个个“小球”。帐篷里,搭在树杈上的毛竹是孩子练习芭蕾舞的把杆,他们一只脚搭在毛竹上,另一只着地的脚早已湿透。
关於放了一曲《天鹅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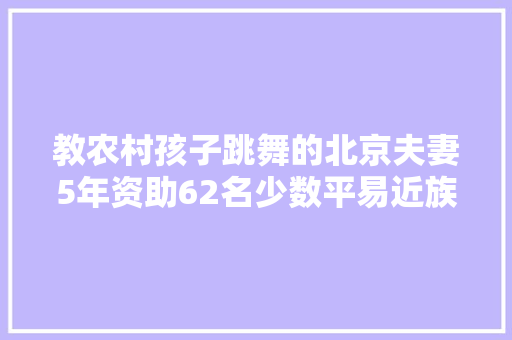
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西席,体形清瘦,有一双爱笑的大眼睛,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伴着雨声,关於的双手逐步打开、脚尖踮起、下巴微抬,嘴里数着拍子:“12345678……”
妻子张萍在一旁抠舞蹈细节,轻拍孩子的肩膀,提醒他们体态要放松。她盘着跳芭蕾的“丸子头”,刘海被梳到脑后,干净利索。
“孩子们扶着把杆向后踢腿时,泥都溅到我的脸上。”回顾起当时的场景,关於兴致勃勃。
自2016年起,关於夫妇来到云南省砚山县者腊乡那夺村落履行“彩云操持”,教偏远屯子的孩子跳芭蕾舞。张萍更是辞去事情,扎根那夺村落。五年间,他们帮助了62名少数民族孩子到昆明的艺术院校学习。
孩子们会叫关於夫妇“阿爸”“阿美”,那是彝语里对“爸爸妈妈”最亲密的称呼。
张萍帮练舞的孩子绑头发。新京报 吴采倩 摄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五一”长假前夕,朱仝开车穿过红土高原上的辣椒地,来到盘龙乡翁达村落小学。
他是张萍的二舅,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奔波于各个村落庄,把学习舞蹈的孩子们接到砚山县的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孩子们喊他“阿公”。这几天,他要接小茹和别的二十多个孩子到学校进行5天的集训。
如果不去舞蹈,这个13岁的屯子女孩放学后要干很多农活,去山上摘辣椒、打窝窝(锄地)、放牛,嘴边还留着一道被牛顶破的伤疤。“她没有父母,随着姑姑生活,我们都把她当自己的孩子。”
5月1日的早上8点半,课程开始。
张萍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欢迎孩子们。看到没有扎好头发的女孩,她上前帮着梳头,发尾一卷,发套一套,再拿U型夹固定,丸子头就绑好了。“练舞的女孩要把头发梳好,要干干净净的”。
张萍拿绳子帮孩子排练弦子舞。新京报 吴采倩 摄
本日要学习的是弦子舞,这是张萍编排的彝族舞蹈《幸福弦子跳起来》。她自幼喜好舞蹈,曾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编导,随后与关於相识相爱,成为了一名自由舞蹈编导。
教室里的孩子们身穿蓝衣黑裤,手里拿着圆肚龙头的木制弦子,龙头挂着几串彩色绒球,随着节奏被晃得哗哗直响。
“停!
还是不齐”,张萍皱起了眉头。
排练的效果彷佛差强人意。张萍溘然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一根粉色的塑料绳回来。她让孩子们排成一排,再跟另一位老师把绳子拉直,横在孩子跟前。音乐响起,她跟孩子们一起迈动脚步,嘴里还喊着节拍:“1、2、3、4、抬,跺!
”她们的舞步逐渐变得整洁有序。
好不容易到了晚饭韶光,孩子们拖着酸痛的腿,一步一步轻轻地跳下楼梯。
学校的炊事由张萍的家人掌勺,孩子们坐在一楼的食堂,饭前先背诵“彩云训诫”:“戴德天地滋养万物,戴德国家培养护佑,戴德亲人养育之恩……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人。”
“希望他们懂得戴德,这些食宿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张萍坦言。等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张萍才开始用饭,会有孩子在一旁等她,“老师等您吃完,我帮您洗碗,由于你是我最喜好的老师。”
感想熏染到孩子们的诚挚,张萍很愉快,“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那夺村落。新京报 吴采倩 摄
“屯子孩子学舞蹈有什么用?”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张萍会和远在北京的关於视频谈天,有时候一聊便是三四个小时。
夫妻俩如今分工明确,张萍扎根砚山县卖力日常传授教化,关於在北京远程关注和辅导,他会联系北京的老师给孩子们更多专业的培训,有时候还会对接一些北京的演出和学习。直到每年的寒暑假,夫妻二人才会在砚山“合体”传授教化。
为什么要教屯子的孩子舞蹈?
这要从关於夫妇的发展路径提及。关於是北京人,但他年幼时随母亲下放到屯子,童年的回顾里满是蚂蚱、野外和山村落。田埂上的那抹夕阳,是贰心中最美的画面。而妻子张萍出生于云南省砚山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屯子姑娘,由于学习舞蹈飞出了大山。
他们曾在河北发起“田埂上的芭蕾”公益项目,周末驱车270公里,到村落庄里教孩子们跳芭蕾舞。
2016年夏天,张萍看到朋友发的照片,那是几个穿着彝族衣饰的孩子,他们赤脚站在一壁土墙下,头发缭乱,眼睛又大又亮。“他们的脚常年不穿鞋踩在牛屎和泥巴里,然后一层屎一层泥,裹出一个硬壳。”
张萍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问朋友这些孩子在哪儿,朋友见告她在“那夺村落”。
那夺村落,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这里曾是国家级穷苦县下属的穷苦村落,四五年前还没有通电话,全村落共有72户347人,村落里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
进村落只有一条黄泥路,车子进不去,全靠步辇儿。
第一次去那夺村落,张萍穿了一双高筒靴,回家时上面粘满了黄泥。村落里条件艰巨,很多屋子都是黄土墙。只有村落长家有厕所,那是一个大粪坑,上面架着两条木板,布满鸡屎,走上去滑溜溜的。张萍第一次去时,冒死抱住一旁的柱子,恐怕掉下去。
村落里孩子的现状令张萍揪心,她想为孩子们谋“另一条出路”,关於收到妻子发的图片,也从北京飞到云南。
一个扛锄头的小女孩途经彩云艺术公益志愿中央。新京报 吴采倩 摄
“谁家有娃娃的,快到广场上凑集,北京的老师来了。”村落里的喇叭回荡着村落长的声音,孩子们排队站在黄泥地里,他们对舞蹈没有观点,对芭蕾更是一无所知。
彝族女孩可媚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虽然她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但至少比起干活,舞蹈更轻松,还能变美。家人起初不同意,屯子里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劳动力,他们放学后要到山上割猪草、种玉米、摘辣椒等等,晚上才能回家写作业。
张萍刚进村落,谣言就随之而来:一个北京女人来村落里拐卖儿童、练舞蹈会生不了孩子。
这令张萍哭笑不得,她只好找来很多舞蹈家与孩子合照,见告村落民练舞蹈并不会影响生养;并约请村落干部同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为了能让孩子学舞蹈,关於和张萍花了大量的韶光进里手访。他们创造,这些孩子包括孤儿、单亲、事实孤儿、留守儿童,大多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当问起父母,他们的眼里总会涌出泪水,却又不愿多说。
屯子孩子学舞蹈有什么用?这是村落里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张萍一直地用方言阐明:“学了舞蹈,你的孩子会变俊秀。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出路,找事情是没问题的。”
2016年,四个初学芭蕾舞的彝族小女孩。受访者供图
“你们一来,北京都变得残酷了”
芭蕾,这种源于17世纪的欧洲古典舞蹈开始在那夺村落“生根萌芽”。每到寒暑假,关於夫妇就会从北京赶到村落庄里。
跳芭蕾须要的把杆、舞台、灯光和音响等,当时村落庄里统统没有。关於和村落民上山砍了毛竹,去掉枝叶,洗净,往两个树杈上一架,便成了独特的把杆。梯田是舞台,太阳是灯光,水牛脖子上的铜铃是音响,孩子们在水田旁、竹林中、桂花喷鼻香里,踮起脚尖,翩翩起舞。
他们最开始是在黄泥地上起舞,后来红土高原上多了一顶绿色军用帐篷,关於称之为“帐篷艺术经典大讲堂”。
他自傲地先容名字由来,“我曾在国家大剧院办过讲座,那里有一个艺术经典大讲堂。”他们还约请老艺人、舞蹈老师、各地志愿者来这教孩子们舞蹈、画画和唱民歌等,把帐篷真的变成了一个“大讲堂”。
2017年,“彩云操持”的孩子们在帐篷里练舞。受访者供图
“阿哥弦子响,阿妹脚板痒”,彝族的孩子都会跳弦子舞。但他们没有“舞蹈”的观点,对芭蕾更是一无所知。那一个个好奇的小脑袋问张萍:“我们学这个能干吗?”她随口答道:“能去北京”,孩子们便举动手欢呼起来:“我们要去北京了,我们要去北京了!
”
为了排练去北京演出的舞蹈,张萍又变成了“严师”。
她哀求孩子们上午9点30分必须凑集,定时等她来。第一次凑集时,她从砚山县的家中驱车来到那夺村落,却只看到一半的孩子,生气地说:“来日诰日再不准时,我就不来教你们了。”
第二天,张萍提前到了练舞的空地等孩子们。到了韶光,孩子们从山上、田间、菜地里飞奔而来,衣服满是泥土和草渍。原来为了学舞蹈,他们早上五六点就得起床提前把农活干完。张萍心疼孩子,便不再催着他们定时到,只是温顺地说:“别急,你们安全到就好。”
2017年,那夺村落村落主任和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跳弦子舞。受访者供图
2017年1月,关於和张萍顺利带着12个“彩云孩子”前往北京。
那是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山村落,他们先是坐大巴去到县城,再坐火车前往北京。孩子们没出过远门,晕车晕得厉害,在大巴上吐了,在火车上还是一贯吐。张萍慌了,“我怕他们身体垮了,带不回来怎么办?”
奔波数日,他们终于安全抵达北京。可媚记得,刚下火车时,她觉得地板仍是晃动的,晕车的觉得还没散去。那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关於对他们说:“你们一来,北京都变得残酷了。”
孩子们不仅参加了文化培训活动,还参不雅观了清华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在天安门广场上,关於突发奇想,“彝族的孩子们,跳个弦子舞留念吧!
”村落长弹起弦子,孩子们随着旋律迈起步子,三步一跺脚,赢得周围游客的掌声。
张萍想得更多,“他们学了舞蹈,感想熏染到了快乐,快乐之后还能做什么呢?”她和关於希望能把孩子们送到昆明学习,让他们变得专业,真正走出大山,找到得当的事情。
2017年8月,关於夫妇带领那夺村落4个彝族孩子,正式考入昆明市艺术学校,这是昆明市唯一的公办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孩子们毕业后可以参加高考。
这或许是“另一种出路”。
村落庄有很多孩子念到初中就辍学,有些女孩子早早就嫁人生子,父母不在身边管得也少。张萍把六年级毕业的孩子送到昆明,在那学习六年舞蹈,“至少让他们安然地度过青春期。”
张萍顶碗即兴跳了一段蒙古族。新京报 吴采倩 摄
“让孩子看到这天下更多的可能性”
逐渐地,那夺村落修了水泥路,还建了露天舞台。
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完舞蹈,关於夫妇请全体家长吃“杀猪饭”,并赠予新年礼物。几轮敬酒下来,关於感想熏染到了村落民的激情亲切与信赖,“那是一种请托,我不能辜负。”
2019年的某一天,张萍和关於传授教化结束准备开车返回砚山县。离开之际,张萍侧头看了眼关於,说了句:“我要回来了”。
“我也看了她一眼,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关於知道,妻子并不是在跟他商量,而是在奉告,他知道张萍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一年6月,张萍从北京辞职,放弃了在北京打拼二十年的统统,回到家乡砚山县。“彩云操持要往下连续发展的话,必须要有人扎根在这里。”
张萍留在了那夺村落,当时“彩云操持公益志愿做事中央”也已经建成。
那是一栋两层的木制建筑,上面挂满了张萍独创的画作。她捡来村落民扔掉的旧家具、旧木板,创作成一幅幅有民族特色的木画。连地上的石板,都是她从别处找来的石头,一点一点铺成了想要的图案。
二楼的木制凉亭,是孩子们练舞的地方,对面是群山和水塘。每逢节假日,他们就把腿搭在木栏杆上,伴着关於的口号,整洁地压腿、劈叉、练舞,成群的黑山羊、戴着铜铃的水牛、穿着彝族衣饰的老奶奶会从楼下途经……
关於和彝族孩子在那夺村落跳芭蕾。受访者供图
不但是那夺村落的孩子,临近村落寨的孩子们也会翻过一座大山,步辇儿一个多小时来到这儿。
关於夫妇教孩子们舞蹈,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昆明的志愿者教孩子们画画、书法和历史,二楼还设立了“南开书屋”,孩子们可以在那看书、做作业。
“刚开始的想法很大略,要让孩子们有一个一起活动的地方。起初只有七八个孩子,这里还可以知足他们练舞、用饭。”张萍说,到后来,加上附近村落落,有20多个孩子,“大家都站在走廊上压腿,很危险,公益中央已经不能知足传授教化的需求了。”
张萍还有一种紧迫感,送去昆明的第一批孩子“大彩云”即将毕业。
受家庭经济和先天条件所限,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参加艺考去上大学,他们的就业怎么办?
2020年8月,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彩艺学校)在砚山县正式成立。这是张萍想到的办理方案,一来办理了“大彩云”的就业问题,二来形成了“彩云操持”的造血机制,办理了资金问题。
“毕业的孩子可以回到这里,连续教弟弟妹妹舞蹈,这也是在反哺家乡。”张萍先容,彩艺学校也会招收县城里孩子,并收取一定学费,这部分收入则用于连续帮助屯子孩子。
关於认为,这样才能形成“彩云操持”的“闭环”:发掘屯子里适宜舞蹈的孩子,把他们接到学校来学习舞蹈,再把念完小学的他们送去昆明连续学习。六年后,得当的孩子会连续考大学,其他孩子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教弟弟妹妹们舞蹈。
如果孩子们想回到大山里连续种玉米、辣椒,关於以为那也是“很棒的选择”,“彩云操持只是想让孩子们看到这天下更多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身穿彝族衣饰的小女孩在彩艺学校。受访者供图
“生平一村落一件事”
到2020年,“彩云操持”先后共选送62名彩云孩子考取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昆明市艺术学校、云南省艺术职业学院,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由“彩云操持”自筹办理。
可媚作为第二批送出去的“大彩云”,今年即将从昆明市艺术学校毕业,现在在彩艺学校教孩子们舞蹈。
“弯到脚背正上方,然后再转开,再落,让学生充分感想熏染到这个发力过程是什么样的,外旋是怎么做到的。”集训前夕,关於联系了北京的专业舞蹈老师,通过视频给可媚等几个“大彩云”培训,让她们学习传授教化知识。
当初学舞蹈,纯粹是出于女孩子的爱美生理。可媚彷佛真的变美了,但她知道自己跟那些又高又瘦又美的舞者有差距,初中才开始学舞蹈,先天条件和根本也比不过。她依旧乐不雅观,“能回来教小朋友也很棒,我往后可以像张老师一样,当一名编导。”
张萍也能清晰地感想熏染到村落民的变革。
那夺村落村落民一开始叫她“张老板”,再到“张老师”,现在很多孩子叫她“张阿美”,称呼关於“关阿爸”。村落长说,他们是村落庄里的“第73户”。
每到那夺村落祭龙的日子,张萍作为那夺村落唯一能靠近龙树的女性,可以向龙树磕三个头,再喝三杯甜水。毕摩(彝族中会邪术的人)在她身边念念有词,送上诚挚的祝福。
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关於以为自己也变了。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名专家,是各大比赛的评委、考委,他以为自己有点“飘了”。当回到屯子,孩子们牵起他的手时,他才意识到“我是一名老师,我要去教他们”。
戴着帽子的可媚在教孩子们跳街舞。新京报 吴采倩 摄
两人分隔两地,有人曾疑惑他们的感情涌现问题。张萍不以为然,“越好的关系越放心,越是须要有共同的空想,我们只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实现目标。”
“生平一村落一件事”,这是关於夫妇共同的信念。
对付未来,张萍还是有信心的,常常有歌舞团向她打听孩子们什么时候毕业。她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屯子里的孩子,也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他们的志愿团队。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孩子们坐在舞蹈室的地板上,等待着“阿公”送他们回家。一个孩子刷着热门的短视频,阁下的孩子随着哼:“什么是快乐星球?”,远处的孩子应和着:“便是这里呀!
”
文 | 新京报 吴采倩 演习生 兰涵
编辑 | 左燕燕 校正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