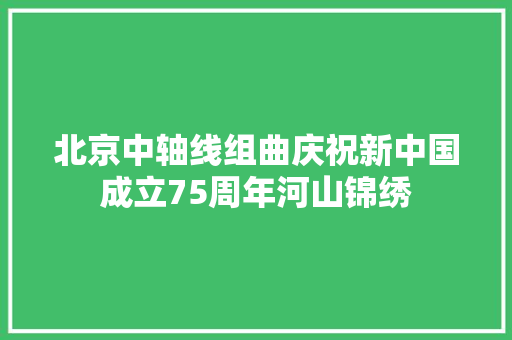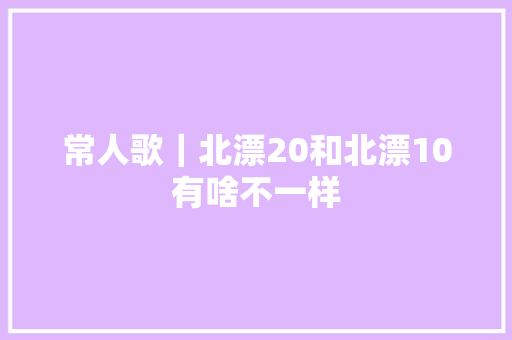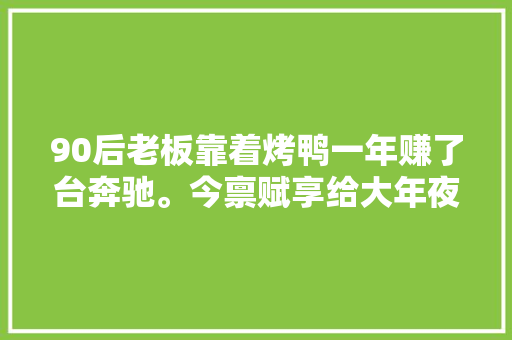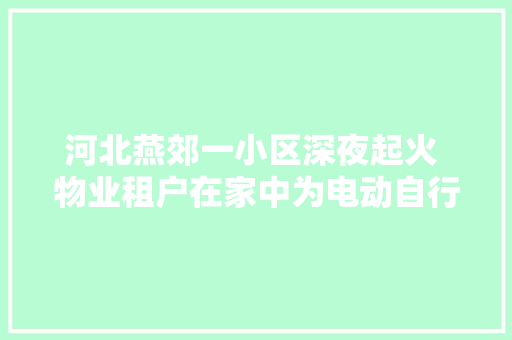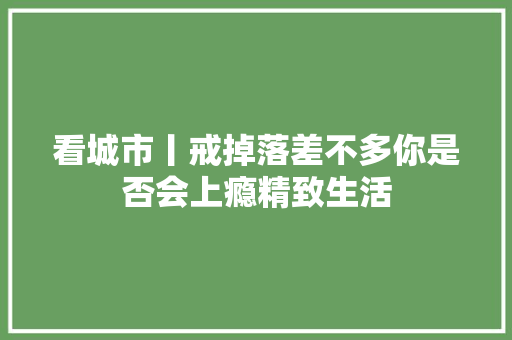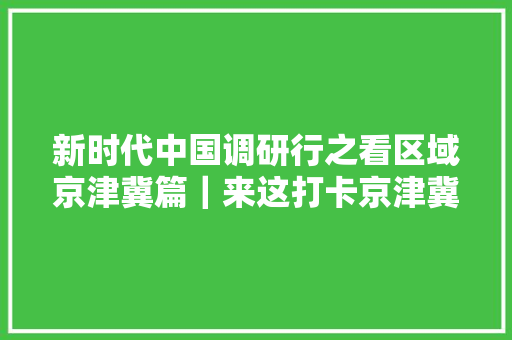大戏看北京
本栏目与北京戏剧家协会共建

“常常会有人问我,你年轻的时候在哪儿?出国读书了吗?”“我说,没有,我一贯在舞台上。”“哪个舞台?”“北京曲剧。”“哦,北京曲剧,北京曲剧是什么?”“看来很多人还不理解北京曲剧是什么。”
——许娣如是说
在接管《北京纪事》的采访时,许娣说话豁达,笑声清亮——大部分人对她的角色印象,同样勾留在此。
五年前,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许娣涂着高饱和色系口红,踩着高跟鞋,出演了剧中罗子君的妈妈薛甄珠,走路带风,坦直明快,浑身散发着市井气息,很多网友评价“许娣演活了一个欢天喜地又生动繁盛热闹繁荣的老太太,真是绝了”。赞誉中,她也凭借这个角色,得到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
许娣饰演薛甄珠
大概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过了知定命的年纪,以影视演员的身份可以在荧幕前,得到如此大的成功,成为年轻不雅观众追剧的“动力”。
好奇的人,开始追溯她的履历,创造在追求声量和流量的娱乐圈中,除了一部部影视作品中经典的人物形象,许娣鲜有声响。身处名利场,她对名利却始终没有过多热切的渴望。“我真是不太把这个看得很重。”不争,不比较,不乘胜追击,是许娣的生活哲学。
这也可以在她艺术生涯的前半生,得到呼应。一个险些“隐形”的演员,在一个地方戏的舞台上耕耘了大半辈子。
很少有人知道,许娣是曲艺曲剧演出艺术家魏喜奎师长西席的弟子,17岁便进入北京戏曲艺术学校学习北京曲剧。在北京曲剧的舞台上,她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小白菜、《龙须沟》中的程娘子、《茶馆》中的康顺子。1997年,她荣获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北京曲剧第一位“梅花奖”得到者。
虽然她现在凭借影视作品得到了广泛的有名度,但在接管媒体采访时,她多次绝不掩饰笼罩地表达了自己从艺的初心和对北京曲剧的热爱。
从十七岁学习专业到现在,对北京曲剧的热爱早已融入到血液里,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太大的野心,坦诚接管生活赠送的统统,她更乐意往前看,随遇而安,笑对过往。一个义务感极强的人,每每会轻看光环。
今年,许娣65岁了。在“女性演员年事危急”鼓噪确当下,许娣彷佛为这个命题做出一种解答——如水,清淡般流过,但总会留下波光。她的故事关乎选择与执着,关乎时期,也关乎个体。
以下是许娣的自述:
从白丁到梅花奖我一贯特殊不自傲,到现在也是如此。
1974年,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北京曲剧团到我们学校招收学员班的学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京曲剧是什么,老师让我去试试,就去了。口试时讲了一个故事,可能老师以为我的朗诵还符合曲剧团的招生标准,之后就一起考了进去。
进团后,我完备两眼一抹黑。我们班有少儿合唱团的,有学京剧的,有学舞蹈的,就我是一白丁,什么都没见过,也什么都不懂。统统都觉得太难了。
由于没有受过声音的根本演习,我一贯都不自傲。
当时我的声音弗成,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大白声,声音也唱不长久。为了练习声音,每天只要琴房一空出来,我就钻进琴房,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摁着琴键,自己练声。现在回忆起来,我那个笨方法还挺好,能掌握音准(笑)。我就这样练声一贯练到2008年退休。接到退休关照的那天,我看着钢琴感叹,面壁三十多年的练习啊,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还真的就做到了。
后来拜师魏喜奎师长西席学习这个事,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在我的心里,只有精良的学生才会被送到魏师长西席那里,我从来没敢想过有一天会随着魏师长西席学习。
1986年,有传言说魏师长西席要让我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定要把这生虎子给抠着出来”。这么大的一个戏让我这个“白丁”演,我惶恐不安又以为不可能,我能入师长西席法眼?
许娣与师傅魏喜奎
但那个时候,魏师长西席真把我叫到家去了,从第一场到末了一场的唱,细细地给我说了一遍,还留我在她家里吃了饭。我才以为这个事儿,是真的。我那时候便是不自傲,师父也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直到魏师长西席去世后,魏师长西席团里的好朋友刘淑珍老师才跟我说,“你师父是喜好你的,当初你演小白菜的时候,她特意喊我去戏院看,说你有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1989年12月在天津演出的时候,我和魏师长西席走在马路上,她溘然说:“我一贯也没有徒弟,我想收你。”转过年,就正式拜师了。我也不知道师父怎么就看上了我,我以为自己太不精良了,条件真的很差。但师父切实其实定和鼓励给予我极大的勇气,我见告自己不能气馁,一定要通过努力填补自身的不敷,负责演好每一个角色,让不雅观众以为我是一个好演员。这个想法一贯伴随着我的艺术生涯直到现在。
1996年我得到了第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演出奖。领奖的那一刻我特殊的骄傲,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北京曲剧这个剧种骄傲,这个奖是全体剧团和剧种所得到的名誉。
作为北京唯一的地方戏,看着她一每天发展壮大。我至心肠感到骄傲和自满。现在,我也收了自己的弟子王玉。希望能将师父的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把北京曲剧发扬光大,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一辈子的诚笃人最初在学员班的时候,由于演唱的不敷曾经动过转行的动机。
我们声乐老师带我偷偷去考过话剧文工团,结果人家特喜好我,一壁试完就迫不及待地给团里打电话问情形,结果我和声乐老师刚回学校大门就被拦住了,学校卖力人指着声乐老师的鼻子就骂:“你如果把许娣弄走了,你吃不了兜着走。”想飞的心就这样被压下来了,往后就再也不敢萌动了。现在回过分来看,多亏了那时候的诚笃,才有了现在的许娣。(笑)
北京曲剧团成立于1952年,相较于京剧、昆曲,北京曲剧是非常年轻的剧种,短缺不雅观众根本。场下不雅观众的数量,从少到多都是一场一场唱下来的。剧团效益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多打一份工来补贴家用。那时人为不高,交完孩子的托儿费,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我就跟我师长西席说,要不我也去找份打字员的事情,挣点外快?我师长西席一听就武断地反对,“你不是干那个的,你就好好练你的。”从此,我就再也没动过别的动机,齐心专心扎在团里,老诚笃实地练声练唱、排练、演出。
1986年,有时的机会下,我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他没有风雨衣》。面对镜头,我手足无措,连走路都不会了,由于我只会在舞台上行动。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真不喜好拍电视剧,由于不习气(笑)。
许娣在《三国演义》中饰演甘夫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镜头前的人物塑造,那种细腻情绪的刻画与表达,对我在舞台上的艺术创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初涉影视作品,还算成功。陆陆续续地收到不少剧组的邀约。
但我始终以为北京曲剧的舞台才是我毕生追求的奇迹,影视作品虽然能得到更高的有名度,但初心不能忘。以是,一贯以来奇迹的重心都放在舞台上,直到2008年退休后,我才将重心转移到影视作品的创作上。
纯粹的灵魂 才能塑造出无瑕的角色演员是人塑造人的艺术,不仅是角色形状,更主要的是塑造角色的灵魂。
精良的演员,首先要做个年夜大好人。纯粹的灵魂才有可能塑造出无瑕的角色。我一贯十分感激父母对我的教诲,他们教会我自觉、自律,安分守己、老诚笃实、大公至正地做人,这种精神一贯伴随着我在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戏曲界有句老话:不成魔,不成活。我以为这句话是对一名演员艺术哀求最好的概括。台上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磨炼与思考。我曾为自己条件差而感到苦恼和绝望,也曾为自己努力付出得到回报而欢欣鼓舞。这统统都离不开苦行僧一样的修炼。成活的条件是成魔,成魔的根本是“磨”,这个过程,很漫长。这种练,特殊苦。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磨炼,改动自己,完善自己,才能在技艺上不断精进。
日常生活中的许娣丨受访者供图
作为一名演员,最幸福的时候便是与不雅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一瞬间。不雅观众跟随着演员的情绪而流露出的喜、怒、哀、乐,会给予一名演员莫大的造诣感。这种愉悦,是一种境界,也是痛楚修行之后的快乐。
如今,我仍在连续修行。无论是在舞台还是影视作品创作中,我时候见告自己,角色是演员的生命,负责对待每一个角色,才不会辜负自己的人生。
第一次与北京曲剧重逢,我正值花样年华的十七八岁,北京曲剧正值花样年华的二十三岁。我们都是青葱少年风华正茂,我们相互搀扶、相互陪伴、相互造诣,走过了四十七年。
今年是“北京曲剧七十年”,而我也已过花甲耳顺之年的65岁,正向古稀之年迈进。我为魏喜奎师长西席等一代艺术家创立的北京曲剧而骄傲,为我自己曾经在这一方寸舞台上努力奉献过而自满,为我们的后来者生动在舞台上而备感欣慰,相信北京曲剧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采写丨马捷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