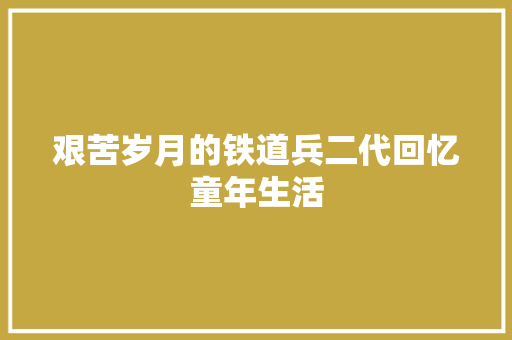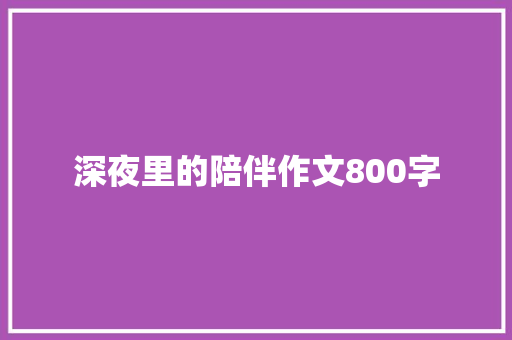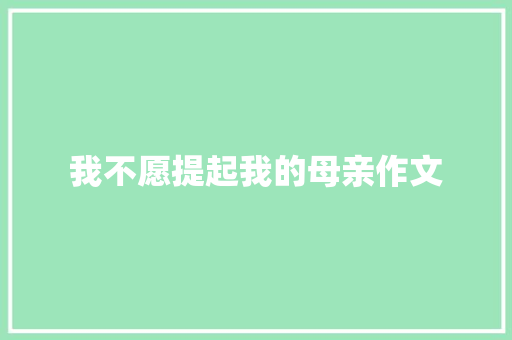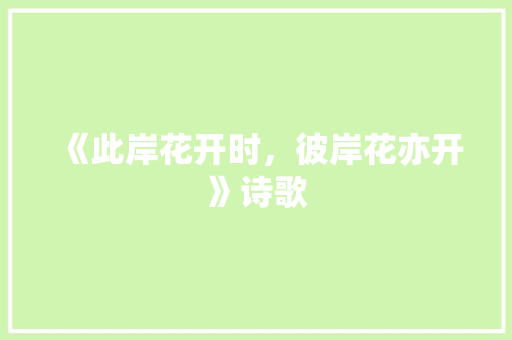母亲老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腿脚也不怎么机动,无情的风霜在她的脸上留下道道皱纹。看着她干瘪的身影,他眼睛有点湿。
这回,他打算再不接管母亲的安排。以前,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如今,他决定自己拿主张。

他十八岁了,有着健壮的身子。用家乡人的话说,可以吃沉了。可是长这么大,除了农忙时回来帮家里干点活,他大抵没有干过什么活。母亲从没有哀求他。在母亲眼里,他最要紧的便是读书!
就如现在,母亲坚持着她的想法——立时去复读。
娃娃啊,别多想!
一次弗成,咱再考一回!
那二次弗成呢?他没好气地打断。对付母亲而言,这彷佛她在地里撒下一把种子,一行豇豆一样自然。
母亲的步伐彷佛更快了,明显看不出他的落寞。
从前,母亲送他,路面可以看到高低不平的影子,高的是母亲,低的是儿子。而现在,长高的是儿子,变矮的是母亲。贰心里难熬痛苦。脚步越走越慢,远远的,落在母亲的身后。
爬上一个土坡,母亲停下来,坐在土墩上,端起水杯,咕咚咚喝了半杯水。
而他欲言又止。他要去表面打工——自己高中毕业难不成还没一碗饭吃。
妈,我不惦记书。他的声音低得自己都听不清楚。你嘟囔啥?可能太出乎猜想,母亲被水呛得咳嗽起来。
他不敢再说什么。见母亲咳嗽不止脸面通红,他有点腼腆。他宁愿母亲给自己一巴掌,或是大骂一顿,可是母亲没有。
那天晌午,母亲破天荒要他一起去麦田收麦子。麦田里,金黄的麦子一浪一浪涌来,没有一丝风,只有蝉们在聒噪。八棱形状的崇文塔,遥遥与他对视。他暗想佛祖可会佑他前路平坦?
割麦子没他想得那么大略。同样是一把镰,母亲很快把他甩在身后。她摆荡的双手彷佛机动无比,镰刀所向披靡麦子乖巧躺下。而他,每割一小块,得费九牛二虎之力。那尖利的麦穗,在他身上留下许多划痕,被汗水一渗,火辣辣疼!
他的胳膊和腿还瘙痒非常,起了不幼年红疙瘩。
你吃不下苦!
母亲的声音不大,却深深烙在贰心里。是的,如果他打退堂鼓,母亲肯定不同意他出去打工!
他不想要这样的结果,他咬牙坚持。纵然他的心思不在这里——面前的麦田,只能管饱他和母亲的肚皮,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空想。他如果能空手发迹,母亲就不会为家里的些微收成而忧虑,她可以和别的有钱母亲一样在家里做做针线,乃至愉快坐在女人堆里谈天。
父亲不在了,母亲像男人一样扛起这个家。既当爹又当娘,地里的庄稼要务弄,灌溉、除草、施肥一样都不能少;他上学更要挣钱苦撑,逐日没命地干活,让她过早朽迈,他劝过她,说自己不读书,让她不种麦子,她禁绝许。
他的邻居、他的堂妹堂姐,还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先他一步走出村落落,走到全新的陌生的城市。如果大字不识一个的邻居在城里可以容身,那么他也可以,可以在城市拥有一份事情。
明天将来诰日,他离开村落落。村落落里随处可见的野草,翻滚的麦海,还有清新的空气都远远抛在脑后。连母亲苍白的头发、无奈的眼神也逐渐疏离在视线之外。
当鳞次栉比的高楼涌如今他的面前,他就像久离树林的鸟儿回到枝头一样雀跃不已。
他开始在异域的街头穿梭,在劳碌的清晨、鼓噪的薄暮,在汽车的引擎声和灰尘的肆虐中,怀揣一张薄薄的毕业证独自行走。
你学历太低!
我们这儿不缺人,请试试别的公司!
多少天多少月,他得到险些千篇一律的回答。那些高大时尚的玻璃大门将他拒之门外。待在狭窄逼仄的出租屋,痛楚的他无奈地盯着扭捏的15瓦灯泡发呆。窗外的蝉鸣溘然入耳!
便是这耳熟能详的蝉鸣,把他的乡愁唤醒!
小小村落、袅袅炊烟。他想起无边无垠的麦田,想起麦子的暗香以及故乡院落里倚着门扉的瘦弱身影。
他回到家乡,生他养他的崇文乡。
母亲喜极而泣。复读之前,带他登了一次崇文塔。崇文塔属楼阁式砖塔,平面呈八角形,共十三层,总高度八十多米,根据八卦悬顶的古建筑事理设计,从塔下至塔顶全部用青砖建筑。全部塔身为八棱形状,底层每边九米,周围共计七十多米,每层各有四窗,每层表面有四个佛龛,交叉而上。佛龛内置明代石刻佛像或坐或立,形态互异,极为生动。第二层内铸有金属站立佛像一尊。二层南向塔门刻有“崇文宝塔”四个字,由塔内可弯曲攀登,直至塔顶。母亲说,崇文塔为倡导泾阳、三原、高陵三县学童努力向学而建,是时任明朝刑部尚书的泾阳县人李世达所修。母亲把“努力向学”四个字咬得很重,她居然能记下如此拗口的书面措辞,一定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自此,他像变了一个人,勤奋学习废寝忘食,考上了一所一本高校,现在深圳事情。
他是我表弟,姓樊名向学,注定与崇文塔有难以割舍的宿缘。
作者:申宝珠
来源: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