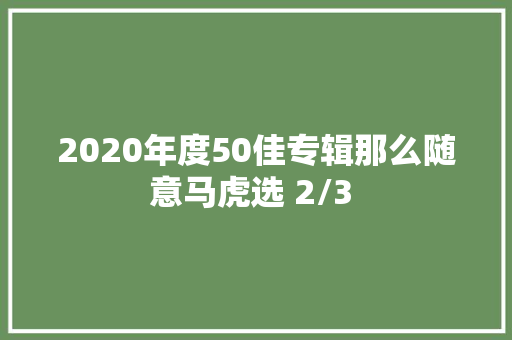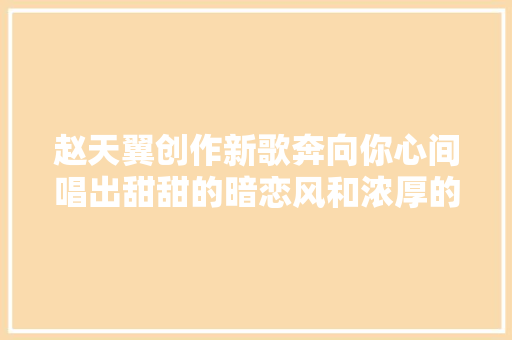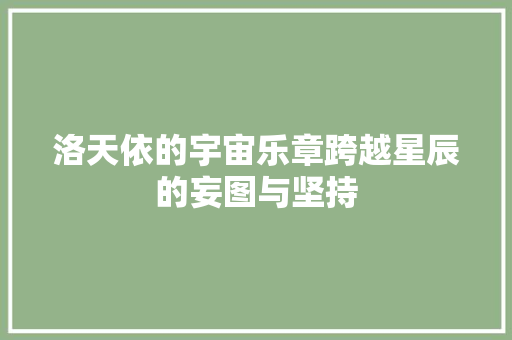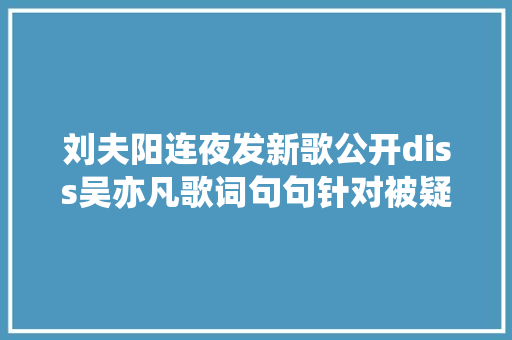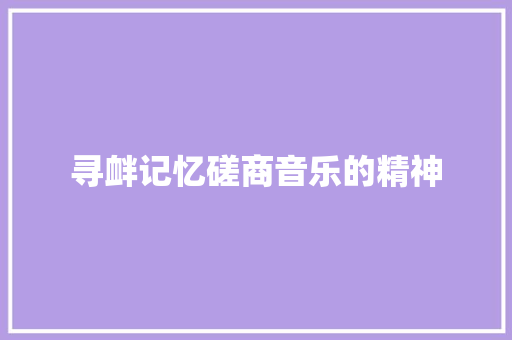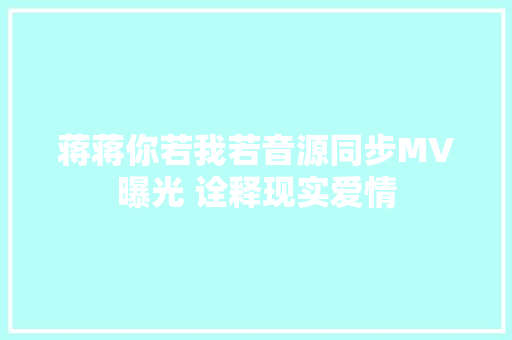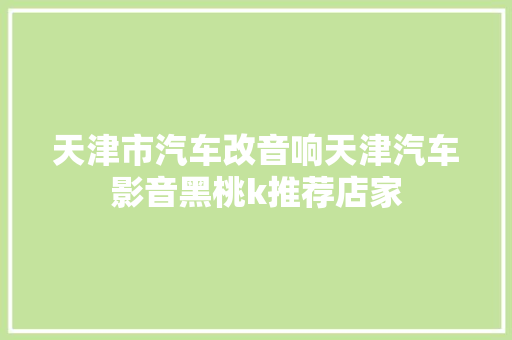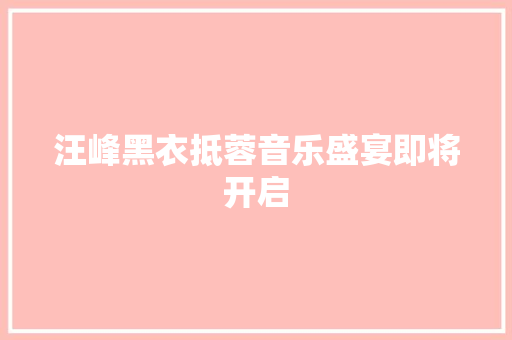后来创造Yoyo便是岑宁儿。她用了十多年韶光在音乐的台前幕后事情,从台侧的二声、三声变成唱主旋律的那一个,但站在聚光灯下唱主旋律绝不是她的人生目标。
李宗盛收她作徒弟,张培仁和贾敏恕赏识她,陈奕迅让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独唱一曲。岑宁儿得到偏爱,是由于十年过去,她一开口,仍旧有天然和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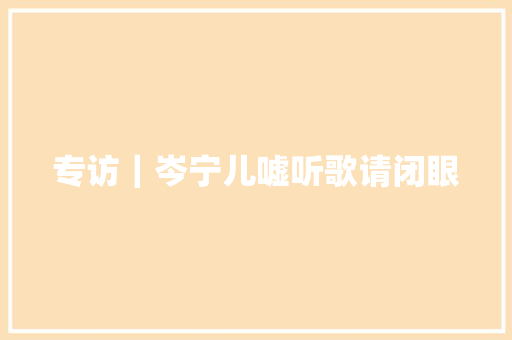
当年她穿T恤板鞋就敢站在舞台中心,由于“这件衣服是新的啊”。现在她上台仍旧朴素得像学生,不是女文青的标榜,而是她真的恨不得隐在阴郁里唱歌,只闻歌声。
12月12日,岑宁儿的现场专辑《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在网易云音乐独家发布。这是StreetVoice街声与Blue Note Beijing联合推出“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现场录音专辑系列操持后,发布的首张专辑。
岑宁儿北京Blue Note现场
1
岑宁儿出生于喷鼻香港,12岁开始念英文学校,17岁去加拿大读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2005-2009的北京生活让她学会把“左转”说成“左拐”。在当年这座一天做不了三件事的弘大城市,担当音乐剧助理的岑宁儿碰着李宗盛,开始思考“要做音乐的演出者,还是音乐的创作者”这个问题。
2007年一整年她还做过一份工,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剧组担当场记/翻译/导演助理。从只跟南京部分,到拖延至一整年。阴郁没有侵袭她,充足的理性和内心的通亮让她仍有能量和饰演张纯如的郑启蕙(Olivia Cheng)合写主题曲并录唱。
2008年,岑宁儿创造自己做什么都回到音乐,因此逐渐放下其它爱好如黑白胶卷拍照,接管“职业音乐人”的身份。她大学学习过爵士乐,但唱过爵士酒吧以为“不知足大家都在饮酒谈天的状态”,也认清自己并不适宜当个爵士歌手,“骨子里不足自由不足即兴”。
可能的路逐一试过之后,岑宁儿决定把精力放在两件音乐工作上——为别人做和音,为自己写歌/唱歌。
作为和声,她涌如今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方大同、杨千嬅、卢凯彤、容祖儿……的舞台上。2013年岑宁儿在《明报》开过一个专栏(可惜没坚持下去)。她这样描述和音:“我一贯不肯做任何会令我不能当和音的事。这不是很多人明白的执着,里面有不是很多人能想象的收成。”
把自己完备交给一个旋律、一个主音,“像变色龙一样无限靠近主音,没有压力和没有自由度”并存。晚上,她在酒店的电视机前感叹自己的好运气。不仅是能够去那么多城市、登上那么多舞台、与那么多好乐手互助的幸运,还有作为和声纯粹浸在声音里的幸运。何况做和音还能赢利,能经历不断建立新风格的寻衅。武林小辈杂学百家的快乐路。
2015年岑宁儿的第一张个人专辑《Here》发布,华语金曲奖和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新人单元皆对她青眼有加。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是我养音乐还是音乐养我?”思考下来,“还是我养音乐比较好,主要的是找到平衡。”
这一年她没接任何和音的事情,专心做自己的专辑。《Here》是一张眇小的专辑,interlude是来自东京、台北和印度的声音。它是岑宁儿听到的声音落在心里泛起的荡漾,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己跟自己对话,并总能成功把自己从泥沼里拉出来的拉锯战。
她的《明报》专栏里有一篇叫《语泄》(Verbal Diarrhea),写自己的“怕吵”:“不仅是频率上的,也有感情上的。”如果字面理解她的音乐,岑宁儿的音乐的确是“怕吵”的。
最近三年,她和三位朋友组成一个四人互勉小组,每人每月必须在“街声”平台上上传一首demo,做不到的人有惩罚。他们不常见面,不算严格意义上氛围热烈的“音乐沙龙”,倒是更像共同促进会,与各自的“Freelancer
北京之后长期生活在台北,在台湾人的音乐平台上发布作品,干净的人声和大略配器,岑宁儿很随意马虎被归入台式小清新的行列。但仔细听,《Here》的大略里有空间感和韶光感。
岑宁儿喜好原声乐器能供应的空间感。如果是不大的现场,一个鼓、一把吉他、一把贝司、一个键盘就够了,“可以两把吉他的话,不如把一把琴换成和音”。韶光感是她个人的,有台湾indie女声的调调,有翻唱作品各自的风味。《不枉我们张山十年》唱的是她全体中学时期参加的合唱团,六个特殊要好的小朋友组成“张山合唱团”(粤语“嚣张”读Hill Cheung,翻译过来便是“张山”),有浓浓港味和人情味。
岑宁儿的中文只念到小学六年级,往后的进步全靠自己读书和大学时期参加中文辩论社团,“《明报》专栏没有一篇没用到Google翻译,也多亏编辑帮忙修正。”
如果请别人捉刀,大概岑宁儿的歌能更好。她的词像剔了骨的鱼,逻辑清晰分明。缺陷,好友陈咏谦看得很清楚:“你的词太理性。”她当时还未完备理解,想着“写词不便是写内在的过程吗”。
后来在Youtube看到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在线写词教程,岑宁儿第一次创造写词如何让人共鸣可以被量化,原来中文传统的“赋比兴”是普世的道理。
“发展中很看重脑筋的部分,但音乐里大都要用到的是心。音乐是我最‘存心’的一件事,是用来平衡我的全体人生的。”
2
岑宁儿想有一个严格的、可以倚赖的导师,希望类似的四人音乐小组能多点音乐的谈论,而不仅仅是相互督匆匆对方交作业而已。
她的境遇实在蛮有普遍性。耗时的、密切的、须要碰撞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时期变得奢侈,我们只好变成孤单的战士。
岑宁儿又是后天混血的人,北京、喷鼻香港、台北,乃至去加拿大,提起行李箱就可以走,去哪里都没问题。只有一次,她和巡演军队七天跑过七座城市。持加拿大护照入境时,海关很大略的问题:“你从哪里来?”她累糊涂了,茫然不知所答。海关:“你到底从哪里来?”她的脑袋里开始跑马,城市一座座翻页。海关不耐烦了:“哪里是你的家?”她快崩溃了:“天哪,这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
”
由于在哪都没有扎根,以是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用用力拔根,但情绪依然投射到每一个住处,“每次搬家都会很有感触”。
海关事宜之后,她发挥一向的理性思考见告自己,虽然倾慕从小在一个地方终年夜的人,“但纵然一座城市也在不断变革,我不走,它也在变。家里人常常念的某个摊位,不也早就没了嘛。”
她生在喷鼻香港,但并不十分“喷鼻香港”。朋友说她是唯一一个没看过周星驰电影的喷鼻香港人,一天晚上强制她连看五部。觉得怎么样?“便是很无厘头很可笑。”
接管不同的文化,但缺少最“家”的那一份。这同时意味着开放和核心的一点空。她写了一首歌叫《没故事的人》,光名字就非常符合某种时期特质,她音乐里的间隔、韶光、自我意识的确认和专注力的缺失落亦是时期通症。
“有人以为我的歌是无病呻吟”,但她的“无病呻吟”至少是诚恳的。《空隙》里的词念着念着就变成唱的:“我这么幸福/没任何权利不知足/我说不出/怎么敢埋怨那不存在的苦”。生活的顺遂,不代表“苦”便是假的不是吗?
有朋友说她的音乐“太顺畅了,就像你的人生一样”。岑宁儿接管,但也只能耸耸肩。和你我大多数人一样,她不是猖獗找南墙、寻天下尽头的艺术家性情。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逐渐进步,创造不同的唱法,大概今日比昨日更懂力用在哪里,大概来日诰日想插电了扩充音乐的维度。
在“街声”上传作品之初,岑宁儿质疑过总是写眇小事物和个人思考的意义。后来她释然了,“不想由于对自己的批驳,让那些大概对别人故意义的东西无法出世。”
上海弹唱分享会
3
岑宁儿翻唱过台湾女歌手巴奈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这首歌她听一遍哭一遍,实际上只要听巴奈唱歌她就很随意马虎掉眼泪。“这歌直接就打到心里去了,它是统统问题的答案。”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年夜胆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
她用最大略的配器和本真的声音唱这首歌,和另一首著名的翻唱作品《光之翼》截然相反。“《光之翼》是音乐的技能问题,我希望只管即便和原唱不一样。这首歌不须要,它本身就很够了。”
李宗盛也问过她一个音乐上的终极问题:“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她至今仍旧常想,现在的答案是:“创作是照镜子,是对自我的深挖。有人用创作和时期与社会连接,我只想回到自己,不要太有包袱。”
喷鼻香港有一个由视障人士策划的《暗中作乐》音乐会,现场无任何光源,一片漆黑。岑宁儿连续参加了三届“切实其实上瘾”。不唱歌的时候她乃至可以躺在台上,可以拉筋。不用关注自己的样子,并且全场公正,她也无法关注别人的样子,只有声音。
后来她养成在录音室也把灯关掉的习气,在阴郁中更能关照自我。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听她演唱会的时候闭眼,试试看回到声音的纯粹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