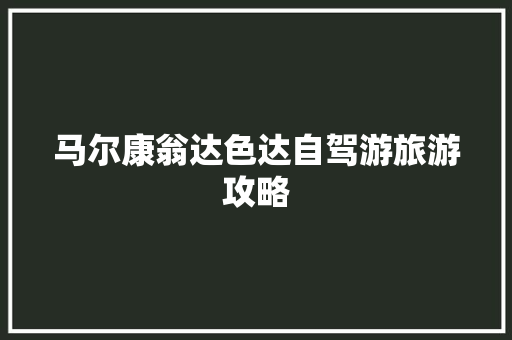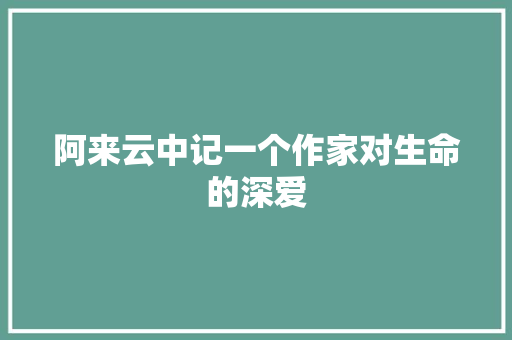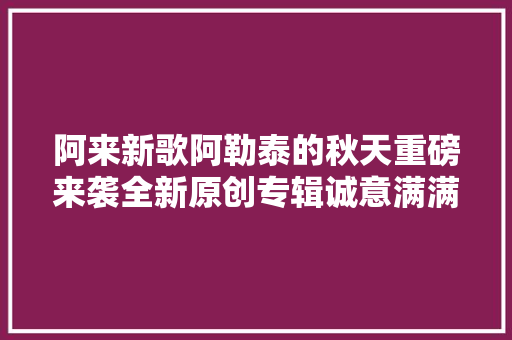李舫,作家,公民日报外洋版副总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家学会副会长。在散文集《纸上乾坤》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舫写《苟利国家死活以》《春秋时期的春与秋》《千古斯文道场》《在火中生莲》等佳作,见识宽阔,雄迈沉潜,有一种巾帼不让男子的浩然之气。
李舫的文章深受欢迎,比如她写城市的《成都的七张面孔》《能不忆江南——杭州,一座天城的前世今生》 ,都曾在网络上刷屏。不只长于写城市,李舫还长于写人,身为媒体人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她,对中国当代文学深有不雅观察,对海内浩瀚实力派作家深有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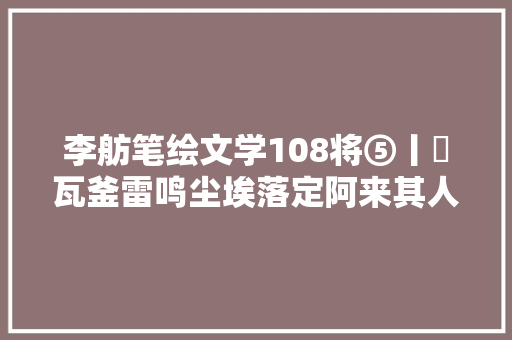
2020年11月起,李舫特殊在封面新闻开设文学专栏“文学108将”,用生动活泼的措辞,为108位中国当代作家描像,讲述不为读者理解的故事。
文/李舫
“来日诰日我过生日,你可一定要来!
”
阿来郑重地发出约请。
阿来,熟习的朋友都叫他“阿哥”。
对朋友们来讲,博学诙谐、古道热肠的阿哥,不仅是个小说家、散文家,还是个百宝囊、百科全书,凡是碰着字典和度娘都查不到的疑难杂症、疑难问题,朋友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阿哥。
“阿哥,地质学里没有提到这些岩石,到底如何区分火成岩、水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
“阿哥,小鸦跖花,属于毛茛科鸦跖花属;条叶低头菊,菊科低头菊属;蓝玉簪龙胆、高山龙胆、山景龙胆,都属于龙胆科龙胆属——这些难道不对吗?为什么植物大纲里找不到?”
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阿来都能随口说出答案。他是地质学家中的地质学家、植物学家的植物学家,我们笑他,还是“书呆”中的“书呆”、“花痴”中的“花痴”。迟子建描写阿来,“当一行人热热闹问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
阿来(郭红松绘)
就像麻利地从身后的箱子里取一道道锦囊,阿来的箱子里搜罗万象,高下五千年,周遭八万里。古今中外、妍媸妍媸、小人得志、魑魅魍魉;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直播带货、降维打击、阴郁法则——都在他的锦囊里。格非说,“一个作家,你跟他聊几句,就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可是你永久不知道阿来的边界何在,他没有边界。”是的,阿来无远弗届。
偶或,阿来也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山中驾驶,时常碰着一个被压扁的波浪型路牌标志,提醒司机把稳,前方有连续急转弯。
“哦,那个不知——知道!
那个是——小心高压线!
!
”阿来小心论证,大胆猜想,末了,用他的聪慧大脑,斩钉截铁地给出了答案。
阿来善饮。对付朋友们来说,阿来的酒量是个谜,由于没有人见到他喝醉过,他有且只有过一个对手——吉狄马加,但是至今未决胜负。阿来饮罢顷刻变成麦霸,引吭高歌,载歌载舞,憨态可掬。有时候,阿来会用藏语演唱《祝酒歌》,歌声深奥深厚而忧郁,“歌词说的是,纵然你酣醉,也要像孔雀一样优雅,这便是我们藏族。”阿来说。
酒神也常会碰着酒鬼的困扰,阿来谆谆告诫那些酡颜脖子粗的“鬼”:酒醉伤身,酒醉伤神,酒醉伤情,由于——
阿来想不起来了,取出手机找到段子,递给身边的助手说,你来读!
助手一看便是老手,接都不接阿来递过来的手机,大声“读”起来:深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游客回到了旅社。半晌,他不满地叫了起来:“喂!
做事员,你们的电梯坏了吗?”“师长西席,电梯仍在正常运行,只不过您进的那是电话间。”
这个梗够冷,大家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可是,那边厢,阿来早已拍着桌子,笑得不能自抑。
阿来的酒量大,烟瘾更大。有人笑他吸烟只用一根火柴,早上点燃一根烟,能一根接一根吸到晚上。这或许不无夸年夜,但是喷云吐雾、云蒸霞蔚,方有才华横溢、文思泉涌,这倒是事实。
这些年,阿来居住在成都。而我由于事情缘故原由,极少离开北京。得知我和朋友去成都,阿交往往会盛情发出约请:“来日诰日我过生日,你可一定要来,六十大寿哦!
”
于是,一年多韶光里,我手捧着鲜花、鲜花、鲜花,为阿来祝贺了三次六十大寿。公历、农历、藏历——一个都不能少。就像一个天真又饕餮的孩子,阿来无比渴望一个盛大、抑或并不盛大的生日聚会,有亲朋环抱,有美酒相伴,有鲜花怒放,有洒满巧克力和水果屑的蛋糕,主要的是,在这样场合大家无拘无束,尽欢而散。
“来日诰日你们可都一定要来哦,我——”
“阿哥,知道吗?你已经一百八十岁了!
”
在阿来蠢蠢欲动为自己谋划第四个六十大寿的时候,我们果断地制止了他。
“真的吗?我以为我才八岁呢……”阿来看着鞋尖,委曲地说。
终于有一天,不服老的阿来开始服老,他放下手里被磨得卷出了毛边的《陈寅恪合集》,哭丧着脸,叹着气说:“唉,我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
“——孩子!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阿来瞬间云开雾散,转阴为晴,旋风一样平常地从大门刮出去,转瞬间又旋风一样平常从大门刮回来,手里多了一篮子煮熟的鸡蛋:“见告你们一个好,来日诰日我要过生日啦!
”
一百八十岁的阿来,有颗八岁的童心。
不睬解八岁的阿来,便不会懂得一百八十岁的阿来;不睬解一百八十岁的阿来,更不会懂得八岁的阿来。
“那是个下雪的清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呼唤。”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老麦其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下了傻瓜二少爷,阿来笔下这个大智若愚的傻瓜、以及这个傻瓜所具有的超时期的触觉和预感,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神奇航程。
在21世纪将要拉开华幕之时,阿来携着他史诗般的作品《尘埃落定》横空出世,从此,中国文学的广阔高原,一座奇峰凌空耸立。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便就此尘埃落定。
阿来笔下的傻瓜二少爷,不知不觉令人想起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永久长不大的侏儒奥斯卡。面对无法理解的天下,奥斯卡学会了尖叫,他的尖叫有着神奇的浸染,让他不喜好的东西轰然瓦解。不久,奥斯卡喜好上了铁皮鼓,鼓声是他的另一种尖叫,是他对付这个他不喜好却又无可奈何的天下的一种无奈之举。
阿来的小说,犹如铺设了沉重蒺藜的笔墨迷宫,令人悲哀、困惑,令人沮丧、绝望。凭借着傻瓜二少爷的感知,阿来以辛辣和荒谬重写了一个彷佛早已被我们遗忘的天下——一个被铁皮鼓敲响的天下。所有的聪明人都认定冒傻气的二少爷一定与现实生活扞格难入,而事实上,偏偏是这个傻瓜,具有类似巫人般的特异功能,他对客人的到来、官寨里的怪事、复仇杀手的现身、旦真贡布的被刺都有未卜先知的预感。末了当仇人向他下手时,他沉着以对,以一个预言家者的敏锐与气度,像一个真正高原男子汉那样主动接管父亲仇人的刀剑。正是这样一个傻又不傻还带着先知预言家的人,给人无限遐思,对与错、真与假、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郁、战役与和平,都值得我们重新打量。
在马尔康,“阿来”这两个字注定有着分外的含义。带着敦厚的憨笑,拖着沉重的脚步,阿来从他身后敦厚沉重的高原走来,犹如晨曦浮动在大地之上。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是武断;他的神色,有些落寞,但是沉着;他的笔锋,有些滞涩,但是凝重。阿来出生于马尔康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马尔康”,在藏语意为“火苗兴旺的地方”,以嘉绒十八土司中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起来的马尔康,是阿来的发展之地,也是他的成熟之地,他生命的道道履痕都始终环绕嘉绒。熟读阿来小说的读者大概未必知道,少年阿来还曾经是一位墨客,他由诗而走进文学,他的一首诗至今在马尔康被人们传唱:
我在这里
我在重新出身
背后是孤寂的白雪
面前是通亮的阴郁
啊,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措辞
从马尔康走出的阿来,以更加洒脱、轻松的姿态,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中短篇。在散文集《大地的阶梯》中,阿来写出了游走西藏的旅途中写的所看、所想、所感、所闻,他将对这块地皮的情绪倾诉到他的行走里,一位法国汉学家乃至认为,《大地的阶梯》的文学代价实在超过了他得到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尘埃落定》。在将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空山》中,阿来再次显示了他操纵故事和措辞的能力,叫机村落的藏族村落落里的6个故事,道出了阿来心目中的村落落的秘史。在这本以千百年来在藏人中口口相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底本创作的小说《格萨尔王》中,阿来则写出了一个民族的慈悲,阿来谦卑地将这次写作称为“持重的学习进程”,“时时窥见到历史依稀的身影”让他肃然起敬,也让浮想联翩,他倒转时空,对历史和传说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虚构,这是一本发展在非虚构力量之上的小说,正由于如此,它有着阿来其他作品中所没有的时期意义。非虚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阿来近年来写得最疼痛、最挣扎也是最好的一部著作,阿来称这部作品为“不是小说的小说”。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瞻对”,究竟为何在两百多年的韶光里,成为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英国军队等各方力量的必争之地?阿来致力讲述的不仅仅是川属藏民独特的坎坷命运、精神传奇,更多的是对付他热爱的这块地皮的未来命运的反思。铁凝评价阿来,让人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穿越纷繁繁芜的信息与各式各样的不雅观点的年夜水,以文学的办法建立与中国的血肉关系,创造史诗的努力。诚哉斯言。
很多人以为阿来这种高产的作家一定都是在书房里奋笔疾书,实在不然。他热衷行走,喜好不雅观察,迷醉于勘探,沉吟于思考。阿来自言一贯是用“笨办法”创作,每部作品动笔前他都习气到当地去走一走、生活一段韶光,披星饮露,摩崖面壁。
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不雅观察、勘探、思考中,他不断地为自己的作品建立事宜的“现场”。正是在不断回溯“现场”的路上,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迎刃而解。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阿来不仅陷入巨大的震荡和悲痛之中,更陷入巨大的绝望和颓靡之中。很永劫光他不能从这种状态中规复过来。此后他便同身边很多朋友说,你们不要写关于这园地动的小说,由于我们写不了,没有任何想象力能让我们创作比现实更惨痛的虚构作品。然而,经由了10年的沉淀,阿来却食言了。“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那天,我溘然被一个细节触动内心,想起在地震中失落去的那么多生命,不禁热泪盈眶。我以为开写的时候,真正到来了。”
阿来凝神看孩子们画唐卡
也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不雅观察、勘探、思考中,阿来一气呵成写出了散文集《草木的空想国》。帕慕克说过:我们生平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个中的环境。阿来深以为然,他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有人认为这是狂妄的话,他却认为这是谦善的话。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善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于是,在一次病后的彻悟之中,阿来以草木为媒,写出了他的人生感悟,他将目光投向成都乃至马尔康的一千多栽种物,将它们从远得不能再远的背景中拉进时期的风云里。
在马尔康,阿来见证了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藏民族的寥廓宁静,见证了土司部落从富余、繁华、精细到贫穷、衰落、土崩瓦解的全体过程,见证了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也是在这里,他见证了那些暗香浮动、自然流淌的活气勃勃,见证了随着寒风而枯萎的花朵、随着年轮而老去的巨柏、随着韶光而荒凉的古老文明。阿来的目光,掠过高原,掠过天空,掠过河流,掠过冰封的大地,掠过凋落的光彩,然后——抵达不朽。
这便是阿来,他用温暖包裹起彻骨的寒凉,用锋芒挑落被华美尘封的沧桑,他是这个时期寂寞而执着的布告官。当然,我们从来未曾忘却马尔克斯的那句谶语:生命中所有的残酷,究竟都要用寂寞来偿还。
人物小档案
阿来:1959年出生。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写作诗歌,后转向小说创作。家乡河流的名字是第一本书的名字:《梭磨河》。后陆续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旧年血迹》《月光里的银匠》《格拉终年夜》《迢遥的温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瞥见》《草木的空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
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尘埃落定》《格萨尔王》《迢遥的温泉》和《云中记》等多部作品译为英、法、意、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数种措辞在外洋出版。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用度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