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名收藏家冯玮瑜又有新作面世。《藏富密码》一经出版,她系统收藏的明清御窑黄釉瓷再度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番禺得意堂见到她的时候,冯玮瑜刚从景德镇赶回来。她愉快地表示:终于看到了黄釉龙缸成品,便是太大了,自己扛不回来。原来,得意堂大厅里摆放的这些黄釉瓷,都是近两年来她联合景德镇名家打造的复制品、衍生品……
深入互换下去,进一步理解到,看起来优雅灵秀的冯玮瑜,身上竟潜藏着如此强大的爆发力和想象力——她于收藏之余写书、开讲座,更参与到黄釉瓷的传承性研发和石湾陶塑的开拓性创作中,以此来活化传统,表示出一位收藏家的文化情怀和当代视野,特殊值得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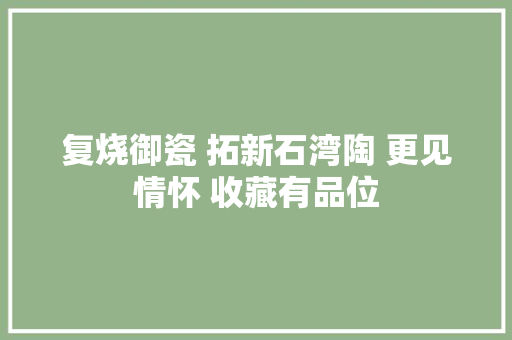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 江粤军、李巧蓉
复烧黄釉瓷,
调配颜色
是第一个拦路虎
提及复烧黄釉瓷,冯玮瑜表示,动机闪现于两年前她应某拍卖公司约请,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皇家气候”的明清御窑黄釉器个人收藏展。由于她作为内地私人藏家,首次以序列形式收藏和展出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展品来源清晰,流传有序,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是一个学术性展览,到场的不雅观众很多,有人想买点纪念品,创造什么也没得买,乃至连图录都没有,感到有些失落落。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开拓一些衍生品,让大家去分享这样一种文化?回来后,我开始找景德镇的陶瓷名家一起研发,只是没料到这么难。”
御窑黄釉瓷颜色很高等。唯其太高高在上,反而这个题材过去没人系统收藏,景德镇也没人复烧过。“由于存世量太少了。里外全黄的器物,明清皇宫里只有天子、皇后、皇太后才能用;到了贵妃这个级别,就只能等而下之,用里白外黄的;再往下的级别,不能用这种纯黄色,还必须加彩,譬如加绿彩、粉彩平分歧颜色。”
以是复烧黄釉瓷,调配颜色是卡在面前的第一个拦路虎。要人工复原当时的泥料釉料,要找到一个最得当的配比,把泥料淘炼得跟过去一样,必须反复试验,一次一次复烧。“当时的御窑非常严苛,所有进宫器物都可谓万中挑一,以我们现在的财力物力要达到当时的宫廷标准,相称有寻衅性。但我仍旧希望保持颜色不‘扮装’,只要有瑕疵就必须敲掉重来。虽然再补色很随意马虎就能掩蔽掉黑点,但那样就不是原生态了。”
同时,为了达到过去那种晶莹剔透的瓷质,冯玮瑜坚持用天然矿物釉料烧制。这样一来,成品率也会大打折扣。如果用稳定性强的化工釉料,只要把烧窑的温度曲线做好,基本能烧出来统一的、千篇一律的东西,合格率还能靠近百分之百。“但化工釉烧出来的颜色是实的,没有活性,灯光打得再好也不通透。”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旧藏清代康熙黄釉锥拱缠枝莲纹梅瓶被冯玮瑜拍得后,自然成了她的“心头好”。这件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浇黄釉锥拱缠枝莲纹梅瓶》来论证其为康熙御窑器,连故宫也没有同款收藏。该瓶器型挺立有力,肩部浑圆大气,满刻的缠枝莲纹几无败笔。
这样一件高端黄釉瓷,在冯玮瑜的“严苛”督导下,景德镇的师傅基本上做到完美复原。作品上的缠枝莲纹,靠暗刻浇釉烧制而成,必须刻得恰到好处,太浅太深都出不了效果,而且通体同等,对艺人的哀求很高。“一个很好的刻工,一个月只能刻两件作品,一旦烧坏了,就得从头来过。以是烧成十个往后,师傅们都说要歇一歇,太累了。”
还有小小的葵口杯,一打灯,就可以看到里面那些暗刻的条纹,一根根晶莹剔透,险些别无二致。便是这么一个鄙吝械,实在是上了十几二十几道釉的,每一次上釉,都要等它自然风干后再上一次……
而所有这些复制品、衍生品,冯玮瑜都会盖上她自己的印章,也不进行做旧,她便是想见告大家,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今人对前辈的礼敬。
对话冯玮瑜——
为了做秋瑾,我专门去了一趟绍兴
广州日报:听说您除了收藏明清御窑瓷器,也收藏石湾陶,一个觉得极为“阳春白雪”,一个觉得彷佛有点“下里巴人”,这个反差让人有点惊异。
冯玮瑜:我和我师长西席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们的上一辈就喜好收藏石湾陶。从小,我们就知道这是广东很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石湾窑在全国也是比较有名的民窑。事实上,石湾陶的艺术表现力是极强的,尤其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特殊能展现人物的内心天下,是其他材质无法替代的。至今我们的收藏基本沿袭了三个方向:一是明清官窑,但我紧张钻到了单色釉这一个领域;一因此岭南名家为主的字画;其余便是石湾陶。
广州日报:您大概收藏了多少件石湾陶?
冯玮瑜:至少有两三百件吧。2014年1月我在广东省博物馆做过一个专门的石湾陶艺展,画册里面收录的就靠近两百件了。
广州日报:您有没有特殊侧重哪一方面的题材?
冯玮瑜:石湾陶从瓦脊文化发展而来,以是过去基本以仙、佛、道为题材。人物性情也不是太光鲜,譬如过去大家做王羲之,阁下必定要做一只鹅,如果没有鹅,别人就认不出来那是王羲之了,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但本日如果还是重复这些的话,我以为没有太大意思。我希望能够收藏一些反响这个时期、展现人性光辉时候的作品。
广州日报:便是说您也会以藏家的身份去引领创作?
冯玮瑜:引领不敢说,我会融入到题材设计里面,和年轻陶艺家一起互助一些作品。画册中就有一些创作手稿,见告大家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东西,作品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譬如我很喜好历史人物苏曼殊、秋瑾等,都会希望陶艺家去考试测验。我会多方面找资料给他们做参考。为了做秋瑾,我乃至专门去了一趟绍兴,到她的故居拍了很多照片。还有一件董其昌的陶艺作品,由于我收藏了一件他的书法作品,我便想能有一个石湾陶将他的书法融入进去,这样我的收藏也打通了。
广州日报:您参与创作的作品,一件大概须要多永劫光才能完成?
冯玮瑜:肯定会比较慢,有的乃至两三年才出得来。这对陶艺家来说是不小的寻衅。我们也要找对人,不是每个陶艺家都乐意陪我耗的。石湾陶在最壮盛的时候,价格乃至比官窑还贵。虽然本日没那么火了,但陶艺家做出的作品仍旧不愁卖,走商业路线可以很快赚到钱。如果仅仅为了经济效益,不必要做这种打破。很愉快的是,不少陶艺家尤其是有美院教诲背景的年轻人,乐意为它注入新鲜活力,想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做些新的考试测验,提升自己,以是互助都挺愉快的。
《姐妹情深》衣服像大妈,纠结“换衣”复烧三次
广州日报:每一个创意您会哀求对方做几件呢?
冯玮瑜:手上基本都是原作。原作都只有一件。如果要翻模,必须将原作切开,那原作也就没有了。有时候作品出来的效果特殊好,陶艺家也会跟我说能不能翻模,一起互助分成,市场上肯定受欢迎。但我都谢绝了。由于翻模跟原作还是有差异的。翻模往后,还须要再精修,如果是少量翻模,作者还会亲自修一修面部表情,但如果要家当化,那作者是没办法独立完成的,只能是见告工人眼睛的位置、嘴角的地方该当怎么修。而石湾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真切,翻模出来的总归跟原作有差异。以是,目前我还没想过要迁就市场。
广州日报:您参与创作的作品中,有没有哪一件是您最满意的?
冯玮瑜:由于每一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哪怕是做出来我不太满意的作品,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比如说《姐妹情深》这一件,人物的神色特殊俏皮可爱,造型我非常喜好,但身上的衣服不适宜她们,穿得像大妈似的,给作品减分了。后来我们以为必须重新上釉复烧,而复烧作品很有可能就会烂掉。为了烧还是不烧,我们开了良久的会——不复烧的话,实在还是一件不错的作品,只是没达到我们想要的最佳效果;复烧的话,可能就没有了……这件作品复烧了三次,每一次都经由激烈的思想斗争。以是,只管终极出来的效果还是不足完美,但弥足宝贵。这件作品后来还做了画册的封面。
广州日报: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石湾陶创作中?
冯玮瑜:比较早了。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刚开始可能只是跟陶艺家讲一些观点、故事,逐步再从讲故事进一步到和陶艺家一起打草稿共同创作。以是,现在很难精确到某一个韶光点。紧张是我们这里离石湾也近,有韶光就会过去找一些陶艺家谈天,聊着聊着就进入状态,逐渐就深入下去了,这种觉得有点像过去文人墨客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很文雅、很享受的过程。
广州日报:的确是。紫砂壶由于有了文人墨客的参与,大大提升了它的品质,这对付提高石湾陶塑的文化秘闻也非常有帮助。
冯玮瑜:艺术创作本来便是精神迸发的产物,因此特殊须要互换,须要各种头脑风暴、不雅观念碰撞,才能涌现好作品;收藏虽然须要财力作底,同时更须要真正的热爱和投入,如果纯挚是投资,会损失掉很多乐趣。因此,我和石湾陶艺家们很合拍,大家都很欢迎我去。我对陶艺家有所帮助,同样,从陶艺家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我的创意是实现不了的,譬如窑温达到1300℃往后,我想要的那种形态就会撑不住,会崩掉,得换一种姿态或者表现形式。这个互动的过程很故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