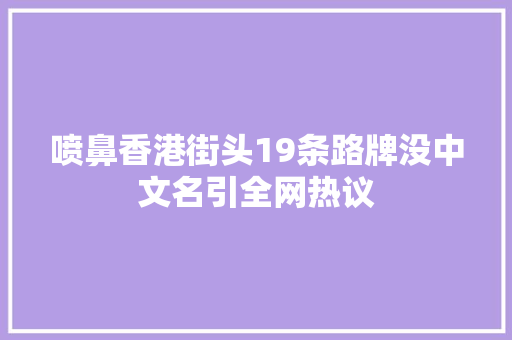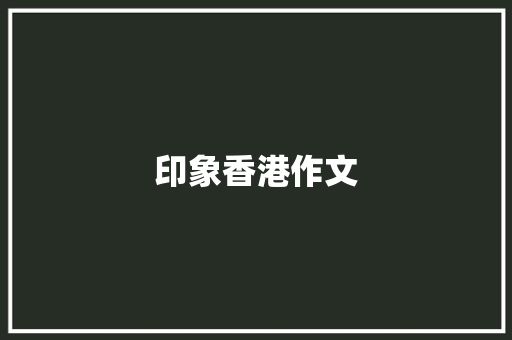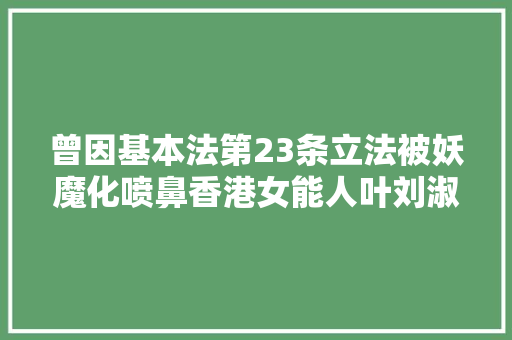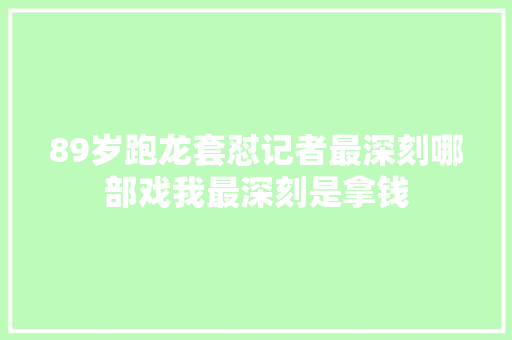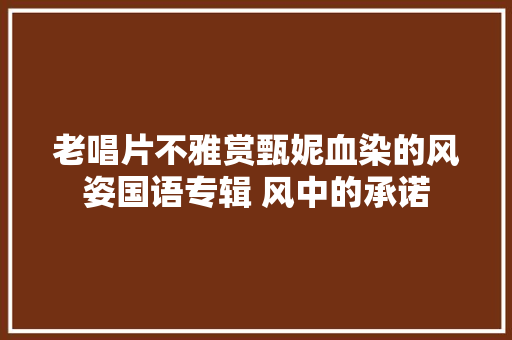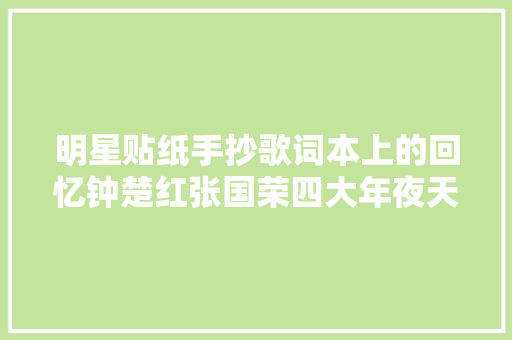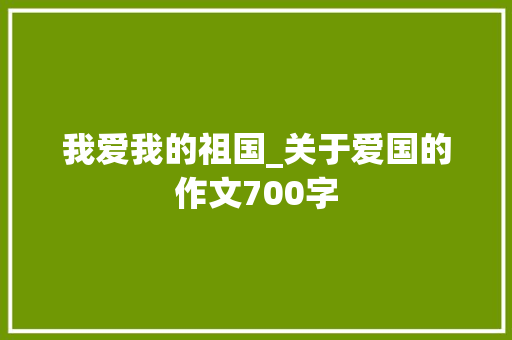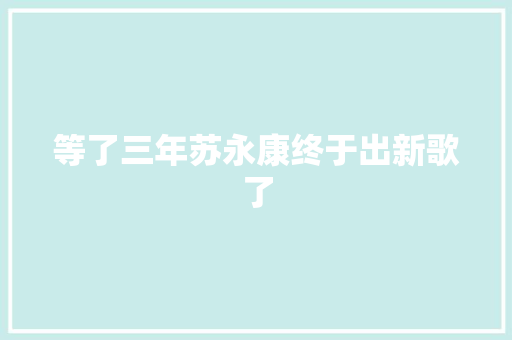他著作等身。他用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两广总督叶名琛》(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Kuang, 1852-1858;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思念他在牛津大学的已故博士导师 Mr Geoffrey Francis Hudson。他把Sun Yatsen: Hi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1987年版)献给双亲,把《孙逸仙在伦敦:三民主义思想探源,1896-1897》(联经2007年版)献给他在九龙华仁书院恩师罗伦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并借此思念蔡成彭师长西席、刘敬之师长西席、江之钧师长西席。他把《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广东公民出版社2016年版)献给他在华仁书院的大师兄林钜成医师,感谢他1963年以来赠医施药“恩同父母”的“再生之德”。
他是悉尼大学终生讲座教授,先后被挑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院、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他叫黄宇和。
黄宇和
“孤独仔”的苦难童年
黄宇和是穷苦人家出身。他的生日,护照上登记的是1946年11月29日。小时候大人叫他“和平仔”,说是抗降服利之后出生的,“宇和”即宇宙和平之意。不过母亲说他是猴年出生的,他印象很深,而猴年是1944年。以是他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年出生的。
黄宇和出生地倒是清楚的,跟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广东省番禺县石楼镇茭塘村落。父亲黄鉴波,1926年1月出生,排行第七。不幸的是,他的二哥三姐四哥五姐六哥全部短命。母亲陈慕贞,1926年2月出生于临近的赤江村落。黄宇和父母结婚时,父亲虚龄18岁,实龄大概16岁。祖父母均不识字,父母则粗通文墨。
茭塘村落是个单姓村落,全村落两千多口人都姓黄,共有四房。黄宇和家在二房宗族里是个小户,常常受陵暴,父亲就常常被恐吓说“淹去世你这个孤独仔”。在黄宇和的童年影象里,母亲家教很严,不许可他和村落里顽童一道玩耍,而父亲常年在外地谋生,偶尔回家一趟,过一两天又出远门了。黄宇和说自己从小缺少父爱,这也造成他独立、敏感的性情。
黄宇和记得,父亲一开始是在广州大同酒家当学徒,在那儿的烧味部学习烤鸭、烧乳猪、叉烧、白切鸡等技能。解放前夕,大同酒家迁往喷鼻香港,黄父也随之到喷鼻香港谋生,留下母亲在老家抚养儿子、伺候双亲。
黄宇和说,在番禺七八年的屯子生活,让他有一些村落庄社会的履历,理解屯子的风土人情。譬如,屯子很讲究孝道,父母健在,总得有子女照料。祖父在父亲结婚后,就不再与祖母同寝,目的是避免祖母有身,若祖母与媳妇同时生孩子,在村落民看来是有失体统的。还有,茭塘村落是禁止女儿外嫁的,并勾引她们“梳起”,黄宇和的大姑就终生没有嫁人。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事孙中山研究,频频到乡下做野外调查,理解孙中山童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以及祖籍源流等问题,很有帮助。
祖母、祖父去世后,母亲申请到喷鼻香港探亲,后来就留在喷鼻香港了。天故意外风云,正当母亲携两名幼子到了喷鼻香港,那家大同酒店关门了。父亲失落业,一家人彷徨得不得了。父亲应一位朋友的召唤,到该朋友原来任职的喷鼻香港上环集市阁下的新光大酒楼做烧腊,但有一个条件:每月只能拿200块钱的基本人为,顾客给的小费全部归这位朋友所有。当时的小费收入,比基本人为多两三倍。无奈之下,黄父只得答应,勉强可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母子只能寄居在外婆家。外公外婆有六个子女,她们住在九龙牛池湾一家斋堂里的一所偏厢。该斋堂是出家人住的,但她们穿便装,是佛家带发修行的姑娘,俗称斋姑。前来乞助的母子暂时就与外公外婆一家挤在一起。除了外公外婆有自己的床以外,别的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男的都挤在一张床,女的挤在另一张床,挤不下的就打地铺。
牛池湾位置偏远,当时是喷鼻香港大多数双层公交车的终点站。往东是牛头角,再往东翻山过去,便是专门栽种泰西菜(清凉菜)的穷山沟,地名叫官塘。再往东翻山过去便是鲤鱼门,即喷鼻香港维多利亚海港东边的入口,当时是很荒凉的地方。从港岛靠西的新光大酒楼所在的喷鼻香港上环到九龙半岛靠东的牛池湾,须要坐电车,转轮渡,再转公交车,实在是很远。加上住处狭小,也容不得再增加一个人了,以是父母虽然同在喷鼻香港,也只能两处罚居。
黄父在新光大酒楼烧乳猪、烤鸭子。如果碰上宴会,包括婚宴、寿宴、满月宴,根据喷鼻香港那时候的风尚,宴会可以举行三轮,第三轮凌晨一点开始。也便是说,办酒宴的话,就得忙到半夜一点钟往后才能收工。黄父夜里要睡觉,就把几张木椅拼在一起当作床铺,每天凌晨三点必须起来开始烤叉烧、烤鸭、油鸡等。由于从五点钟开始,酒楼阁下的上环街市,就有大批工人来吃早饭,饭后即开工。然后是中饭,一天到晚忙个一直。下午三点到五点,饭铺容许他离岗两小时,可以利用这个间隙安歇,黄父就蹲在酒楼某个角落里打盹。
黄父在喷鼻香港加入了工会——协德互助社。根据该工会的规定,凡是有事情的人每月必须安歇一天,这一天让没有事情的人来顶替。可是黄父也不能安歇,他要长途跋涉到牛池湾看望妻子和儿子。父子也就这样每月一次的见面机会。安歇当天,黄父早上起来,买一斤猪肉,走很远的路,带到牛池湾,这样一家算是改进炊事,每月有一顿饭有肉吃,有肉汤喝。
在外婆家寄居了一个月之后,母子三人搬到另一家斋堂,住在斋堂阁下的一间小屋里。那间屋子过去是用来养猪的。房东认为租给人住能发更大的财,于是在烂泥地上灌了水泥后,就出租了。猪屋非常矮小,放了一张床,就再也放不下其他家俬了。床是高下两层的,兄弟俩睡上层,母亲睡下层。由于空间太小,小孩子上床时也直不起腰,只能爬进去睡觉。夏天喷鼻香港热得要命,屋里就像蒸笼一样平常。平常都是坐在地上,伏在床上做作业的。用饭的时候,就移开教材,把饭菜放在床上。
黄宇和小时候吃的饭,是用碎米(便是机器蹍米时蹍碎了的,喷鼻香港话叫米碌)煮成的,掺杂着小石子、老鼠屎、蟑螂屎。本来便是商家很难卖出去的。只管这样,家里还是无法每次购买时就付钱,而必须由外公外婆做包管人,恳请老板容许记帐,到月尾父亲领到人为时,结算一次。穷汉的孩子早当家,黄宇和小小年纪就帮忙收拾家务,他每顿饭菜大概只有一毛钱的预算,用这一毛钱买一碗豆腐,或一把大芽菜,或者一些细芽菜,或一片晒干了的鱿鱼。早餐是没有菜的,只有酱油捞饭。那时候母亲去工厂做塑胶花,补贴家用。
在喷鼻香港上小学
黄宇和说自己在喷鼻香港念书的过程有点像孙中山,都跟教会有关系。他最初在茭塘村落上过三年多小学,同学都是同宗的堂兄堂弟,只有三两个外村落的同龄学童。到了喷鼻香港,他进了天主教会创办的牛头角庇护十二小学。从牛池湾到牛头角的公交车儿童票要一毛钱。家里没钱,黄宇和只能走路上学,这段路要走一个小时,然后花半个小时从山脚爬到山顶。到了牛头角山脚,看到同学们吃面包做早餐,他倾慕得很。由于学生很多,学校校舍不敷利用,就分成上午班、下午班,各有自己的校长和西席军队。黄宇和上的是上午班,中午十二点下课。同校的大部分学童都是赤脚上学的。放学回家后,他要打水、检枯枝烧柴做饭。
虽然以前在番禺乡下没有学过ABC,但黄宇和第一学期就考了第一名,可以免交下个学期的学费,学费要两块六毛钱。他到喷鼻香港上学后第一次打仗到基督宗教《圣经》,还是英文的。学校里有个小教堂,每周有两节圣经的课,个中一节要到教堂去唱圣诗,在那里接管宗教气氛的熏陶。很快黄宇和就受洗信教了。
小学五年级念到大约一半,黄宇和决定报考九龙华仁书院的六年级(华仁书院是一所中学,但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招生,以便招揽喷鼻香港的少年英才)。考试科目包括口试(看仪表教养)、口试(考英语流利的程度),朗诵一篇英语散文,主考官均由洋人神父担当。华仁书院是一所很好的男子中学,招收的学生都是精英。为了考进这个学校,有的父母不惜让儿子重复读六年级。黄宇和很努力,他考进了这所二战后改由耶稣会士管理和传授教化的书院。
这个期间,黄宇和一家已经搬到九龙老虎岩木屋区居住,那里完备是难民住的,一旦发生失火,十分危险。1960年代港英政府把木屋区拆了,把难民迁到官塘,官塘过去都是菜地,政府建了徙居区,房租要28元一个月,即是是超级廉租房。从官塘去旺角区的华仁书院上学,路途就更远了。黄宇和是一贫如洗的徙居区唯一一个在华仁书院上学的。
黄宇和在同学当中可以说是“鸡立鹤群”,用他自己的话,他成了同学的“眼中钉”。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巨室子弟,他们有司机接送上放学,而黄宇和在买不起公交车票时就走路上学,要花一两个小时,每次走到教室时都是大汗淋漓。同学们穿着锃亮的皮鞋,他穿的是一块钱一双的次货布鞋,穿久了脚板破了一个洞,就用厚厚的报纸垫着,以防伤脚。同学们都穿着俊秀的校服,黄宇和母亲就在地摊中挑了颜色附近的一套衣服,好在天主教重视教诲,校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扉页献词
中学的四位恩师
谈起华仁书院,黄宇和对个中的几位恩师深怀感念之忱。
没有这几位老师的教诲和帮助,黄宇和进不了喷鼻香港大学,此后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大有不同。他首先提到的是数学老师蔡成彭,“对我恩重如山”。蔡老师也是贫苦出身,少年时父亲离世,母亲抚养他终年夜成人,供他上学。以是蔡成彭老师读中学是跳班式的,唯读了中学一、三、五年级(喷鼻香港中学学制五年),毕业后考入师范学院,凭奖学金读了一两年就出来教书了。他的宗子比黄宇和大,教科书用过后,就传给黄。黄家的情状便是蔡老师见告江之钧老师的,江老师替黄宇和一家支付在官塘徙居区每月的房费,解除黄的后顾之忧。曾几何时,浩瀚老师听到诋毁黄宇和的谰言,对黄宇和持疑惑态度时,唯有这位蔡老师始终相信他笃学向上的意志。数十年后,黄宇和饱含深情地表示:“知我者,莫如蔡师。”
教国文的刘敬之老师也给黄宇和很多辅导、鼓励和帮助。那个年代的喷鼻香港,没有多少人乐意学中文,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黄宇和课余就去普通话夜校学习,同学都不理解,说他发神经。到了中学六年级(大学预科)时,刚退休的刘敬之以为这个小年轻有志气,便免费辅导他。每个星期天黄宇和都到刘老师家里去,学习古文,练习书法。到了中午,刘老师又留他共进午餐,这奠定了他的国学根本,让他受用终生。
江之钧老师紧张讲授英国文学,很有英国名流风姿。黄宇和在华仁书院读书,得到江老师很多帮助。
罗伦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可以说是黄宇和在泰西史方面的启蒙导师。她在1965年1—4月曾责任辅导黄宇和阅读英国史,教他如何剖析问题,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中国老师强调的去世记硬背完备不同。这种思维办法、逻辑辩证对他往后治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宇和说他能跳班考入喷鼻香港大学,罗老师功劳很大。
1964年夏天,全喷鼻香港举行统一的中学会考,黄宇和过关后连续在华仁书院念大学预科。预科要念两年,第一年(即中六)念普通科(Ordinary Level),第二年(即中七)念高等科(Advanced Level)。不幸的是,普通科念到一半,即1964年12月下旬,黄宇和获知新光大酒楼将在年底卒业,父亲再次失落业,百口一下子陷入饥饿的惶恐之中。当时家里积累下来的钱,哪怕买发霉发臭的米,也只能撑持四个月。在这种情形下,黄宇和有两个选择,一是用余下的四个月在校念完普通科(1965年5月1日开始考试),再找事情;一是在念普通科的同时,自修高等科——那时考大学须要先后参加普通科和高等科的测试。
喷鼻香港大学是当时喷鼻香港唯一的一所高档学府,对考生的最低哀求是通过三门普通科、两门高等科的考试,而黄宇和经由1965年1—4共四个月的奋战,在5月首先考了普通科三科,紧接着考了高等科三科。由于得到罗伦士夫人及刘敬之老师辅导,全部及格通过。就这样,黄宇和跳班(没有念中七)考进了喷鼻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九龙华仁书院文科中六、中七两级预科班考入港大的只有三位同学,个中之一便是黄宇和。
喷鼻香港大学
鲤鱼跃龙门:港大三年
1965年9月,黄宇和迈进喷鼻香港大学的大门。那一年全体喷鼻香港有20万中学毕业生,而喷鼻香港大学全部学系(包括医科、理科、工科、文科)合计共招200名,可见竞争之激烈。
进入大学,便是其余一个天地了。到了大学,修的科目跟英国一样。那时喷鼻香港的中小学是不教中国近代史的,这门课到了大学阶段才有。
喷鼻香港大学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乃至中文课当初也用英语讲授,由于早期的洋教授能看但险些不能说汉语,他们就像教外国人那样上课。黄宇和是从预科一年级直接考入大学的,成绩不是很空想,无法得到奖学金。他就申请文学院学生会一个免息的贷款操持,毕业后还贷。卖力贷款的学生会干事特意跑到官塘徙居区调查,创造黄家确实穷得叮当响,于是第一年就发放贷款。第二年,黄宇和考了两个奖学金,此后就不用贷款了。
在港大,黄宇和最初住在校外的一所天主教会青年宿舍,后来学校里面宿舍——卢格堂(Lugard Hall)——有床位,他就搬进去住了。夏天放暑假,其他同学回家学习、放松两不误,黄宇和回家则不能读书。一对来悛改西兰的夫妇,John McLevie 和Elaine McLevie。McLevie师长西席在港大教诲系任教,他就跟陆卢格堂舍监建议让黄宇和暑期连续住下去,舍监赞许了。这样,黄宇和可以利用暑假连续用功。第二年夏天,由于山体滑坡,卢格堂成了危楼,舍监就建议McLevie夫妇向大学堂(University Hall)舍监乞助,让黄宇和住进大学堂。大学堂是一栋古喷鼻香古色的建筑,冬暖夏凉。没有住所之忧,黄宇和又可以发奋学习了。
黄宇和坦言,由于有了这些居住便利,他才能在毕业前实现赴牛津深造的梦想。他说,能先后住进卢格堂和大学堂,证明他与孙中山有缘份。住在大学堂时,清晨在附近的薄扶林水塘阁下跑步;住在大学堂,清晨在半山的甘德道(Conduit Road)跑步时,脚下便是甘德暗渠。而1883—1886年孙中山在喷鼻香港读书时,喝的干净水正是薄扶林水塘储存、甘德渠勾引而来的。黄宇和由此溯源,并构建了他的“孙中山污水革命史不雅观”(详见其即将出版的《历史侦查》)。
此外,对付曾在港大有过集体住宿的经历,黄宇和在接管采访时表示,大学的团体生活跟他以前的独学鲜友很不一样。但他在港大除了却交曾钰成这位死活之交之外,至今只有两三位从华仁书院期间就交往密切的朋友。当讯问在港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时,黄宇和讲述的是其余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没有涌现辅导老师的身影。港大之于他,最大的好处是供应了一个自由阅读的环境,中文的、西文的,黄宇和迫在眉睫,手不释卷。
薄扶林水库
在牛津研究帝国主义
在港大读了三年(港大学制文科三年),第三年黄宇和申请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到了牛津,黄宇和才深切体会到港大与天下一流高校的差距。他说,那时候港大紧张传授教化办法是lectures,老师在教室上讲,同学记录讲义,老师开一些书目,同学到图书馆借阅;而牛津、剑桥紧张传授教化办法是tutorials,一位导师手把手教导一到两位学生。而黄宇和与其导师Geoffrey Francis Hudson,自始至终是一对一的,相互切磋谈论。
在牛津,黄宇和两年半韶光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便是后来出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在1968年去英国深造之前,黄宇和长期在喷鼻香港学习、生活,他深切感想熏染到被殖民的滋味。神父教导他要讲文明守规矩,碰到交通灯,红灯停绿灯行,但现实情形是,洋人常常穿红灯,根本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老师教导他买邮票要排队,洋人却不管这一套,随便插队。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黄宇和感到困惑:为什么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自身亲历的帝国主义,给黄宇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一探究竟。
但“帝国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他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个案,作深入的理解。有一天他看到一本书,个中一处提到“不战、反面、不守、不去世、不降、不走”的钦差大臣叶名琛。这个“六不”的骂名让黄宇和陡然生疑,堂堂封疆大吏竟然这么昏庸无能?从这个疑问出发,黄宇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终极他在英国公众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创造了一批原始文献。这些材料很多是用草书写的,都是文言文,里面夹杂着粤语方言,利用起来相称困难,而黄宇和正好是广东人,中六时私下跟刘敬之老师练过书法四个月(1964年9月—12月)、学过古文八个月(1964年9月—1965年4月),如鱼得水。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系统地用过那套文献。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黄宇和在牛津的博士导师是Geoffrey Francis Hudson师长西席,他从前专攻中东考古,后来治学兴趣有很大的转变。在黄宇和眼里,这位导师学问很广,虽然不识中文,但能别出心裁地看问题,把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看问题,给他很大的启示。 Hudson每周抽一个下午专门辅导黄宇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不仅如此,对付黄宇和研究过程中碰着的困难,比如他到外地调查,没有足够的旅费返回牛津,导师就年夜方解囊。Hudson为人谦善,品性清高,举手投足尽显英伦贵族的名流风姿。对付Hudson的培养,黄宇和充满感激,他在博士论文完成后对导师说,这本书将来出版就署我们合著,导师婉言回绝道:“不!
不!
那是你的劳动成果,我只不过是从旁赞助而已。”黄宇和感慨地说,他在喷鼻香港时对英国人恨之入骨,到了牛津则对英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显然Hudson师长西席便是他钦佩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造就的典范。
博士毕业后,黄宇和被挑选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研究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相称于美国的博士后)。他利用三年留校教书的韶光连续修正博士论文,197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付梓。两年后,黄宇和当选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2001年、2012年分别获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