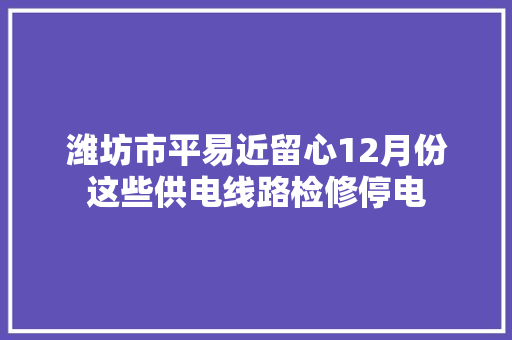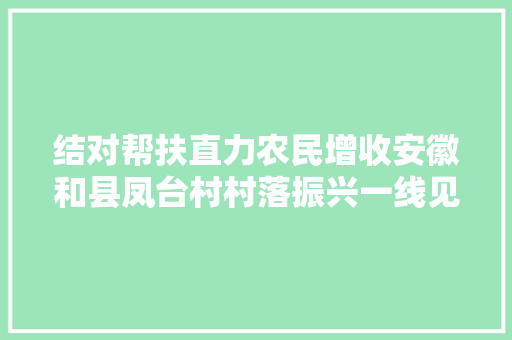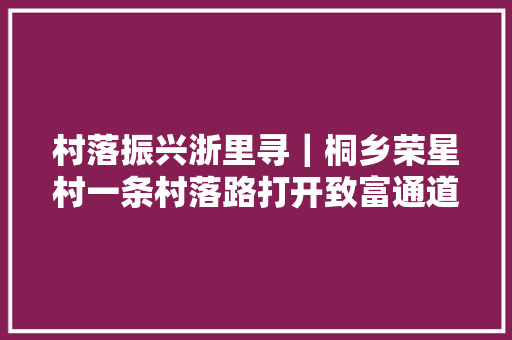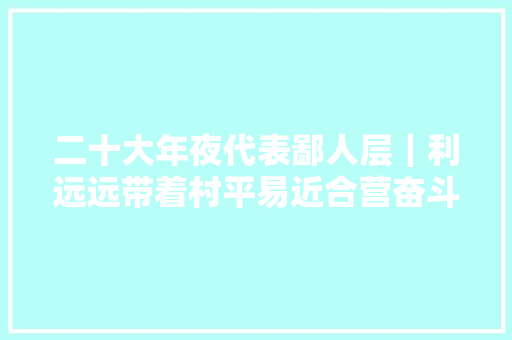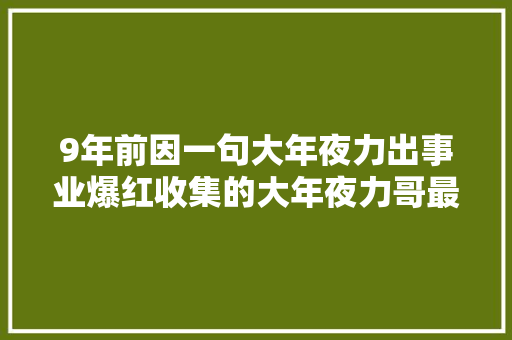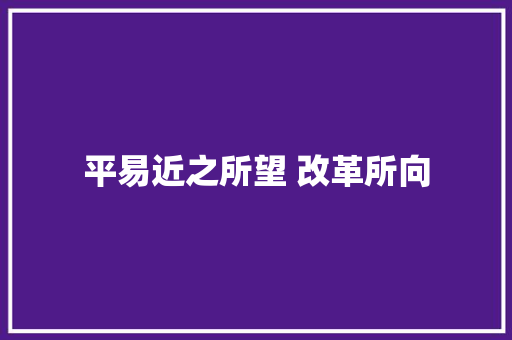怀安县朱家庄村落,一个闭塞的,仿佛与世隔绝、遗世而独立的小山村落。
这个古老的村落落,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村落落依山而建,三面环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阵势高旷,黄土坚实。站在村落落的高处俯瞰,全体村落落尽收眼底,山坡上一排排的土窑洞,断垣残壁,既悲壮苍凉,又蔚为壮不雅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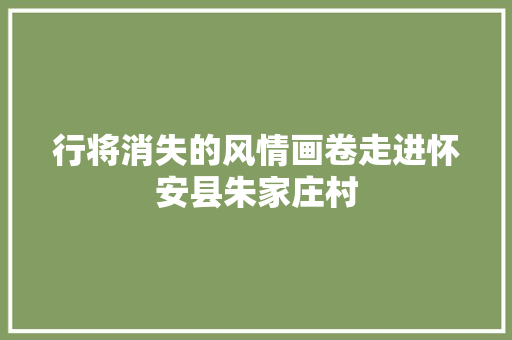
这一排一排的土窑洞,便是人们所说的“怀安碹窑”,历经风雨,年久失落修,或坍塌,或破败,仅少数有人居住的保存还算无缺。
陪我采访的村落党支部布告张余成说,全村落除了小学是瓦房外,剩下的全是碹窑,共599间,最多时曾住有900多人,现在,村落里就剩100多人,窑也大都闲置了。
看着这些残破的碹窑,我一下子想到了“寒窑”这个词。一问,果真,这些窑都是贫穷百姓居住,富余人家少有住的。
怀安历史悠久,但居于南北交界处,自古以来为战役所困扰,是贫穷掉队之地,有钱有势之人险些不在此定居。当地百姓农耕为生,为理解决生存须要,就地取材,发明了“土碹窑”。根据民国23年的《怀安县志》记载,怀安境内有村落落323个,村落落名字中含有“窑”字的就有60多个,足见当年的情景。
和其他地方的窑洞相差异的是,“怀安碹窑”不仅是土碹窑,而且是平地起窑。
张余成说,建窑并不太难。碹窑从和泥、抹泥板子开始,“挖来黄土掺点稻草,做成泥坯,干透后,就着木匠师傅做好的一个拱形木头模子,就像燕子垒窝一样,开始搭建,先建后墙,再由左到右,碹成门洞,末了配置门窗,确保光芒充足,满室通亮。碹窑建好后要保养。头几年,窑顶要除草,再夯实,以免长草。每年秋收后,可以在上面堆放玉米秆,晒葵花籽,晒玉米等。”
“怀安碹窑”大多是三间,即一窑三孔构架,中间一孔为正窑,两侧分别为配窑,作起居室和炕室。炕室必配一炕以取暖和,本地谚语有“家暖一盘炕”的说法。三间碹窑一样平常一间宽⒉5米,深6米,高4米多。
走进碹窑内,这无梁之殿让人慨叹:不用一砖一瓦,不需一梁一椽,仅靠坚实的黄土,就可以居而有其屋,难怪有人称道:“碹窑是黄土建筑文化中的奇葩,是天人合一的践行,是力学事理的诠释。”
碹窑的空间显得逼仄,人一多,就挪不开身。空间狭小还不是碹窑最大的缺陷。碹窑最怕水,如果夏季雨水多,土墙受潮,就有坍塌的危险。在村落民张爱家,他指着墙上斑驳的水渍说,这便是前些年下大雨时留下的痕迹,夏天房顶得用塑料布遮盖,要不就会漏雨。
74岁的张爱和老伴居住的是三孔碹窑,整顿得干净整洁。小院不大,种有几畦青菜,一些花草,绿油油的,平添了许多活气。精神矍铄的张爱说,他们有4个孩子,但都已离开村落落,在外事情。老两口每年会到城市里跟孩子们住一段韶光,然后再回村落居住。“习气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离开了就想得弗成。”
“我们的村落落快要消逝了。”张余针言带凄凉。他说,村落庄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事情或者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自己今年59岁,是村落里最年轻的人。原来,村落里有小学,还能听到孩子们的欢笑,有些生气,现在,随着小学的迁居,孩子们也走了,村落里整天暮气沉沉的。“哎,是真正的老人村落。”他喃喃自语,“现在有老人在,过年时,孩子们还惦记着回来看看,等老人们过世了,这村落庄可不就没有了。”
我们在一座久无人住的碹窑前停下脚步。这窑已经十分破旧,窑洞顶上长满了杂草,墙体的黄土斑驳不堪,窑洞木门上的油漆早已淡褪,迂腐的木窗下缭乱放了几捆木柴,最右边的一个曾经堆放农具的窑洞,已经坍塌。“没人整顿,逐步都会变成这样的。”张余成说。
在外来人眼里,朱家庄古朴、安谧,像田园诗一样平常浪漫美好。可在朱家庄村落的村落民眼里,这里的日子并不惬意。地里只能栽种谷黍、土豆、玉米等,村落民靠天用饭,土坷垃里刨食,一年费力,换不来几个钱。毛驴是这里的紧张交通工具,村落里的路有一层厚厚的浮土,驴车碾过,扬起一片尘土。
“岁数大了,走不出村落落了。”跟张爱一样,有孩子在外的老人,不习气表面的生活,总是眷恋生养自己的地皮。他们喜好聚在村落口的大杨树下,聊聊景象,聊聊收成。他们的生平,始终与泥土相伴。走得再远,也要落叶归根。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碹窑,已经成为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栖息地,无论世间若何沧桑和变幻,他们一往情深。
伫立在这片黄地皮上,一眼险些可以望穿几代人。高山、黄土、窑洞、毛驴,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时期变了,年轻人不知足于住在窑洞里,他们有梦想,神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是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家乡,离开窑洞。这是历史发展的一定趋势,没有谁能够阻挡。
碹窑折射着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厚重历史文化,如今它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濒危的居住文化遗存,保护的事情实在是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