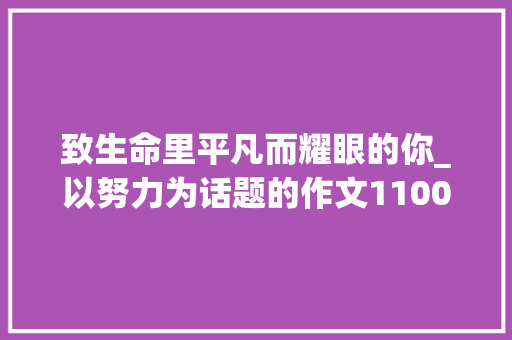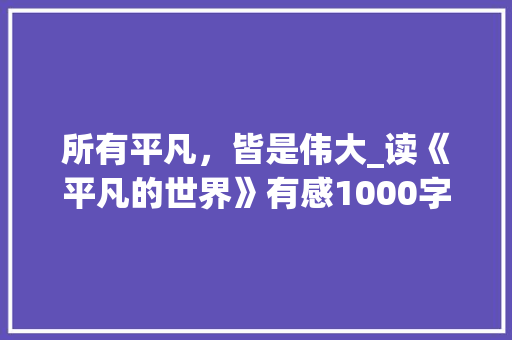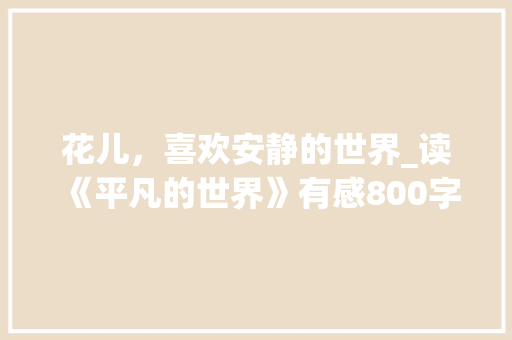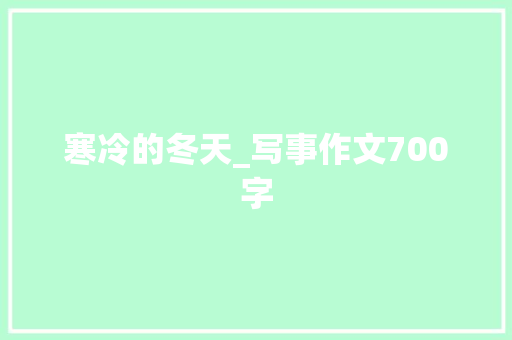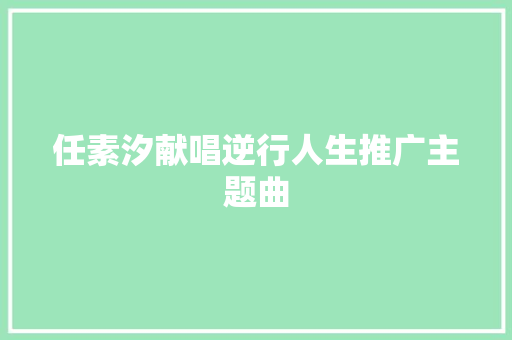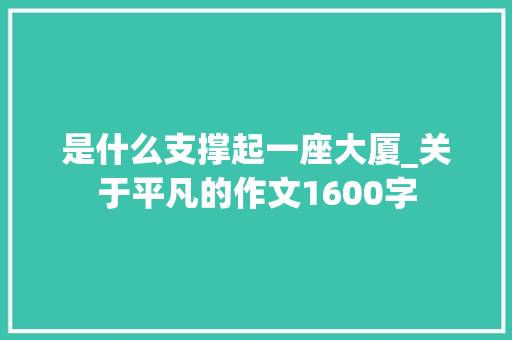“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1982年5月,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刊发于《收成》第3期。这部小说从萌生写作欲念到终极完成历时近三年,深入描述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命运选择。《人生》甫一刊出,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环绕“人该当如何生活”的旷日持久的谈论就此展开。这一谈论差不多可以视为发轫于1980年且搅动一代人精神的“潘晓谈论”的延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空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间隔,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等话题被频繁提及,引发年轻人在“祖国命运和人类出息”的意义上思考人生选择。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咭片子《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响持续发酵,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路遥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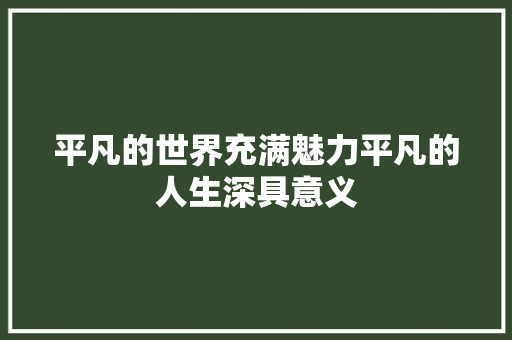
1988年,思虑中的路遥郑文华摄
路遥(左一)在铜川煤矿采访何志铭摄
2015年版电视剧《平凡的天下》剧照
小说《人生》揭橥之后,我的生活完备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评论辩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各类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节制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纭向我求教:“人该当若何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备被淹没了。其余,我已成了“名人”,亲戚朋友们纷纭上门,不是要钱,便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事情,彷佛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
路遥并不谢绝“鲜花”和“红地毯”,他也因自己长期牛马般的劳动换来了“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但对具有极强的自我反思能力且有更大抱负的路遥而言,绝不可能长久沉溺于这种“广场式”的生活,重新投入沉重的劳动,或许更能让他感到生活的充足。更何况,这个时候,已经有人认为《人生》是路遥写作“无法超出的高度”。路遥显然不认可这一论断,而回应这种论断的最好的办法,便是创作出真正具有个人写作打破性的主要作品。
创作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欲念就此萌发。这一部尚处于想象中的作品,即便不是他“此生最满意的作品,也最少该当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便是后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天下》。
为这部想象中的作品,路遥开始了艰巨且漫长的写作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艺术”和“生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路遥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内外的主要长篇小说。海内以《红楼梦》和《创业史》为重点。这也是路遥第3次阅读《红楼梦》,第7次阅读《创业史》。此外,他还广泛阅读了各种“杂书”,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等专门著作。而为理解作品所涉的1975至1985年这十年间的各种主要事宜,他集中阅读了《公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等报刊的全部合订本。这个事情完成之后,路遥再度“深入生活”——已然熟习的生活“重新到位”,不熟习的尽快熟习。路遥提着装满书本资料的大箱子奔波在村落庄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理解上至省委布告、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形,熟习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内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年夜小靡遗的生活细部,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
此后,路遥开始了长达3年辗转于铜川陈家山煤矿、从陕西作协临时借来的小房间、新落成的榆林宾馆、甘泉县招待所等地的艰巨而漫长的写作。对付视创作为一种劳动,坚信唯有持续不断的劳动才能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精神成果的路遥而言,永久不损失普通劳动者的觉得,像牛一样劳动、像地皮一样奉献,乃是当仁不让的选择。正是在充足的劳动中,个人的生命得以圆满。统统如歌德所言,对付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快的人,创造本身便是一种幸福。这是有追求的作家的任务、义务和代价所在。
在准备和正式写作《平凡的天下》的6年间,路遥险些捐躯了全部的个人生活,他与全体文坛彻底隔绝,无法与父母妻女共享明日亲之乐,乃至不能在养父病危和离世之时略尽孝道……永劫光的离群索用心系一处,便是为了倾生命之全力完成《平凡的天下》。生活的极度艰巨、生命的过度损耗,乃至是去世亡的威胁也不能阻挡他奋进的步伐。在内心极度孤独分外渴望家人和朋友的温暖时,等待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老鼠。
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天下》终于完成,路遥为此书的写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英年早逝显然与此密切干系。
“鉴于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
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天下》无疑是路遥此前生命履历和艺术履历的融通和汇聚,包含着他超越“新期间”的潮流化不雅观念,从延安文艺的基本传统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时期和生活的“深奥深厚的历史不雅观”。这种历史不雅观表现为对延安文艺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潮流的内在连续性的贯通理解。路遥的文学不雅观和天下不雅观,扎根于个人的生活和生命履历,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不雅观初步形成期间,即与“公民文艺”及其根本的代价关怀密不可分。此后虽有不同程度的调度,但在总体性意义上反响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公民伦理为根本塑造时期新人,坚守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核心却一以贯之。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求“新”与“变”成为文学不雅观念的潮流。“现实主义过期论”一度甚嚣尘上。因此,自《平凡的天下》第一部写作完成至路遥逝世后多年,路遥和他的《平凡的天下》始终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这便是关于《平凡的天下》的评价问题。
从萌发《平凡的天下》的写作欲念到该书第一部写作完成的近4年间,路遥无暇顾及文坛风潮的变革。然而要考虑作品揭橥、出版的刊物、出版社时,路遥险些是惊惶失措线面临着来自“日月牙异”的文学潮流的巨大打击。
先是《当代》年轻编辑周昌义的婉拒,再是作家出版社的退稿。二者险些有着同样的逻辑,也从侧面表明路遥的文学不雅观念在1986年的时期语境中,“被迫”有着“反潮流”的独特意味。
时隔20余年后,已有悔意的周昌义以“记得当年毁路遥”为题,回顾彼时他最初阅读该书第一部时的感想熏染:“还没来得及冲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觉得便是慢,便是琐碎,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猜想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造成这种阅读感想熏染的缘故原由,是当时的文学潮流:
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盛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盛行当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迫在眉睫,不仅要读情绪,还要读新思想、新不雅观念、新形式、新手腕。那些所谓的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
周昌义的如上反思与作家出版社编辑认为该作“不适应时期潮流”,属“老一套的‘恋土’派”的不雅观点一模一样。他们的见地,均指向《平凡的天下》的不雅观念和写作手腕,其核心是对文学的代价和意义的不同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的转型阶段,《当代》曾给路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若无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对其首部中篇小说《触目惊心的一幕》的欣赏,并在此后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其文学不雅观念和写作手腕,其时尚处于写作不雅观念转型期的路遥或许不能武断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决心。而此番以现实主义文学重镇著称的《当代》的退稿,无疑对路遥打击甚大。令路遥始料不及的是,第一部在《花城》揭橥之后,是年冬在由《花城》和《小说评论》共同主理的《平凡的天下》(第一部)北京研讨会上,路遥及该作遭遇了更为剧烈的“批评”。
这次会议约请了朱寨、廖俊杰、何西来、雷达、蔡葵、曾镇南、白烨、王富仁等当时最主要的文学评论家,阵容可谓强大。会议纪要后来以“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为题刊发于《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虽在结尾处述及部分与会专家对该书的多少见地,该纪要仍以充分的、高度切实其实定为核心:
漫谈会上,评论家们给予小说以这样的总体评价,认为《平凡的天下》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屯子生活全景性的图画。
然而,在路遥好友白描的笔下,这次研讨会呈现的是另一番样貌:“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落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落败的长篇小说。”
面对这样的评价,路遥表面淡定,但内心想必悲愤交织。回到西安后,他特地前往位于长安县的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永劫光,猛地跪倒在墓碑前,放声大哭”……
北京研讨会后不久,《小说评论》《花城》等杂志相继刊发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天下〉(第一部)》、丹晨的《孙少平和孙少安》、李健民的《从现实和历史的交融中展现人物的心态和命运》、李星的《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天下〉》等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该作的思想代价和艺术造诣。尤其是曾镇南一反其时唯“新”是举的批评潮流,高度肯定《平凡的天下》“守‘旧’持‘常’”乃至“‘土’得掉渣”的特色,认为该作已经显露出作者“概括广阔而繁芜的时期征象的不平凡的艺术魅力”,“不仅是一轴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社会历史画卷”,还是“一部荡气回肠、内涵丰富的人道命运交响乐”。他还充分肯定了该作所采取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镇南的评论,已经涉及《平凡的天下》的思想代价和艺术造诣等多个方面。此后评论界对该作的剖析,路径和侧重虽有不同,但核心不出曾镇南文章所论的基本范围。无奈这些声音一韶光并不能转变文学潮流巨大的裹挟力量。《花城》在刊发该作第一部后再无后续,第二部并未在文学期刊揭橥,第三部则在较之《花城》更为“偏远”的《黄河》刊出。如上各类,均解释路遥和《平凡的天下》,面临着巨大的评价危急。
对如上问题产生的缘故原由,数年后路遥有这样的阐明:除文学形势的转变以外,第一部故事尚未有充分的展开,遑论巨大高潮的涌现。评论界的保留见地,在预见之中。近两年之后,三部全部出齐,又过了四年,路遥逝世。在此期间,《光明日报》刊发蔡葵的《〈平凡的天下〉的造型艺术》,《文学评论》刊发李星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艺争鸣》刊发白烨的《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天下〉》。李继凯撰写的四万余字总论路遥创作的长文《沉入“平凡的天下”——路遥创作生理探析》也在路遥逝世前完成。另有多篇关于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的主要文章肯定路遥和《平凡的天下》。只管如此,《平凡的天下》仍旧未能改变其被文学史“遮蔽”的命运。在多部主要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平凡的天下》始终是“在”又“不在”的——屡被提及,然而其作为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适可而止的阐释。虽未亲见《平凡的天下》所遭受的文学史“冷遇”,路遥其时仍旧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致蔡葵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其时批评界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冷漠态度并不正常,由于“我们和缺少当代主义一样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而“鉴于我国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数年后,路遥再度申明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缘故原由:“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往后相称长的时期里,现实主义仍旧会有发达的生命力”,由于“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紧张该当是一种精神”,更何况,“稽核一种文学征象是否‘过期’,目光该当投向读者大众。一样平常情形下,读者仍旧接管和欢迎的东西,就解释它有情由连续存在。”此前一年,《平凡的天下》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位居榜首。此后近30年间,该作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一贯位居各大阅读调查榜前列。如上各类,充分证明了路遥的远见,“现实主义还是有广阔的改造前景”,也再度表明基于公民伦理的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代价。
“无论是县委布告、大学西席,还是工人、农人,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看《平凡的天下》”
真正改变《平凡的天下》第一部揭橥之后冷遇的,是由中心公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同名广播剧。说来竟是有时,1987年春,路遥前往北京办理出国访问干系事宜,为方便与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同乡好友海波见面,路遥住在鲁迅文学院招待所。某一日外出办事返回招待所时,在无轨电车上偶遇中心公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编辑叶咏梅。叶咏梅曾在陕北插队,还曾在《陕西文艺》演习,从前即与路遥交往甚密。在拥挤的车厢里,叶咏梅一眼就认出了路遥。她问他为何近年杳无音信,近期在写什么作品?路遥憨笑着回答她,写一部《平凡的天下》。叶咏梅再问,你以为写得若何?或许因北京研讨会所致的生理阴影并未散去,路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并送一本请叶咏梅自己判断。曾将《人生》改编为广播剧的叶咏梅从《平凡的天下》中,体会到路遥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并唤起了在陕北插队的回顾。她决心将该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再度回到普通劳动者中间。叶咏梅还专程前往陕西采访路遥,深入理解《平凡的天下》创作过程中的各类情形。该剧由对广播有个人独到理解的青年演播者李野墨演播。李野墨大胆采取了一些极富创意的表现办法,为该剧增色不少。
1988年3月27日,广播剧《平凡的天下》开始在中心公民广播电台播出,直至8月2日播送完毕,历时4个月有余。可以说,它改变了《平凡的天下》的命运。该剧播出之后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谈论,几近数年前电影《人生》放映之后的轰动效应。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动情地评论辩论他们的感想熏染。有人认为《平凡的天下》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饱含着对祖国、对公民的爱,表现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听众们敬佩路遥“敏锐的不雅观察力”以及“对人类之爱的强烈追求”。
广播剧的热播带动了小说的销量,先前第一部印数仅三千册,且险些无人问津,甚至任务编辑压力甚大,不承想广播剧播出之后,该书数次加印仍供不应求。一年后,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央拍摄的14集同名电视剧在中心电视台播出,使得该书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平凡的天下》电视剧播出时,作家王安忆正拿着路遥给的一摞“路条”行走在陕北,险些每到一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评论辩论《平凡的天下》。“每天吃完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时”,“无论是县委布告、大学西席,还是工人、农人,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如果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天下》。”虽因各类缘故原由,该剧未能展现小说的全貌,但仍旧不失落为一部有艺术品质的作品。它的主要代价还在于,推动和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2015年,56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天下》播出。此时间隔小说全部写作完成已近30年,间隔路遥离世已有20余年,该剧仍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发了新一轮的不雅观剧热潮。这解释,时隔多年,《平凡的天下》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仍旧活在普通劳动者中间,并且还将一贯活下去。
被《平凡的天下》照亮的人生
1992年11月17日,路遥永久离开了这个他活过爱过也写过的平凡的天下,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但他不息的奋进精神和以生命为代价创造的劳动成果,仍旧活在普通劳动者中间。他以巨大的激情亲切关怀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以友爱和同情温暖那些尚处于奋斗中的孤独的个人。他使他们即便身处现实的冰冷之中,也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他勉励他们:“只有冒死事情,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落也是壮丽的凋落。”他见告他们劳动和奋斗着的生命是幸福的。他还以道德和生命的空想之光照彻生活暂时的暗夜。他爱他笔下的平凡的劳动者。这种爱也得到了普通劳动者积极而持久的回应。这些普通劳动者年事互异、职业不同,他们或身处学校、工厂、临时搭建的工棚内,或在任何一个城乡交叉地带,虽身处困境却为空想默默耕耘努力奋斗。支撑他们的,始终因此艰巨奋斗开启美好人生的素朴的空想——这空想也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精进力量内里相通。
2019年9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期精神”而被付与“最美奋斗者”名誉称号。他的《平凡的天下》“勉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发奋图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期年夜水”之中,在献身集体奇迹的同时充分实现个人代价。这也是路遥文学不雅观念的要点所在: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奇迹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劳动才能变得有代价。为此,作家该当永久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态度上,理解他们,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反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意志,同时也用自己的笔丰富和提升他们的精神天下。
由此,他和那些仅仅关注个人的情绪体验,拘泥于一己之悲欢的写作拉开了间隔;和疏离于正在行进中的日月牙异的现实生活,一味凌空蹈虚不着边际的写作有了区分;他还和那些极力铺陈天下的阴郁面的另一种观点化写作大相径庭……由于,对付一个严明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任务感都是主要的;还由于,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便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平凡的天下》因此成为普通劳动者的枕边书,成为他们励志的宝典,成为他们须臾不离的精神的寄托。他们的生命因《平凡的天下》的存在而变得不同。也因此,30余年来读者大众的阅读热度始终不减。万万千万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的青年人,他们的人生因《平凡的天下》和路遥而被照亮:
——这个虔诚的文学圣徒,用他生平的文学创作和精神力量,为一代人的发展和奋斗源源不断地注入着营养。在他身后,读着他作品发展起来的一代人,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的时候,都在心里为他留着一块净土,建筑起一座精神的纪念碑!
——最让我冲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巨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他常常在我碰着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战胜它并年夜胆地走下去。
——当我重新读着《平凡的天下》的时候,我创造我还可以冲动,我还可以从平凡中读出高尚。我还可以有梦想……我依然还有生活的激情亲切。
《平凡的天下》内蕴着“崇高的纯挚和静穆的伟大”。它让那些普通劳动者相信,平凡的人生深具意义,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内在的代价和肃静。无私奉献努力奋斗的普通生命也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只要天下奋进的力量不息,那些如孙少平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就仍须要《平凡的天下》,须要被不息奋进的力量唤起,去追求美好人生代价的实现。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1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