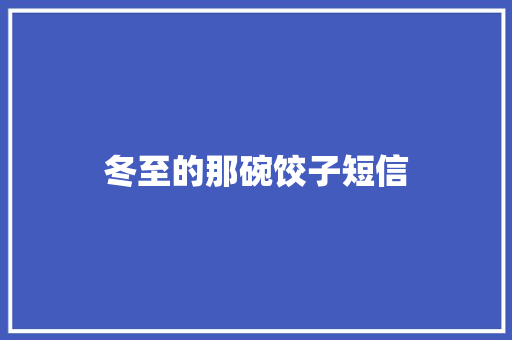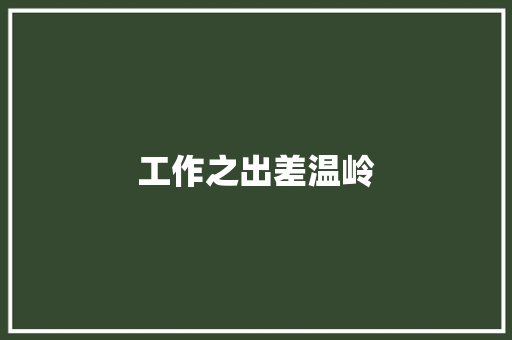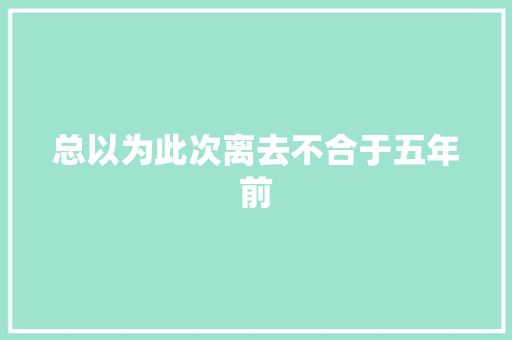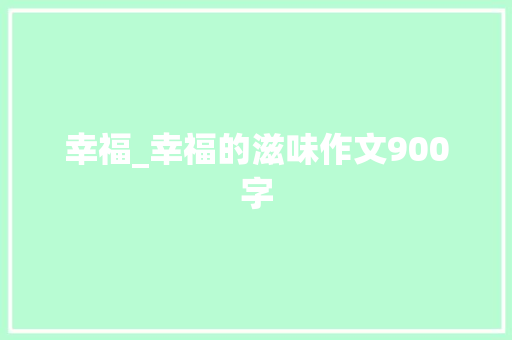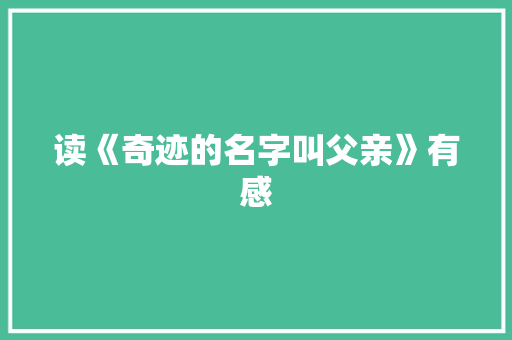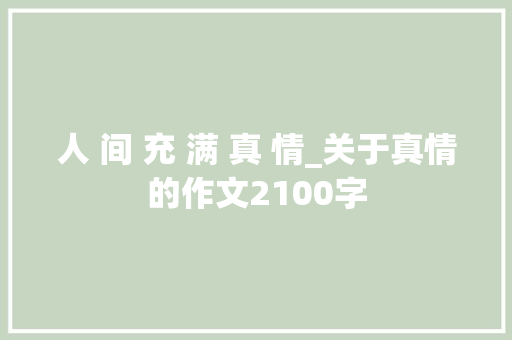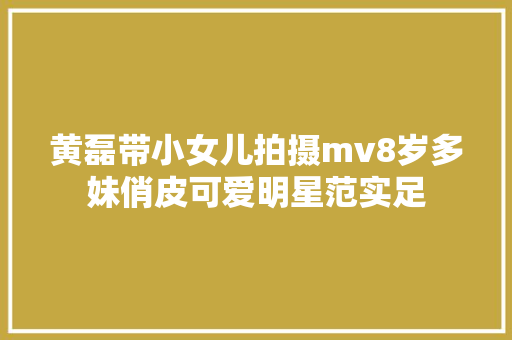古代家谱一样平常不会登录女儿,吴孟复《梅尧臣年谱》所依据的《梅氏世牒》就没有记载梅尧臣女儿的资料,年谱中的干系信息来自欧阳修所撰的《梅圣俞墓志铭》。《墓志铭》载:“(梅尧臣)初娶谢氏,封南阳县君;再娶刁氏,封平恩县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埛,曰龟儿,一早卒。女二人,长适太庙斋郎薛通,次尚幼。”梅尧臣有五男二女,有一子早卒,以是尚有四男二女。这个早卒的儿子,梅尧臣集中有《书哀》《悼子》等诗,对其追思吊唁。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太庙斋郎薛通,一个在梅尧臣去世之前,年纪尚幼,待字闺中。实际上,梅尧臣集中还提到一个早逝的女儿。欧阳修《墓志铭》只记录早卒的儿子,却未提及这个女儿,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女性既在家谱的普遍缺席,过早夭亡乃至让她们在父亲的墓志铭缺席。好在梅氏集中多有记录,这就给我们重新考索的空间。女儿入诗,实在有源远的传统,最为有名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到了宋代,对女儿涉笔最多最早的士人,无疑要推梅尧臣。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不难厘清梅尧臣三个女儿的信息。

大女儿十九岁嫁给了薛通,梅尧臣《送薛氏妇归绛州》有言“看尔十九年,门阃未尝履”。这首诗写于嘉祐元年(1056),梅尧臣已经五十五岁。由此可以推知,宝元元年(1038),三十七岁的梅尧臣和第一任妻子谢氏生下大女儿。庆历四年(1044),谢氏去世,梅尧臣写有《悼亡》一诗。据欧阳修《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所载:“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阳县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邮。”大女儿即谢氏三十一岁时所生,在其七岁时,亲生母亲就与世长辞。
庆历五年(1045),梅尧臣《史尉还乌程》,个中有曰:“七月行丧妻,是月子又去世。买棺无橐金,助贷赖心腹。娇儿昼夜啼,幼女饮食止。行路况炎蒸,悲哀满心耳。青铜不忍照,干瘪邻于鬼。八月至都下,少长疾未已,一婢复嗑然,老媪几不起。”诗中的“幼女”便是大女儿,这时年仅八岁。欧阳修所说谢氏有两男一女,个中一男(小名十十)在这年七月离开人间。嫡亲之人在两年之间相继拜别,对梅尧臣可以说是双重打击。梅尧臣《悼子》言其丧妻丧子的惨状甚为悲切,“前时丧尔母,追恨尚无及,迩来朝哭妻,泪落襟袖湿。又复夜哭子,痛并肝肠入,吾将仰问天,此理岂所执”,结尾呵问彼苍,天下岂有此理。然而恶运还在降临,家中老小生病,奉养的仆人有的放手凡间,有的卧病不起,生活犹如一个烂摊子,竟不知从何整顿。
朱东润著《梅尧臣传》书封
二
就在这一年,欧阳修的女儿欧阳师短命。梅尧臣在开封因船只搁浅,延误行程,听到后写诗抚慰欧阳修。《开封古城阻浅闻永叔丧女》曰:
去年我丧子与妻,君闻我悲尝俛眉。今年我闻君丧女,野岸孤坐还增思。思君平昔怜此女,戏弄膝下无不宜。昨来稍长应慧黠,想能学母粉黛施。多少很多多少恩爱付涕泪,洒作秋雨随风吹。风吹北来沾我袂,哀乐相恤唯己知。自古寿夭不可诘,天高杳杳谁主之。以道为任自可遣,目前况有宁馨儿。
两人是亲密好友,生活碰着不幸总会相互安慰。从其阐述来看,欧阳修平时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含饴膝下,有过许多欢快。女儿八岁短命,欧阳修与其相互陪伴的韶光不长,但也不短。梅尧臣能够理解其心情,不仅是因去年体会到嫡亲之人拜别的悲痛,可能还由于梅尧臣的大女儿与其同龄,同样都是八岁。诗中所言“想能学母粉黛施”,大概是根据其女儿学母扮装的发展日常,悬想同龄的欧阳师应是如此。可是欧阳修的女儿夭亡,梅尧臣女儿的生母也去世。两个家庭,扮装的学习者和被学习者都少了主要一环。人生无常,天意难问,寿命是非到底由谁掌握,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些彷佛难以得到准确的回答。梅尧臣让其节哀顺变,以道自任,或容许以排解丧女的沉痛,毕竟上天并没有做绝,膝下尚有这样值得疼爱的小孩。欧阳修此时还有六岁的儿子欧阳发,且在这年又诞下了欧阳奕。这应是梅尧臣诗中所说的“宁馨儿”。
欧阳修丧女之后有《白发丧女师作》《哭女师》等诗,前诗曰:“吾年未四十,三断哭子肠。一割痛莫忍,屡痛谁能当。”欧阳修庆历五年为三十九岁,未满四十,但连遭一男二女的短命。男孩是第一任妻子胥氏所生,在欧阳修三十二岁的时候短命。欧阳师是长女,其后欧阳修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次女出生不久就夭亡,乃至都来不及给她起名。欧阳修疼爱长女,可能由于这是唯一的掌上明珠,但也没能逃脱命运的戏弄。欧阳修晚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然而又是因病夭亡,五十八岁的他再次痛失落爱女,虽无名字,但朝廷后来赐封此女为乐寿县君。欧阳修生平共有三个女儿,其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在世韶光最长,且有名字留存的长女。这在《哭女师》有真切而动人的描写。
同样在这一年,谢景初生了女儿,梅尧臣有《戏寄师厚生女》一诗曰:“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何时某氏郎,堂上拜媪叟。”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浙江富阳人,庆历六年进士,梅尧臣之妻侄。从诗题可见,其创作态度是戏谑的,但对古代重男轻女的征象却有细致的刻画。男孩可以耕读传家,女孩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注定要离开父母,常住夫家。众人生男会奔忙相告,生女却只能面面相觑,木鸡之呆。女大当嫁,诗中结句说不知将来会是哪个半子向谢景初夫妇拜别,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有趣的是,谢景初后来有个非常有名的半子——黄庭坚,黄庭坚适值生于庆历五年。不过他所娶的继室谢氏应是梅尧臣所写这个女孩的妹妹,当代学者已经考证出其生于嘉祐元年(1056)。谢景初当初看了黄庭坚诗歌后就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说“吾得婿如是足矣”,而黄庭坚听说之后就带着自己的诗集上门提亲,从而匆匆成这门婚事,成为一段佳话。婚后感情美满,无奈相处只有短暂的六年。
庆历六年(1046),宋敏修的女儿夭亡,梅尧臣写了《宋中道失落小女戏宽之》。欧阳修周围的士人普遍有这种相互戏谑的创作态度,宋人深知这种态度可以用来消解生活的苦难,超越难以名状的悲痛。悲哀是真的,但生活不能只有悲哀,活着的人还要连续往前看。原来自己丧子会呵壁问天,但宽慰欧阳修的时候已经清楚寿命是非不可诘问,由于很难知道谁该为此事卖力。此诗则进一步解构生命:“宋子失落汝婴,苦将造物怪,造物本无恶,尔责亦已隘。且如事情器,宁复保存坏,收泪切勿悲,他时多婿拜。”宋敏修由于女儿夭亡,怪罪于苍天,但梅尧臣指出彼苍本身无善恶之分,寿夭乃自然之理,就像工匠制作用具一样,难道能够担保其后不会破坏吗?正如用具有其利用寿命,人也有其死活。造物的工匠无法担保东西永久不坏,造人的彼苍同样无法确保人的龟龄。以是请不要悲哀,来日方长,往后可以生更多女儿,有更多半子。宋敏修哥哥宋敏求是1019年生人,宋敏修此时不过二十多岁,比较于梅尧臣、欧阳修都算是年富力强。
在这两年之中,亲人朋友中有人生女,有人丧女,梅尧臣都有与之干系的诗歌,或从自身出发宽慰,或超越自身宽慰,乃至完备调侃,情绪脉络非常清晰。对付子女的出身与拜别,彷佛逐渐看开,不过,只有在察看犹豫者的角度,才会有这么多抽离的旷达。如果身陷个中,感想熏染可能又会不同,如果还能化解,那就足以称得上切身的旷达。
三
谢氏去世之后,梅尧臣为其服丧一年。庆历六年(1046),四十五岁的梅尧臣续弦,第二任妻子为刁氏。结合上述的剖析,梅尧臣绝对不会长久沉浸在丧妻丧子之痛之中,选择重新开始生活通情达理,也是防止沉浸于悲痛之中的最好办法。袁采曾说:“中年往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无与之抚存。饮食衣服,凡闺门之事,无与之收拾,则难于不娶。”这确实是当时男性的一个普遍行为,梅尧臣无缝衔接,或许更能解释他并无妾媵,家中急需女主人主持内闱,照顾子女。
庆历七年(1047),刁氏婚后一年就诞下梅尧臣的二女儿。由于头胎即是女儿,宋敏修还拍手称快。梅尧臣有诗《宋中道快我生女》曰:
尔尝喜诅予,生女竟勿怪。今遂如尔口,是宜为尔快。亦既以言酬,固且殊眦睚。慰情何必男,兹语当自戒。
结合前面宋敏修由于丧女之痛,梅尧臣宽慰其将来会有更多女儿和半子来看,在重男轻女社会中,这种祝愿明显不会讨人喜好,大部分人可能更愿要个男孩光宗耀祖。可以想见,宋敏修收到梅尧臣诗歌后,对其调侃的祝愿不以为然,以是可能也反过来诅祝对方:刁氏这胎生女不生男。宋敏修当了一回预言家,结果如其所说生了女儿。梅尧臣说,虽然你会为预言应验而高兴,我也会为此而怨恨,但是让人情感得到抚慰又何必是男孩呢,生了女孩同样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慰情何必男”就该牢牢记在心中,不断用来自我警觉。
这个女儿不到两岁就夭亡,在欧阳修的《墓志铭》乃至都没有提及,实在梅尧臣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在其身上倾注大量情绪,集中频频涌现。
二女儿小名叫称称。名字含义则如梅尧臣说“我名命汝,平御妾媵”,希望其将来为人妇后,长于持家,公正公道。梅尧臣有《咏秤》诗:
贤人防争心,权衡为之设。后世失落其平,有星徒尔列。物物尚可欺,铢铢不须别。将淳天下民,安得必毁折。
在此之前的墨客绝少题咏这件物品。次女名字跟秤的特性干系,朱东润认为此诗便是指这个女儿。诗中说,秤是圣人为公正而设的,但后世风气转变,不追求公道,尔虞我诈,让它形同虚设。秤可以担保天下的公正,存在有其必要性,想让民风淳正,就不能让它受到摧折毁坏。事实确实相反,就犹如女儿命运一样。
庆历八年(1048),不到两岁的女儿夭亡,此时他已年近半百。梅尧臣为此写下三首悼亡诗和一篇砖铭。我们不妨从诗看起,《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其一:
生汝父母喜,去世汝父母伤。我行岂有亏,汝命何不长。鸦雏春满窠,蜂子夏满房。毒螫与恶噪,所生遂飞扬。理固不可诘,泣泪向苍苍。
女儿是梅尧臣再婚之后的首胎,夫妇两人没有由于重男轻女的现实,而对女儿的降临感到沮丧,这正是序言“慰情何必男”的表示。面对女儿夭逝,其心情不再像前面宽慰、戏谑别人那样轻佻。他陷入自责之中,难道女儿遽亡是因自己德行有亏。但是他察觉到的自然征象,又不敷以支撑这种想法。乌鸦、蜜蜂子女成群,与墨客的处境刚好相反,但它们的德行并非完美无瑕:蜜蜂有毒刺蜇人,乌鸦则聒噪烦人。德行与子女命运没有太强的联系。梅尧臣以为天理无法深究,只能无语泪流,面对苍天。这个“诘”字在三年前就涌现过了,天高难问,命运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不愿定。
其二:
蓓蕾树上花,莹絜昔婴女。东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爱命亦然,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哭泣显然无法完备宣泄心中的悲痛,看到树上含苞待放的白色花蕾,就会想起同样洁白晶莹的女儿。梅尧臣在《小女称称砖铭》对其形态也有刻画,称其“禀气血为人,丰然晳然,其目了然”。不过春华苦不持久,东风一吹,就凋落在地,尘归尘土归土。人亦是如此,虽然无比宠爱,但也无法担保永恒,随时都会像花一样陨落。苍天并不与人共情。梅尧臣本就说过“造物本无恶”,他不会去责怪上天。无善无恶,同样就无情无义,最伤心的还是与孩子血肉相连的父母。两首结句都写父母之哭,但上首写梅尧臣泣泪,这首则写妻子刁氏泣血,悲哀程度大大不同。泪水已干,继之以血,血泪未干就像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哺乳的奶水一样。对女性而言,这是有生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痛楚。
其三:
高广五寸棺,埋此千岁恨。至爱割难断,刚性挫以钝。泪伤染衣班,花惜落蒂嫩。天地既许生,生之何遽困。
女儿的棺椁不过五寸,埋葬的却是千年的遗憾。至爱本来就难以割舍,纵然最为刚强的人,遭受这种打击也会不知所措,变得迟缓。第五句写到落泪,可看作与前两首的勾连,第六句写花落又照料了第二首。花卉不可避免会凋零,但有些难免不免凋零得太早,与《砖铭》所言“鸟兽蚁蚁犹有岁时之命,汝不然也”一样。墨客前此反复说过,诘问苍天是没故意义的,但他还是有巨大的困惑,既然让她们来到这个天下,为什么又让她们如此匆忙地离开这里呢?
“生之何遽困”即《砖铭》“何病夭之遽”。梅尧臣《砖铭》对这种困惑着笔更多,“耳鼻眉口伯仲备好,其喜也笑不知其乐,其怒也啼不知其悲;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饮乳无犯食之禁,爱恶无有情之系:若是则得天真与保和,何病夭之遽乎!
”诗歌的容量无法倾泻巨大的困惑,以是通过另一种文体承载其情绪。诗歌毕竟要讲比兴,要温顺敦厚,但情绪的开释更须要体量更大的文章。梅尧臣的答案是“得不推之于有时而生,有时而化,有时而寿,有时而夭,何可必也”,这统统都是有时的,难以预见。这不便是《庄子》所说“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测其所将为”吗?末了,梅尧臣仍是自我和解:“汝之魂其散而为大空,其复托为人,不可知也。其质朽而为土,不疑矣。富贵百年者尚不免此,汝又何冤!
”寿命之是非,不能改变去世亡的相同命运,由此视之,彷佛又不必以为冤屈。这种思想在上述宽慰别人的诗歌中是一以贯之,墨客终极还是要通过笔墨走出悲痛的困局。
这个故事值得考索一番,是因欧阳修所写梅尧臣墓志铭中只涌现短命的男孩,而没有涌现这个也在梅尧臣生命史留下主要一页的女孩。
秋庭戏婴图
四
另一个女儿,梅尧臣去世时年纪尚幼,还未出阁。在其晚年诗歌偶有提到。嘉祐元年(1056),梅尧臣五十五岁,某次参加朱处仁(字表臣)宴会迟到,写诗呈给杜挺之解释个中缘由。《将赴表臣会呈杜挺之》曰:
莫怪去迟迟,予心君亦知。膝前娇小女,眼底宁馨儿。学语渠渠问,牵裳步步随。出门虽不远,情爱未能移。
诗中所言“娇小女”“宁馨儿”应是梅尧臣的三女儿,此时出生不久,已经牙牙学语,对天下充满好奇,且学会走路,对父母有很强的留恋性。可以推测,女儿大约两三岁。四年之后(1060),梅尧臣撒手长逝,以是欧阳修说她年纪“尚幼”。
关于家庭的温馨,与子女相处的欢快,在梅尧臣诗歌颇多描写。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在风雪天想再游金山寺,家人担忧其人身安全,以景象恶劣劝阻,其《瓜洲对雪欲再游金山寺家人以风波相止》所说“忽牵儿女恋,空听远钟撞”。因家人牵念,不能任性出游,只能与家人一起,在远处听金山寺的钟声。皇祐元年(1049),濛濛小雨,天色将晚,梅尧臣赶路回家,仆人饥馁,路又泥泞难走,可谓舟车劳累,但快到家的时候,仍旧感到身心舒缓,疲累不再,其《雨还》曰“关已度兮心缓,家将至兮涉溪。喜膝前兮童稚,饷灯下兮女妻”,最主要是立时可以见到妻子和小孩。这些描写,如果非要探求文学传统,那可以上溯鲍照《行路难》:“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只不过在梅尧臣笔下,这类书写反复涌现,虽有传统可循,但足以解释他乐意与家人相处,且能在个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正因如此,出门在外的他特殊害怕家人的顾虑和担心。《登瓜步山二首》有“舟师添系缆,儿女望人回”,正是叙说这种景况。皇祐三年(1051),梅尧臣爬瓜步山,在山上碰着狂风雨,下山时还电闪雷鸣。“心速湾犹远,行迟伴屡催。”内心虽然焦急,但离渡口尚远,行动迟缓,差错还屡次敦促。船只终于靠岸泊舟,儿女正在家中期盼父亲的归来。以上这些诗歌不难创造一个共同点,表面的风雨多么的难以预测,但家庭永久是可靠的避风港。
五
理解以上这些信息,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核阅梅尧臣的一些诗作。
(一)梅尧臣《汝坟贫女》。朱东润说这首诗是诗史,各种文学史教材或宋诗选本都会提及这首代表作。这首诗写于康定元年(1040),梅尧臣三十九岁。如果我们知道此时他的大女儿刚刚三岁,那么或许更能理解贫女嗷嗷无告,僵去世河边对他的触动。诗中说“大雨甚寒,道去世者百余人”,但触动心弦的是贫家女的惨剧。“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孤苦无依,去世后都没人帮你下葬。白居易有诗曰“贫家女难嫁”,贫女想要探求依傍,无疑难上加难。梅尧臣末了说“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死活将奈向”。贫女既没有依赖,又不能代父应征,那活着到底要怎么办?是连续挣扎,还是一了百了。梅尧臣充满困惑。
与此类似的还有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淘渠》所写:“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落脚非有挤。嫡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去世兽颠啼。”根据前面的考证,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梅尧臣的三女儿刚刚出生。虽说这类描写早有王粲《七哀诗》、杜甫三吏三别等珠玉在前,但关注这种征象于女儿降临之后,可能并非韶光上的巧合。创作源于生活,知人论世或许不能忽略这类情绪共振。
(二)王昭君是北宋中期文坛一个重点关注和书写的历史人物。王安石写成《明妃曲》之后,梅尧臣、欧阳修、刘敞、曾巩、司马光等人都有唱和,形成一组同题诗。宋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有风雅的研究,如内山精也《传媒与原形: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梅尧臣、刘敞已有干系题材的创作。
关于诸家《明妃曲》的异同,内山精也指出要从“年事辈分的差距”上寻求,“凡是青壮年期间多作讽刺社会抵牾的政治色彩浓厚之作品的墨客,到了中晚年就会转成不涉政治的作风”。欧、梅与王、刘、曾等人并不是一辈人,以是像王安石更方向在诗歌里面磋商出处、君臣关系的问题,而两位年父老却没有回应这一话题。朱刚说这是两代人的代沟。
梅尧臣和作每每被学者视为是对欧阳修的重复,如其“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图画去世误人”“男儿返覆尚不保,女子轻微何可望”,与欧阳修“汉计诚已拙”“红颜胜人多薄命”相似。换句话说,虽然两人政治地位悬殊,但老友之间的不雅观念互有影响。欧、梅诗歌自然不能说与政治绝缘,至少都批驳了汉朝和亲政策,但两位年父老不谋而合地关注女性的命运。这就不能仅仅阐明为年父老“看破”,“身心的朽迈”,或为了“保身”,而是与其个人履历,尤其是女儿的命运有关的。
在嘉祐五年(1060)《和介甫明妃曲》之前,梅尧臣早有昭君题材的诗作。嘉祐三年(1058),刘敞写下五古《王昭君》,梅尧臣有《依韵和原甫昭君辞》,其后两人又各写了一首。看两人关注的地方,仍是女性无解的命运,如刘敞“图画固难恃,远嫁委尘埃。十步一反顾,百步一徘徊。出门如万里,泪下成霰摧……”,梅尧臣则有“未弭后世患,玉颜困黄埃……在昔李少卿,听笳动悲哀。壮士尚如此,蛾眉安得开”、“一嫁他乡去,不复临镜台。……故国万余里,此生那得回。乃知女子薄,莫比原上莱。”。这些与两年后所写的《明妃曲》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是一为五言,一为七言,以是不必强调两年后所写受欧阳修影响。
明妃出塞图
梅尧臣第二首通篇描写远嫁他乡的痛楚,在异国他乡,重回故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中间铺排生活他乡的困顿,无不表明女性的命运,远比地上的草芥卑贱。如果结合上述的女儿诗歌,我们就可以理解梅尧臣这种心情是如何产生的。嘉祐元年(1055),梅尧臣送十九岁的大女儿出嫁,其目的地是绛州(今山西临汾)。对付宣城梅氏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远嫁。女儿想要回来外家,恐怕不太随意马虎。严格来说,山西临汾在汉代算是南匈奴的地盘,蔡琰《悲愤诗》所写塞北环境之恶劣,应是这个地方,而昭君出塞或许经由这里。可以想象,女儿远嫁之事对梅尧臣的冲击,这种事情很难不影响其昭君书写的立意,或许因此更能共情昭君阔别故土,身入异邦的命运。因此看到刘敞的诗歌,立时想要唱和,一首不足,还要再写一首。两年后诗坛兴起昭君故事创作热,梅尧臣又写一首。立意不像年轻人那样锐志翻新,梅氏不去回应,而是重复两年前的旨意,或许这种守旧的重复才能有效纾解心中的沉郁。新鲜只是一时,重复才是永恒而稳定的。红颜薄命看似陈腐的议论,其背后仍有其生活履历的投射,可以说,纵然平常,也是深厚的平常。
轻微年轻的王安石(嘉祐五年,四十岁)纵然理解,也不屑在诗中表达。王安石也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在其三十岁时短命,其他两个后来分别嫁给吴安持、蔡卞。在他诗集多以“吴氏妇”“蔡氏妇”涌现,这些寄赠女儿的诗歌多在晚年退居南京所写。女儿与王安石分开之后,书信往来极为频繁,所谓“家书无虚月,岂非常归宁”。书信多是用来表达思念之急迫,见面之艰辛,所谓“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泣”。笔墨上的往来无法取代回家真切的打仗。或许只有在这种情绪的煎熬下,墨客到晚年才会更加思念不在身边的子女,才能体会女儿远嫁之后“知汝悲惨正忆家”的心情。
“昭君不归”的主题是当时成年女子命运的缩影。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立时自作思归曲”“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虽与王安石原作离题,但明显更为普遍。七年之后,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明妃小引》又重申此意,“汉宫诸女严妆罢,共送明妃沟水头。沟上水声来不断,花随水去不回流。上马即知无返日,不须出塞始堪愁。”这样看来,“不归”的主题更受墨客的青睐,更具普遍性和生命力。
以上从女儿的背景切入,至少能够读出诗歌不一样的情绪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