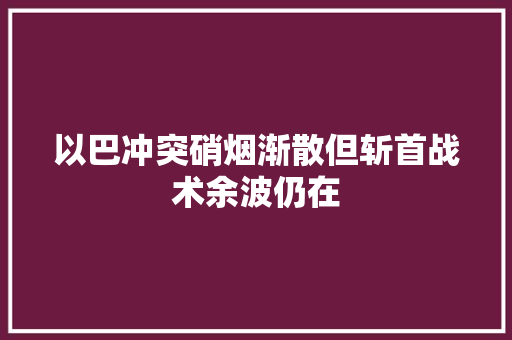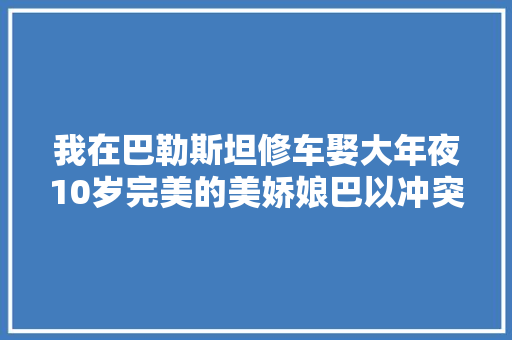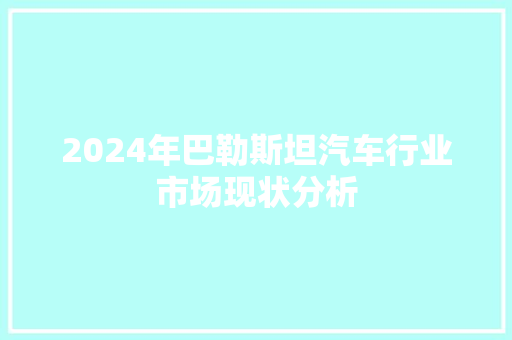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著名墨客,也是全体阿拉伯天下伟大的墨客。他的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措辞,多次获国际大奖。达尔维什的故乡位于加利利地区的比尔瓦村落,在1948年中东战役中,这里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达尔维什在以色列境内生活多年,多次被捕入狱。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去世于美国休斯敦赫尔曼纪念医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他举行了国葬。
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全面先容这位伟大的墨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诗苑译林”丛书,在诗歌界享有极年夜名誉。随着近年来诗歌阅读逐渐复苏,2013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启动了这套图书佳构的出版,不仅延续名诗精选和墨客翻译的编辑方针,更致力于补充现当代天下诗歌汉译史上的空缺。这次出版的“达尔维什诗选”,便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地译介达尔维什的诗歌。澎湃新闻得到授权,摘录诗选译者之一薛庆国所写的媒介,原题为:《用栀子花的叫嚣,令祖国回归!
》,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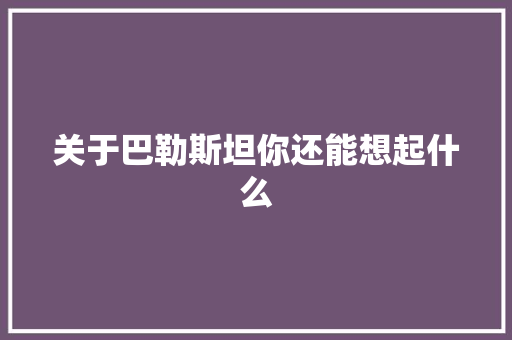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关于巴勒斯坦,还能想起什么?
旷日持久的冲突,失落去领土的国家,凄凄惶惶的公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房屋,向仇敌抛掷石块的少年,蓄着胡子的人体炸弹,戎马生平、却在重兵围困下受辱至去世的传奇领袖阿拉法特……这是环球化时期传媒留给众人的一个悲情民族之印象。
巴勒斯坦大墨客达尔维什的诗歌,也向天下诉说了这个民族的不幸、苦难与抗争;但它更以动听至深的办法,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肃静、情绪与审美——那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也是属于人类的。
1941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落落比尔瓦。1948年,为躲避第一次中东战役的炮火,他随家人前往黎巴嫩避难。战后,因家乡遭焚毁,他被迫搬家另一被占城市海法,在那里读完中学。毕业后,他加入同情巴勒斯坦奇迹的以色列共产党,并担当该党机关报的编辑,其诗歌生涯也从此开始。1961至1969年间,他被指控从事反对以色列盘踞的政治活动,先后5次被捕入狱。
1970年,达尔维什前往苏联,在莫斯科社会科学院学习一年。此后,他经朋侪先容前往开罗,在著名的《金字塔报》作家俱乐部任职,结识了多位阿拉伯天下一流的文学家。1973年,他又流亡至贝鲁特,担当《巴勒斯坦事务》月刊主编和巴勒斯坦作家及协会主席。1982年,以色列为打消巴解组织而入侵黎巴嫩,他被迫辗转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后受阿拉法特委托,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并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1987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并应阿拉法特之邀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1995年,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后,他作出了回归祖国的决议,晚年在巴城市拉姆安拉及临近的约旦都城安曼两地定居。
2008年,他前往美国休斯敦接管心脏手术,8月9日因手术意外失落败而去世,享年67岁,其尸首被用专机运回拉姆安拉安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告,举国哀悼3天,为这位伟大的“巴勒斯坦的情人”举行国葬。
2008年8月10日,巴勒斯坦民众在拉姆安拉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吊唁达尔维什。
自196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无翼鸟》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得到过苏联列宁和平奖、亚非作家同盟莲花奖、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荷兰克劳斯亲王奖、马其顿诗歌金桂冠奖等10多项国际大奖,其作品被译成20多种措辞。他的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在阿拉伯天下广为传唱。
海法——贝鲁特——巴黎——拉姆安拉,构成了达尔维什半个世纪流亡生涯的紧张轨迹。与流亡地的变换相对应,达尔维什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次中东战役结束后,达尔维什流落到被以色列盘踞的海法定居。在此度过的青年期间,是墨客创作的第一阶段。其间,他陆续出版了《无翼鸟》(1960)、《橄榄叶》(1964)、《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1966)、《黑夜尽头》(1967)、《鸟儿去世在加利利》(1969)、《我的爱人从梦中醒来》(1970)等诗集。这一期间,达尔维什亲历了祖国沦陷、无家可归的不幸,也参与了收复故土、追求自由的抗争。他的诗歌(个中不少是在狱中写就)阐述了自己“被从故土连根拔起”的苦难,也表达了刚毅不屈的意志。这一阶段诗作的基调是悲愤的,但也流露出对正义奇迹的崇奉,对回归家园的信心;诗风总体上普通晓畅。因此,他被冠以“爱国墨客”、“抵抗墨客”的称誉。
自1970年开始,达尔维什先后在莫斯科、开罗和贝鲁特等地流亡,并在贝鲁特工作近10年。这一期间,他陆续出版《我爱你或者不爱》(1972)、《7号的考试测验》(1973)、《那是她的图像,这是情人的自尽》(1975)、《婚礼》(1977)、《高影赞歌》(1983)、《海之颂的围困》(1984)等诗集,以及散文集《关于祖国的事》(1971)、《平常悲哀日记》(1973)、《别了,战役……别了,和平》(1974)。客居他乡,频繁出入车站、码头和机场,墨客深切体会到无家可归的悲惨,对个人与祖国命运的思考也趋于冷峻。流亡生涯的艰辛,对故土和祖国的思念,成为墨客第二阶段创作的主要主题。较之前期,这一阶段的诗作更有深度、繁芜性和抒怀义味,意象更加丰富而密集,基调是沉郁、深奥深厚的。部分作品是长诗,具有戏剧化探索的特点。
1985年起,达尔维什开始了在巴黎的10年旅居生活。他创作了《她是一支歌,她是一支歌》(1986)、《更少的玫瑰》(1986)、《我见我所愿》(1990)、《十一颗星辰》(1992)、《为何你将马儿独自抛下》(1995)等诗集,以及散文集《为了忘怀的影象》(1987)、《描述我们的情状》(1987)、《等待野蛮人》(1987)、《临时话语的临时过客》(1991)。达尔维什认为,就某种意义而言,在巴黎,他的诗歌才完成了真正的出身。阔别祖国的间隔感,使他能够以“察看犹豫者”姿态镇静地核阅祖国、阿拉伯民族乃至天下,并从一个新的高度思考诗歌和人生。他开始思虑:自己来自一个个体缺少自由、群体未获解放、国家没有依托的国度,这一背景必定要让自己的创作受到制约?还是有可能使之变得更为丰富、深刻和独特?伴随着思考,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祖国和流亡地依然是主要主题,然而,墨客处理的角度和高度有了变革,他在个中贯注了更多人性的、情绪的、美学的乃至神秘主义的元素。这一阶段的诗中还大量涌现具有中东文化特色的神话历史意象,首创了一种秉承文化遗产的当代神话构造,呈现出史诗般的磅礴大气。由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1993年巴以双方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令人失落望,墨客的部分作品也流露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无奈与挫败之感。
1995年,达尔维什终极结束长达25年的流亡,回到巴勒斯坦定居。其间他潜心创作,完成了《陌生女人的床榻》(1999)、《壁画》(2001)、《围困的情状》(2002)、《不必为你的行为道歉》(2003)、《宛若杏花或更远》(2005)、《蝶之痕》(2008)、《我不想结束这首诗》(墨客逝世后于2009年出版)等诗集,还揭橥了散文集《在场的缺席》(2006)、《归者的困惑》(2007)。世纪之交的中东并未迎来和平的曙光,巴以双方的流血冲突陷入恶性循环,墨客的定居地拉姆安拉一度被以军围困3年之久。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墨客忍受着挫败和失落落之痛,致力于创造一个措辞中的诗意祖国,以此抵抗沉沦。他的晚年诗作更加关注有血有肉的个体命运,喜好表现生活细节之美,倡导人性主义,反思民族文化,核阅生命与去世亡,呼吁自由、爱与希望。这一期间的作品中,他尤为器重因心脏病发而住院抢救时写下的长诗《壁画》,期望以此留下一部如壁画般不朽、如阿拉伯古悬诗般具有永恒意义的精品。
达尔维什虽在阿拉伯天下拥有大量读者,并深受巴勒斯坦公民的爱戴,但他的许多诗作理解起来实在颇有难度,由于个中涉及许多背景知识,如墨客的独特经历,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中东地区极为丰富的宗教、历史、神话、传说等文化遗产。总体而言,祖国、流亡、抵抗、人性主义、措辞与诗歌等等,是解读达尔维什作品的多少关键词。
巴勒斯坦虽然是“像芝麻粒一样纤小”的国度,但这片地皮人杰地灵,既有肥沃的野外、丰富的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残酷的文明,更是天下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在达尔维什笔下,墨客对祖国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祖国是母亲或姐妹,是爱人与情人,是“我的女主人”,是我“诗歌的火焰”和“旅途的食粮”。在墨客看来,人终将化为尘土回归故地,与大地合为一体,通过滋养大地、孕育新生而归于不朽;因此,人与地皮死活同命,荣辱与共。但是,随着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宣告建国,巴勒斯坦公民开始遭遇丧土失落国之殇与背井离乡之痛,其创痛之深、历时之长,实属全球罕见。祖国,在墨客眼里不再那么浪漫了。那是“遗忘了拜别者腔调的祖国”,是“在歌声里和屠宰场不断重复的祖国”,是“屠杀了我的祖国”。与祖国、地皮有关的统统,都充满了痛楚的悖论:“我们”身处的地方,是“我们在个中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回归故土,只是“返回一个石质的梦”;身陷囹圄的爱国者只能想象:“大地多么辽阔!
/针眼里的大地多么俏丽”;到处为家的流落者只能哀叹:“我们旅行,去找寻零”;祖国,是“那个我没在护照上找到戳印的国家”。
饱受了流落失落所之苦,墨客对祖国的认知渐趋平和而深刻。祖国深藏于内心,呈现于日常,她便是“转辗于机场的旅行箱”,“便是喝到母亲的咖啡/便是晚上可以回家”。墨客乃至不无调侃地建议,“用一头普通的驴作为(国旗的)象征/那该有多好”,“选一首关于鸽子婚嫁的歌曲(作为国歌的歌词)/那该有多好”。祖国像杏花一样透明、轻盈、柔弱,却难以记述,无法形容。墨客晚年还对用空泛的政治口号曲解祖国表示厌倦:“当一位作家仰望星辰,却不会说出‘我们的祖国更高……更美’,这时的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也对利用祖国进行政治投契予以当心:“赞颂祖国/就跟诋毁祖国一样/是和别的职业类似的一门职业”。他还深刻反思本国、本民族政治与文化中的各类弊端,在《如果我们想要》、《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你》等诗作中,许多短章都表示出这种冷峻的反思意识。
流亡,是达尔维什诗歌的另一主题。墨客和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亡者一样,对付居无定所、辗转四处的流亡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他的诗中,身份证、护照等证明文件,成为被剥夺、被驱离者身份的不幸象征,而机场、港口、车站、旅店、背包、道路、大海、飞鸟等意象,则浓缩了浪迹天涯、无家可归者的伤感和痛楚,正如他在长诗《高影赞歌》的感慨:“我的祖国是背包/只是没有人行道/没有墙/脚下没有地皮/可让我为所欲为地去世去/周遭没有天空/可让我穿行到先知的营帐。”有时,墨客以反讽的笔调书写流亡者的窘境:“我们变成/摆脱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更多的时候,墨客笔下流露出愁断寸肠的忧思:“我们的岁月年华/如何飘零在回归的路途/我们把生命遗落在何处?/我问一只/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顿时,它在泪水中/燃烧。”
1995年,达尔维什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定居。虽然回归祖国,但他对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深感失落望,也无法认同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乃至民众的许多行为和不雅观念。在归国之前的诗作《原形有两面,雪是玄色的》,就已流露出这种不满,有些评论家乃至揣测,这是一首墨客跟阿拉法特直接对话、表达蕴藉批评的作品。归国后,现实中的巴勒斯坦与墨客空想中的祖国相去甚远,因此,他在无奈中写下“巴勒斯坦远得没有边”,“此刻,在流亡地,是的,在家中”这样的诗句。墨客感想熏染的,是“在场的缺席”的悖论:地理意义的在场,却难以肃清生理层面、思想层面的疏离和缺席。到了晚年,墨客对“流亡”的认知又有了深化,他开始认同巴勒斯坦同胞爱德华·赛义德所推崇的“流亡的愉悦”,在承受流亡这无法卸去的包袱之同时,也自觉地把流亡视为获取自由和创造力的独特源泉:“自由人便是选择流亡地的人/那么,在某个意义上/我便是自由人/我前行……于是方向变得清晰”。
在达尔维什的诗歌生涯中,“抵抗”一词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核心观点,并呈现出一道由朴素渐臻深刻、由单一逐渐丰富的嬗变轨迹。早期他理解的抵抗,表示为与盘踞者作军事的、政治的抗争:“抵抗盘踞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更是他们的责任。抵抗有许多形式,例如刚毅不屈,谢绝接管以色列旨在抹杀巴勒斯坦的所有图谋,或寻求多种斗争路子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做事。”到后期,他从诗性高度诠释抵抗的真谛:“每一首俏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守卫生命的诗歌,是一种实质上的抵抗。”
达尔维什抵抗不雅观的这一嬗变,与当代巴勒斯坦奇迹的演化态势无疑有着直接的关系。摆在墨客和无数巴勒斯坦人面前的一个残酷现实是:由于巴以双方的力量比拟日益悬殊,通过武装斗争得到解放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会让巴勒斯坦公民在遭受巨大捐躯的同时,还遭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严重后果。然而,墨客的认知逐渐向美学的、文化的抵抗不雅观过渡,却并不仅仅是接管无奈现实的被动选择,而是表示了墨客对自身义务更深刻的觉知。在收复失落土杳然无望的现实面前,墨客并没有陷入绝望,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少之又少,摆在他们面前的决议只剩两个:要么活下去,要么活下去!
他有权守卫自己,而紧张武器便是掩护自己的属性、权利和身份,然后用统统路子保留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当代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深刻困境在于,他们不仅失落去了地皮,被剥夺了与地皮密不可分的政治身份,而且他们的文化属性也面临日益消解的危险:一方面,以色列刻意抹杀他们与这片地皮溯之久远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被环球化时期的传媒故意无意地贴上“胆怯”、“极度”的标签。面临这样的困境,诗歌作甚?墨客作甚?达尔维什给出的答案是:诗歌固然无法收复失落地、推翻暴政,但它也有“丝绸的力量和蜂蜜的刚强”;抵抗偏见,抵抗遗忘,抵抗狭隘,这是身为巴勒斯坦墨客的意义所在。诗歌是柔柔的,但墨客的义务和包袱却并不轻松。在《你扛着蝴蝶的包袱》一诗里,达尔维什对话自己,用“蝴蝶的包袱”来感叹墨客所肩负的民族义务与社会任务之重,勉励自己“对不可能说不”。
在达尔维什看来,诗歌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感召具有群体意义的民众,唤醒他们的义务意识;也在于启迪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意识,让他们在困境中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从而守卫、丰富、发展民族和个体的身份属性。他曾写道:“巴勒斯坦人并非一份职业或一句口号。他首先是一个存在的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颤;他相应身体的自然希望、而不是别的号召做爱……他繁衍子嗣,为的是保存种姓、延续生命,而不是求去世,除非到后来他变得生不如去世!
这意味着,长期的盘踞未能抹杀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如愿以偿地征服我们的措辞和情绪,令其在围困之中枯竭。”而显然,展示巴勒斯坦人的审美能力,是墨客抵抗盘踞和抹杀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达尔维什在“祖国回归”的伟大命题和诗歌的艺术魅力之间实现了对接:诗歌,“它可以/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叫嚣,/令祖国回归!
”无疑,这样俏丽的诗歌,在温暖着、抚慰着一个悲情民族的同时,也在改写着、重塑着天下对这个民族的认知。
达尔维什与丽塔。
作为“抵抗”墨客的达尔维什,不仅深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公民的爱戴,而且受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天下范围内读者的尊重乃至仰慕,其缘故原由之一,就在于他的作品一贯具有崇高的人性主义维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举行的一次巴以作家对话会上,达尔维什直言:“我们的脸庞是悲哀的,但它不仇恨;是真性的,但它不屈服;是受压迫的,但它不卑微。”在他的所有诗作中,都找不到源于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抵抗的是压迫,无论这压迫来自阿拉伯暴君或以色列盘踞者。这一人性主义态度,大概与达尔维什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他在海法就读中学时,一位名叫苏珊娜的犹太女西席对他关怀备至,被他视若“母亲”。他的初恋情人,是一位名叫“丽塔”的犹太少女,后来,丽塔成了达尔维什诗作中涌现频率最高的女性,是他叙事诗中“我”与之倾诉衷肠的情人或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丽塔与枪》一诗便阐述了阿拉伯青年与犹太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这一恋情以丽塔被枪杀而闭幕,“在丽塔与我的眼睛之间”的那杆枪,分明是恶行战役的象征。在《梦见白百合的士兵》中,墨客记述了与一名犹太士兵的对话,这位沙场上的杀手,内心深处也藏着一个或许与巴勒斯坦士兵无异的欲望:“我要良心一枚,不愿填塞步枪/我要妖冶的日间,不要猖獗的/法西斯的胜利光阴”。在《共同的仇敌》中,墨客设想敌对双方的士兵在女友面前说着相同的话语,“失落败只是个孤零零的词语。然而每个战士,在他爱人面前却不是士兵”;“两方的去世者直到末了才懂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去世亡。/这个中意义何在?意义何在?”
在后期诗作中,达尔维什还超越政治,对巴以冲突的文化、历史缘故原由作深入的探究与反思。他为巴勒斯坦这块地皮的先人迦南人哀叹:“你的不幸,是你挑中的园圃/靠近了神的边界”;他还表达了对人类历史的感慨:“大地便是流放地,/历史便是一场悲剧,它始于该隐和亚伯的/家庭之争”。通过这种将冲突根源远溯至人之初、历史之初的策略,墨客一方面传达了对付巴以两个民族骨血相残、相争相残的讽刺和太息,另一方面也让巴以冲突成为人类无休止冲突的一个隐喻,巴勒斯坦的悲剧,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普世意义。
末了,还有必要谈谈达尔维什的措辞不雅观和读者不雅观。他在《为悬诗而歌》中写道:“再无地皮承载我,/唯有我的话语携我同行。”作为一位家园被剥夺的墨客,这确是绝不造作的由衷之言。措辞不仅是他的唯一同行者,也是他最器重的唯一财富。在达尔维什看来,人类的恩怨纷争,相对付漫长的文明史而言不过是充满荒诞的闹剧。只有措辞才能记录历史,并让未来的人类文明具有无限可能。在许多诗作中,他都表达了用措辞、诗歌降服去世亡、得到诗性永生的年夜志。晚年,对付朋友提出的问题“艺术是否真像你在《壁画》中所说的那样具有降服去世亡的力量?”他如此作答:“这不过是人类制造的一种幻象,以证明我们的确存在于世上。但这幻象是俏丽的。”实在,措辞降服去世亡并不是幻象,达尔维什的诗篇,和人类灿若群星的文化年夜师留下的作品一样,确实具有传之久远、得到永生的生命力。
措辞还标志着措辞利用者与自身文明和先人的血脉接续。达尔维什十分器重自己来自中东这片文化沃土的身份,为自己传承的文化遗产自满:“这便是我的措辞,/我的奇迹,我的神杖,/我的巴比伦花园,我的方尖碑,/我的第一身份”。同时,他理解的遗产又不仅仅是传承,而且意味着创新:“墨客必须有一份新的祝酒辞/和全新的歌曲。”他的不少诗篇,还表达了措辞和诗歌的神秘性:“诗歌是嫡的妻子,昨日的闺女/它扎营在写作和措辞之间/一块模糊的地域。”
在阿拉伯读者眼里,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的情人乃至圣徒,人们期待他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但达尔维什没有陶醉于此,相反,他一贯承受着民族代言人和诗歌艺术之间的巨大张力,他曾发出感慨:“做一个巴勒斯坦人很难,做一个巴勒斯坦墨客也很难,由于他必须同时兼顾内心和外界,同时实现诗歌的美学和功能。他既要抛下神话的政治性,又要洞察现实的诗性,做到墨客与政治家的二体合一。”他并不回避墨客应秉持的社会任务,同时又对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被刻意标举保持警觉;他致力于通过诗歌提高祖国公民的个体自觉和审美情操,又不愿捐躯诗歌的艺术性降格以求。实际上,他诗歌生涯的创新与变革,每每伴随着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读乃至责怪,但是他淡然以对:“我感谢他们的误解,/然后,又去探求新的诗篇。”奇怪的是,在达尔维什后期,他与读者大众的关系还呈现出某种神秘性。巴勒斯坦各地为他举行的大型朗诵会每次都座无虚席;他朗诵的部分诗作,实在颇为晦涩,但现场总是鸦雀无声,许多听众似懂非懂,却听得泪流满面。
达尔维什长眠之所。
达尔维什博物馆。
在俯瞰拉姆安拉城区的一个山丘顶部,坐落着达尔维什的长眠之所。庄严肃穆的墓地一侧,是设计得极富艺术气息的达尔维什博物馆,近旁的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阿拉伯语笔墨:“由祖国,赠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我,一定要去一趟巴勒斯坦,向伟大的墨客问候、致敬。在那风动云动的山顶,我还要去凝望他吹入长笛里的迢遥色彩,去聆听他在泥土上描绘的马的嘶鸣,去欣赏杏花如何露出水汪汪的微笑,去感想熏染云朵如何盈满诗的眼眶。
我还一定要去寻访那素洁如玉、馨喷鼻香如缕的花儿。是的,是它,便是它,启示墨客写下这样的诗句:
“用栀子花的叫嚣,
令祖国回归!
”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著 薛庆国、唐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