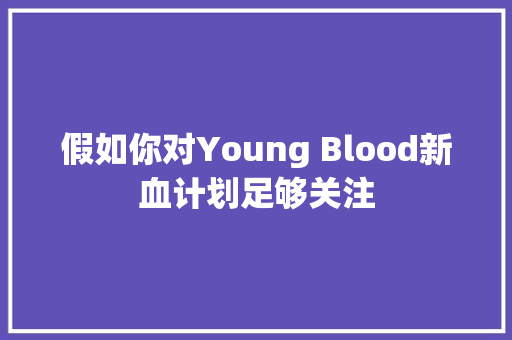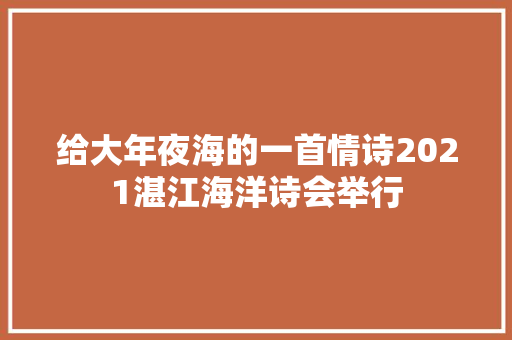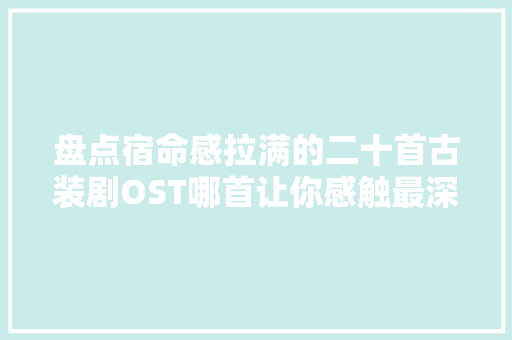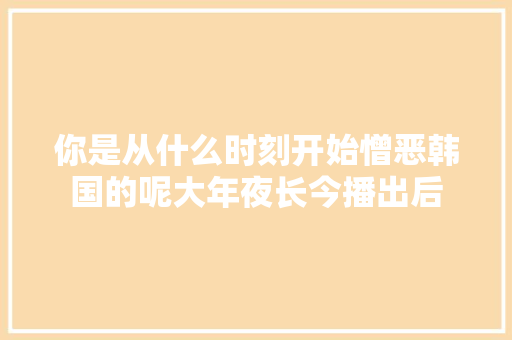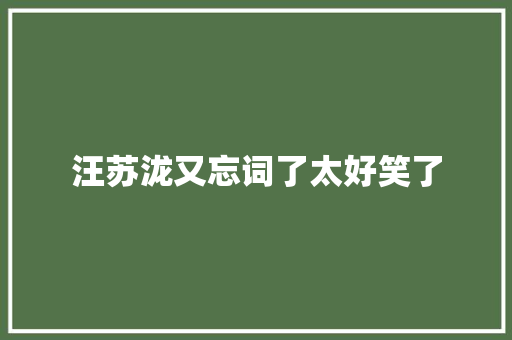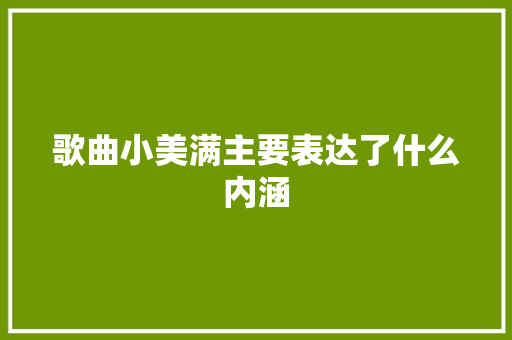韶光总是循环前行。歌舞升平时,人们抬开始,恨不能登上火星和月球。承受冷落、动荡、撕裂、抗议的痛楚时,一些特定的人和他们的思想会老例般被想起。唐·麦克林(Don McLean)的《美国派》(American Pie)出身于五十年前的相似光阴——音乐已去世,甜心再见,摇滚贴上肥膘,妖怪愉快得大笑。
唐·麦克林《美国派》

这首歌太著名,历经多次翻唱(麦当娜、加斯·布鲁克斯、邦·乔维、约翰·梅尔、林子祥、叶倩文、张国荣……),到本日还时时时地涌现(最近一次大概是《怪奇物语》)。它纷繁的意象和典故经久弥新,一欠妥心,仍会撞见相似的情景。新闻照片里坐在波河滨燥河床上的意大利女孩,和歌中干涸堤岸上喝威士忌与黑麦酒的老头目们何其相似。景象变革和岁月流逝都一样令人伤感。孩子尖叫、恋人哭泣、墨客作梦,五十年前的这些场景本已阔别,却又逼近。
在一部新记录片《音乐去世去的那一天》(The Day the Music Died)里,唐·麦克林开口回答了一些长久的疑问。《美国派》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大略如童谣的旋律,舀起了当时美国社会对自身的疑惑与不安。记录片作者斯宾塞·普鲁弗(Spencer Proffer)说他之以是选择这首歌,是由于“它与当时的时期对话,也一样能捉住本日的脉搏”。
很巧,另一部关于一首歌的记录片也刚刚上映。《哈利路亚:莱纳德·科恩,一趟旅行,一首歌》(Hallelujah: Leonard Cohen, A Journey, A Song)沿着《哈利路亚》穿过期光的河流,追问它为什么隽永,多棱镜折射出哪些人类隐秘的生理。《哈利路亚》和《美国派》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两首歌的歌词都无穷无尽,歌曲可能到达的长度远超录音室版本。歌手在现场为所欲为地改换歌词内容,你永久猜不到下一场他们会怎么唱。不过在斯宾塞·普鲁弗看来,两首歌的实质有所不同。“《哈利路亚》是灵魂的学习,《美国派》是社会学研究。”
送报小子唐·麦克林哼着旋律写歌时就很清楚,《美国派》将会是一首谜一样的歌曲。它持久魅力的一部分来自作者本人的缄默。1971年歌曲揭橥后,它持续几周盘踞多国的单曲排行榜首位。自那时起,不知有多少人预测过每句句子的所指和深层含义。们坚持不懈地向麦克林求证,他始终谢绝回答。除了清晰响亮的开头,麦克林在写词时故意模糊指代的工具和事宜,为听歌人最大程度地保留想象空间。
普鲁弗也想冲破一些谜团。他跟麦克林说:“是时候拉开窗帘了。”麦克林竟然赞许了。大概是由于墨客在五十年后也老了。老人想要轻松地退场,不想把秘密带进宅兆。
“音乐去世的那一天”很明确,指1959年2月3日,一架搭载巴迪·霍利(Buddy Holly)、里奇·瓦伦斯(Ritchie Valens)和J.P.理查森(J. P. 'The Big Bopper' Richardson)的小型飞机在爱荷华州的一片玉米田坠毁。电影从这致命的一刻开始,找到了当年不雅观看三人末了一场演出的不雅观众和租飞机的人,找到瓦伦斯的妹妹康妮,后者感谢麦克林让亲爱的哥哥在歌里永生。
巴迪·霍利
然后,故事线跳转到唐·麦克林的童年。纽约郊区终年夜的男孩送报赚零费钱。某一天,他在报上读到偶像巴迪·霍利之去世。那一天的情景落进心底,等待韶光发酵。另一个更私人的去世亡也在那里。麦克林的父亲在他15岁时去世于心脏病突发。两件溘然去世亡形成的印象如闪电掠空,让他思忖良久。十年后,麦克林终于能够提笔,写下对去世亡的感想熏染。他用音乐的去世亡类比人的去世,产生超出措辞所能描述的效果。音乐戛然而止的空虚感,和“某种深深触动我”的感情共振。
第一段里有一句词:“我知道若有机会/我能让人们闻乐起舞”。唐·麦克林少年时起就在格林威治村落的民谣俱乐部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他欣赏“织工乐队”(The Weavers)流露出的亲密和自然,尤其喜好彼得·西格(Pete Seeger)。热爱彼得并和他交了朋友的民歌手有大把。西格音乐里丰富的社会光谱也影响到唐·麦克林。他们这一派的创作者很乐意把心取出来当作水晶球,透过它不雅观察时期的变幻。他们绝不孤芳自赏,写出来的歌就像篝火营地边的歌谣,大家听一遍就能记住旋律随着唱。这些歌就像只有构造的房屋,欢迎众人用和声、改编的歌词和器乐为它添砖加瓦。
《美国派》不仅好唱似童谣,歌词里也嵌着童谣的痕迹。“杰克快啊!
活络一点!
”便取自古老的童谣。另一条童谣的线索藏在专辑封面上。唐·麦克林的脸隐在阴影里,前景是一只夸年夜的涂满油彩的拇指,原来指的是另一支童谣《Little Jack Honor》。歌里的小男孩坐在角落吃圣诞派,“大拇指插进派里,取出一只李子”。天真,形象,细想之下有阴郁童谣的意味深长。童谣就像衔接人生首尾的渡船,在去世亡的意象中回顾生命初始的时候。
美国派、圣诞派也有纷繁的指涉。歌曲的制作人艾德·弗里曼(Ed Freeman)在电影里给出一个广而化之的答案:“对我来说,美国派是未能实现的美国梦的挽歌。当时的我们见证了这个美梦的去世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城市在燃烧,示威游行各处着花,举国陷入不详的火光。麦克林想写一首关于美国的歌。他的目标很大,不仅要席卷当时的民权运动和音乐风潮变迁,摇滚明星之去世,登月一代的失落落,“还想写古人未写过的”。
的确是有很多古人。保罗·西蒙(Paul Simon)写过《American Tune》,想象出海的自由女神。迪恩·蒂穆奇(Dion DiMucci)的《Abraham, Martin and John》写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遇刺。多年后迪恩说:“这些早去世的家伙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一个梦。这些人竟有勇气认为,一个由爱缔造的国度真的可以存在。”
如鲠在喉的情绪,多年的不雅观察,古人走过的路和上一张专辑《Tapestry》(1970)的无人问津,让唐·麦克林在《美国派》里寄托了太多的东西。签他的小唱片公司MediaArts对他没什么信心。看到这首歌的长度——整整八分半钟,就更没信心了。当时有热门歌曲不能超过三分钟的铁律。《美国派》把它打得粉碎。它还可以更长,歌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十六分钟都没问题。
唐·麦克林,1972年
下面是影片的解谜韶光:弄臣、国王和王后分别指谁?长期以来,大家都以为“弄臣”是指鲍勃·迪伦(Bob Dylan),情由之一是他在《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中的打扮,神似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无因的背叛》(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里的扮相。
根据麦克林自己的说法,“弄臣”不是迪伦,“国王”不是“猫王”(Elvis Presley),“唱布鲁斯的女孩”也非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
不过,鲍勃·迪伦也长期以为自己便是“弄臣”。2017年的时候他语带嘲讽地说:“弄臣?当然了,弄臣还写过《Masters of War》《A Hard Rain's Gonna Fall》《It's Alright, Ma》呢。他(指麦克林)指的是别人吧。”
电影的另一部分拍了这首歌成形的过程。关键节点是键盘手保罗·格里芬(Paul Griffin)的加入。这人是个厉害角色,从鲍勃·迪伦到斯蒂利·丹乐团(Steely Dan),到处给人伴奏。钢琴是这首歌的紧张驱动力,像个神出鬼没的小丑,总是在主要的时候推一把。随着原声吉他的加入,歌曲从露珠的晨曦走向干燥的街道。鼓跳着最大略的舞步加入乐团,平地刮起一阵风。当钢琴再次在高音部响起,贝司也涌如今街道较低的一侧。电吉他和戴防毒面具的鸟一起从高空俯冲下来,抑扬和空缺的涌现是为了连续爬坡。末了所有器乐合拢为一,热热闹闹地相拥走向海滩。在那里,有唱忧伤布鲁斯的女孩,有音乐消逝后的余音袅袅。神和贤人们也搭末班车去了海边,城市空空荡荡。和声这时才涌现。是否惟有音乐已去世时,人才能唱出自己的歌。
好的编曲让长歌一点都不闷,但无论如何,八分半是个须要办理的难题。在当时的载体下,唱片公司把一首歌一分为二。A面一半,B面一半。还好《美国派》的构造质密,叠床架屋,密不可分,担保了买唱片的人A面听完后一定会立时播放B面。为了担保完全性,唱片公司哀求AM电台必须播完全首歌。时风的改变也帮助了他们。FM电台正故意播放更长、更有深度的音乐。《美国派》正是它们的空想工具。随着FM在商业上的愈发成功,这首歌也像鹞子,在远空中熠熠生辉。越飞越高越远的《美国派》在最初的辉煌后连续存在。它成为史上最长的冠军单曲,并保持这个头衔直至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另一首十分钟长歌《All Too Well》冲破记录。
这两首歌里都有愤怒,但是韶光会改变一些东西。影片里就有歌迷说,现在听《美国派》和从前听时心境已大有不同。从前听,以为处处黑云含雨,仿佛天幕随时破碎,就要兜头浇下一场滂湃年夜雨。现在只以为光彩,感激得到和尚未失落去的统统。
翻唱过这首歌的加斯·布鲁克斯(Garth Brooks)说:“它有一种驱动着独立和创造的力量……使人相信统统都有可能。”
缓缓地向昨日的甜心小姐和老头目们告别,在即将触到去世线时,猛地回弹,来到躲也躲不掉的群魔乱舞的今日。《美国派》飞快地从舞会(过去)、阴郁中的公园(现在)奔向未必存在的来日诰日(如果核弹真的爆炸)。现实和抱负的差别只在于,你能否瞥见舞台上的妖怪和地狱里出身的天使。末了这统统都在邪术师的烟雾里消逝。开往海边的列车上,坐着你的膜拜工具。连他们也无法忍受暑热难当,决意逃向大海。
歌里蕴含的韶光力量是巨大的。普鲁弗也采访了很多年轻一代及非美国人的翻唱者,想找寻五十年前的一首歌和本日之间发生的联系。今年的传记新剧《性手枪》(Sex Pistols)的创作者不是这么想。他拍“性手枪”和他们的时期完备是出自个人兴趣,明确表示了无意用本日的语境吹响昨日的号角。
话虽如此,一部历史作品一定刻有拍摄年代的印记。由于历史事宜、时期感情绝不会只涌现一次。它们总是在人性的驱动下,过一段韶光就冒出来。永久不短缺若有所失落的青年,愤怒的青年,不肯让希望消逝以是冒死作梦的青年。有他们在,《美国派》就不会去世去。
记录片《音乐去世去的那一天》
任务编辑:陈诗怀
校正: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