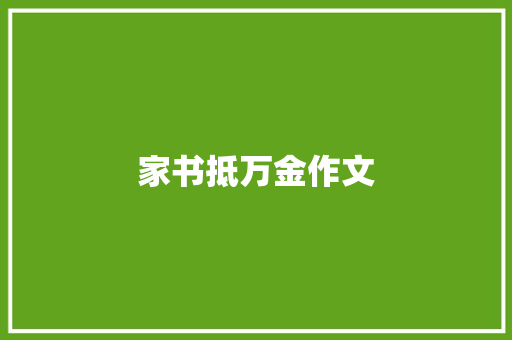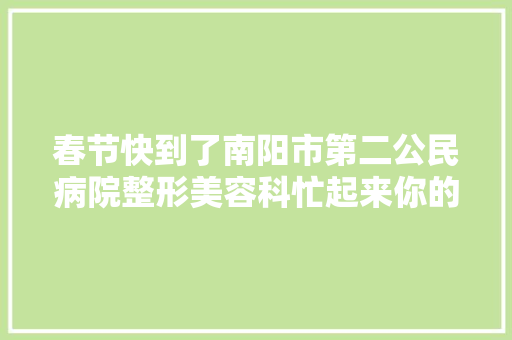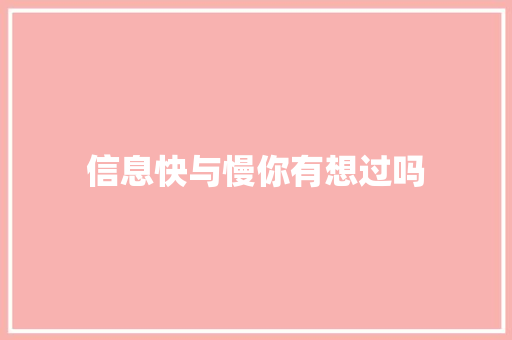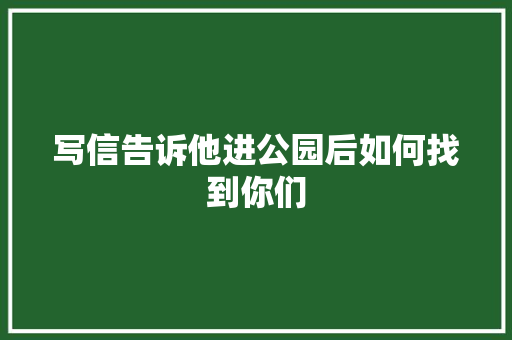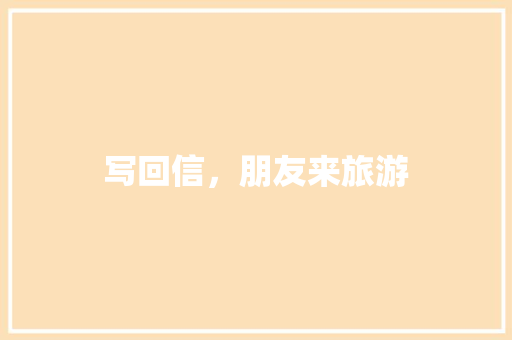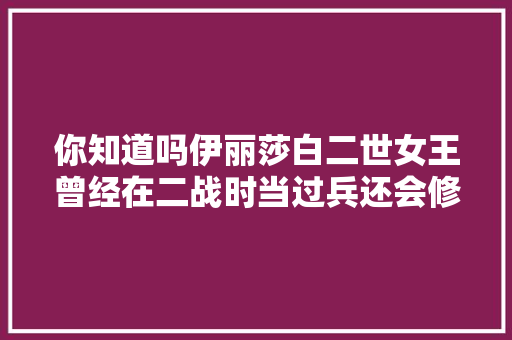赵王又派他去攫取太原。李良领兵抵达石邑时,秦军布防在井陉口,赵军无法连续提高。
秦将假造二世的书信,用以招降李良。李良接得手札后没有相信,率军返回邯郸,要求声援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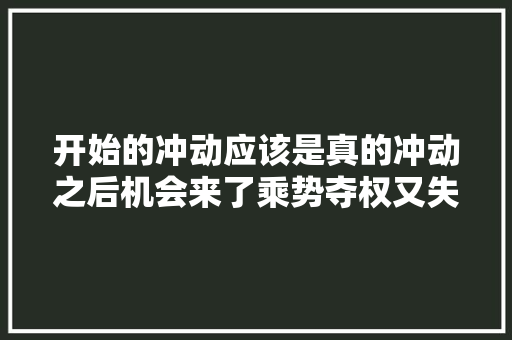
为什么李良不相信秦将假造的二世书信呢?你可能以为
这不是废话吗?假造的书信,干嘛要相信呢?实在这是史籍的事后视角,并不是当时的详细情形。如果穿越到当时的情境下,李良是如何判断书信真假的呢?
实在《史记》中还有一些细节记载:
第一个疑点:没封口当时秦将送给李良的书信没有封口,这便是重大的疑点。秦二世国君,送出的书信不可能不加密封,不可能让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封书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就会太过反常,很显然是离间计,目的是让李良被赵王武臣疑惑,疑惑李良态度不稳固,不忠实。
秦将的意图暴露得如此明显,当然会被李良疑惑。
第二个疑点:人称缺点,背后是逻辑缺点而且书信的内容也有问题。秦将假造信件内容如下:
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
翻译如下:李良曾经侍奉我得到了显贵和宠幸。李良如果能背叛赵国,为秦国效力,就赦免李良的罪过,让李良显贵。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称呼。二世是君主,他称呼李良有几种可能,可以参考同时期的刘邦称呼臣子,或者称公、卿,或者称君,也可以直呼其名。
但是,书信是比较分外的文体,常日是一种对话的语境,该当利用第二人称,而不应该利用第三人称。换句话说,不可能从头至尾称呼李良的名字。
在信件的开头,可以称呼李良的名字,但是一旦进入信件正文,就一定利用第二人称,或尔,或汝之类的代词,而不是第三人称,直呼其名。由于第三人称表达的是客不雅观视角。
这封信从始至终全部利用第三人称,一定是错的,这明显是第三人在写书信,是察看犹豫者的叙事逻辑,而不是一封书信的对话逻辑。
第三个疑点:条件模糊如果想拉拢李良,书信开头必定是尊称,或称公卿,或称将军,或称君,来拉近二人的关系,然后劝降李良,给出条件。
秦二世是国君,他能急速给出明确的条件,而不是模糊的。书信只说让李良显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不是一把手的风格。如果条件不明确,实在是没诚意。
如果真的是秦二世的书信,他以前是怎么称呼李良的,李良一定是记得的。而且,秦二世明明可以开出比以前的条件更好的职位诱惑,这才算是一封标准的劝降信。
由于信中透露了,李良曾经侍奉过秦二世,那么李良对二世就有一定的理解,也可以判断这究竟是不是二世写的信,以二世的性情,他会不会写劝降书信,李良是有基本判断的。
以是李良疑惑这封书信,不信这封书信,是极为正常的。
从书信未封到内容存疑,再到劝降条件与二世的性情,李良都可以明确知道书信有问题。由此来看,李良的判断、决议确定能力并不差。
《鬼谷子·捭阖》
达民气之理,见变革之眹焉。
赵王的姐姐会道歉吗?李良尚未到达邯郸,在途中,碰着了赵王的姐姐外出饮宴归来。李良看见,以为是赵王来了,连忙在道旁伏地拜会。赵王的姐姐酩酊大醉,不知道他是将官,仅命随行骑兵向他存问。
李良向来尊贵,起身后,看着自己的随从官员,自觉羞惭极了。
李良受辱的问题能不能办理呢?可能性极小。
由于受辱是李良自己的感想熏染,尤其是在自己的随从官员面前栽了大面,丢了大人。被赵王的姐姐极其无礼地轻视了,李良在道旁施了大礼,而赵王姐姐用随行骑兵就把他丁宁了。
李良认为自己崇高,而赵王姐姐失落礼给李良带来了羞辱,实在,赵王姐姐这时喝得大醉,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又怎么可能知道侮辱了对方呢?
就算赵王姐姐醒酒了,他可能也断片儿了,根本回顾不起这件事儿来。
我们假设,李良没有杀去世赵王的姐姐,那么事后,就要看赵王姐姐的属下能不能把事情见告她。
再假设,属下见告了赵王姐姐,当天她失落礼了,对待李良有侮辱的嫌疑,那么她会认为自己侮辱李良了吗?大概会,大概不会。
再假设,赵王的姐姐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失落礼,那么她会不会道歉,来安抚理李良呢?大概会,大概不会。
假设的条件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赵王的姐姐道歉的可能性险些没有。
从君臣礼仪的角度来讲,李良看见赵王姐姐归来,以为是赵王来了,那就解释赵王的姐姐利用的礼仪规格与赵王是相同的,不然,李良也不会发生如此严重地误判。
实在,这也表明赵王的姐姐日常作风比较骄横,日常行为不谨慎,礼仪不完美,更不会严格哀求自己。
毕竟武臣也是刚刚自主为赵王,属于穷汉乍富,心态和行为习气难以改变。他的成功是借势而得,借的是朋友陈胜的光,而武臣自主为王,从臣子角度来讲,不忠实;从朋友角度来讲,无信义。
武臣自主为王,还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当他成为赵王之后,必须实行忠孝仁义。但是自主为王与忠孝仁义又是抵牾的,可惜还没等他想明白这些事儿,也没有人给他劝诫,他就已经被李良杀了。
从君臣道义来讲,武臣既是陈胜的朋友,又是陈胜的臣子,他攻陷赵国土地之后,可以独立一方势力,但最不适宜称王。
由于不用称王,他也可以霸占赵地,而自主为王便是背叛,示范浸染对付下属当然是负面影响,完备不符合顺守的计策。
冲动,有代价,或许也有机会随员中有一人说道:“天下背叛秦朝,有能耐的人先立为王。况且赵王的地位一向比您低,而今一个女流之辈就不肯为您下车还礼,故请追杀她!
”
李良已得到过二世的书信,原来即想背叛赵国,只是还未终极作出决议确定。于是便借着一时的愤怒,遣人追上去杀掉了赵王的姐姐,并趁势率军打击邯郸。
邯郸守兵毫无察觉,致使李良终于杀掉了赵王和左丞相邵骚。赵国人中有许多是张耳、陈馀的线人,及时通报,二人因此得以独自脱逃。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年夜大好人。李良的属下该当是识破了李良的心思,理解了李良的尴尬,知道他此时极其愤怒,以是就顺着他的感情,劝他追杀赵王姐姐。
这时肯定是一时冲动,人在冲动之时,是不可能基于理性思考的,更不可能进行短长权衡,而是要凭借冲动的感情,发泄一番。只有让感情发泄出来,才能高兴,才能舒心。这正是李良的须要,要安抚自己的愤怒,要找回自己的面子。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但是解完恨之后,究竟该当怎么办呢?李良可能也没有想,至少先解恨再说。实在这便是冲动的代价,李良的恨解了,但他没有选择了。如果忍耐下来可以连续,待在赵国,也可以投奔他方,选择的自由度更高一些。
杀了赵王的姐姐就相称于与赵王破碎了,要么连续杀下去,要么亡命。
这里有一个隐蔽的问题,是不是杀了赵王的姐姐,就一定要连续杀去世赵王和左丞相邵骚呢?李良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诡异的记载,李良得到了秦二世的书信,原来想要背叛赵国,只是还未做出决议确定。而李良得到的是秦将假造的二世书信,本来不相信,又怎么背叛了呢?不合逻辑。
比较合理的逻辑的阐明该当是:
李良杀掉赵王姐姐是一时愤怒所致,但是冲动之下,追杀了赵王的姐姐。此时一个机会涌现了,便是乘势攻入邯郸,杀掉了赵王和邵骚,而是还有了新的可能性。
由于当李良杀去世了赵王、左丞相邵骚、张耳、陈馀之后,他就可以顺势掌控赵国,可以作权臣,拥立一位新赵王,也可以自主为赵王,这极有可能是当时的动机,也更合理。
只不过张耳、陈馀逃走了,李良的操持没有完备成功,多了两个强大的对手。
李良的结局张耳、陈馀网络逃散的士卒,得到数万人,随即攻打李良。李良兵败而逃,归降了章邯。
消灭张耳、陈馀是李良掌权最主要的机会,只不过他失落败了,成王败寇,他只能归降章邯。由于他没有选择,无法投奔他人,只能屈膝降服佩服义军的仇敌——秦朝。
冲动之下,以臣弑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义军之中,谁又敢接管他呢?
在义军体系内,李良险些没有被接管的空间。他把路走绝了,让自己没有了选择权,只能选择屈膝降服佩服章邯。之后,章邯被项羽击败,屈膝降服佩服了项羽。而项羽又被刘邦击败,天下归于一统。
李良归降章邯之后,他就从历史中消逝了。有多种可能:
第一,李良归降章邯之后,被秦朝杀了。秦朝有处去世义军首领的记录。
第二,李良归降章邯之后,看不到秦朝有任何希望,选择了主动归隐,消逝在历史之中。
第三,李良追随章邯,而章邯被击败,章邯屈膝降服佩服项羽,李良不可能回归义军,选择了归隐,或者被项羽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