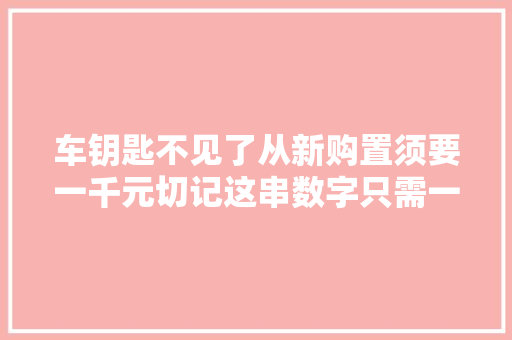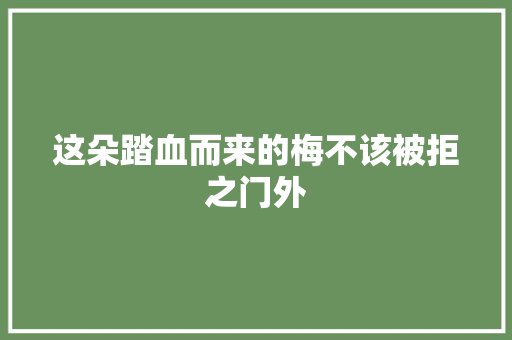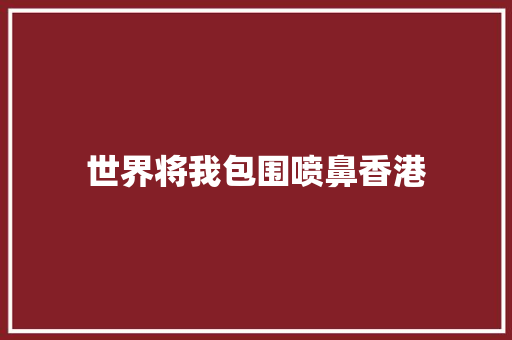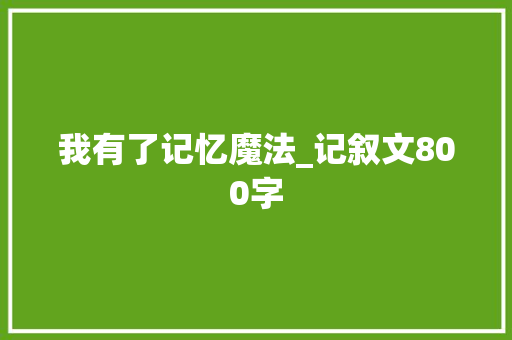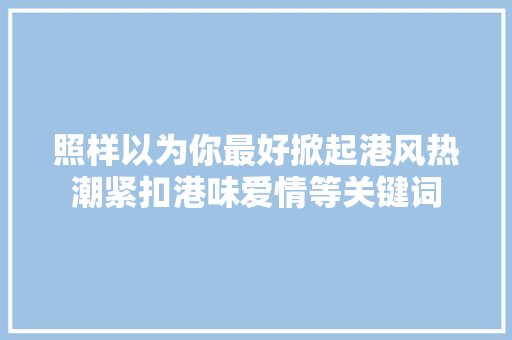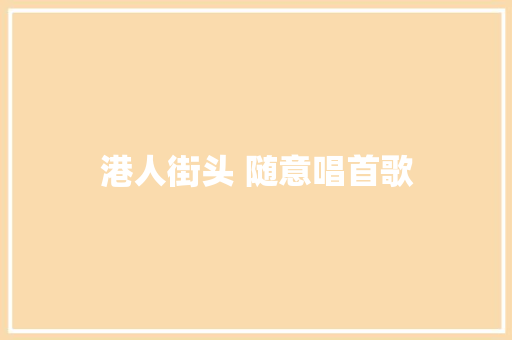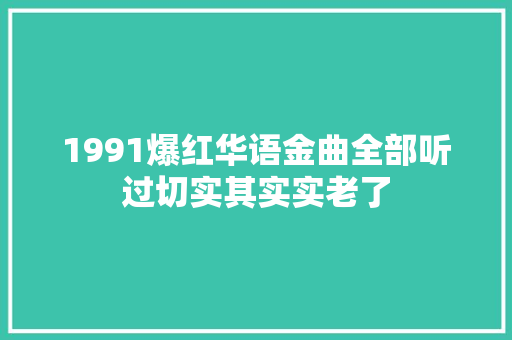文:潇湘客下
图:网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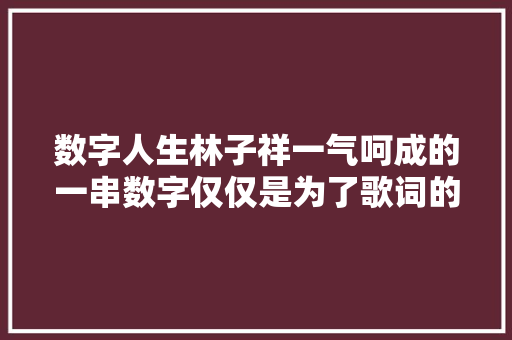
喜好光顾KTV的年轻人,时时会听到隔壁的包厢里传出持续串怪异的吼叫,仔细一听是用粤语唱的,并不是周杰伦的碎碎念。紧接着,当唱到“变咗1004”时,声带便撕裂了,唱歌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再往下唱就变成了鬼哭狼嚎。
不怪唱歌的人五音不全,要怪就怪他轻易去寻衅这首翻唱难度极高的《数字人生》。
这是林子祥的歌,创作于1986年,至今已有34个年头了。
这首歌之以是能够被人们记住,大概是由于它独特的歌词:整首歌险些都是由数字串联的,读来朗朗上口,充满韵律感。其余,有着“铁肺”之称的林子祥持续串令人应接不暇的连珠炮弹般的高音,也成为了KTV爱好者喜好寻衅的难度之一。
这首歌流传了这么多年,但提及它时,人们更多的是想起它怪异的歌词、高难度的唱法,仅此而已。
可是,又有多少人关心,歌词里面的一串串数字,到底是有何用意?
01 歌曲出身背景
听说,《数字人生》这首歌,是林子祥和编曲钟定一在一起打台球的时候,林子祥忽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鬼主张:把数字串联成一首歌来演绎。
林子祥的用意是,用数字反响当时的喷鼻香港人沉浸在成本数字的天下,“填满生平全是数字”,“烦恼生平全为数字”的情状。
此话还得从喷鼻香港的社会经济背景提及。
实在,从1840年中国割让喷鼻香港岛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朝鲜战役爆发一个世纪多的韶光,虽然喷鼻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跟日后的飞黄腾达比较,那切实其实是寰宇之别。
一者,在这段韶光里,喷鼻香港经历了二战的摧残。二者,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对西方市场险些做到了完备开放的状态,外国的资金、货色、人才,不必通过喷鼻香港,就能深入中国腹地。以是,当时的喷鼻香港经济飞腾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到了20世纪,喷鼻香港对付英国而言,军事计策意义远大于经济方面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向苏联,经济培植、科技发展也依赖苏联。以是,这个时候的喷鼻香港,在经济方面和内地关联并不大。反倒是从内地迁徙到喷鼻香港的人,繁荣了喷鼻香港的经济。要知道,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实在是上海,这是名副实在的国际化大都邑,有“东方巴黎”之称。后来抗日战役爆发了,很多上海人便坐着轮船,到喷鼻香港来避难,个中便包括了后来以邵氏影业有名的邵氏兄弟。
邵逸夫及其家族成员
而喷鼻香港的真正崛起,是在中苏关系彻底分裂,中美开始建交后。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开始洞开大门,引进西方工业生产设备,准备和西方成本主义国家打仗。
但是,和西方国家广泛进行贸易,建国后双方都未曾有过,也不太清楚贸易规则。再者,中国当时在系统编制上也对西方的职员、资金进入有所限定。这样,就对贸易的进程有所阻碍了。
那怎么办呢?只好先找一个贸易往来的中转站。于是,喷鼻香港等来了机会,开始迎来了经济的腾飞。
20世纪70年代起,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喷鼻香港一举成为了亚洲地区压倒一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央,有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号。随后,喷鼻香港成功完成了从以制造业为中央到以金融做事业为主的经济转型。
喷鼻香港的金融业非常发达。到了1986年,也便是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出身的韶光,喷鼻香港的四大证券交易所合并,市场的交易总额达到了1231.28亿港元,喷鼻香港顺理成章成为了天下三大金融中央(纽约、伦敦、喷鼻香港)。
以是,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喷鼻香港人,对金融领域是非常痴迷的,炒房、炒股、赛马,一点都不陌生。
电影《窃听风云》中有一个场景,一个阿婆炒股,市值惨遭腰斩,收市后阿婆就绝望地从高楼跳下去了。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的喷鼻香港,就发生过全民痴迷炒股的一幕。
正如歌词里说的,“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看看计数机里囚禁多少很多多少人质”。
在当时,一串串鬼魅的数字,完备囚禁了喷鼻香港人的灵魂。
02 歌词里面的数字代表了什么?
《数字人生》的词作者是喷鼻香港著名词人潘源良,林子祥、叶倩文、王杰、谭咏麟等著名歌星的很多歌曲,都是由他来填词的。作为喷鼻香港王牌填词人之一,潘源良自然不会随便填上一串数字来敷衍听众。
我们创造,林子祥在唱《数字人生》的时候,虽然唱的是看似很随意的数字,但听起来却朗朗上口,毫无违和感。轻微懂点粤语的人会知道,这些数字用粤语读起来,实在和唱歌没有什么差异。以是,只要你会粤语,不管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都能大致唱出它的调调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潘源良在填词的时候,作曲已经出来了(舶来品)。这时候,潘源良想的是,如何将粤语的九个音调,奥妙地和歌曲的腔调逐一对应。于是,经由一番推敲,歌词就出来了: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
之前看过一段林子祥登台演唱《数字人生》的视频,当时他已年届古稀。看的时候真为他捏一把汗。倒不是担心他唱歌高音会上不去,我们担心的是面对这么多繁芜随意的数字,年迈的他会不会忘词。后来终于知道,只要明白歌词在韵律上的玄妙之处,这担心就属于多余的了。
当然,从字面来看,歌词里面的数字也不是完备没故意义的。
如“明明刨正23,为何弹出41”,歌曲的间奏伴有跑马的号声,意思是市民赌马,买了2号3号,结果跑赢的是4号1号。
“4.34价位暴升变咗1004”,讲的是股市指数暴涨。正如前面所说,炒股是那个期间喷鼻香港街头巷尾热门谈论的话题。
而后面的“0 4 3 4 0 4 3 4,0 2 3 2 0 2 3 2……”,便是当时的股民热衷的股票代码了。
03 陷在数字里无法自拔的市民
在听林子祥不需换气快速说唱那一段数字歌词的时候,听众会不自觉地陷入为数字天下所猖獗迷炫的状态里面。正如歌词所说的,“凭号码来认识/你的IQ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统统”。
那个时期的喷鼻香港,正属于投资的狂热期间。而对数字狂热的背后,则是人们对灯红酒绿的物质天下的痴迷。
而现在的内地,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在当代,人和数字,早已紧密相连,无论是你的身份,你的身型,还是你的财产,你的统统,都须要用数字来量化。
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套房?你有多少辆车?你有多少人脉?这些都是当代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不自觉会去衡量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关乎你的社会地位。
当然,对有钱人的艳羡,对当权者的崇拜,不独是当代,自古便有之。可是能够将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量化到如此精准的程度,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古人知道沈万三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但沈万三到底有多少钱,平民百姓却没有办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目,也并不在乎详细数目是多少。而现在,马云、王健林到底有多少资产,普通人也能很轻易地就查出来,由于时时时就会有富豪榜之类的东西发布出来,供人敬仰。
陷在数字天下里无法自拔的市民,很随意马虎会忘却了冷冰冰的数字以外的天下的温度。他们或许不知道,也并不在乎,同样拥有100元公民币的张三和李四,虽然同样买回了几瓶烧酒,但他们却绕了不同的巷子,和不同的人讨价还价,这些都不是数字能够表示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一样是富豪的马云和王健林,在亿万身家的背后,连接的也是不一样的人生阅历,这些也不是数字所能表示的。
但,被“数字化”了的人类,会在乎这些吗?
04 有没有数字化以外的感知工具?
人类的“数字化”认知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相反,它是经历了漫漫历史长河才达成的。而这个“数字化”的认知模式,则依托于人的“视觉”感官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的视觉感官开始打败了味觉、触觉、听觉感官,成为了支配西方人思考的紧张形式。这种以视觉作为强势感官的思维办法,开始被人们归为“理性”的范畴。从那时候开始,绘画开始讲究人体比例(达芬奇解剖尸体理解人的构造),物理讲究实验对照(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医学更讲究临床研究。这便是所谓的“眼见为实”了吧。
既然是视觉占主体,那拿什么来精准衡量我们的视觉认知呢?于是,“数字化”便成为了理性、科学的根本,成为了我们视觉的表达工具。
这种思维从工业革命开始,传遍全天下,当然也轰开了我们的国门。
以数字来衡量统统,固然有它的好处,最少可以做到精准无误,这样才会有社会秩序的存在。在古代,秦始皇也要统一度量衡,才能使一个国家有效运转。但问题在于,习气利用数字的我们每每会忽略,这一串串数字,并不是事物的本身,它们只是衡量事物本身的工具而已。
比如,我们说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46,但“智商146”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这个东西吗?人的头脑里面并没有数字,146不过是为便于人们理解和比较,用来表达智力程度的工具而已。
再比如,人们说马云身价2388亿,“2388亿”也不是物质本身,它代表的是当下马云所拥有并能支配的社会资源而已。
正如波茨曼在《娱乐至去世》里面所说:“我们认识到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真面孔,而是它们在措辞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措辞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当代人随意马虎将数字看作是事物的实质,崇拜数字,实在和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似,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字是万物的本源,可是他们更多是用来作哲学、数学的研究而已。而当代人呢,则是利用它来作为抢夺资源的借口,金钱至上,这些都固化成了一串串高高在上的数字。
数字化令人逐渐分开了人可以去感知的“温度”。那么,有没有数字化以外的感知工具呢?
自然是有的。
波茨曼说:“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期间,大自然的措辞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措辞。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也便是说,在“视觉化”、“数字化”占主导之前,人类还有更和谐的感知天下的办法,大概是各种感官的综合,反正并不独倾向于“数字化”模式,这使得人类的生活更有神秘感、崇高感。
比方说,中国的厨师在传授炒菜秘方时,会说“放少许盐”,“节制火候”,这是游离于数字计量体系之外的,由于我们的数字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依赖“手感”来把握的东西。有人考试测验过将这些详细到以确切的数字来描述,如“放少许盐”变为“放3克盐”,可是炒出来的菜还是欠“火候”,少了鲜美之感。
这表明,我们的措辞在描述触感的时候,是很贫乏的。可是,这样的觉得又比纯数字精妙得多,最少这里的措辞是有温度、有弹性的,而不是硬生生的去世板的数字。
看看计数机里面囚禁多少很多多少人质?
大概从数字堆里面解脱出来,人才会有更多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