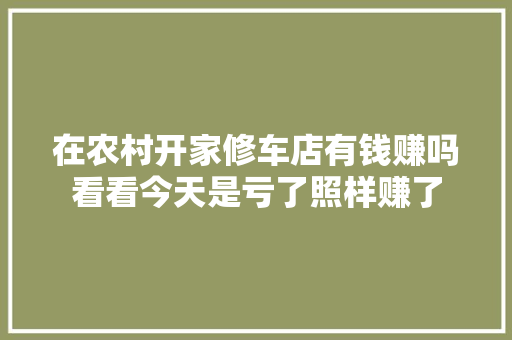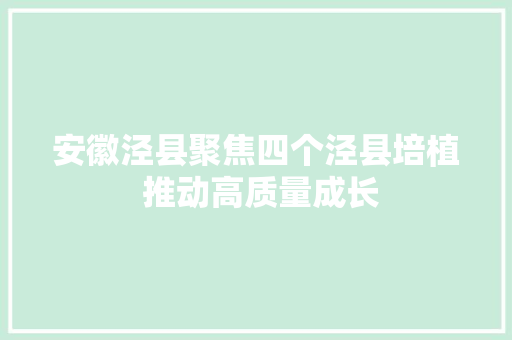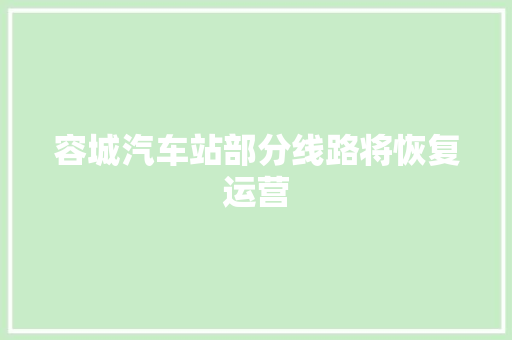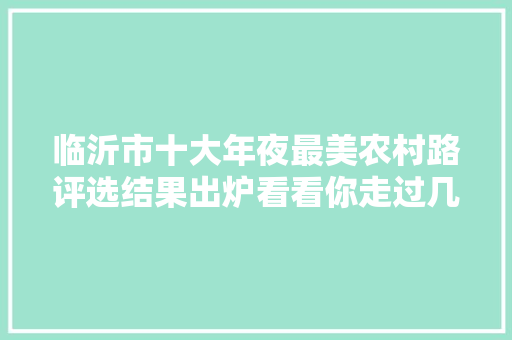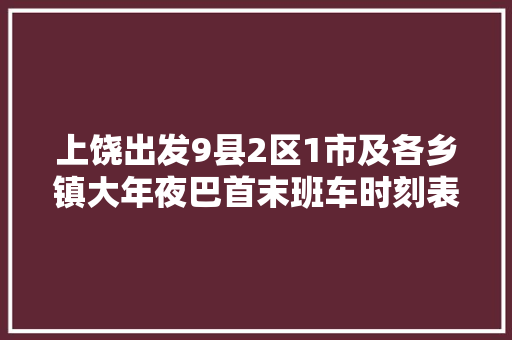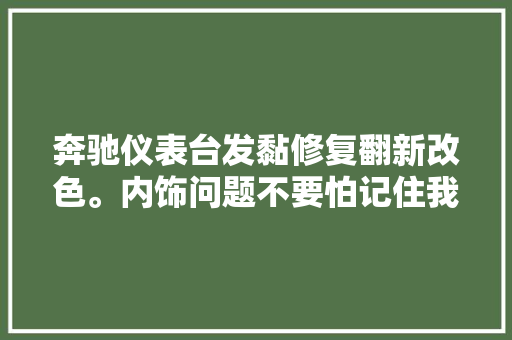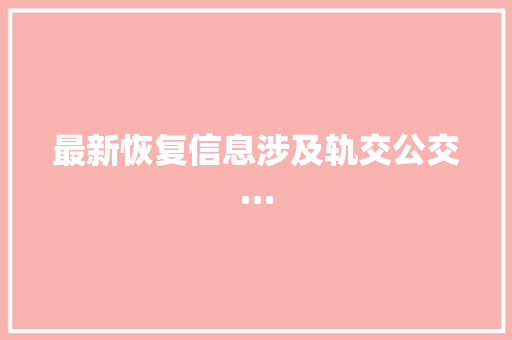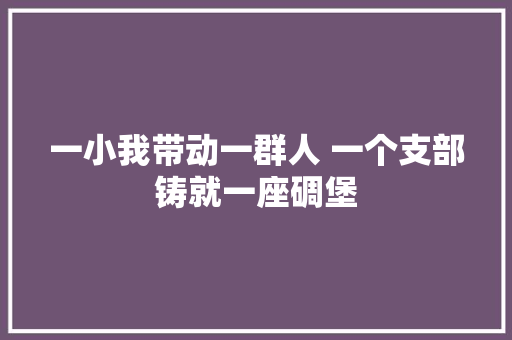为何重大,他不阐明,只是“想通过唱歌通报此刻‘六’字头末了的心情”。就像他漫长的46年创作生涯中的700多首歌,无论音乐风格如何变革,隽永、深邃,年夜胆注目韶光黑洞的词意不变,隐约窥见生命奥义的敏锐知觉也未变。
《星》确是亚洲公民的共同影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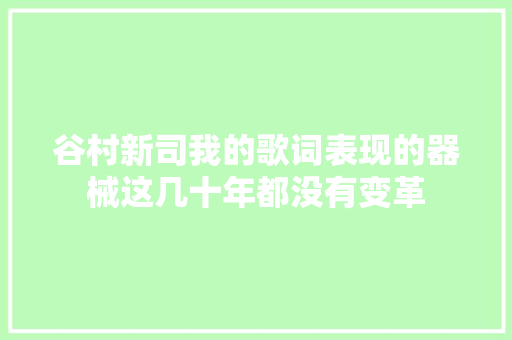
六十九岁这一年,谷村落新司在上海再一次唱了《星》。不仅在9月21日晚上海大剧院“38年的星”演唱会,去年同样在这里的“谷村落新司演艺生涯45周年”演唱会上,他亦唱了这首歌。
谷村落新司演唱会 本文图片由主理方供应
这首他唱过无数遍的歌,不仅每每在外洋的演唱会必唱,还在今年发行的新专辑《38年的星》中又重新录了一版。“编曲完备和当年一样,只是声音显而易见地老了。一首歌就像一瓶酒,刚酿成时芬芳剧烈,随韶光变革会逐步变得醇厚。”
你可以说他守旧,也可以理解为早慧的人对宝贵之物的爱惜和守护。他珍惜这首歌,“《星》是打开全亚洲大门的钥匙,能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收录《星》的同名专辑发行于1980年4月。这是一首孤独的歌,封面上谷村落在幽蓝的路灯下低头行夜路,城市如荒野和他一起静默。这张专辑很成功,尤其是《星》,被改编身分歧措辞的版本在亚洲流传,关正杰的《星》(郑国江填词)和邓丽君的日、粤两个版本在华语区尤其有名。在中国大陆,沈小岑收录在第二张专辑中的日语版《星》则犹如在岩壁上凿开一个洞,歌迷们开始想尽办法搜集日语歌曲,产生了对表面天下的好奇心。
演唱会海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星》确是亚洲公民的共同影象。它的孤独和光华不须要措辞的通报就能击中民气。谷村落新司所作的旋律兼具日本传统歌谣的忧伤,以及唐诗疏朗、开阔、悠远的意境,在文化附近处更引人共鸣。
舞台上,这个瘦小又快乐的老头很早便窥到命运的奥秘。想象茫茫黄色草地、远方的群山和凉风的场景时,谷村落新司并不知道这是哪里。一贯到歌写完,才想起来“这样的景象一定在中国”。写下这首歌的时候(1980年),谷村落新司不过32岁。
吹入胸中的寒风和激情亲切的梦想交织;散落四方的命运之星既是他告别的工具,亦是将迎来更多后来者的亘古不变的存在。
被很多人翻唱过的《星》日语原名译为“昴”更准确。昴星团是夜空中最通亮的星团之一,在秋冬时令尤其光华残酷。谷村落的《昴》不是乐不雅观,也不是悲观,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诉说。它就像无法言说的命运本身,迷茫、孤寂、抵牾,又仍旧是有希望而通亮的。
他把这首歌叫作“幸福的歌曲”。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自少年时已开始
采访谷村落新司的时候,目光总是被他细长的手指吸引。这双手本身就拥有丰富的语汇,相形之下谷村落本人反而没有那么健谈。他的人和歌一样安静。
不抵牾的却是谷村落新司身上浓浓的昭和遗风,4000多场演唱会和3000多万张唱片销量的数字可见他的勤奋。他是范例的战后日本一代人代表,自傲、朝气发达而对邻国友善,始终致力于关心儿童奇迹和音乐教诲奇迹。这位大叔无可指摘,这天本乐坛一位挺括而备受尊重的前辈。
谷村落新司演唱会现场
他是有定力的人。无论政治潮流如何变革,他始终以一位艺术家的良知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曾是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滕俊杰和谷村落是近二十年的老友。他记得谷村落近乎天真的羞辱:“安倍、小泉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过不去,他直接去找小泉,跟他说对中国的态度必须改变。日本必须跟中国站在一起,我们亚洲两个国家要负起这个任务。”
在谷村落新司生动的年代,旺健而丰硕的昭和时期即将步入尾声,却也迸发残酷光芒。《银河英雄传说》的开篇,田中芳树的“提高!
再提高!
”至今令人浑身一震,“奥特曼”系列的发达、昂扬,以及对社会、科技和自身境遇的反思精神都是真实的昭和写照。当时,这种乐不雅观的国民精神被称为“一亿总中流”,即有一亿人口认为自己是中产。
那个时期,民众相信奋斗能带来更好的生活,相信自己文化的独一无二性。无论银幕还是文学形象里,男女皆剑眉星目、康健爽朗。虽然昭和时期并非每个男人都是高仓健,每个女人都是山口百惠,但他们的确这天本当代史上最令人怀念的形象。
日本文化固有的“物哀”和“武士道”,对传统文化的恪守和对外来文化高度收受接管的两极,都在开放的昭和时期后期得到平衡,亦在谷村落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示。
他身上还有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融,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自他的少年时期已经开始。有一条传说,说他17岁时去东京武道馆看了披头士的东京首演(1966年7月1日)。一问,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但有一点是真的,16岁时谷村落新司和伙伴们组建了第一支乐团Rock Candie,“风格偏村落庄民谣”。
谷村落新司演唱会
更猖獗的是,1970年这支乐队还做了一次“美洲大陆巡演”。实际情形和听起来的很不一样,“我们首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由于穷,只能搭乘横穿北美大陆的巴士一起去纽约,路上睡觉什么的都是在车上办理。”这样一起走一起演,舞台便是街边,用了十天的韶光还真的抵达了纽约。
在纽约,除了演出当然更要看演出。谷村落新司看了不少摇滚演出,创造“音乐原来可以喊也可以叫”。“在Janis Joplin的现场我流下了眼泪,原来音乐还有这样的可能。”
次年返国他便组建了新乐队Alice。这支乐队持续了约十年,见证了谷村落从籍籍无名的少年景为整日本人尽皆知的超级明星。
1976年,他创下一年演出303场的日本音乐史记录。此时他已经奠定自己的风格,青春的躁动汇入大河奔流。“在不同的期间人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音乐也在一直变革。但是歌词表现的东西,这几十年里都没有变革。它们是我的人生不雅观不断累积而就的结晶。”
年轻时对人生中各类抵牾的敏锐感知,和年纪渐长后更加真切的思考,出道46年,唱了4000多个现场的谷村落新司的创作始终环绕这同一个主题。
“栽培了常石磊”,是一个俏丽的误会
谷村落新司第一次踏上中国的舞台是1981年8月2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中国歌手们共同参加了《Hand in Hand北京》的演唱会。此行亦让他的目光投向了全体亚洲地区。
第一次来上海则是1994年在万体馆的“亚洲巡覆信乐会”,他代表日本出席。
去年的演唱会上,他又一次讲了当年和谭咏麟、韩国赵容弼三人如桃园三杰般赌咒,要让音乐、让亚洲成为一体的大愿。
他是个天真的人,这样的欲望听起来难免不免太过艺术家的一厢宁愿,纵然在政治氛围浓厚的1980年代,亦未必有能够生根萌芽的土壤。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滞身体力行地搭建中日沟通的桥梁。
谷村落新司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演出的视频截图
2010年上海世博会,滕俊杰希望约请谷村落新司登台。不巧,那段韶光谷村落有整日本的二十多场演出,世博会恰好卡在巡演中间。谷村落希望滕俊杰给他三天韶光考虑,谁知一天后他便回答:“可以”。为此他打了很多个电话说服与报歉、做出很多赔偿,方能成行。
同样令滕俊杰印象深刻的是谷村落新司作为艺术家的敬业。唱了无数遍的《星》,“为了每一次主要的中国约请,他一定是负责走台的。而且他一定是每次走台的演出都是直接开口唱,绝对不敷衍。”
除了光鲜的舞台和政治层面的互换,谷村落也乐意花韶光面对面地与中国年轻人互换,努力把很难以言传的音乐教授给中国的学生。
2004-2008年,谷村落新司在上海音乐学院担当客座教授期间,“每个月都有一周的韶光在上海度过”。谷村落老师的课很实在,他请每位学生作词,然后帮助他们完成谱曲、编曲、上舞台的全过程。“我很看重把握每位学生的个性。”
外界流传的“栽培了常石磊”,反而是一个俏丽的误会。“我到的第一堂课,学生们给我做了个欢迎仪式,常石磊为我唱了一首歌,对我说:您能来我很高兴。”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他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人,我惊异于当时的上海还有那么有才华的音乐人。常石磊那个时候什么都已经会了,险些不怎么来上课。我们的全部交集便是那一次欢迎仪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