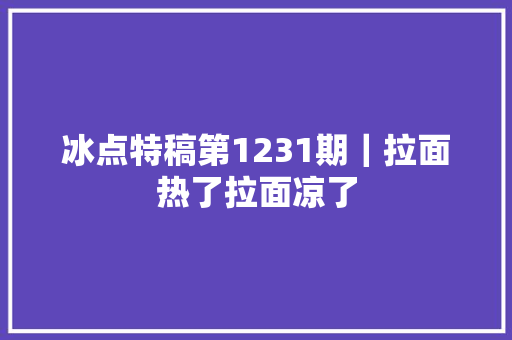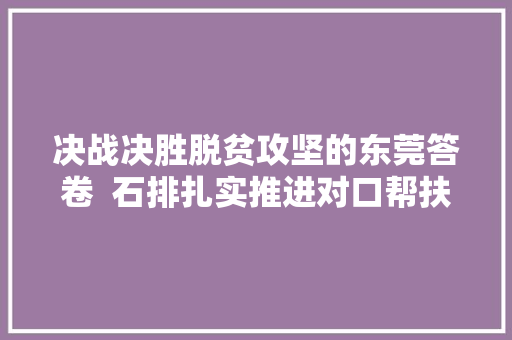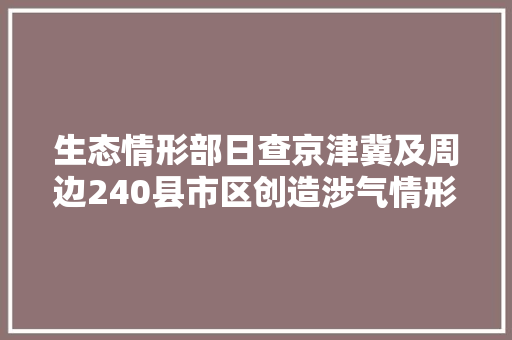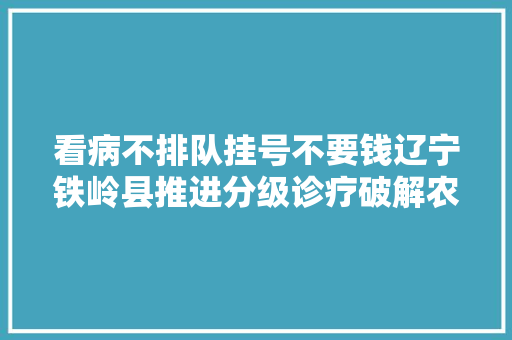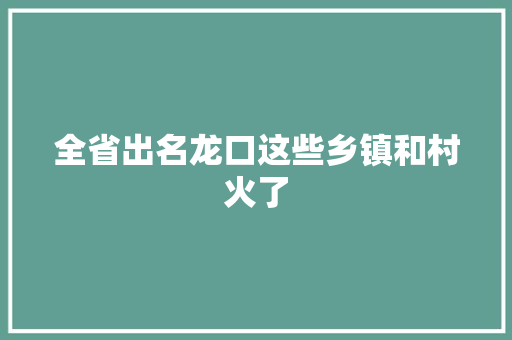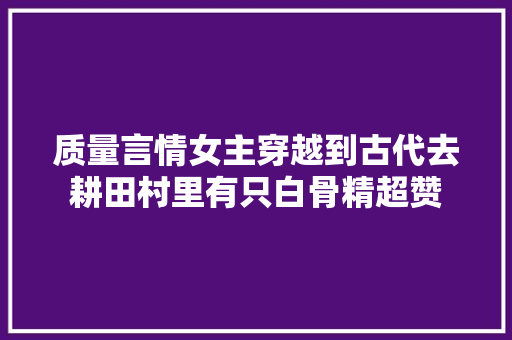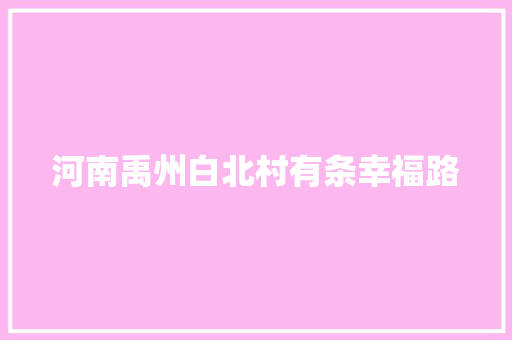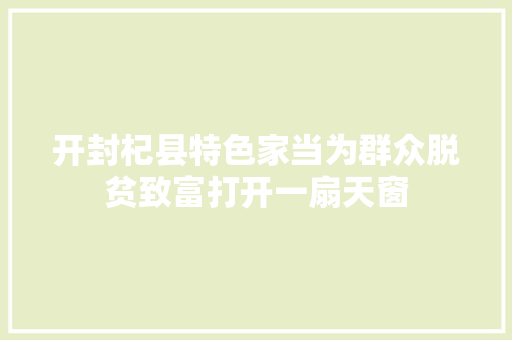6月30日,朱强在当晚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距。郑梦雨摄
江南梅雨歇。夜幕降临,水乡巷陌间,胶片投影机发出的光柱伴着蝉鸣,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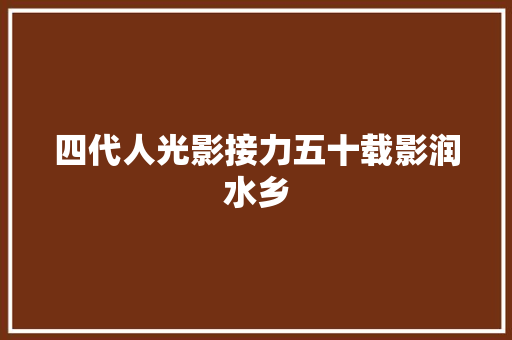
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小村落里,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50余年。“流动电影院”又开场,“哒哒”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迁徙改变了整村落人的文化生活。
数字时期的陡然降临“逼退”了胶片电影,而胶片放映的传统技艺和古老滋味,却在他们的双手中,在一帧一帧的胶片画面间,一代代承续着。
第一代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落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光阴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
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垂垂靠向岸边的村落庄。几样物件看似大略,却寄托着当地村落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能、电工、利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巨,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军队要照顾20到30个村落。”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顾。虽然险些一年四季都流落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不雅观众围上来,他也会以为自己的事情有了意义。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称于一全体县城的人都来了。”
为做事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专场”。他回顾,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时,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
在他印象里,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部分苏联译制片。故事片《白毛女》以及被称为“老三战”片的《出生入死》《隧道战》《地雷战》等最受百姓欢迎。“潜移默化中,看电影成了村落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须要。”王志华感叹。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逻辑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州里。
第二代
村落村落挂银幕,大家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公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不雅观众太多了,恐怕放映机有缺点,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顾道。
在很长一段韶光里,放电影都是村落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羊毫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落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凌驾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用饭。村落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落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胶片一旦转起来,就要从头至尾放完,非极度情形中途绝不停机。“只要有人看,我们就放,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赖。”朱文炳说,一次放映时溘然下起大雨,不雅观众志愿帮忙抢救机器。
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还有很多人满心欢畅地站着等。深夜电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那是冬天,到处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朱文炳说,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期,何其有幸。
第三代
大树剪下枝,又生出枝繁叶茂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由于履历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连续奔波在各个村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以为,总会有一些村落民由于路途迢遥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事情的空隙韶光,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屯子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便是十余载。
“要想把村落民重新拉回银幕前,就得理解他们的真切想法。”朱生荣说,以前村落民娱乐休闲办法少,幕布一拉,不管放什么,附近十里八村落都会赶来看。“90年代,很多村落民虽然家里有了电视,但随着村落庄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特殊是偏远地区,大家住得散,内心感到孤独,很想求个热闹。”
“平时难得打照面,实在就趁着看电影的机会,大伙儿聊谈天,互换互换,这是在家里看电视得不到的乐趣。”朱生荣说。
村落里办喜事,乡亲们也会找来朱生荣的电影队。“有一户人家喜逢老人百岁五世同堂,我就给他们放了一部《五女拜寿》。”朱生荣说,虽然放映队的任务不再纯粹是放电影,但能给乡亲们带来快乐,繁荣屯子文化阵地,他的事情就故意义。
“就像从大树上剪下一株枝条,把它扦插在地皮里,又生出了枝繁叶茂。”从小在电影队里终年夜的朱强这么形容父亲的放映队,而这枝条也逐渐在朱强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第四代
光影经年沉淀,再次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义务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海内影院开始大量遍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落庄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末了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以为,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
从小在电影幕布前终年夜,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朱强说,时至今日,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城南往事》,“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表现手腕还是精神内涵,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恰巧碰着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
查阅资料,他创造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热友追捧。
至此,朱强开始到处征采老式电影机和干系设备。“前几年,全国各地不少老影院倒闭,一样平常会对音响等设备进行变卖,他们出售的音响设备不仅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我常去购买。”几年下来,光是购买各种电影机设备器材,花费就超过150万元公民币。
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种经典放映机。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期的影象,也为几代放映员供应了“重温手艺”的地方。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供应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小暑”过后,梅雨暂歇。朱强想利用难得的晴好天气,为离洲泉不远的乌镇乡亲放一场露天胶片电影。
卸设备、架放映机、调音响,朱生荣父子闇练负责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很快,两台珍藏的老式35毫米电影胶片放映机就迁徙改变起来。
“哒哒哒……”经年沉淀的光影,在白色的幕布上,再一次光彩动人。(段菁菁、郑梦雨、席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