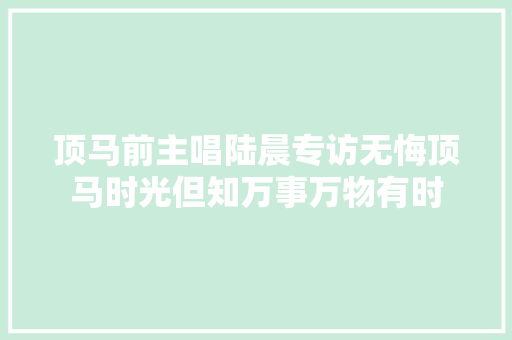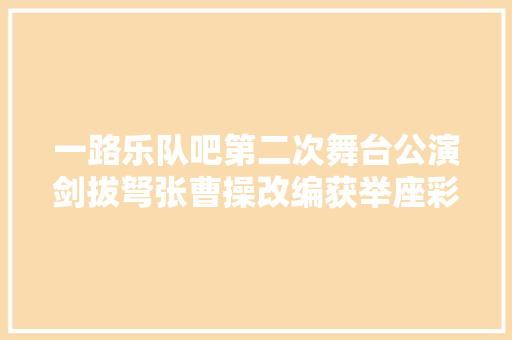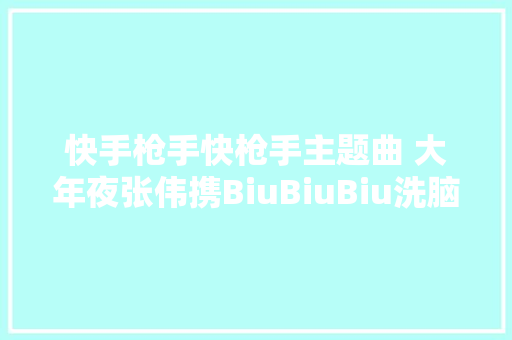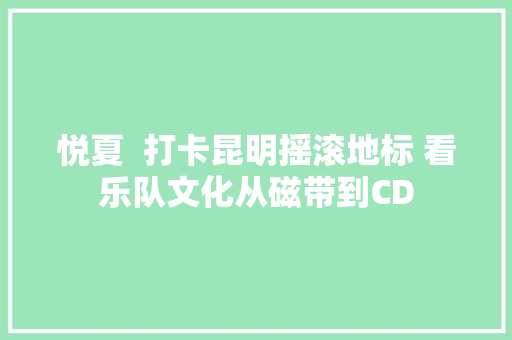/张月寒
新木马乐队成员(由左至右):吉他手邓力源、主唱谢强、鼓手张大伟(高源 摄)

木马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旧城之王》。就像站在一片华美的废墟上,“木玛”谢强戴着旧时摇滚之王的帽子,用他“特有的拖音强度”,诠释着对生命某一阶段的理解。你看他的记录片,看他的现场演出,会很随意马虎生发出一种感慨:这是一个真正的摇滚明星啊。然而,那天在北京一个影棚,向我走来的谢强,脸上没有任何扮装。蜕除了舞台装扮的摇滚明星,现实里非常谦和、沉着。
学会摇滚
谢强出生在“铁路上拉来的城市”株洲,铁轨很早就成为他生命里一个意象,对父系生活办法的逃离也是通过铁路。他15岁坐火车来到北京,进入迷笛音乐学校,那是1995年底。
迷笛音乐学校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很多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都曾在这里学习。90年代,迷笛的传授教化还不是那么有系统有脉络,更像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面孔乐队的主唱陈辉、零点乐队的老五、黑豹乐队的丁武,都在迷笛讲过课。
谢强很长于社交。他的学习便是混入不同的圈子,跟不同的人交往。“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得到和给予,是通过人际交往完成的。”在北京,他住过很多文艺青年的聚居地,迷笛、工艺美院、圆明园村落,每天阅读睡觉弹琴饮酒写东西。为了生存,他也去卖过打口碟,混迹过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他住在美院两年,在那里排练,跟美院的老师一起玩乐队,也在美院蹭课,聊着蹭着,很多美术的知识也学习到了。
谢强在《乐队的夏天2》现场演出(《乐队的夏天2》节目组供应)
当时北京给摇滚乐的舞台还不太多,很多乐队都在“走穴”。有时一些使馆、文化部的活动,也会请乐队演出。“乐队的演出费,都是用外汇券结账。当时玩摇滚给人一种很高真个觉得。”
谢强混迹于这些现场演出,刚开始须要买票,后来人混熟了,就不用买了。在台下,他不断摸索别的乐队若何演,找机会和大咖搭话,也期望有一日,自己可以成为台上的那个人。
迷笛在很长一段韶光里,都是谢强借住的地方,“三个人挤一个小房间”,也是他结识人的地方。他先认识了吴维(后来的生命之饼乐队主唱)、曹操,三人组了一支没有名字的乐队。后来,他又结识了从高中退学来迷笛学习的胡湖。1998年,谢强和曹操、胡湖组建了木马乐队。
或许是来京几年后惦记家乡的味道了,乐队组建后不久,谢强就极力奉劝队友去长沙排练,情由是北京生活本钱高,末了还加上一条“湘女多情”。他们在临着湘江的山里租了一幢二层的屋子。扒歌、创作、排练,一批成形的作品出来了。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谢强回到北京,出火车站直接打车去了迷笛学校,在小房间里猖獗写词,终极形成了木马乐队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雏形。2000年初,摩登天空发行了它。
那一期间,中国最早的一批乐评人也开始涌现。受这些乐评人的文章影响,很多年轻的摇滚创作者以为摇滚乐必须有一种精神,谢强也是个中一员。他猖獗杂糅,把垮掉派墨客艾伦·金斯堡、作家卡夫卡、导演大卫·林奇等人的东西往自己的作品里糅,往摇滚里糅,以是当时一些作品,他以为很“上精神”。但现在看来,谢强跟我说,他以为摇滚乐“精神特主要,但精神也没那么主要”。
木马美学
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谢强最先出圈是由于他的眼线。《旧城之王》的音乐响起,镜头前一个特写镜头,他眼睛微挑,眼线的弧度完美显现。弹幕上立即惊呼:啊!
眼线画得比我还好。
一贯以来,乐队的走红,和他们的整体风格以及亮眼的主唱有关。这种风格,不仅表示在音乐的风格上,也表现在主唱和乐队成员的服装、造型、范儿上。
据凯文·J.H.德特马的《摇滚!
摇滚的前世今生》一书所述,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首创了摇滚歌手撩拨不雅观众的先河,他在舞台上的做派是每场秀最赚人眼球的部分:大背头、画眼影、涂唇膏,穿着有个性。
很多乐迷评价木马的演出“撩拨且妖娆不腻”。这是浓郁,无论是妆的浓郁、造型的浓郁,还是早期歌词里青春撕裂的浓郁。浓郁感来源于北京带给谢强的第一眼感想熏染。一个少年,溘然从南方到北方,这种位移让他在色彩上体会到一种急剧变革。“阳光残酷”从纸面跃到现实,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意义。还有大片大片的干,任何水分,在这片地皮彷佛都会很快蒸发、消逝,这让“一年有半年都不才雨景象”的南方孩子,颇感惊异。
在美院的浸淫也构成了他视觉审美的一部分。木马乐队早期,造型是他们吸引不雅观众的一大成分。预算有限的日子,谢强拉着乐队成员去天津、武汉的旧货市场,淘国外流回的旧衣,只要几块钱一件。有时能淘到一些大牌,穿上身,以为全体人都不一样了。后来,帽子的涌现,让他终极形成了自己的演出标志——海盗帽、大的圆礼帽、绒质的圆顶无檐帽……帽子成为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到本日,谢强以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木马美学”,外界评论他们是“华美摇滚”。
“旧城”之王
谢强经历过“土摇”最辉煌的期间,也体验过作为一个摇滚明星,在舞台上忘我演奏、汗水与不雅观众泪水融为一体的那种极致。他找到了一些那么亲密,骨子里和创作上都分不开的乐队成员,只管他们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今年,在这个不雅观众基数更大的平台,他唱的是一首关于失落落的歌。
失落落感来源于巡演路途中的感想熏染。他创造很多城市的老城区都在逐渐消逝。所有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没有差异。这种变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旧城虽然脏乱差,但那里人们脸上的神色是生动的。新城虽然簇新当代,但整洁里边有一种潦草。在旧城那些脏乱差里,在那些看似的缺点中,实在有一种精确。”谢强说。
这些年,“摇滚乐中央”北京也彷佛逐渐蜕变为旧城。北京曾是每个玩摇滚的人都必须来的一个地方。“90年代,当人们说喜好中国摇滚乐,实在说的便是北京摇滚乐。”当时很多乐队的演唱办法,比如说崔健、黑豹、唐朝,都是用北京话的口吻唱出来的。而且北京的使馆、对外文化单位多,最早一批打仗摇滚乐的人,是通过与这些涉外职员的打仗,以及打口碟的传入,才逐步打仗到摇滚乐。在那个年代,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土壤。
后来,五道口的亚梦、幸福村落年华、嚎叫俱乐部,东四的忙蜂、黄亭子的莱茵河声场和王勇的Keep in Touch酒吧等,给了乐队更多的现场演出舞台。再后来,是著名的D-22时期。
D-22是2008~2010年全国最生动的独立音乐演出场所,它的老板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在美国和中国经营独立音乐厂牌。那一期间D-22出了一批代表乐队:Carsick Cars、刺猬、Joyside、后海大鲨鱼、嘎调等,在中国摇滚史上留下光芒的一笔。木马乐队在D-22只登台过一次,但谢强常常去那儿看演出。他欣赏刺猬乐队,不是那种玩动静的乐队,“不像有些乐队会故意玩大招,怕别人以为自己没有技能。刺猬真的因此写歌为重点,旋律大略却生动,不是一味地模拟西方”。他跟Joyside关系也很好,“他们特殊朋克,但是又有一个深有追求的主唱,这点让他们跟别的朋克摇滚乐队拉开了细节上的差距”。
他们都曾狠狠躁过一阵。但如今,就像很多摇滚人的青春,北京作为旧时摇滚中央的地位,也彷佛一去不复返。“它不可避免地被分解、解构,分解往后造成新的起伏。”
这实在类似谢强在巡演过程中的城市不雅观感。当各个城市间物质的差异越来越小时,很多音乐创作者也不再以为须要离开他们熟习的环境、家乡的美食以及相似文化背景的不雅观众了。谢强见告我,不但是近年,早些年的一些乐队,也已通过口音、歌词,来分解北京给予他们的措辞感想熏染。比如舌头乐队,他们的歌词已经不是北京的措辞了,新疆味儿的唱腔涌如今他们的作品里。近几年,有更多乐队是带着自己的地域措辞特色在创作,比如《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人气很高的五条人。“中国新一代的摇滚人,他们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革,新一代可以打仗到的音乐种类,我们当年无法比较。他们很多很小时就去国外看过音乐节,心里面更有创作自傲。”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时期”。谢强现在认为摇滚乐不是关于反抗,也不是关于不满,所谓的反抗,只是在探求平衡。“不懂探求平衡的反抗,便是屈曲。”于是,他从嚎叫变为吟唱,从在音乐中找答案,变为如今的娓娓道来。这个旧城摇滚人,此刻说:“摇滚乐只是一个空的容器,主要的是它背后的人,在里边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