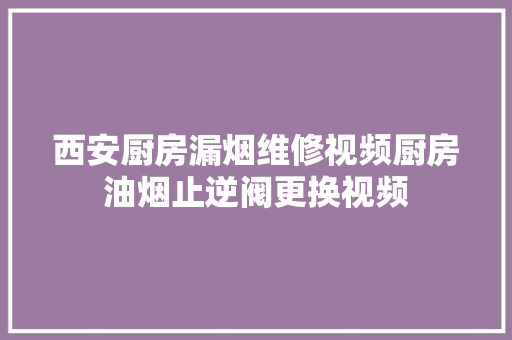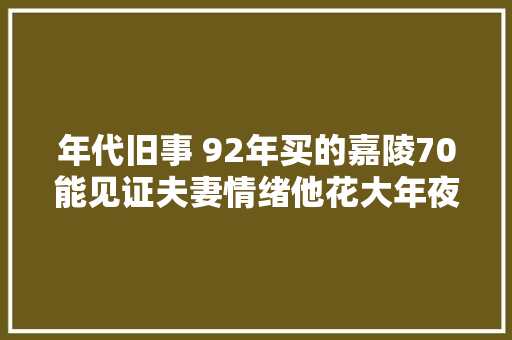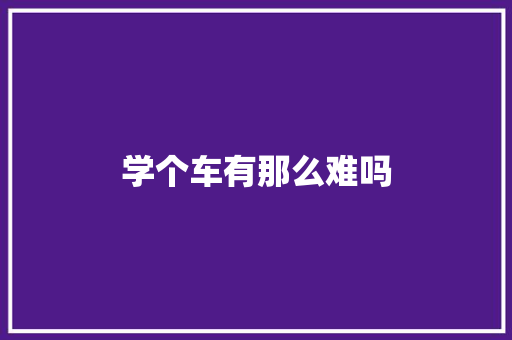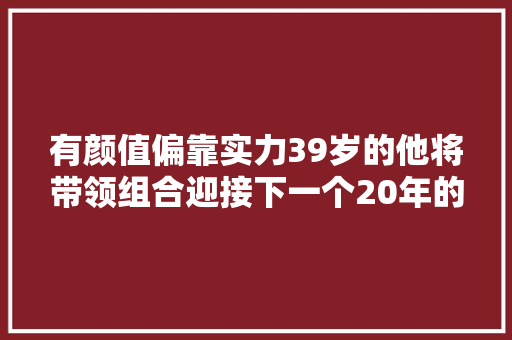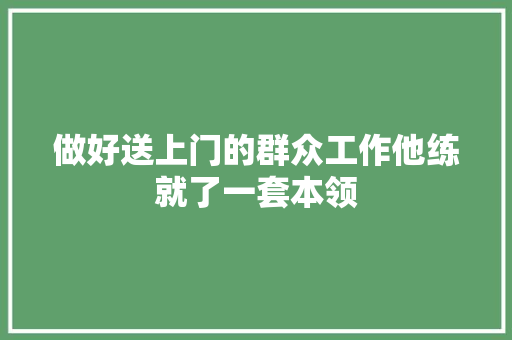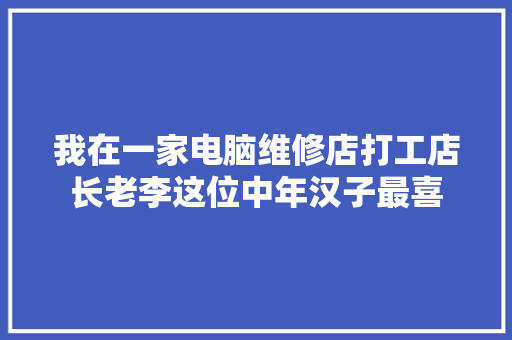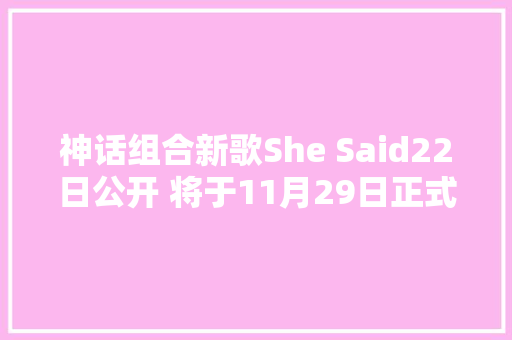秃尾巴老李的民间形象
小时候我觉悟不高,没有孔役夫那种“不语怪力乱神”的气概,反而常常被这种龙争虎斗斗法降妖的故事哄得五迷三道,还曾经为了一个孙悟空的头像买了一整盒“龙牧壮骨颗粒”,以是你要问我拼音排序表咋背我溜不下来,这种故事我倒是时时时拿出来咂摸咂摸滋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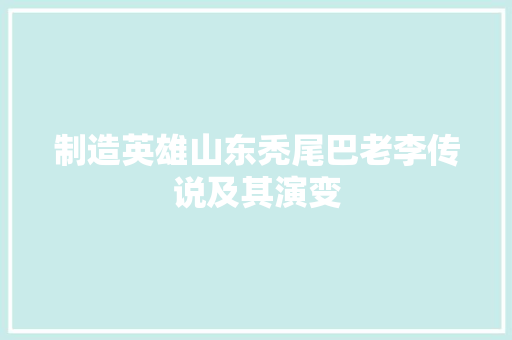
莫言师长西席为“秃尾巴老李”题写的墨宝
但是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纯洁程度的不断低落,我越咂摸这个故事越觉得出来一种奇怪的割裂感:首先“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本身的叙事就有很强的断裂感,从黑龙给娘上坟那里一截两半,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故事,一个犹如“二十四孝故事”一样平常平和,另一个却又有很强的争斗色彩;其次,地域上存在很大的割裂感,“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基本流传于即墨、诸城、滕州等地,虽然比较分散,但是流传范围基本在山东地区,那为何非要提所谓黑龙江一嘴呢?而且这个故事在东北也有一定流传度,至今黑龙江仍有黑龙潭、黑龙庙等相似敬拜场所;再其次,经上网搜索,关于“秃尾巴老李”的这个传说各市之间都各具特色,例如诸城结合苏轼在本地做官的历史典故将“苏轼祈雨”的故事融入个中,即墨又有“黑龙戏锦鲤”之说法,每年农历六月十三都会举办龙王庙会……如此各类,彷佛都找不到一个得当的阐明,而且对付这样一条“黑龙”,为什么要去结合本地特色去传承阐述呢?这种神话阐述又是如何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呢?这些问题也便使得全体传说割裂了起来。
关于“秃尾巴老李”的故事书
史估中对付“秃尾巴老李”相似故事的记载是出自袁枚的《子不语》,全文如下:“山东文登县毕氏妇,三月间浣衣池上,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心异之,以为暮春时不应有李,采而食焉,甘美非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产一小龙,长二尺许,坠地即飞去。到清晨必来饮其母之乳。父恶而持刀逐之,断其尾,小龙从此不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小龙并没有“老李”一称,并且仅为全体传说中的极少一部分,对付黑龙服丧与双龙缠斗的故事完备没有提及,可以确定的是,《子不语》中的这个故事,完备是一种古代条记小说的写作手腕,形式大略,内容浅近,那么可以确定的是,“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流传至今,是经由一代一代改造改动而成的,那么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从西方之“诠释学”的研究方法或许能得到一些新鲜的思路。
袁枚《子不语》书影
在磋商之前,我们最好先界定一下我们要磋商的两个问题:1:对“秃尾巴老李”传说故事的增长有何浸染?2:为何要增长“二龙相争”一故事来与黑龙江相结合?
第一个问题是神话叙事的历史性的问题,经查阅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黑龙与白龙争斗以及老李哭丧之事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闯关东期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神话叙事的角度来磋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叙事功能》一文所提出的理论,他在此文中对付“历史性”是如此定义的:“我们书写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是如此的历史天生物。“我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历史的见证物,而我们自身也深受全体历史的影响。“而“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亦是如此,山东人在闯关东的历史事宜中进一步改造了这个神话,而他们自身也是与这个传说相结合的历史天生物。保罗利科强调:虚构叙事中也有模式化情节,且叙事情节发展是时序性的。具有构造脾气节与反复涌现之整体意义的叙事,皆有其传统根基。他称,一种叙事构造只在与一种叙事传统长期联结之后,才可能被我们发掘。且虚构叙事也有实在际的指涉,人们书写历史,并生活在为历史形塑的社会现实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是相辅相成的,历史叙事虽然无可避免的有虚构的身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响了社会现实的“表征”,而虚构叙事则通过其“故事情节的”一种创造性仿照(可以理解为“隐喻”),暂时搁置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从而与历史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共同组成了人类历史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秃尾巴老李全体故事情节及其演化,一定是有实在际指涉的,那么它隐喻着什么呢?这样的隐喻又有什么社会效应呢?
保罗•利科
为了探求这件事情的原形,我们调研团队专门翻阅了神话学的一些资料,精读了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学》与王明珂先生长西席的一些文章,逐渐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自我的一些不雅观点。在从神话学磋商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罗兰巴特从措辞构造层面为“神话”下的定义:从一样平常的措辞构造来看,能指(表达一个意义的措辞形式)与所值(措辞构造所表达的意义图像)共同组成一个故意义的措辞符号,在神话这种虚拟叙事的情形下,原有的“所指”被淡化隐蔽,这种单有“能指”的措辞符号成为一个“形式”,而这个“形式”去探求另一个“所指”而组成新的措辞符号,这便是“神话”,“神话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探求“新所指”背后的“所指”,也便是神话的现实指涉。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
基于这种观点与方法论,我们阅读了大量的神话解构案例,末了在王明珂师长西席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找到了线索:在这本书中,王明珂剖析了“太伯奔吴”的故事。
我们可以用中国文献记载中“太伯奔吴”的历史文本为例,解释巴特对“神话”的认识,也借此考验其学说。当周仍为商的诸侯国时,周王的宗子太伯知道其父故意将王位传给他的弟弟季历。为了不让父亲难堪,太伯携其二弟远奔到江南吴地荆蛮的地方。荆蛮佩服太伯的义行,因此拥护他为吴王。在措辞层面,这个故事中所有的指符(如太伯、周王之子、荆蛮)都有一样平常指意,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人熟知的“太伯奔吴”历史故事,也便是指符与指意共同构成一个意符,人们可由此得知这个史事。然而在神话层面,“太伯奔吴”故事无论以文言文还是以口语文表达,无论是完全版本还是缩为“太伯奔吴”四个字的精简符号,都本身成为一个指符,也便是巴特所称的“形式”。原来的故事内容被淡化或忽略,而巴特称之为“观点”的另一层指意涌现:“一个自中原出走的失落败者成为边远蛮夷的王”。于是,此“形式”与“观点”结合,形成许多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之观点符号,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一个自中原出走的失落败者都能成为边远蛮夷的王。大略地说,这是一种文本“形式”与其所指“观点”共同构成的一个中原中央不雅观“神话”。无论如何,称这个故事为“神话”是根据巴特对“神话”的定义。(注:由于台译缘故原由,王明珂“指符”便是大陆之“能指”,“指意”即是大陆之“所指”,而“观点”为故意义的措辞符号。)
太伯奔吴塑像
从王明珂师长西席剖析的角度来看,“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实在与“太伯奔吴”相差无多,乃至箕子奔于朝鲜、无弋爰剑奔于西羌、庄蹻王滇四则故事,都是同样的叙事模式:“一个来自中原的失落败者在边陲成为了王。”让我们再来回想利科的不雅观点:虚构叙事中也有模式化情节,而老李与太伯的这种“迁远称王”的模式化情节,其所指涉的社会现实也一定有其相似之处,太伯的故事旨在鼓吹一种“中原中央不雅观”,其一在于保持中原在文化上的中央性以及纯洁性,其二在于向外族表示一种边界意识与称雄意识。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难明得“秃尾巴老李”在“闯关东”期间内容得以丰富并得以广泛流传的缘故原由了,让我们先来看“黑龙战白龙”的故事本身也是“英雄徙边”的暗喻描写,乃至可以遐想为山东等地区对付东北原住民(或是沙俄)的一种征服,以此来突出山东等地移民的分外性地位,这种征服不仅仅是武力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征服都可以理解为这个神话的隐喻,而前半段“老李”哭丧的故事本身也是山东的“礼俗文化”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老李”本身是山东人在闯关东期间为了突出其分外地位以及文化优胜性基于古代条记小说特地制造的一个徙边的英雄,其目的,一在于强调闯关东者的民族边界性;二在于为闯关东之后与本地人的共同生活奠定根本。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秃尾巴老李”的故事须要与“黑龙江”硬搭上牵连。
于永华“闯关东”作品
借此机会,我们还想谈一谈神话叙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一个联系,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视神话?由于对付绝大多数的一样平常社会群众而言,若他们难以察觉及理解神话隐喻,那么神话如何影响个人而发挥其社会意义?对此,大林太良对付神话与小说戏剧等虚构叙事的区分给我们带来了启示:虽然都是虚构叙事,但是神话不同于小说以及戏剧,神话的创作没有其紧张作者,流传办法基本上属于社会群众之间的口耳相传,因此并不是个别作者故意识的创作,基本上不会被疑惑“态度问题”;第二,戏剧小说等虚构叙事很随意马虎就被社会群众认定为“不合社会现实的虚构作品”,而神话不同,虽然神话的情节明显与社会现实相互脱节,但是社会群众对付神话这一分外的题材带有一种“无可争辩”的情绪贯串衔接,因此很少有人去辩论一个神话是否符合现实。综上所述,神话因其非态度性、非个人性、无可争辩性而更随意马虎被社会大众所容纳与接管,也是由于此,相较于公民辩论历史的真实性,神话的特质“让它们得以通报一些神圣而不应被争辩的讯息,或被用来通报一些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代价不雅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与禁忌。人们常辩论历史,乃至为了掩护真实的历史而不惜捐躯生命。但人们不辩论神话,这是由于神话叙事指涉的讯息与现实分开,让人们意识到它们是虚构的,因而不应对之穷究。然而神话透过其叙事情节与符号隐喻流露的一些讯息,却在人们心中产生意义,并因而影响社会现实。”(王明珂语)
台湾中心研究院院士王明珂
“秃尾巴老李”这样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英雄也确实起到了其该起到的浸染:在小组调研时,我们查阅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东北地区自从“秃尾巴老李”的故事传入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习俗,出船渡人,船上必须有山东人,如果没有山东人,老李不给护佑,出海随意马虎失事,这便是“秃尾巴老李”传说的“文化渗透”的结果。乃至在五大连池市还有黑龙山、黑龙庙和黑龙冰雕三个景点。黑龙山是一座休眠期火山,海拔516米,山体由黑褐色的火山砾、火山渣组成,远了望去是一座玄色的山体,叫黑龙山确实十分形象,传说这是秃尾巴老李安歇的地方。在五大连池的岸边建有黑龙庙,这里供奉的神像便是黑龙王--秃尾巴老李。间隔庙不远处有一冰雪溶洞,有冰洞和雪洞两部分。个中冰洞全长150米,深23米,洞内均匀温度零下5℃,洞壁上低垂下来的各种形状的熔岩钟乳,晶莹的霜花遍布洞内。洞内人工修砌了各种冰雕,有企鹅、北极熊等。这个中还有一条没尾巴的冰龙,标牌先容:此龙是黑龙王,老家在山东。可见东北地区对没尾巴老李的敬仰和爱崇,这些细节无不突显出“秃尾巴老李”的传说给东北公民带来的崇奉印记。
五大连池“黑龙山”(别号老黑山)照片
实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更像是一场类似于意识形态渲染的文化渗透,而这种文化渗透,也确确实实达成了想要的效果,让我们再次回顾保罗•利科的那句话:“我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历史的见证物,而我们自身也深受全体历史的影响。”这不得不能说是一句洞察深刻的名言了,而在目前的山东,关于秃尾巴老李的一些纪念活动仍旧在进行,个中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就有即墨、莒县、文登、诸城四处,我想,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的不仅仅是那一个一个的故事,故事大家都会讲,要保护的,实在是“秃尾巴老李”故事背后所隐含的那一段历史,当我们口口相传把这个故事传下去的时候,也应该去关注闯关东这样一段分外的历史大迁徙,这样才可以把“秃尾巴老李”这样一个神话传说传承好,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很遗憾的创造,不用说闯关东这段历史,就连“秃尾巴老李”这样的传说,在年轻人中的有名度并不高,由于神话其特有的口口相传的特性,使得其传播须要通过“父老传与子子孙孙”这样的模式,而现如今,随着屯子年轻人大量迁移到城市,这种口口相传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那种“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阁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生活彷佛已经成为一种过去式,在这种时期背景下,如何去保留下这种老故事,亦是“讲好中国故事”所要仔细考虑到的问题。
本次三下乡的旗帜
撰稿人:赵奕同 闫丙玉 郑媛媛 孙传娣
编辑人:闫丙玉
图文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子赴秦鲁豫三省城乡领悟发展实验区开展关于城乡领悟发展现状调研团队
日期:2022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