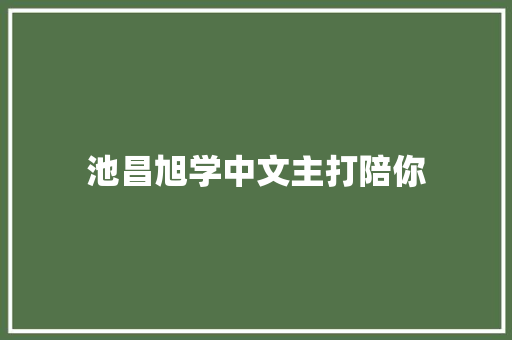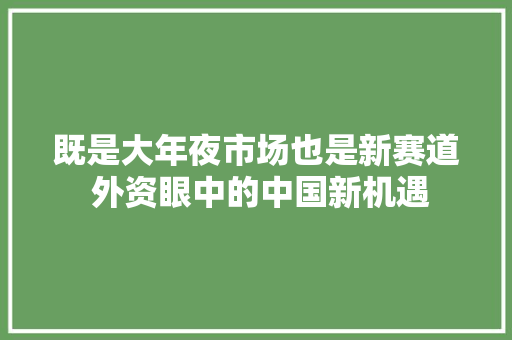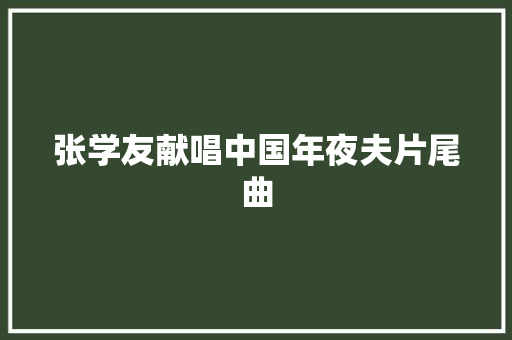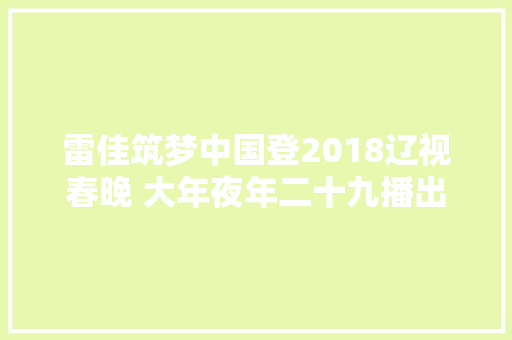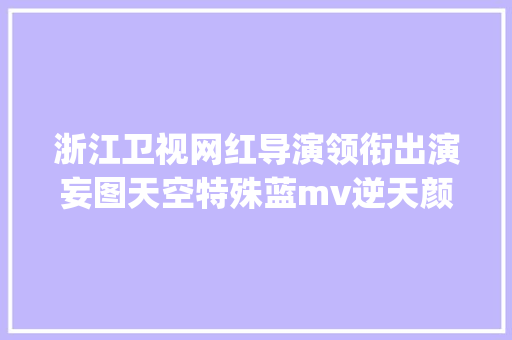家,甲骨笔墨形就像是一只猪居于屋舍之中。上半部分是房屋的象形,下半部分是“豕”,即猪。上有屋遮顶,屋下养头猪,在中国民气中,家便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住所,可以立足,有家当可以生存。由于稳定,以是有留恋,有温馨。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中国的节日,向来与家有关。比如春节团圆,过年回家,以家庭团圆作为一年的终点和新一年的出发点。中秋节,更直接被称为“团圆节”——一家人围坐一堂,吃月饼赏月,这样的幸福,古今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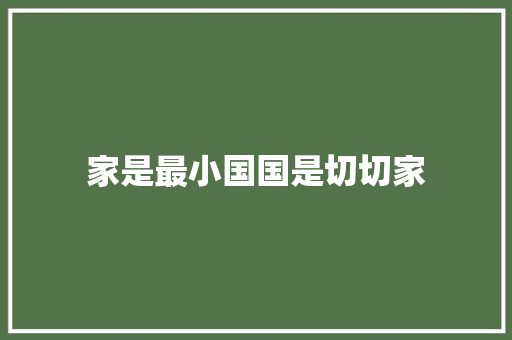
再看“国”字。国,始见于西周金文,左边是一个方框,象征一片地皮,右边是戈,表示以兵戈来保卫这片地皮。后在表示“国土”的“口”外边加了“国界”,仍表达以“戈”卫“国”的意思。到了小篆期间,在“或”之外又加了一个方框,表示国界、边陲。
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战乱和磨难的中国人深知保家卫国、守卫版图的主要性。“国”的字形演化,说的是国家有疆界,须要防卫力量,在边界线上有战士守卫,国家才能安定,仇敌才不敢反攻袭击——对付古人而言,国便是须要用生命守护的那一片地皮。
由己而家,由家而国,是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个人、家庭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从一个更广大的角度去思考立家立国的根本。由于感念个人出息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我们主动融家庭情绪与爱国情绪为一体,既重视亲情更心怀天下,既讲究孝悌更倡导效忠,于是有了烙印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有了杨家将一门忠烈。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与家教传承。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处处彰显著我们这个民族对付家的坚守、对付国的热爱。从《礼记》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到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陆游的“去世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到于谦的“一寸赤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家国情怀深植于中国民气坎,岁月深长,情绪深邃。
近代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激荡着家国情怀的叫嚣和抗争,激发起全体中国人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伟大力量。
1935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的赵一曼在与日军战斗中受伤被俘,被折磨得白骨遍露、血肉模糊但至去世不屈。在开往刑场的列车上,她给自己年幼的儿子连写两封遗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诲你。在你终年夜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却你的母亲是为国而捐躯的!
”
正是由于有万万千万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把“小爱”升华为“大爱”,捐躯个人和家人的幸福,用鲜血和生命去践行自己的崇奉与追求,才有了7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那声荡气回肠的“中国公民从此站起来了”!
心底的家,让人温暖、优柔;肩上的国,让人年夜胆、武断。爱家更爱国,这份刚柔并济,托举出了中华儿女的铁骨柔肠。中华民族之以是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实现民族复兴之以是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离不开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
作家路遥曾写道:“祖国是什么?她是炊烟,是鸽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烈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打发……”
近则身家,远则天下。一近一远,构筑了中国人的精神天空。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