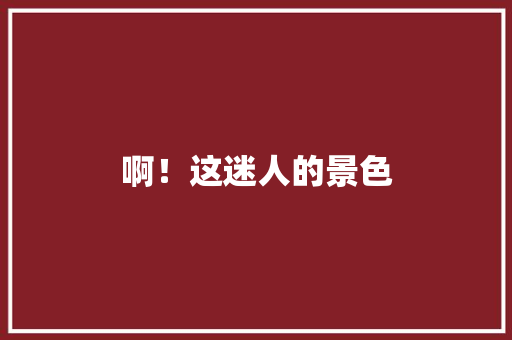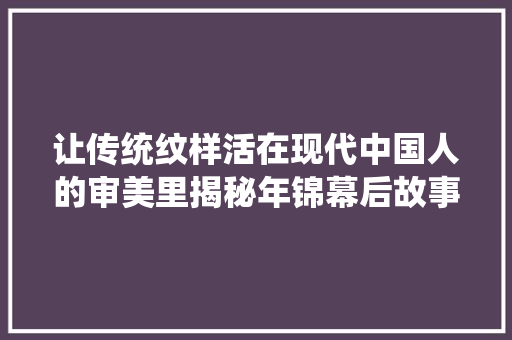日本正仓院藏琵琶背面的宝相花图案 图片为作者供应
莫里斯图案 图片为作者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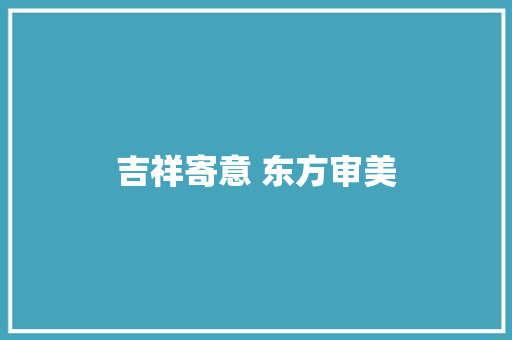
缠枝花图案 图片为作者供应
团花图案 图片为作者供应
敦煌卷草纹图样 图片为作者供应
装饰图案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之一,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性,表示了人类热爱生活和追求美好的真切欲望。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无数经典的图案形式,如青铜器上庄严肃穆的兽面纹、玉器上恬淡高雅的卧蚕纹、瓷器上烂漫自然的花鸟纹、建筑中敦厚严谨的快意纹、织物上繁复纤巧的八达晕等,这些图案或抽象或具象,或写实或写意,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图案体系。在当代设计中,从国潮设计中的日用商品,再到国际秀场上的衣饰家居用品,中国传统图案作为主要的视觉样式和文化形态,不仅表达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旨趣和社会情绪,也以充满时期气息的新面孔引领着天下文化潮流。
流动的线条 连绵的文化
早在18世纪,图案设计的“中国风”就曾席卷欧洲大陆,如洛可可艺术中的亭台楼阁类建筑图案、秋千仕女类人物图案等,都表示出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19世纪英国学者欧文·琼斯在其著作《装饰的法则》中,首次将中国景泰蓝和瓷器上的图案进行了整理和剖析,并指出:“中国人在呈现自然之物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他们蕴藉而立体的图案表现办法比西方图案更具艺术感。”这对往后欧洲的艺术走向产生了主要影响。
19世纪英国学者威廉·莫里斯被视为当代设计的先驱,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将东方图案转化为经典的欧洲纹样,比如他设计的莨苕叶纹,叶子和花朵环绕S形主茎进行各种翻转和波折,极富柔韧性的波状线条使人在视觉和生理上产生一种愉悦感。这种具有想象力的植物形态又启蒙了欧洲的新艺术运动。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慕夏,正是在东方艺术的影响下才形成了一种极具识别度的设计措辞,进而风靡全体天下。
威廉·莫里斯的莨苕叶纹实在是一种以波状藤蔓为紧张构造的卷草纹,这种纹样最早见于古希腊罗马期间的建筑和陶器上,叶形多呈掌状叶,到了拜占庭期间波状形态更为繁复,成为教堂建筑和家具装饰的紧张纹样,从文艺复兴期间开始又成为宫廷的专属纹样。实际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从爱琴海畔远征中亚、印度,卷草纹便开始向东方传播,一起浸渗了多种风格,在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样式,如伊斯兰天下将卷草纹变革为极富几何性和规律性的阿拉伯藤蔓纹等。
在中国魏晋期间,卷草纹紧张以金银花的茎蔓为原型,经由提炼加工后,形成了花瓣苗条、叶形简练的S形波状装饰带,也被称为忍冬纹,紧张用作建筑的边饰,如门框、碑刻边饰等。同时,由于波状构造自然产生一种连绵不断、循环往来来往的艺术效果,它也成为佛教艺术的紧张装饰纹样,常涌如今佛龛外沿、石窟壁画的边饰等位置。后来,古代匠师们根据波状构造伸缩性好、节奏感强的特点,开始基于装饰空间的大小和形状来进行灵巧变革,生发出了弧形、圆形、桃形等多种形式,卷草纹扩展至佛像的圆形头光、背光、藻井,乃至边角空隙等位置,在佛教建筑中营造出彼此不雅观照、相映成趣的艺术氛围。卷草纹因其极强的适应性,迅速被运用于金银器、铜镜、玉器、瓷器、漆器、石刻、织锦等工艺品上。
到了唐代,古代匠师们大胆地在波状构造中添加了不同种类的花卉、枝叶、果实,形成了忍冬卷草、葡萄卷草、莲花卷草、牡丹卷草平分歧形式,这种变幻莫测的组合形式更是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成为唐代的盛行纹样,以是,日本人又称其为唐草纹。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唐代壮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以卷草纹为代表的植物纹样完备取代了以云气和动物为主体的纹样风格,匆匆使人们的审美意识整体转向了愉悦心情的植物花卉,这也正如花鸟画自唐代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一样,表示出了面向自然、重视人性的新意见意义,这对往后中国图案艺术的发展和整体审美意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卷草纹这种外来的艺术样式,在落足中国的土壤后,本土匠师们主动追寻艺术表现的丰富性,灵巧调度变革,形成了一种本土化的新样式,表现出全然不同于西方天下的审美意见意义,比如古希腊的掌状叶纹、拜占庭的华美卷草等,都表示出一种有条不紊的理性美感,而中国的卷草纹则通过伸展回转的曲线产生了一种富有韵律的流动感,其连绵起伏、活气勃勃的视觉形象又被授予多福多寿、龟龄万年的吉祥寓意。在中国,许多主要建筑的形象塑造中,传统图案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浸染,如公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墙楣和廊柱上能看到莲花卷草纹,那简洁明快、朴素大方的样式展现出了崭新的时期内涵,散发着中国传统图案耐久的艺术魅力。
瑰丽的花纹 领悟的审美
如果说卷草纹是中国装饰图案中利用最为普遍、最具特色的纹样,那么宝相花则是最富有东方意境的纹样,它以其饱满圆润的形式美与完全圆满的意象美,充分彰显了唐代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宝相花以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为原型,纹样中既有含苞欲放的蓓蕾,又有盛开或半开的花朵,这是将不同时令的花卉形态集中起来,形成的一朵四季开放的空想之花,也是我国残酷辉煌的图案体系中一枝最为瑰丽的花朵。
宝相花最初紧张涌如今织锦上,这与当时的染织工艺技能密切干系。魏晋期间,随着中亚纬锦不断进入中国,中原织工开始学习这种纬丝显花技能,终极创制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纹样和织物。《隋书》中记载了隋文帝收到波斯供献的精美金锦后命何稠进行仿制,末了得到了比原物更加精美的织锦。《历代名画记》中提到在唐太宗期间,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大胆接管外来图案样式,设计出了许多锦、绫的新花样,后来因窦师纶被封为“陵阳公”,故这些图案又被称作“陵阳公样”。隋初何稠仿制的波斯锦该当是带有强烈波斯风格的联珠环团窠动物纹锦,初唐窦师纶的“陵阳公样”该当因此花卉作环的团窠动物纹锦。后来,波斯风格的联珠与动物形象逐渐被中原地区所喜闻乐见的花卉替代,中间的动物纹完备消逝,纹样外围的花卉团窠环越来越大,形成了花卉团窠纹样,即宝相花。
在敦煌唐代壁画中大量涌现了宝相花,其设色方法接管了佛教绘画艺术的退晕法,采取以浅套深、逐层渲染的办法,产生了丰富的色彩关系,形成了繁复瑰丽的图案形式。同时,画工在对花卉进行多角度的描述时,对局部删繁就简,确保了整体构造的明细化和融贯性,采取对称或放射状的排列,产生一种膨胀感和离心力,使整体图案具有非凡的丰满感,这充分表示出古代装饰手腕的高度成熟。工匠的创作已从模拟借鉴过渡到了美妙的创作,图案显现出异彩纷呈的装饰效果。这一富有特色的图案样式迅速渗透到了陶瓷装饰、建筑装饰、金属器皿装饰等险些所有的艺术领域。
从何稠的联珠环团窠动物纹锦,到窦师纶的花卉环团窠动物纹锦,再到花卉团窠宝相花和敦煌宝相花,清晰地为我们展现出对外来纹样的借用、复制、改造的“中国化”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代匠师们基于本民族的审美习气,对外来样式做出了因时制宜的变革和调度,进而引起了图案形式的变迁和艺术风格的变革,终极创造出一系列适宜当时当地公民的生活、风尚和不雅观念的艺术样式,并形成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正如日本正仓院所收藏的紫檀质琵琶上的宝相花纹、家具上的卷草纹等,都解释在文化互换的过程中,中国装饰图案已超过边界形成一种国际风格。毫无疑问,古代匠师们才是艺术的真正创作者,他们信息灵敏、目光锐利并且充满活力,将生活与空想结合起来,创作出了生动的、综合的艺术形式,是审美风尚的真正引领者。
无论是残酷伸展的唐草纹,还是饱满绮丽的宝相花,都是在借鉴接管外来样式的根本上,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样式,其严谨的构造和流畅的线条又成为后世纹样的典范,如卷草纹的延展式布局成为往后缠枝花和穿枝花的根本骨架,宝相花的闭合式构造又为大团花和小皮球花的涌现供应了基本参照。从忍冬纹到唐草纹,再到缠枝花和穿枝花,从联珠纹到宝相花,再到大团花和小皮球花,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图案体系在借鉴外来艺术形式时充分表现出一种罕见的适应能力与再生能力,古代匠师们以高超的应变能力和高度的艺术素养,大胆将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形式进行利用和转化,终极形成了与本土相匹配的艺术风格,不仅开拓了新的装饰艺术领域,还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影响力,这正是中国传统图案形成其永恒而独特魅力的主要根本。
装饰图案承载着一个极为广袤的天下,我们很难用一种大略的陈述来给中国传统图案定义,它将多彩的生活办法和审都雅念融为一体后而形成一个艺术体系,这是一种乐不雅观、自傲的态度与强健的创造力、适应力,更是东方人文精神的详细显现。
(作者:魏丽,系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西席)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