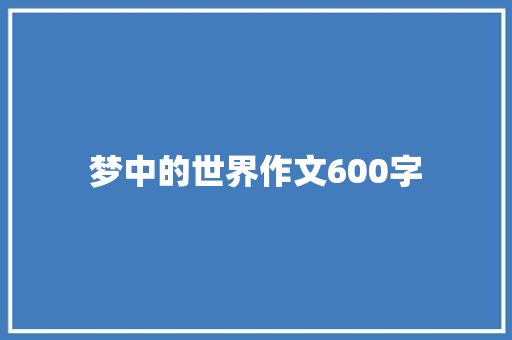《诗经·周南·麟之趾》:家族繁衍之歌
【按】近有空闲读些诗经的篇目,偶有所思,且以记之,虽多谬误,仅供批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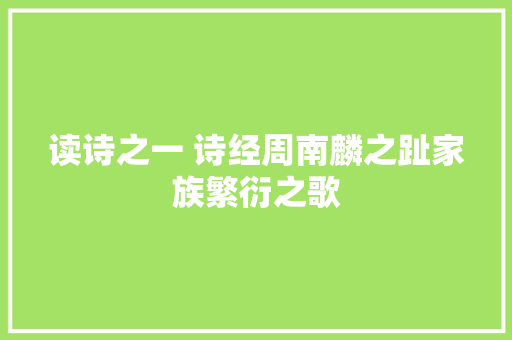
诗经中的国风均为采集先秦时期西周至春秋期间各国各地的民歌歌辞。它所记载反响的是西周至春秋期间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风尚,所歌所唱的是当时百姓的所思所念、所爱、所恨、所言、所行。国风中的诗歌,必须立足于先秦时期百姓的态度,从民歌歌辞的角度,结合诗歌的文本本义,结合先秦百姓日常的思想、情绪、行为,才能得到精确的剖析和解读。至于后世结合不同情形的引申、引用、拓展,既可能立足于其本义,也可能会有较大的扩展乃至曲解。但无论如何它不能取代诗歌的本义素心。
读诗之一:《诗经·周南·麟之趾》:家族繁衍之歌
《诗经·周南·麟之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一首,是流传于先秦时期西周至春秋期间周南地区(成周之南,即本日洛阳南部的中原地区)的一首民歌。全诗三章,每章三句。三章回旋往来来往,反覆唱叹,形成视觉意象与听觉效果的交汇,营造出一种热烈的颂扬效果。其文本如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一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汉代《毛诗序》认为这首《麟之趾》的主旨是赞颂文王、周公的子孙仁厚有德。《毛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又言:“《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
宋代朱熹也认同这一解读,他在《诗集传》中说:"序以《关雎》之应得之。""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墨客以麟之趾,兴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敷,故又太息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麇身牛尾而马蹄,然后为王者之瑞哉!"
宋代严粲《诗辑》:"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有额者宜抵,唯麟之额,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触,唯麟之角,可以触而不触。"同样认同歌“公子仁厚”之说。
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麟趾》,美公族之盛也。"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此诗乃"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
那这首诗歌到底是歌“公子仁厚”呢,还是美”公族之盛”呢?细读细品此诗此歌,彷佛不是纯挚歌咏贵族公子的,紧张是歌唱公族繁衍之盛,且很可能是歌颂周公的诗,是百姓歌唱周公家族繁衍的民歌。究其缘故原由,紧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此诗收录在十五国风《周南》里面。西周初年,在周武王去世之后,周成王继位。由于周成王年幼,为了加强和巩固西周的统治,周武王的兄弟召公奭和周公旦辅政,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召公奭(誓shì)居西部宗周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周公旦居东部成周洛邑,统治东方诸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周南》,便是网络的周公统治下的成周南部地区即今天河南洛阳以南的中原地区的民歌。《周南》、《召南》合称二南。《召南》则是召公统治下的宗周南部地区的民歌。因此,《麟之子》很可能是周南百姓有感于周公及其子孙的良好管理,使周南的百姓生活康宁,因而歌之。
第二,诗歌中的公子、公姓、公族,该当是公之子,即周公之诸多儿子,公孙应理解为公以下的同姓后人,即周公之后的同姓子孙,公族应理解为公之族人,即周令郎女所形成的各个家族分支。召南、周南的存在,只能在周成王之后西周灭亡之前。此诗歌的产生韶光也只能是西周期间,而且很可能是西周中期之前。这首诗歌中的“公”,只能指周公,不可能指周文王。由于周文王在历史上从未称之为“公”,而是或称西伯,或称文王。
第三,诗歌中歌咏的“麟”,其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构字是大母鹿身下或公鹿旁加小鹿。金文蜕变为麐,金从甲骨文的构造来看,便是带着小鹿的母鹿或公鹿。而麒的金文和小篆的写法,是鹿字右边加上长腿形,便是一个腿长颈长的长颈鹿的形象。《说文》中阐明:”麟,大牡鹿也。”“麐,牝麒也。“也有版本说:”麟,大牝鹿也。”朱骏声说:"经典皆以麟为之。" 段注曰:"经典无作麐者。"更进一步阐明道:“单呼麟者,大牡鹿也;呼麟麟者,仁兽也。麒麟可单呼麟。”薛注张衡《东京赋》“解罘放麟”云:"大鹿曰麟。"由此可知,所谓麟,便是成年的大鹿、有子的大鹿,有雄有雌。而鹿则是未成年未有子的小鹿。麒和麟都与鹿有关,但麒是与麟不同的动物,很可能是长颈鹿之类。可能正由于甲骨文中的麟字包含了成年鹿和小鹿的形象,以是才有后世产生麒麟送子的美好喻义。
第四,秦代及之前,并没有类似本日的麒麟形象和传说。关于麟的最早历史记载见于《春秋》。《春秋》记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战国期间的《春秋左传》第一次把麟与孔子联系起来,并与人们对吉与祥的期待联系起来,但总体上还是相对客不雅观的记述:“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锄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不雅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战国时的《孟子》云:“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贤人之于民,亦类也。出其类,拔乎其萃。”孟子也只是把麒、麟、凤、凰分别看作走兽飞禽中的一类罢了。可见,战国期间之前的所谓麟该当是似鹿的一种动物,可以被捕获,还不是什么神兽、仁兽。到了汉代《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不仅把麟与孔子联系起来,而且赋于其仁的含义,还进一步增加了独角等的特点,用以证明儒学的至高无上、独一无二和刘汉皇权唯一神授性。如果以战国往后特殊是汉往后人们对麟的再创造来解读《麟之趾》,肯定不能理解其真正的实旨。
如果上面的理解精确的话,麟便是成年有子的鹿,那么,《麟之趾》以麟起兴,歌唱公之子、之姓、之族繁衍之盛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诗歌中的“振振”一词,在诗经中多有利用。如《召南•殷其雷》中有“振振公子,归哉归哉”。《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等。过去有把振振阐明为“仁德信厚”,也有阐明为“浩瀚”、“盛多”。但细品各诗,还是阐明为“浩瀚”、“盛多”更为合理。这是由于:
第一,甲骨文的“振”字意为手持“辰”(原始的一种农具),在田地里劳作。振的本字是“辰”,有人认为是原始的石制农具,也有人认为是蚌壳制成的农具。振的本义是“在田间挥锄奋力耕种”。振的引伸义为挥舞、举起、振动等,其与“仁德信厚”无意义上的关联。但从其本义可以产生通过劳动使庄稼长势更好、收成更多成果的意义,因此振振连用,可以表示努力以达成得到更多、更盛收成的含义,符合“振”字含义的引伸逻辑。本日我们利用的针言”振振有词”的“振振”仍旧是说话盛、多的意思。
第二,诗歌起兴分别提到了麟之趾、之定、子角。如果前面剖析精确,麟即成年有子的鹿。则麟之趾为其蹄或蹄印,麟之角则其有多个分叉的角。这与歌咏公子、公族浩瀚繁盛便是同等的。汉代铸“马蹄金”、“麟趾金”,其紧张寓意恐怕也是希望象这样的财富如马蹄印、麟趾印多多益善罢。只有“麟之定”中的“定”的理解是难题。过去都把这里的“定”阐明为额头,即麟之额。甲骨文的“定”写作如图,意为从表面走进家里方心安,身定,引伸义为安定、确定等。表示家的符号内的是甲骨文的正。正的本义该当是人脚立在地上站正。正的甲骨文上面的符合应指代人的躯体正面。再看征字的甲骨文,其本义便是人站立或走在或口或路上,引伸为征伐。字中的方框,不是指城邑,而是指人的躯体。但无论如何,理解为额头则是不符合造字及其引伸的逻辑的。实际上,这里的“定”应理解为身体、躯体。麟有四蹄,如果成年鹿再随着小鹿,在地上奔跑,就会留下一个一个、或者很多的蹄印,表达由一而多的含义。而鹿的身体上有诸多斑点状花纹,也表达由一而多的含义。同样,鹿角形成的一个个分叉构造,也与家族繁衍分支浩瀚契合。
因此,《诗经·周南·麟之趾》是歌咏周公子孙后代、家族分支浩瀚的民歌。反响的是周南百姓对周公的爱戴、感念和祝福。当然,此诗歌可以用来祝贺公族生子,这也是表达一种道喜与祝愿。
以是《诗经·周南·麟之趾》是家族繁衍之歌。用本日的措辞笔墨翻译过来应是:
麟的蹄印多又多,周公的子孙盛又多,唉哟哟就象麟的蹄印一样多。
麟身班纹多又多,周公的后人盛又多,唉哟哟就象麟的斑纹那样多。
麟角分枝多又多,周公的族枝盛又多,唉哟哟就象麟角分枝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