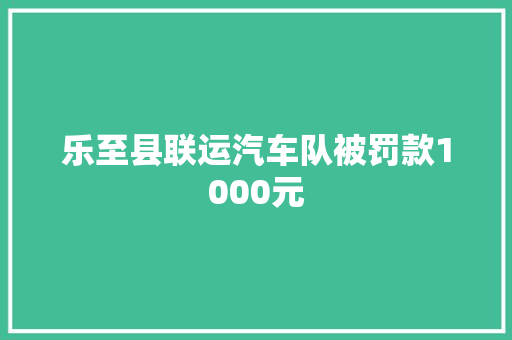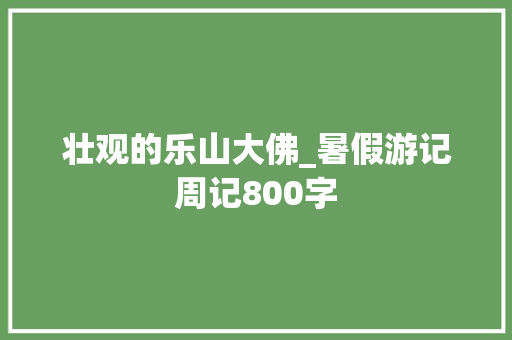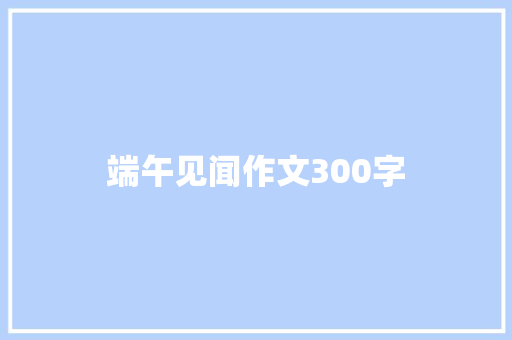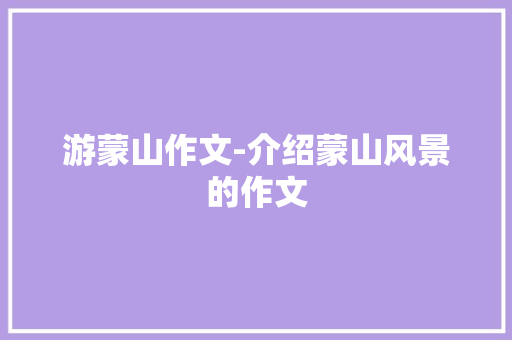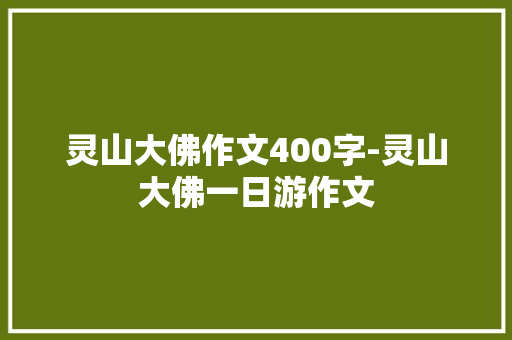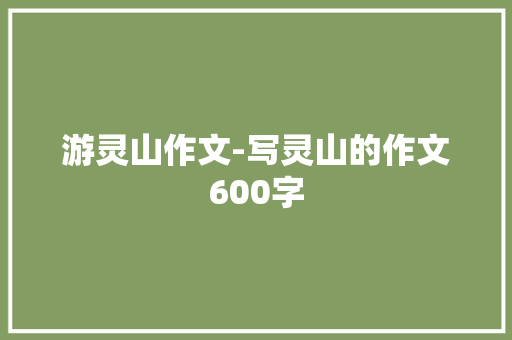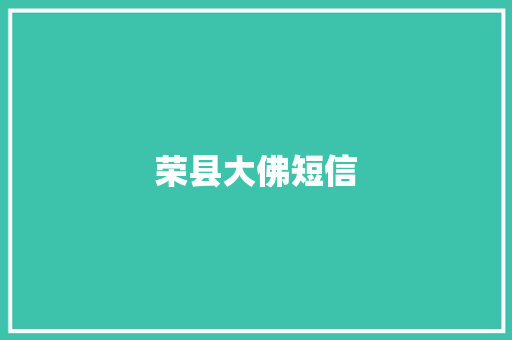一条东去的河流,携带远古的历史、残酷的文明,流过甘谷,流过甘谷的大像山,这条河流叫渭河。一条西来的古道,驮载他乡的风情、他乡的佛陀,经由甘谷,经由甘谷的大像山,这条古道叫丝绸之路。 山水与古道,自古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千百年来,悠悠渭河,滋润津润着大像山、茂盛着大像山;茫茫丝路,装点着大像山、繁华着大像山。而这座站立在中国父亲山——秦岭西真个陇右名山,也深情地遥望着渭河的潮涨潮落,记录着丝路的荣辱兴衰,也收藏着甘谷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 一座大像山,半部甘谷史。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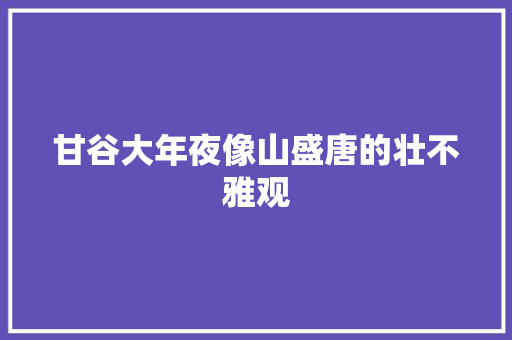
一个云淡风清的秋日,我轻轻走进大像山,踏进山门的瞬间,我回望了一眼来时的路。远处的渭河,内敛着深奥深厚的俏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山下的水上公园,倒影着山间的景致,装点着今人的思想。大像山上,秋光流韵,梵音渺渺,一派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景象。这样的光阴,离尘凡很远,离心却很近。 一位身着僧袍的和尚,手捻佛珠,迈着禅意的脚步,从我面前缓缓走过。那如风的背影,逐步融入山中,好似一幅笔墨浅淡的插图,装帧在大像山的历史影象中。影象中,还有那些大像山的过去,大像山的从前。 大像山,因其山巅修凿一尊20余米高的大佛像而得名,也因这尊大佛像而名扬四海。然而,在甘谷,关于大像山的名称,还有其余两种叫法:文旗山和大象山。一个来自民间,一个来自宗教。在民间它被称为文旗山。文旗山与其东侧的簸箕山统称旗鼓山,两山一左一右,犹如两面迎风飘荡的旌旗。自古崇文尚武、任侠好义的甘谷人就把攀升于右的叫武旗山,把飘扬于左的叫文旗山。左文右武,文张武驰,实则寄寓了甘谷人崇文尚武的美好情操。而关于“大象山”的叫法,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大像山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题写山名,赵老依据释迦牟尼“乘象入胎”的传说,题为“大象山”。如今这方牌匾就镌刻在大像山下,于是也有人称“大像山”为“大象山”,虽然读起来一样,听起来相似,但含意却大相径庭。而在甘谷依然习气地称这座山为大像山。 大像山自古便是一座历史名山、人文圣山。它来自于中华民族的父亲山——秦岭,怀抱着中国母亲河的摇篮——渭河,出身名门,天生丽质。横亘中海内陆的秦岭素有“中华龙脉”之称,经由千百年的历史蜕变与积淀,已形成了博大、厚重、深邃的秦岭文化。大像山作为秦岭西端一支独立的余脉,饱受秦岭文化的感化与滋养,显露过中华文明的曙色与晨光。当秦安大地湾文明在距今约4800年前忽然沉入黎明前的阴郁后,直至进入“三皇”的神话时期,这里便涌现了奇迹:走来了伏羲与女娲。而传说中的人文开山祖师伏羲,相传就出身在与大像山相邻的甘谷县白家湾乡古风台,那里的乡民至今利用的八卦灶台、八卦鸡笼,便是那个恍惚的神话时期存留至今的物证。而近年来在大像山上创造的陶罐、陶片,则无言地诉说着远古先民那段迢遥的史前历史,它们闪烁着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光芒。
大像山不但秉承了秦岭浑然博大的气质、深邃厚重的风骨,而且被古老悠久的渭河浸润得风采绰约,丰润富丽。渭河作为中华文明的一支主要血脉,是中华文化之轴,中华文明的书页从这里开始依次翻动。大像山怀抱着渭河,汲取着渭河的精华,接管着渭河的营养。1300多年前,年仅29岁的玄奘离开长安西行取经,便是沿着这条著名的河流,走上陇东高原,走向西域圣地的,他是否到过大像山,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记载。然而没有记载并不能断定贞不雅观三年玄奘离开长安西行后,就未登大像山。在玄奘法师看来,大像山离长安不远,当然不算“西域”,也就不便多留笔墨,也未可知。 大像山还因山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重视。远在东汉元年(公元23年)七月,天水成纪人隗嚣,自称年夜将军,薶血加书,移檄告郡国,起兵陇右,讨新都侯王莽,后勒兵数万,东征西讨,尽据凉州之地,盛时曾在大像山置歇凉台、阅兵台、挝鼓台。清《伏羌县志》载:“文旗山上有平台,昔王莽篡权,冀人隗嚣叛逆应汉时,阅兵于其巅,旁有挝鼓台,里人犹能道之”。 曾经气吞山河、一呼百应的隗嚣,终极以悲剧的色彩被史家列入《僭国传》。然而,作为历史人物,他为大像山涂上了第一抹文化的底色。他是第一位走进大像山,而且是第一个被大像山记住的历史人物。隗嚣拜别了,只给后人留下风一样黯淡而忧伤的背影。 隗嚣走了,泯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中。然而,他乡的佛陀,却沿着一条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大道,来到了甘谷,来到了大像山。 隗嚣埋没100多年后,即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叮嘱消磨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历史上一条叫丝绸之路的古道,横空出世。这条著名的古道上,不但有婉转悠扬的驼铃,成群结队的马帮,更有温顺的丝绸、文化的青鸟使和含容的佛祖。佛祖经由大像山时,选择在此小憩。然而,这一坐便是千年,坐过了隋唐五代,坐过了宋元明清,坐成了千古名山,坐成了陇右名胜。 从此,大像山花喷鼻香满地,佛光残酷,寂寞唱歌,荒凉生花。 从此,佛给山一个名传名久的载体,山为佛一个缘起缘灭的平台。 佛为大像山点燃了生命,注入了灵魂。有了生命和灵魂的大像山注定要被万万千万的众人瞻仰、朝拜。
3
今日我也是和万万千万的众人一样,怀着一颗大略而平常的心,来朝贺年夜像山的。穿过牌坊式山门,一只匍匐于地的鼋鼍背上,驮载着一方玄色的石碑,石碑书写着“羲皇故里”四个古朴的大字,从碑上的笔墨可以知道,这方碑石是“伏羌士庶人等”,于1928年农历4月,因原“羲皇故里”碑被毁而规复重修的,是迄今创造最早的一块称为“羲皇故里”的石碑。而原碑究竟立于何时,史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已无从查考。然而,与此不远的塑于元代的甘谷华盖寺伏羲洞里的伏羲像,却是天水地区最早的伏羲塑像。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但它们都彷佛在无言的证明着一个事实,甘谷是人文开山祖师伏羲最初的故乡。我为故乡历史的深邃和人文的辉煌感到骄傲。想至此,我加快了脚步,匆匆走向供奉人文开山祖师伏羲的大殿:太昊宫。 太昊宫亦称伏羲殿。它前瞰地皮庙和梅葛殿,后邻地藏殿,“负苍岩,瞰清渭,谷回川抱,形家目为胜地”。太昊宫始建于明万历48年,清同治元年回民叛逆时被焚,光绪10年重修,1988年重修山门,1995年重修大殿并塑像。殿宇座南向北,巍峨宏敞,山门为斜拱出挑垂花门,悬山顶,门额上有清代优贡李维屏真书“太昊宫”三字,丰满憨实,遒劲有力。 穿过垂花门,走进太昊宫,我仿佛走进了中原文明幽微的源头。伏羲大殿前的四株古柏,犹如四位温文尔雅的君子,一袭碧绿的长衫,散发着古朴纯然的气息,古拙苍老,文质彬彬,悄悄地守望着古老的伏羲,也守望着古老的文明。大殿内的伏羲,目光炯炯,孔武有力,即有人文开山祖师的慈详,又有征服天下的睿智。双手托八卦于胸前,手掌宽大而手指苗条,即有改造自然的力度,又有创造文明的灵秀。胸前的八卦,即表现出了伏羲超人的聪慧和创造力,又表现出伏羲旋转乾坤的大无畏气概。伏羲分腿端坐于分心石上,全身赭石色,筋骨突起,肩披桑叶,腰围虎皮,气质憨实,神态自然,精神抖擞,即有神的威力,又有人的亲切。大殿内东壁绘女娲练石补天图,西壁绘伏羲画演八卦图,正中是一幅伏羲生地甘谷古风台的写实画,殿顶绘六十四卦及河、洛二图。站立殿前,凝望伏羲,我沉浸在一片旷远的历史长风和悠悠的文化墨喷鼻香中,赏心悦目。
清风徐来,吹响了檐角的铃声,我仿佛听到了那首古老的歌谣:“甭看冀县(甘谷)地方碎,伏羲天子头一辈,桑叶儿衣裳脸上黑,伏羲爷生在古风台。”古老的歌谣传唱着历史荒远的真实,追怀着先人永恒的灵魂。6000多年前,一个叫华胥氏的俏丽女子,迷失落在雷泽古地的路途上,幸而她创造了一行巨大的脚印,于是她踩着巨人的足迹,一贯向南山走去。当她的双脚和巨人的脚印叠合的瞬间,她有一种被蛇缠身的觉得,有一股幸福的暖流从腹部迅速传遍全身。于是,她有身了。12年后的正月16日,她在被后来称做朱圉山的一个岩穴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伏羲,自命风姓。这个洞后来就叫伏羲洞。洞前不远处的那块又高又大的平台就叫古风台。伏羲在这个台上,仰不雅观天象,俯察万物,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与乌龟发言,和鲵鱼谈天,开天明道,创立八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兴婚姻嫁娶之礼制,开渔猎畜牧之先河。他只在人类灵魂的深处轻轻一划,便天清地明、海晏河清,便龙飞凤舞、鸟语花香。那一画开天的手势,像挥别,又像召唤,至今仍保存在人类心灵最优柔的角落;他只用简大略单的阴阳两种符号,便揭破了宇宙的秘密,解析了天下的构成,掰开了人类的双眼。 伏羲大殿屋檐下、柱子上雕刻的牌匾楹联,吸引了我的目光。屋檐下是四位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家的墨宝,赵朴初的“人文开山祖师”匾,启功的“一画开天”匾,舒同的“开天明道”匾,黎泉的“与天地准”匾,这些富丽如秋、丰澹如海的牌匾,在光阴的抚摸下,愈见岁月的风采,展示着一代学人博识的学问和深厚的学养。而柱子上的两副楹联,写尽了伏羲的功绩与辉煌,伏羲的传奇与风骚。一副是光绪翰林王海涵的手笔:绍皇开泰运,厥后有石子访道,伯约怀忠,问化育根源,发蒙在炎黄颛喾而上;望古动幽情,其下则烟火成邻,桑榆布荫,幸邃初风景,复睹于金戈瓦砾之余。另一副是宣统知县雷光甸的联墨:从一画开天,说什么鸟篆虫书,佛经梵字,到卦台前齐俯首;继三皇立极,看后来帝升王降,商质周文,于史册上见传心。 伏羲的身后,走来了孔子贤人石作蜀,走来了蜀汉大将军姜伯约,亦走来了关西师表巩建丰,走来了陇右诗圣王心如。有风吹来,拂过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远古的星辰,明朝的阳光。
4
一场风随着另一场风,把大像山吹拂得温润如玉。太昊宫的风,辽远,渺茫。而文昌宫的风,清澈,明净,有五谷的芳香,有文字的暗香。每次来到大像山,文昌宫是我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在大像山所有的喷鼻香火中,惟有文昌宫前的喷鼻香火馨喷鼻香馥郁,幽淡芬芳。文昌宫里那盏文化的长明灯,从明朝点燃后就再也没有熄灭过。它是甘谷文化一方圣洁的天空,甘谷文明一脉潺潺不断的溪流,明净而高雅,孤独而自傲。千百年来,它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甘谷的文化学人、文艺才俊。因而,每次登临大像山,我都要在文昌宫这座逼仄的小院里盘桓良久,燃一炷喷鼻香,点一支蜡,不是由于迷信,而是由于对文化的一种景仰,对文人的一种敬仰。 大门洞开着,门首有一副砖刻的楹联,写着“阁凌碧宇迎朝爽,门对朱山映晚霞”,是高古的隶书,古风犹存,让人很随意马虎想到古代。跨进门槛,那座久负盛名的文昌楼映入眼帘,这是一座重檐六柱六角亭式的楼阁,也是一座沾满文化墨喷鼻香的楼阁,一座文质彬彬的楼阁。那些刻画在六角墙面上经久弥新的字画,常读常新的诗文,在岁月的濡染下,愈见风采。何晓峰的“兰竹图”依然洒脱着,马晞的“喜鹊闹梅图”还在热烈着,魏学文的《兰亭序》风采依旧,显示着一位老书法家深厚的笔墨功夫,而武克雄连绵不绝的草书,又疏放着一个文人文雅的情怀:“山头禅室挂法衣,窗外无人溪鸟飞。薄暮半不才山路,却听泉声恋翠微。”品味着这一幅幅或清新、或圆润、或古拙、或清瘦的字画,让人感想熏染到他们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佛法心性。
历史有时很长,长得让人一眼望不到边。历史有时很短,短得只有一转身、一转头的功夫。当我还沉浸在“兰亭”的优雅,“兰竹”的从容时,只一个轻轻地转身,一次逐步地转头,却让我彷佛跌入到历史的冰凉中,再也无法优雅和从容了。那株曾经遭受过巨大创痛的古柏,就站立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它沉默着,似在提醒,又似在诉说。丰茂的树冠仿佛提醒人们,今日安定和平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又多么宝贵。而那片烧焦的树根又仿佛在诉说清同治二年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那段不堪回顾的往事。地方志上这样记述:“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回民反清,阴历四月,焚大像山梵宇祠庙,毁塑像,方丈河州人孟喇嘛被杀。”这场劫难使大像山所有木构建筑,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所存留的光阴痕迹一同化为灰烬。只有这株古柏,作为历史的见证,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楼构数椽容膝易,窗开三面会心多。”历史的书页频频翻动,而柏树无言。 行走在风雅的文昌宫内,一块镶嵌在厦房南墙上的《大像山创立文社碑记》,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块碑文,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光阴,却依旧可以闻到文字的暗香。这些温润如水的古墨,至今都是湿润的,触摸上去,还留存着历史的余温。光绪28年(1902),有“陇右诗圣”之誉的邑人王权师长西席,在大像山文昌宫,创立“大像山文社”,“每月朔望,人各持钱十五文付社长综理,违约者倍罚。届春秋二祀及浴佛日会期,则备具牲酒供品,前夕聚拢阁下,虔奉喷鼻香烛,清晨畲荐奠献如仪,魁阁之祭亦分往。将事祭毕,饮宴因之,讲论道艺,竟日乃罢。”为纪念这一盛事,满腹经纶的王权师长西席,写下了富丽的《大像山创立文社碑记》。如今这块碑文就镶嵌在文昌宫厦房的南墙上,堪堪百年光阴之后,依旧文字芬芳,触摸上去,还留存着历史的余温。1980年5月,这里又创立了“大像山文艺学会”,以文会友,以文结友,吸引聚拢了100多名甘谷文艺才俊,吟诗作赋,泼墨作画,成为弘扬古冀文化的一个主要场所。 默诵着古色古喷鼻香的碑文,盘桓在同样古色古喷鼻香的文昌宫院内,我思绪万千,感慨良多。面前文昌帝君前的喷鼻香火,幽幽地亮着,不壮盛,也不寂寥,但在万千的喷鼻香火中,为什么唯有文昌楼前的喷鼻香火馨喷鼻香馥郁,长明不熄?数千年来,大像山下的甘谷为什么会有进士比肩,举人如云的景象?又为什么会在陇上享有文风之地的美誉?是由于文化吗? 文化如风、如水,滋润津润着永恒的山水,亦滋润津润着人类的心灵。众人游山玩水,实在游的是心境,玩的是文化。没有文化秘闻的风景,也只是一种俏丽的存在,究竟不能赢得众人的亲睐。山水如此,人事亦然。
5
秋风徐来,墨喷鼻香氤氲。走出文昌宫,我带着一颗轻松的心,连续朝山上走去。途经百子洞时,我停下了脚步。百子洞前,如今是一座高大华美的永明讲堂。站立楼前,我感到十分微小,也感到十分茫然。一缕远去的流云,把我的思绪拉向了迢遥的过去。过去,这里叫灵岩寺。 灵岩寺,曾经是大像山一处绝美的风景,一首绝致的古乐,空灵似碧海上苍,玲珑如唐诗宋词。然而,这方绝美的风景,就像那首早已绝尘而去的古乐《广陵散》一样,永久地从人们面前消逝了。历史上的灵岩寺,像潮水一样,在我的影象里展开。 灵岩寺,缘起于百子洞。百子洞原来是大像山的一个天然岩洞。空灵险绝,临崖而立。多少年来,道路不通,人迹罕至。民国36年(公元1947年),麻王(外号)史江家等几位甘谷木工,欲打通甬道,新造鲁班殿。洞打通后,人们惊异地创造,这真是一个绝妙之地,洞内宽通顺亮,飞尘不到;洞外风光无限,天高地迥。临崖眺望,甘谷川口,尽收眼底,远山如黛,渭水如虹,绿树成荫,田畴似锦,烟村落万家,星罗棋布,真可谓“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面对此地此景,有人提出塑麻线娘娘,有人建议塑不雅观音菩萨。正当人们辩论不休的时候,大像山上一位姓郭的师傅却默默地用泥捏塑了几个婴孩的形象,悬于窟顶,人们受到启示,就把这个洞叫百子洞。之后百子洞就开始扩大规模,请神塑像。住进僧人后,就起了个寺名叫灵岩寺。 灵岩寺是大像山的绝妙之作,神来之笔,也是大像山就地取材、巧用地形、因山就势、因势成景的范例代表。墨客王直师长西席曾这样赞颂:“红雨无心舒卷幽篁禅院,白云故意往来悬壁洞天。”曾经的灵岩寺,寺门前两株森森古柏,碧绿青翠,四季长青,宛如两位超尘脱俗的得道高僧,默默地守望着幽雅的禅院、精湛的佛理。垂花门顶额题“灵岩寺”三字,洒脱灵秀,不染尘埃。拾级入门,但见一精雅小禅院,院内翠竹数枝,清新淡雅,院外丁喷鼻香环抱,花喷鼻香鸟语,真乃洞天瑶池,恍若世外桃源。院东北有一小禅房,寂寂的木门里,雕花的窗棂内,住一高僧,在淡泊如水的日子里,饮一盏禅寂的清茶,闲数落花,坐看云起,在月白风清的夏夜里,将禅悟从这扇窗棂通报到那扇窗棂,将月光从这道瓦檐引向那道瓦檐,那是何等的风雅,又是何等的空灵。院北为窟前阁,大庑顶,上覆鸱饰雕甍,下有廊柱,洞顶绘千手千眼不雅观音,两侧绘十八罗汉,逼真真切。阁靠东北有一洞,前行数步,便是“百子洞”。洞内有主室,耳室。主室塑送子菩萨,精美绝伦。端坐佛坛之上的菩萨,左腿上盘,右膝下垂,一小孩坐于腿上,旁边各立一童子,慈悲含容,维妙维肖。两耳室塑有金华、大势至菩萨,后又将城隍、“马三爷”塑像安顿两旁。值得一提的是百子洞里马三爷的塑像。马三爷是甘谷特有的一位地方神灵,又称马三将军,回族,清初甘谷人,家境富余,排行老三,年少有德,因生前常骑黑驴,也称“黑驴马三爷”。病逝后托梦乡人,村落夫以神灵敬祈,颇有灵验,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逐渐作为一个地方神灵被供奉起来。百子洞里的马三爷,戴一回族小帽,穿一马褂,骑一黑驴。将军之职在神灵天下是地位较低的,村落夫将马三将军安奉于此,大概有求子又求德的寓意,期望从这里求来的子孙不但聪明灵秀,而且风致优秀。同时也是甘谷公民和回族公民自古和蔼相处的一个见证。
灵岩寺是大像山最神圣、也最世俗,最无私、也最自私,最尊贵、也最卑微,最诗歌、也最哲学,最抒怀、也最理性的地方。孤独的灵魂在这里能得到安顿,绝望的心灵在这里能长出新苗。以是灵岩寺自建成以来,就喷鼻香火十分壮盛,求子者摩肩相继,还愿者相继而来。每逢月朔十五的日子,那些缺儿少女的妇女,那些为子求孙的母亲,在经历了无数孤独的黑夜和生活的煎熬后,她们怀着十二分的虔诚,迈着匆匆的步履,来到大像山,跨进灵岩寺的山门,来到百子洞的送子菩萨前,在庄严而肃穆的氛围中,请山上的老师傅将绾好的红项圈系在菩萨身后的婴儿塑像上,那一刻,严明而郑重,庄严而神圣,好似生平的幸福和家族的欲望,都在此刻交付给慈悲的菩萨,含容的佛祖了。果真不出一两年,要儿得儿,要女有女,于是就大张旗鼓的到大像山来还愿,一传十,十传百,灵岩寺的一部民间传奇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续写了下来。 然而,灵岩寺在1999年却永久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了。如今高?大华美、窗明几净的三层砖混构造永明讲堂,壮不雅观地矗立在百子洞前,成为大像山一处新时期的新景不雅观。 灵岩寺虽然永久地闭上了她那双清新淡雅的眼睛,但百子洞还在,百子洞里的喷鼻香火还依然兴旺。只是没有了灵岩寺的那缕淡淡清风荡涤俗虑,那份悠悠禅韵整肃灵魂,人们来到百子洞时,还能像从前那么优雅从容,那么心天真念吗?我悄然走过永明讲堂,它视我如一粒尘埃。
6
远去的风景无须过多地追忆,存留的遗迹却要格外地珍惜。再往前走,便是大像山著名的永明寺。 永明寺,犹如一册泛着佛光的经卷,在大像山独立成篇,晏然自处。多少年来,永明寺与大像山,就像清风守候明月,就像流水依偎山峦,顾盼相视,默默相望,用慈悲普济群生,将佛法洒遍山川。 妙相庄严的永明寺,山门为并排连体拱形牌楼状,大块青砖雕刻筑建而成,红墙黛瓦,持重典雅,中门顶额上雕刻着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补初老居士手书“永明寺”三个大字,两边有近代著名高僧明旸法师敬书“风月无边一尘不到菩提地,山河环抱万善同归般若天”的对联。两边门首摹配民国时邑绅士“何佛爷”何鸿吉的题书,左为“出尘入净”,右为“ 无上法门”。三个门象征“三解脱”,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踏进这道门槛,便踏进理解脱境界,摆脱了六道循环的宿命,斩断了尘凡烦恼的纠缠。那儿是水天佛国,婆娑天下。 这是一座布局奥妙,构造严谨的寺庙,保持着远古的风貌,丰裕着佛典的意境,也融入了当地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寺内祥云普照,宁静高远。进入山门的第一座大殿是天王殿,殿内安奉着亲和的弥勒佛,笑口常开,吉庆祥和。两边分别坐着,高大威猛,神勇无比的护国四大天王 ,手持法宝,护持佛法。 客堂和斋堂之间的院子里,是一座三足四层宝鼎。登上九九八十一级台阶就可以看到两边有钟鼓楼,这是全县最大的钟鼓,寺院每天都会按时敲响。走过台阶,便抵达了寺庙的中央、寺庙的心脏。劈面是庄严的大雄宝殿。殿内安奉着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迦叶、阿难二位尊者,双手合十,慈祥可亲,东西两面是姿态互异的十八罗汉,后侧正中是汉白玉不雅观世音菩萨站像。行走在喷鼻香烟袅袅、钟磬声声的寺院,面对维妙维肖的佛像,浩瀚无穷的佛法,人们不禁自问,这便是那万万千万的佛教圣徒匆匆赶赴的梦中之境吗?这便是经卷里岁岁年年传诵的西方极乐净土吗?佛前那永不熄灭的喷鼻香火,便是那永明的佛法、精湛的佛理吗? 徜徉在永明寺院内的佛堂僧舍间,我不能不忆起那位令人尊敬的本逢法师。本逢法师,字印玉,俗名李贵子,生于1928年10月,是甘谷西关南巷人氏。1947年在甘谷报恩寺西禅院礼敬玄大和尚剃度出家,法名本逢,同年于大像山永明寺受具足戒。此后便隐居大像山,把几十载的光阴,付之与大像山,付之于永明寺,常伴晨钟暮鼓,传教无量寿佛。尤其在“文革”期间,法师坚持修行不懈,掩护佛教奇迹,挺身保护大像山佛教文物,对大像山上的国宝“甘谷大佛”的掩护作出了分外的贡献。1992年,本逢法师有感于永明寺有名无寺,与甘谷佛教中央名不符实,便弘扬佛法,悲心宏愿,带领僧俗大众,多方张罗资金,在大像山选址建筑了永明寺。1995年永明寺基本建成,3月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寺院落成、佛像开光、方丈升座和居士菩萨戒传授法会,参加者千余人,从此永明寺又怀复了丛林制度,佛像庄严,殿堂整洁,佛事兴隆,喷鼻香火壮盛,仰慕者相继而来,皈依者恒河沙数,成为甘肃一座汉传佛教正规的禅净双修、念佛为主的十方道场。1998 年、2001年又成功举办了永明寺第一、第二届三坛大戒传授法会,并约请当代著名高僧茗山、一诚、传印、常明、澈性等诸山长老百余人主持和参与法会,全国僧俗受戒弟子达2000多人。从此,作为甘谷佛教中央的永明寺,再次在全国佛教界荣誉日隆,佛光残酷,喷鼻香火壮盛。成为甘谷一带佛教徒神往的净土,精神的圣地。 2014年农历闰9月25日清晨2点25分,本逢大和尚在大像山圆寂。省内外各界人士、诸山长老、四众弟子万余人参加追思大会,为本逢长老送行。 一代高僧走了,留下了他高华的背影,也留下了他与大像山一世的情缘。
7
一枚经秋的红叶,如血,痉挛的叶脉,仿佛诉说流年的悲欣;一丛霜染的黄花,好似易安夫人清丽的脸庞,以绝尘的姿势,诠释秋的内涵。山寺的钟声,空远辽阔,仿佛来自天国,安抚孤独的旅人,温暖故人的心怀。 不知不觉间,我已来到大佛脚下。我看到一个烧喷鼻香的妇人,带着一颗很窄的心来了,匆忙间,将灵魂藏在莲台下,又飘忽地拜别。梵音是永一直止的,千百年来,只有大佛面前的紫丁喷鼻香和白皮松,才能深悟它的空灵和韵致。飘渺的烟雾载着云梦般的世事远去,无影亦无痕。我悄悄地仰望大佛,瞩目大佛。山风掠过耳畔,我仿佛听到了1600年前錾子击打岩石的声音。那是大像山的第一代开拓者们,在几百米高的峭壁绝壁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佛立传、命名。这里有得道弘法的高僧、技艺高超的大师,也有衣衫褴褛的工匠、恳切皈依的居士。他们带着清澈明净的空想,放下爱恨情仇,割舍亲人牵绊,阔别繁华人间,来到这深山古刹,洗尽一身风尘,潜心礼佛。在那些物资匮乏、生活动荡的年代里,在那些凄风苦雨、万籁俱寂的永夜里,他们忍受着身体的饥饿与寒冷,抗拒着内心的迷惑与迷惘,一凿一錾、一笔一画地在百丈峭壁上劳作。錾子撞击岩石的声音,铿锵激越,如木鱼,似鼓点,穿透苍茫的岁月,响彻在古冀的上空。逐渐的坚硬的红沙岩上涌现了石窟和佛像的大体形状,然后又在躯体上凿孔插桩,再在表层敷泥塑成,末了彩绘成型。不知凿透了多少清冷的月色,坐穿了多少风雨的薄暮,才造诣了这尊无与伦比的大佛。他们为大像山创造了艺术,创造了文化,让大像山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今日的繁华似景。然而,那些绳墨规矩的工匠们,那些默默无闻的画师们,在历史的卷册中,却因名分阙如而三缄其口,沉默不言。历史遗忘了那些毕生追求艺术并末了归真于艺术的大师们。因而,每一位来到大像山的游客或者信徒,都应向这些被文化艺术正史打入另册的消隐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没有记载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令人可敬的大师、工匠,乃至连大佛开凿的时期,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以至于让后世的人们辩论不休。目前能看到最早记载甘谷大佛的笔墨,涌如今宋代乐史《太平天地记》中: “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丈,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尺”。然而,这段记述并没有明确解释甘谷大佛开凿的详细年代。不是由于轻忽,而是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古人落笔是慎重的。 人们把追寻的目光转向与此相距不远的麦积山,一篇关于麦积山佛龛的铭文:《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引起了人们的把稳。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伟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龛成,著名文学家庾信专为其撰铭,个中有“冀城余俗,河西旧风”的句子。冀城,即北朝时的甘谷,“河西”指全体黄河以西,包括全体渭河流域及“陇坻”的麦积山广大地区。“余俗”与“旧风”解释,至少在北朝时甘谷佛教已经十分昌盛,开窟造像的条件也已具备。同时,专家又进一步从大佛像外面形态方面进行了论证,得出了大像山大佛开凿于北魏、彩妆于盛唐的结论。至此,一场关于大像山大佛开凿年代的争鸣基本明朗:大像山大佛开凿于北魏、彩妆于盛唐,成为人们认识甘谷大佛的共识。这一认识至少有两点意义:甘谷大佛是渭河流域唯一的一尊唐代大佛,是盛唐文化在渭河流域的一个主要景不雅观和标识,是甘肃石窟长廊不可或缺的一笔;同时也补充了麦积山石窟没有唐代大佛的缺憾。
8
一缕流云打我身边掠过,我站在距地面200多米高的峭壁边,好似站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沐浴着怒放的佛光,悄悄地凝眸大佛,内心充满了神圣和庄严。大佛端坐在一方高34米、宽14米、深4.5米的长方形圆拱形窟龛内,佛像高23.3米,肩宽9.5米,头高5.8米,膝长6米,如此巨大的造像,在甘肃东部地区所有石窟中独一无二,仅此一例,是渭河流域唯一的一尊唐代大佛,也是全国大佛相对高度最高的造像,听说还是仅次于四川乐山大佛、莫高窟96窟弥勒大佛的中国第三大佛。我的目光穿过栏杆,一寸一寸地朝拜慈悲的佛祖。佛祖端坐于莲台之上,温和韶秀,慈祥悲悯。一双含容的眼睛,清澈如水,温暖如春,仿佛穿越千年的光阴,既安顿尘世,又教养民气;苍黑如黛的眉毛,宛如苦海中的两叶渡舟,渡苦渡难,亦渡人渡心;宽大厚重的鼻子,微微翕张,仿佛能感想熏染到佛祖均匀的气息,让游者心平气静,让不雅观者万虑俱消;一对又长又大、又厚又垂的佛耳,像两朵盛开的莲荷,谛听人间疾苦,谛听千年风雷;佛的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大拇指和食指相捻,人谓拈花说法,拨济从生;一袭通肩僧衣,自然得体,生动流畅,灵动洒脱,像要迎风起舞。僧衣之下袒露着一双巨大的佛足,踩着12朵盛开的莲荷。佛足之大,能容纳四个人盘膝而坐,“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瓮。”圆拱形的窟壁之上,布满飞天、伎乐、天王、力士、人面鹤身养活菩萨以及莲叶、卷云等悬塑,凌空飞动,迎面而来,与窟内的大佛,簇拥呼应,相映成辉,十全十美。站立在如此庄严肃穆的佛前,有谁还会将恶行与肮脏携带在身上?纵然曾经走过迷途,错过善良,这会儿佛祖也会体谅,他会给你韶光去填补人生的毛病。 然而,大像山大佛更为奇特的是,在大佛宽厚的上唇上,有一对微微翘起、轻轻上扬的蓝色蝌蚪状短须,如祥云环抱唇边,似浪花荡漾嘴角。这在全国佛造像中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为甘谷大佛与他乡佛陀明显的不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清代有一外地贩子,来甘谷做生意,渡渭时,不慎落入河中,河流彭湃,挣扎之际看见山上大佛,便在心中许愿:如能得救,必为大佛贴金。顷刻,如有神助,得以脱险。还愿时,末了缺了点金子,工匠帮他想了个办法,为大佛画上髯毛。从此,大佛就有了两道蝌蚪状短须。传说虽然不敷为信,但这两道髯毛究竟寄寓了若何的佛法佛理,又隐含了若何的前因后果,今人已无从知晓。而这种佛亦人,人亦佛,佛知人性,人通佛性的奇妙景象,却使原来威严的佛祖,多了几分人性的亲切和尘世的温暖,更让无数潜心礼佛的人,对来世奔赴西方极乐世界的崇奉,更加信服,更加虔诚,也更加武断。 凝望大佛,我还惊奇地创造,无论站在左侧、右侧,抑或正中去看,大佛都堪称完美,比例折衷统一,眼神安详从容,觉得慈祥宁静,而这种效果与我来时站在山下遥望时毫无二致。那么,这种让人叹为不雅观止的神奇,究竟有着若何不为人知的奥秘呢?1983年,全国著名雕塑艺术家温庭宽师长西席为人们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那一年,市价大佛维修,温老亲临大像山,攀上脚手架,登至佛头顶,对大佛进行了全方位的详察,终于创造了个中隐蔽的玄机与奥妙。他阐明说:这尊无论从何种角度仰视都给瞻仰者以毫无“偏差”浑然天成的巨大佛像,正好是靠塑造上的“偏差”来实现的。在这个凡人不易到达的头部位置平视时,全体造像呈现出一种比例失落调、器官错位、狰狞不适的觉得。山下看来炯炯有神的眼珠,却是一块突出于下眼睑的黑釉大缸(一劈两半);竹苞松茂的佛耳,被置于颞部,超出头顶发际线;高高突起的眉棱骨,却阴刻了一道深深的凹形弧线沟,并群青装色;佛的鼻梁直直下垂,形成硕大的梯形体积,佛的上嘴唇赶过下唇许多,而下颌骨却下陷了进去,全体头部微微前倾。凡此各类,都完美地表示了“由丑及美”的辩证关系,从而不露玄机地奥妙办理了因佛体高大而造成的仰视偏差。这是一种若何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又是一种若何让人叹为不雅观止的艺术精品啊。 我悄悄地仰望佛祖,沐浴在一片残酷的佛光中,心灵沉着,灵魂安详。惟觉生命真实,自然永恒,佛光浩荡。
9
无论多么地想要珍惜,相聚之后还是要选择离开。深情地凝望过大佛,我怀着一颗轻松而通亮的心,朝山下走去。 山下的大像山公园里,秋色正浓,游人如织。像山湖碧波荡漾,脉脉含情。岸边聚拢着繁盛热闹繁荣的人流,湖心却是画影清波。公园中,草坪上有执子之手的人,凉亭中有临风赏景的人,他们消磨的是一段安稳散逸的盛世年华;云烟里,山寺有烧喷鼻香拜佛的人,佛前有参禅颂经的人,他们追寻的是一种空山空水的空灵意境。 大像山公园,始建于2012年4月,竣工于2015年5月,占地268亩。是甘谷新景,为民生工程。以生态旅游为主题,以历史文化为秘闻,华美而不失落持重,简约而不失落大气。一泓清澈明净的湖水,停泊在大像山下,如《诗经》里的渭河,波光粼粼,闪烁着动人的荡漾;又如佛前的莲荷,沉静优雅,怒放着残酷的佛光。湖水倒映着山间模糊绰绰的亭台楼阁,回荡着岸边熙熙攘攘的滚滚尘凡。大像山,这座被光阴风雨浸润了千年的陇右名山,如今又有了一湖碧水的守候,就好似又有了一双梦的眼睛、一首诗的意境和一尊佛的含容。 溜达像山湖,我想起了今年四月八时大像山的盛景。四月八转山是大像山由来已久的习俗。这千古流传的风尚,长盛不衰,如今又新修了水上公园,更是锦上添花,热闹非凡。山上山下,游园赏景的人,转山礼佛的人,相继而来,摩肩相继。沿途车如龙,人如潮,商铺林立,人声鼎沸。飘扬的彩旗,飘飞的气球,飘荡的饭喷鼻香,洒脱的墨喷鼻香,把节日的气氛陪衬得吉祥而喜庆,热烈而详和。而到了夜晚,四月八的大像山公园,更是灯火辉煌,声光相乱,仿如一片童话天下。柔柔的月光下,每一处建筑,都跑着灯管,每一条路基,都亮着灯光。天上的月光照着,地上的灯光亮着,而像山湖有情故意地醒着,湖水中流淌着清新的故事、年轻的笑颜。温婉而多情的光影里,一些在白天忽略了的景物,此刻被灯光点亮后,更加触目惊心,印象光鲜。那形似大象的湖水,抒发的是今人的灵感,寓意的却是古人的情怀;那冲天而起的喷泉,是佛前盛开的莲花,亦是古冀怒放的梦想。仰望古老的大像山,亦好似披了一件梦的衣裳,如诗如画,如梦如幻。从山脚的地皮庙,到绝顶的天爷殿,万千的灯火,如万千的星光,装点着大像山,俏丽着大像山。灯沿山走着,山沿灯醒着。那起起伏伏的灯线,勾勒的是大像山的前世与今生,指示的却是大像山的明朝和希望;那模糊约约的梵音,洞穿了谁的灵魂,又惊醒了谁的尘梦。远处戏楼传来优雅传情的秦腔,这是大像山四月八每年必演的戏曲,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秦腔爱好者的脚步与目光,那些古装的戏服,古老的音响,把人们的思绪带到迢遥的古代,而舞台上演绎的那些古代的人事,古典的情怀,更唤醒了今人沉睡的灵魂、迷路的道德。 一群游人的欢声笑语,拉回了我的思绪。我已来到湖心文化广场中心的祭坛上。站立坛上,放眼望去,一座大理石砌就的牌坊式公园大门,雄伟壮不雅观,高大华美,携带着当代气息;一池清粼粼的大象式人工湖,碧波荡漾,天光云影,散发着古典情怀。游人如花,垂柳如诗,曲桥如梦,拱桥如虹,大像山如玉,像山湖似酒。湖中的水榭,温蕴尘喷鼻香,儒风雅韵,静看花开月圆,世海浮沉;岸边的花木,临水而居,风情万种,谛听燕语呢喃,美男婉转。山上山下,佛光与湖光相照映,高山与流水相依偎;芸芸众生,朝佛有登临之美,游湖有山水之乐。 从祭坛下来,我信步来至“大像山赋碑”前,这是一方大理石材质的碑刻,形似展开的汉简,微斜着铺展在大像山公园的碧水蓝天下,上面镌刻着邑人范三畏撰写的《大像山赋》,华滋憨实,气候万千,纸短情长,言简意赅,短短636个字,写尽了大像山的历史与与风采,风尚与人情。每次来到公园,我都要伫立碑前,负责拜读。今日游过大像山,我更是怀着亲切与尊敬的心情,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吾邑名胜之大不雅观,厥为大像之山。山属朱圉,在旧县之东、今城之西,二水夹峙,北奔渭坻;一峰齐耸,文武对帜——所谓文旗,矗东迤西。山以像名,像塑释迦牟尼,像而大哉,法相欲齐敦煌弥勒。异岭共云,同峰别雨,河西旧风,冀城馀俗。子山铭文尚在,嘉祐谬说可释。 “是山也,松花崖有千载之松,而白皮者称焉;飞云岩多四季之卉,而紫丁喷鼻香馨矣。石窟鳞次,甍宇栉比,法苑琳宫,阁道摩空。灵岩、永明之寺,太昊、武当之宫,百子、双明之洞,关圣、鲁班之殿,丘祖、吕祖之不雅观,大佛、三圣之窟,文昌、凌霄之阁;又有羲里、石里之碑,姜侯祠与文社之记,爱民之亭,云封之碣……四季登临,睇远舒心。 “其会也,则有正月上九之会,三月百子之会,四月浴佛之会,七月盂兰之会……而四月之会为最典,以其因于佛诞也。这天也,遍野漫山,朝圣者如织,游山者如醉,紫喷鼻香如云,碧草如茵,或丽日如抚,或小雨如沐。山下散布鱼龙,百戏纷陈,箫鼓生韵,帐幔成阵,列肆如鳞,绿女红男,济济簇新,扰扰如云;村落童溪叟,缓步舒筋;山媪农妇,摩接呼群,其盛况大过于元夜灯春焉,噫嘻盛哉!
“世纪之新,一十五年,山上山下,辟为公园。盛世之作,平生易近之乐。引水围湖,多植菱藕,筑榭于洲,通桥于陆。水禽来栖,群鱼来游。芷兰汀渚,烟波远浮。登榭望山,纵目烟煴爽气;临山瞰园,馥鼻佳气浓郁。心驰瑶池,身在画图。戏台歌管,广场对舞,诗社分题,书友研摩,拳师授艺,歌者练喉,画童写生,学子背书。喧有远韵,静有寻思。远客停车不忍离,虔士朝山忘礼佛。皆一游而永趋,谓人境之仙都”。 吟诵完范老师的赋文,我口啮噙喷鼻香,余味无穷。抬望眼,山上山下,一派天清地明,旷达明净。我赏心悦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像山。临转身的瞬间,我回望了一眼山巅的大佛,他威镇南天,慈悲含容,展露着盛唐的庄严,盛唐的壮不雅观!
(文/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