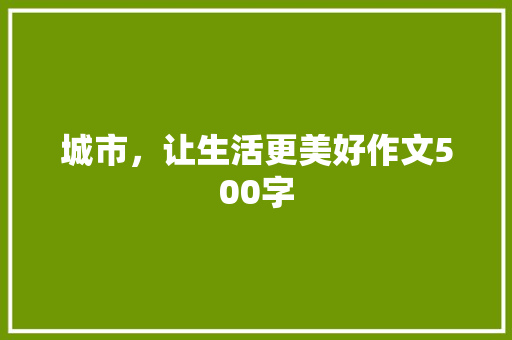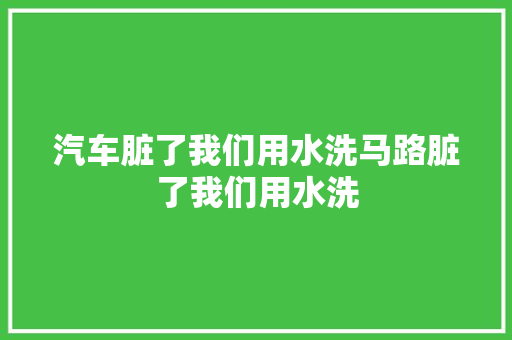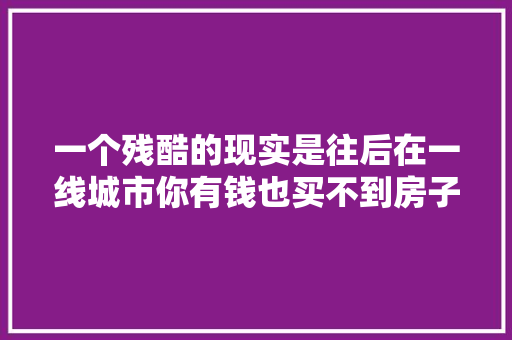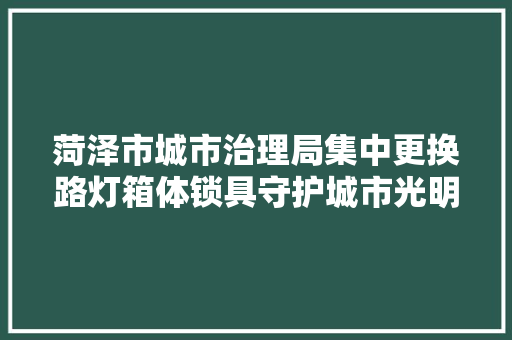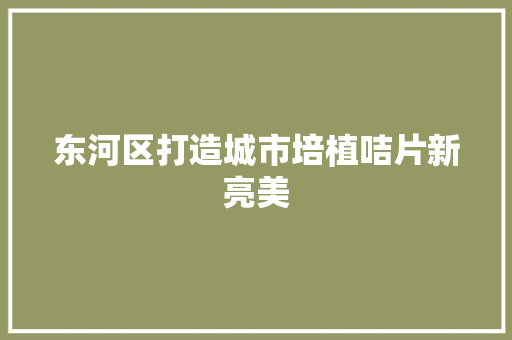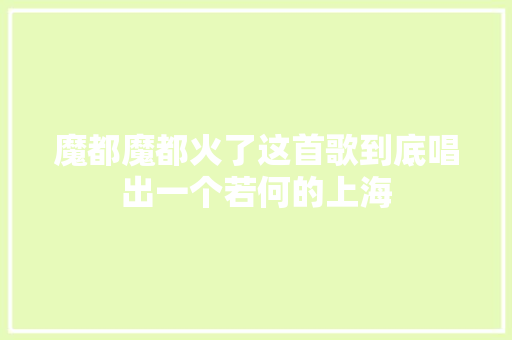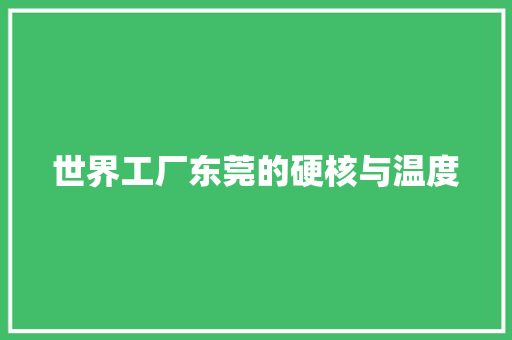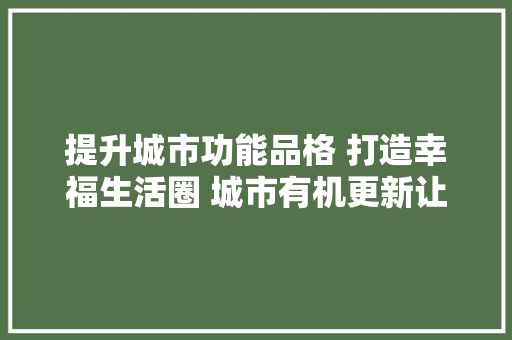城市研究学者哈罗德·乔尼对付城市的描述精准地捉住了城市的特点——变革万千与异质性。而这一主题正是社会学对付城市的主要关怀所在。
从村落庄来到都邑以不同办法谋生的陌生人们是如何生活与行动的?异域人的都邑生存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有机和谐还是失落序混乱?曾经盛行的“漂”话语与当下“附近的消逝”的焦虑,到底折射出当今城市人群的何种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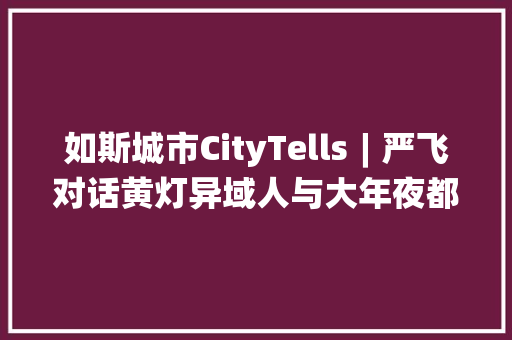
对付这些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在非虚构新作《悬浮:异域人的都邑生存》一书中供应了许多有益的启迪。他通过记录与剖析异域人大都邑生存实景,用“悬浮”来描述流落在城市的中国年轻人所共享的某种心灵状态。
《悬浮:异域人的都邑生存》 严飞 著 空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1
作家黄灯在世纪之初从湘北小城来到广州求学,并在高校任教至今。从检视自己,回望乡土的《大地上的亲人》到不雅观察年轻人命运的《我的二本学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对人的状态的影响,一贯是她所关心与书写的主题。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约请到严飞与黄灯,从作为异域人的都邑生存出发,聊聊城市与人。
——本期高朋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黄灯,学者、非虚构作家
——本期主播
郝汉、灵子
——收听韶光线
06:30 城市如何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
13:36 21世纪初,来到大都会广州是何种体验?
26:15 房产中介、理发小哥等群体,如何构成城市生活的“附近”?
32:05 70后一代城市生活的“确定性”
48:10 城市生活里的“附近”究竟是什么
52:50 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感到“悬浮”?
64:15 重修身边的小天下,如何抵御都邑的冷漠?
75: 55 附近的“技能”,是与周遭事物打交道的能力
——节目内容摘选
——“有机联络”的城市社会
如此城市:社会学出身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乡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期间。那么,这门学科最初是如何认识城市的?
严飞:社会学家之以是把城市作为一个主要的不雅观察工具,实际上是由于城市是村落庄的对照。这种对照的进程是从19世纪中期往后开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在传统的前工业化社会,特殊是乡土社会,存在一种依赖支属关系、从事相似的地皮劳动而建立起来的“机器联络”。但是在成本与工业的齿轮不断推动下,越来越多人从原来的地皮分开,逐步转变成手工业者、工人,来到城市,昔时夜量的人口聚拢在城市中,工业城市才得以出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社会产生了一种差异于乡土社会的“有机联络”的社会性子,它的特点是人们基于社会分工在一起共同生活,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家属亲缘关系。在这样的进程里,我们会创造,人们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利益、左券平分歧根本组成了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里面导致群体之间产生了分解。人群的分解一定导致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的异质性越来越强。
前工业化的村落落里,大家都是支属关系,从事的大多都是农业劳动,是相对同质的熟人社会。但在城市里,正是由于它的异质性,城市里的人会更加关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会是原子化的个体。
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一篇文章《大都邑的精神生活》里说,生活在大都邑的人们最大的特点便是比较“自持”,或者用一个负面的词叫“冷漠”,而且会“工于心计”。
可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办法。
——当“悬浮”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
如此城市:黄灯老师的写作与经历实在深刻地嵌进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悬浮》里谈到的都邑异域人对付城市的神往与体认已经与过去有许多不同。作为来到大都邑打拼并顺利留下来的“早期”中国大都会异域人。在当时与当下,你对城市有何不同的理解?
黄灯:可以特殊坦白地说,只管我的人生变动很多,但在从屯子来到城市的过程中间,我真的没有产生过本日算轻人所感到的“悬浮”的觉得。2002年,我来到广州读书,后来在广州事情,那种不愿定感是没有的。在我们70后那一拨人里,一个人如果能够读到博士,便是在城市能够立足的最好担保了。然而本日的年轻人哪怕读到博士,可能都没有这样的觉得。
2005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全体中国社会是向上发达与热气腾腾的。我记得在当时广州的北京路,人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一样多,摩肩相继的觉得。
2023年1月1日,北京路地处广州市中央,是历史上最早建立广州城的位置之所在。市民在千年古楼遗址参不雅观、嬉戏。视觉中国 图
这些年来,我带过两拨学生。一波是80后,比我小十岁旁边,第二批是比我小二十岁旁边的90后。你能够明显感到,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愿定感与悬浮感明显增强了。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缘故原由不纯挚是由于个体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更多的是个体所能够依傍的东西变得更加不愿定了。
我参加事情进单位的时候,一个工厂都会给你供应住房。虽然孤身在城市,但我确定地知道我跟这个社会的联系是什么,一份事情可以供应什么样的庇护。为什么我没有悬浮的觉得?可能便是由于那时的社会让我感到,人还是能够掌控一些东西的。
2022年8月4日,上海地铁站内,高峰人流密集。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严飞:在本日的城市里面,人们所面临的竞争与本钱都是在一个“内卷”的赛道里面,而且机会的通道逐步变窄。为什么年轻人都在进行考公、考研、考证?实际上是由于人们没有信心在不愿定加剧的社会里面去博取一些东西,而只想捉住一些相对确定的东西。
我之以是用“悬浮”来命名本日算轻人的某种状态,便是由于他们面临更大的焦虑,对付未来有更多的不愿定性。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而越是没有根基,越会想冒死捉住一些东西,让自己仿佛是确定的。
我在《悬浮》里面打过一个比方,所谓“悬浮”,就像一列高速提高的列车越开越快,逐步地飘在了空中,飘在空中往后,人一定是悬浮的,以是车上的人越来越想捉住车的把手、栏杆,来让自己在这个车厢里站稳。但这列车厢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栏杆、把手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我在书里所记录的大都会异域人多是从屯子进城的务工职员。这些人群不像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里面奋斗打拼的人那样有退路,这些年轻城市外来务工职员对付乡土的感情已经非常淡漠,乃至有些人便是出生在城市的,对自己家乡的感情会更加疏离。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城市供应的一些公共做事,没办法在大城市里面上小学,只能去上打工子弟学校。各类现实情形让他们加深与所在城市的隔阂。他们的身份认同会更挣扎与撕裂,他们更会以为自己始终是异域人的状态。
——“附近”的说法,为什么能打动年轻人?
如此城市:谈到这些年来比较盛行的“附近”的说法,严飞老师写到自己身边的家装工人,房屋中介等等,他们构成了您在城市生活的“附近小天下”。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里,该如何认识附近,乃至创造、感知或是重修它?
严飞:我自己对付“附近”的觉得,是“附近”的内涵变革很大。回到80、90年代,所谓“附近”每每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单位大院,或者职工大楼,里面住的是单位的同事。单位制的“附近”是高度同质化的,而它的边界实际上是非常强的,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之间并没有那么多互换。
而且这种单位内部的“附近”,它的交往模式依旧保留有一种强烈的权力逻辑,例如科层体系里面的互换,单位的领导与职工的互换。
但本日的大城市里面的“附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任意性,它变得高度的异质与殽杂,人们会在城市的流动性中产生崭新的交集。这种交叉性是非常强的。正因如此,比较单位制期间的人,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去重新建构一个新的“附近”。越大的城市就拥有越多的人与物、人与空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多重并置之下的丰富“在地性”。
本日谈“附近”,更多还是该当强调它的异质性、殽杂性、流动性,正是由于它的这些特点,人和人之间黏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办法,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带来意外的惊喜,它们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及其闪现出的片段和火花。
——制作团队
——勾引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