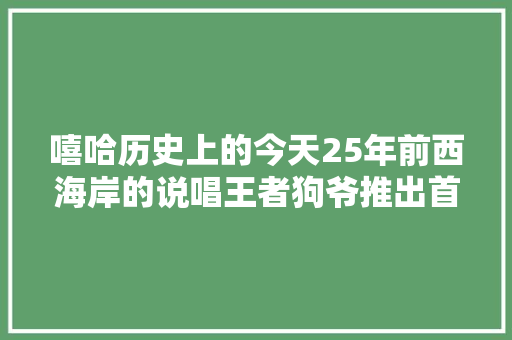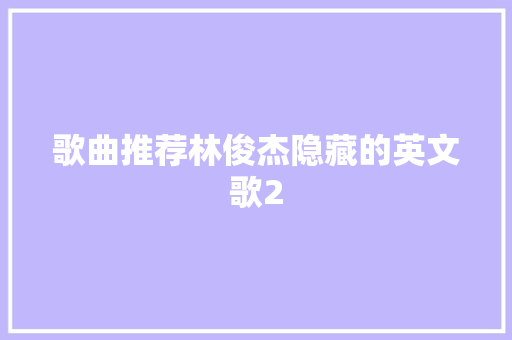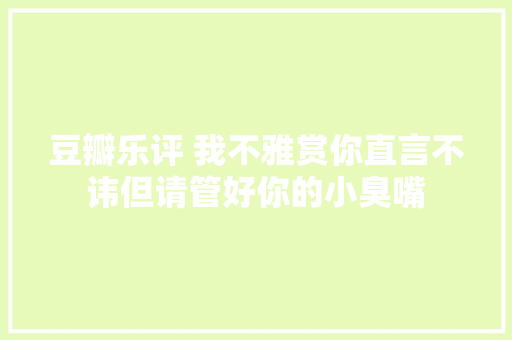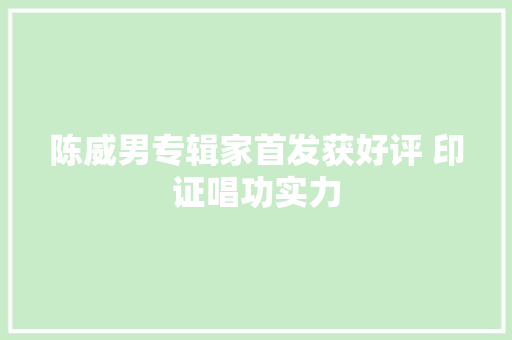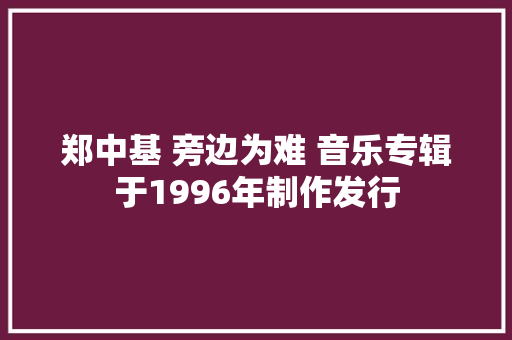开始的三件事
2013年夏季某一天

一个美国朋侪问:“melancholy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我以为词典上的‘忧伤’阐明的不太贴切”。
“那你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词”。
“It means sad。 Sad but beautiful”。
我说:“哦!
是凄美”。
哦!
Mark Linkous,我心里闪过一个更为得当的词。
2010年3月第一周
北京一位独立乐队主唱同另一位主唱说到:“我最近仔细看了闪马(Sparklehorse)的歌词,怎么以为Mark是个要自尽的方向啊”。
1996年1月
为了宣扬1995年首专《Vivadixiesubmarinetransmissionplot》,Linkous接管Radiohead的约请,为他们的英国巡演担当暖场高朋。如日中天的Radiohead永久显得那样的气势磅礴,吸引着台下数千不雅观众。比较之下Linkous以为自己的乐队是如此的扞格难入。
痛恨现场演出,由于讨厌听到自己的声音赤裸、暴露的展示活着人面前。乐队灵魂人物、主唱Mark Linkous承受着巨大压力与不适,但他还是认为英巡对乐队发展是个不可错失落的机会。
1月的一个晚上,结束暖场演出之后,Linkous回到酒店。在过量抗烦闷药和墨西哥安定的相互浸染下(Linkous 多年来一贯遭受烦闷症的困扰,他的精神科年夜夫为担保他这次英国之行顺利进行换了他多年来服用的抗烦闷药,然而他并没有见告任何人),Linkous在浴室溘然晕厥。直到第二天做事生创造他的时候,由于全身力量的压迫,他腿部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滞了14小时。
医护职员试图纠正他的双腿并为他注射了钾溶液, Linkous随后涌现了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导致贰心肌梗去世并伴有肾衰竭,他的心脏曾一度停滞跳动数分钟之久。作为巡演经理的Paul Monahan回顾:“在救护车上,没有人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
几周之后,他终于在伦敦的圣玛丽医院睁开了眼睛:看着自己全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他的妻子Teresa一贯伴随旁边,并偶尔租借《憨豆师长西席》给Linkous当做消遣,他也会笑到伤口疼。只管护士明令禁止,Camper Van Beethoven的David Lowery还是时时偷偷给Linkous喝上几口适口可乐。
三个月多的治疗中,Linkous经历了7次手术、忍受连续的透析,还要接管抗传染治疗。起初年夜夫担心他须要截肢,虽然出院时保住了双腿,他戴上了将伴随他生平的护腿,命运宣告他今后的人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意外之后,Mark Linkous在采访中坦言他那时特殊害怕自己大脑里卖力写歌的能力被毁掉。
这位喜好将内心隐匿在老式收音机般的模糊噪音之后,抑或游丝般柔柔羸弱的高音之下,讨厌演出,讨厌城市,唯独钟意田园的鸡鸣狗吠,钟意开着他最爱的Moto Guzzi 1000S复古摩托车从乡间被野草覆盖的废弃矿场飞驰而过的忧郁艺术家,在那场意外中侥幸逃生。
他还可以连续创作音乐,还可以用从旧货商店淘换来的笨拙Farfisa老式教堂风琴和16键卡西欧采样键盘,或者被他从烂泥巴地里拾起的旧麦克风连续创作,他还可以在他乡下老家自己建起的录音棚里用他薄弱、纤细但无比纯净的嗓音把这世上最忧郁的旋律唱出最虚幻的美好。
从不良男孩到失落意吉他手
关于Mark Linkous独一无二的音乐生命如何成形,还要从头讲起。
1962年9月9日,Linkous在西南弗吉尼亚村落庄小城Clintwood出生,父母自他12岁便分道扬镳,他开始混迹于名叫Pagans的摩托车党,团体内的“朋友”有时会为了一次冰毒交易以60或80英里每小时连忙驾驶。他的母亲不得不将这个问题少年送到住在Charlottesville的退休矿工祖父那里,寻求环境的改不雅观。
Linkous的聪慧资质并没有表现在学生生活里,虽然没有辍学,但是他对学习毫无兴趣。他曾像校园小丑一样平常故意用头撞门,只为让大家书任他撞断了鼻子,或者躲在足球场的下水道里吸食大麻。那段韶光,祖父虽然对他很严格,但依旧给了小Linkous生平受用的两件东西:一件皮夹克和一把Gibson吉他。
70年代开始打仗吉他,Linkous翻唱过许多Black Sabbath、Ramones和Blondie的歌曲。对Alice Cooper的痴迷还让他留起了偶像的发型,不仅如此,他还让祖母缝制了模拟Jimmy Page的衣服,乃至精心制作了KISS演出时利用的闪光烟火。
80年代初,Linkous高中毕业,来到纽约成为power-pop乐队Dancing Hoods的吉他手。不久之后就在这个城市的摇滚场景中落了脚,发布了小有影响的专辑《12 Jealous Roses》和《Hallelujah Anyway》,并与像the Damned和Psychedelic Furs这样的乐队乐手成为了朋友,接着毒品问题彷佛自然而然的找到了他。乐队跑到洛杉矶只为求得大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他们给各种诸如Camper Van Beethoven这样的乐队暖场,还上了MTV的 “120分钟”。
闪马乐队鼓手Johnny Hott有次曾说:“Linkous在Dancing Hoods时很有舞台表现力,由于不是乐队核心,他可以相对轻松的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Dancing Hoods象征希望的合约终极没有到来,随着主唱在唱片厂牌找了事情,贝斯手锒铛入狱,乐队很快终结,Linkous仍旧面临着海洛因成瘾问题。此时这位窘迫的年轻吉他手只能住在海边的面包车里,并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生命,大概下一秒就会永久消逝在大海里。
Tom Waits的神迹
此时,神迹涌现了。他在电台听到了DJ播放英国极简作曲家Gavin Bryars十九分钟版本的《Jesus’ Blood Never Failed Me Yet》。歌曲在神圣的管弦乐伴奏下,一个流浪者和Tom Waits用抖动的声音轻轻重复吟唱歌名六字。这首歌深深触动了Linkous,也让他在地狱半敞的门前掉过分来,重新振作。
跟随这一启迪,他搬回弗吉尼亚父母那里寻求脱瘾帮助。一个月的入院康复之后,他随即和好友,House of Freaks乐队Bryan Harvey和Hott一起搬到了Richmond。在那里,他过着平凡的生活:喝喝咖啡、抽着骆驼喷鼻香烟、吃吃路边烧烤、并以粉刷屋子和洗盘子这样的小活为生,他有时会制作手工陀螺并用散弹枪,将它们打碎。他也偶尔演出,并组建了一个过期的盖尔民谣乐队Flaming Cicadas。
“我回抵家乡放弃追名逐利,只想做好音乐而不在乎其他的统统。”Linkous在1999年回顾道。
后来,Lowery也搬到了Richmond并在那时和Linkous成为了好朋友。他借给Linkous一部只有7轨正常的Tascam 688八轨录音机,Linkous开始用它录制新曲并把录音带发给后来Sparklehorse第一位经纪人Dave Ayers,他们在电话里谈论歌曲的问题。
Ayer说:“每当Linkous录了好作品,他第一反应便是去卡车里播放”。经由考试测验,Linkous将他的歌加上失落真来粉饰他自己本来的声音,有时乃至会用一支在泥巴地里滚过的脏发话器录音。
三个人经由无数次的互换,这些录音终极进化成为Linkous第一张完全专辑----《Vivadixiesubmarinetransmissionplot》。Capitol Records董事长Gary Gersh(签下Nirvana的人)为Linkous奉上唱片合约并在1995年8月为他们揭橥了专辑。
这张专辑可以听到像《Sad & Beautiful World》或《Spririt Ditch》中潜藏在广播声的“保护”下,Linkous那苍白纤细,彷佛一击即碎,你却永久不想打断的柔柔唱腔。或在《Someday I Will Treat You Good》中又能找到盛行摇滚的躁动与力量。专辑还接管了其他艺术家的启迪,比如贾木许和莎士比亚。在《Homecoming Queen》中,开头便是《查理三世》中国王那句:“一匹马,一匹骏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专辑销量一样平常,但为乐队带来了为Chesnutt和Son Volt开场演出的机会。更主要的是,这张专辑传到了在中东为新专《The Bends》宣扬巡演的Radiohead主唱Thom Yorke耳里。1995年秋日,Radiohead约请Sparklehorse参加为期一周的英国巡演。
我想,如果Tom Waits的声音未曾涌如今那片混沌的海边,就不会有这张包含忧伤梦幻歌谣和沙哑摇滚圣歌式的经典专辑,以及之后的统统。
忧伤泥泞中蜘蛛向你问早
之后,就如文章开头第三件事讲的那样,悲剧发生,惊惶失措。
“那是一种持续而强烈的疼痛,一个人被截肢,会有一种称为幻肢痛的觉得伴随着你,这让我崩溃”。
更糟的是,回到家乡的Linkous不得不接管年夜夫为减轻长期慢性疼痛、重新规复腿部功能而开给他的吗啡,药物对他的侵害彷佛人生路上无论如何都避不掉妖怪,将他全体人残酷的、致命的、讽刺的重新拉回阿片成瘾这个永恒的问题之下。
这时他依旧足够倔强。奇迹般的只花了三个月便让Sparklehorse回到舞台上,坐着轮椅与Cracker同台演出。同时,他还与来自乔治亚州同样瘫痪的雅典作曲人Chesnutt成了密友,Chesnutt在Linkous受双腿麻痹之苦时给了他不少鼓励。
那段韶光,Linkous揭橥了Sparklehorse第二专《Good Morning Spider》,映射了Linkous漫长的病房经历,专辑进一步考试测验了实验盛行风格,捉住一幕幕寂寞与幽怨的瞬间,融入歌者未曾流逝爱与原谅。媒体把稳到专辑散发出的幸存者的病态美而大肆鼓吹。这让薄弱的Linkous深感不安与难为情:“很永劫光我都以为们采访我的唯一缘故原由便是我是一个快去世的人”。
按照90年代主流厂牌的标准,Linkous的公司持续施压迫使他砍掉一些广播噪音的潜力作品,就像专辑中《Galaxy/Happy Man》,四分钟的声音旅程开始于怪异交错的乐声,又溘然转换到电波调频的静电人声中,终极爆发在渐起的grunge曲调里。公司认为撤除忧郁的前奏和迷乱的噪音,这将会是一首大热歌曲,然而Linkous却对公司想要重录商业版本的想法不由勃然大怒。
Sparklehorse这张唱片并不卖座,但收入依旧足够养活Linkous夫妇,他们租下间隔Richmond90分钟车程的农舍,那里阔别社会叨扰,足以避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Linkous沉浸在自然的环抱中,溪流缓缓、狗吠乡间、狗熊在野外溜达,蜘蛛在清晨向你问好。这统统都呈现在它的歌词中,真实而动人。他在屋子里开辟了一处叫“Static King(静电王)”的排练室,那里摆放着一台16轨调音台、一打子合成器及其他乐器,个中有把德国小提琴是他在一场暴雪中用20美元在一个毒品贩子手上买的。“Static King”成了他巡演归家的庇护所,他逐渐在那里找到那张最具年夜志专辑《It's a Wonderful Life》的灵感。
冲破沉静的是他乡
为了录制新专辑,Linkous决定离开熟习的家乡,辗转多个城市,并操持与一票艺术家互助。他跑到纽约找到好友Cardigans的Persson,他们在Flaming Lip制作人Dave Fridmann的Tarbox Road Studios录制歌曲《Gold days》、到巴塞罗那与PJ Harvey和Portishead的 Adrian Utley及制作人John Paris互助《Piano Fire》,在《Dog Door》中找偶像Tom Waits演奏相对金属的吉他并交情对唱。
一贯以来,Linkous的舒适区都是“保持沉静”,他早就习气依赖音乐上的噪音声响作为核阅自身繁芜存在的镜子,让有时傻兮兮却极具措辞天赋的歌词,或非常规却寻思熟虑的低保真编曲若隐若现的展示他大智若愚的、大师般的音乐创造力,而不多言。
寻求浩瀚音乐人的互助并非哗众取宠,也决非故意。在他的脑海里早就深谙新作如何制作混音,他清楚每一个细节,知道整张专辑终极的氛围。只为实现心中的音乐抱负,他战胜羞涩,主动靠近那些他敬佩的艺术家。就像在得知Tom Waits喜好闪马之后,他终于灌下几杯野火鸡威士忌然后鼓起勇气联系到他的英雄。二人很快达成共识并交流录音邮件。Waits描述Linkous那阴郁却迷人的音乐时说:“那就像在水下睁开双眼,你会惊异你所看到的统统”。
就如Waits所描述的,Linkous乐于考试测验统统可用的设备。制作人Parish回顾他曾利用一部代价25美元的监听设备Whisper 2000来扭曲自己的人声。
Linkous还找来一部产自70年代,依赖12寸塑料碟片播放的Mattel玩具合成器演奏歌曲,机器中预录了一首欢畅的采样《Guitar in 3/4 Time》,你能从《It’s a Wonderful Life》入耳到它。
对迂腐调性的追求还表示在《Morning Hollow》录音中,他将风琴的踏板装置换上了真空马达,以制造声音的衰减和流动感。
每一个人类都熟知钢琴的声音,然而Mark将它视作外星人带到地球的按钮盒子。他绝非惺惺作态,这便是他看待音乐的视角。
Linkous将这张带着希望的专辑《It's A Wonderful Life》奉献给家人、朋友以及在他濒去世时候拯救过他的歌迷。通过专辑,Linkous试图提醒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他对天下的感激之情在此时膨胀着,通过歌词我们看到他对平凡生活的映射: fever, rabbit dreams,drunken boats,dogs eating birthday cake,sun beams touching his skin,skinny wolves being held at bay。
只管如Linkous所讲专辑表达美好、阳光的一壁,听到他反复吟唱着“It's a wonderful life”、“May all your days be gold my child”我依旧恍惚于我那突降的忧伤从何而来,又如何瞬间抵住我的喉咙,窒息的觉得在歌曲结束之后仍不能消散。但我知道,他尽力了。他的压抑从未真正阔别过这些动听的旋律,这种闪马式一触即碎的美好在那深深的悲惨中变成这世间不可替代的独特情思与倾诉,你的脑海中轮转交错出无数生活的闪耀瞬间与最阴郁的画面。
“我很光彩很多人见告我我的音乐对他们很主要,大概音乐的一部分意义便是鼓励人们在为时已晚之前见告对方他们有多主要”。
困难中的一抹光
专辑发布后一个月,911事宜发生了,这场悲剧在Linkous的心中久久无法释怀,他以为统统都像天下末日一样平常。生命的大厦从那时起便再次变得风雨飘摇起来。他个人的悲剧也开始逐一上演,由于朋友离世,他的烦闷症再次复发,海洛因问题再次成为无法忽略的梦魇。
为了戒毒,2002年Linkous搬到家乡弗吉尼亚400英里以外的蓝岭山脉,持续的偏头痛环绕着敏感薄弱的他,这使得他连睡觉都成为了奢侈。第二年,他到佛罗里达接管了抗烦闷治疗并终极返回舞台,与Flaming Lips和R.E.M.共同巡演。
那段韶光里,Linkous的创作碰着了瓶颈,第四张专辑《Dreamt for Light Years in the Belly of a Mountain》困难出身。他终止了与Fridmann和Flaming Lips鼓手 Steven Drozd的互助,他的古怪行为也惹怒了公司。
在创作中,Linkous有时听到了Danger Mouse《Grey Album》专辑,这是一张Beatles《White Album》和Jay-Z的《Black Album》的混和专辑,Linkous毫无情由的爱上了它。2005年二人终极得以见面,Brian Burton(Danger Mouse)飞到北卡罗来纳州与Linkous开始正式互助,他也希望这能够帮助对方在艺术道路上重新振作。二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的努力,并终极打造了经典专辑《Dark Night of the Soul》的雏形。他们还叫来Iggy Pop、Julian Casablancas、Frank Black、Wayne Coyne、Chesnutt和Persson帮忙他们完成歌词和人声部分。
Burton偷偷找来了大卫林奇为专辑拍摄照片,这让已经很少露出笑颜的Linkous表现出极大的惊喜。大卫林奇被Linkous所传染并全心投入到影像创作中:“Linkous抽着没有过滤嘴的喷鼻香烟,烟灰烧到8英尺长,我看到尼古丁把他的手指熏染成黄橙色并侵浸他的喉咙,改变他的音色。他是个真正纯粹的人,他的温顺、薄弱将他与凡人差异开来,这些都融入到他的音乐中。”。林奇用Piney Woods grunge形容Linkous的音乐。
“每天清晨醒来我都以为很失落望,由于我创造我还活着。”
2006年新年,Linkous的好友Bryan Harvey及妻儿在家中被残酷杀害,惨案震荡了全体城市。Linkous在同年9月25日发布了《Dreamt for Light Years in the Belly of a Mountain》纪念他的石友。相继而来的宣扬巡演并没有冲淡Linkous的悲哀,他和Hott在巡演中彼此拥抱落泪、相互安慰。
在2007年洛杉矶的一场演出中,闪马乐队长期互助的唱片公司溘然宣告与他们停滞互助,比较外洋备受追捧,海内的票房惨淡为乐队之后的巡演出息打上了问号。Linkous后来表示:“之以是迟迟没有打开美国市场,是由于很多人肤浅的认为我们的音乐只有阴郁和沮丧。而大洋彼岸的不雅观众能在我的音乐中看到乐不雅观与希望。”
之后的巡演以及靠近两年的演出,Linkous依旧保持得体的诙谐感,并表现出常有的身体上的病态。他在这段韶光参与奥斯丁Lo-fi传奇Daniel Johnston的巡演并为他弹吉他(你大概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知道涅槃主唱T恤上那只田鸡,便来自这位音乐人83年的专辑《Hi, How Are You》封面),并与电子音乐人Christian Fennesz互助了氛围专辑《In the Fishtank 15》,之后,又在大卫林奇的记录片中配乐。
然而,朋友们无法忽略二心坎的挣扎。没有厂牌支持,常常拖着设备奔波于各种演出,还要与身体疼痛作斗争,只为做音乐。这统统是否值得?
“如果不做这些,我只能一个人随着那些小动物走进森林,然后蜷缩着去世去。”Linkous给出了答案。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在《Dark Night of the Soul》与闪马第五专发布前夕,Linkous与妻子Teresa的婚姻彷佛走到了尽头。他决定搬到了Knoxville,并逐渐喜好上了这座城市,乃至与当地人打起了交道。起初的欣喜被没有妻子伴随旁边的现实泼了冷水。长期以来妻子都担当着守护者的角色,不仅照顾他的康健,更在每一个存亡关头拯救这个薄弱的生命。他第一次,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独立生活。
《Dark Night of the Soul》于2009年6月发布,由于与百代唱片的法律轇轕,这张专辑发布时除了一今年夜卫林奇的拍照图册,只有一张空缺CD,上面写着:为了避免与百代唱片法律轇轕,Danger Mouse无法将音乐收录进这张光碟,因此这是一张空缺光碟,任君处理。
2009年秋日,从欧洲巡演归来的Linkous来到了Electrical Audio studio录制新专辑。不像以往的作品,它将歌曲进行理解构与重修并简化了音乐元素使其更具盛行气息。在歌词方面Linkous也不再字字珠玑。
只是在专辑制作时,Linkous大多在太阳落山时醒来。那种缓慢降临的阴郁,烈酒飘散在空气中的凝重,都准确合营着Linkous日渐严重的烦闷。
更致命的迎头重击终于到来。2009年圣诞节,他的石友Vic Chesnutt自尽。Linkous不仅失落去了一个值得尊敬的朋友,他更失落去了一个与自己如此相似的伙伴—一位瘫痪、病态、扭曲的艺术家。闪马乐队经纪人Dave Ayers说:“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真正担心了”。
之后,Linkous彻底迷失落了,Hott写邮件鼓励他振作,找到属于自己的“铠甲”。
“我已经不知道我的铠甲在哪了”Linkous回答到。
那一天还是到来了
2010年3月5日,R.E.M.经理DeWitt Burton终于帮Linkous把全部家当搬到了Knoxville。
3月6日,Linkous到Knoxville彻底定居的第一天,那是个出奇暖和的冬日。对当地鸡蛋和芝麻菜并不感冒的他为自己点了一餐“棕色交响乐”---培根、黑巧克力和一杯意式咖啡。接着他喝下1/5瓶肯塔基波本威士忌,然后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短信。他开始心烦意乱,却只对Minor和DeWitt说了一句:“这可不好”。
不久之后,Linkous回到自己的房间,那里放着他玄色的ITM来福步枪。他戴上玄色棒球帽,穿上法兰绒衬衫和夹克准备出门闲步。衣服里面是一件闪马乐队T恤。
大约下午一点一刻,Linkous坐在蜿蜒的小道上抽了几支烟,然后双手举起他的来福枪对准自己的心脏。一声枪响回荡在Knoxville。
警察的报告上这样描述:“这是一起自尽”。
结尾的三件事
2017年2月
最近,我又问了那位美国朋侪:“你还记得melancholy的中文意思吗?”
中文精进的他给了我一个更详细的回答:“凄美。相对凄,包含的美更像暗示的感想熏染。当然也要看语境”。
2011年 3月12日
那位曾经嗅出Linkous去世亡意味的音乐人发布了他的新专辑,个中一首歌名叫《闪马》。
新的一天已开始
让我们快乐一点好吗
不要总愁眉苦脸的思考你的来日诰日
只管这是个悲哀而又俏丽的天下
快乐的奔跑的小马
它闪烁着涌现
来,靠近我一些
说,甜蜜的措辞
快,再靠近一点
说,我们的来日诰日
2017年3月6日
又一年的春天到了,除了各种音乐大师的忌日,同时听闻一些艺术家的自尽,人们开始纷纭谈论起有关天赋与去世亡,倔强与薄弱的话题。伟大的艺术家彷佛都要被贴上“英年早逝”、“喷鼻香消玉殒”的标签来注释他们的“资质卓越”与“才华出众”。人生的意义彷佛永久要上升到一种近乎极度的理性揣测。
我一贯以为,一个感性的问题是无法用一个理性的思维去解答的。就像Linkous给我留下最深刻的情绪,并不是对付他悲惨命运的同情或独特音乐的敬仰。永久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是他通过伪装的歌喉塑造的独特的扭曲美,是他依赖各种古怪的发声装置表达最柔柔混沌、充满温暖的悲惨,还有在偶尔探出头的真实人声与狂躁吉他中不遗余力挤出的怪异活力。
他见告我的不止是“凄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还有它最真切的内心感想熏染。
7年过去了,Linkous带给这个天下的抱负和忧伤一贯萦绕在它的音乐能到达的每一个角落。命运或许对他稍显不公,也对很多患烦闷症或饱经药物困扰的艺术家们不那么年夜方,但他们都竭尽所能的,把自己能够给予的对美的惊艳诠释抛向人间,那么,天赋和去世亡就都不是重点。
末了,祝大家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