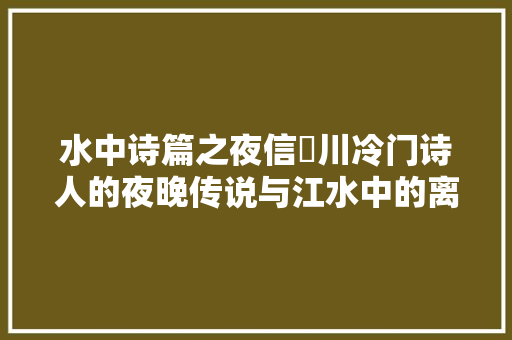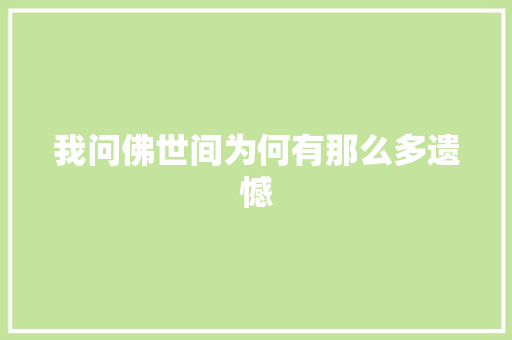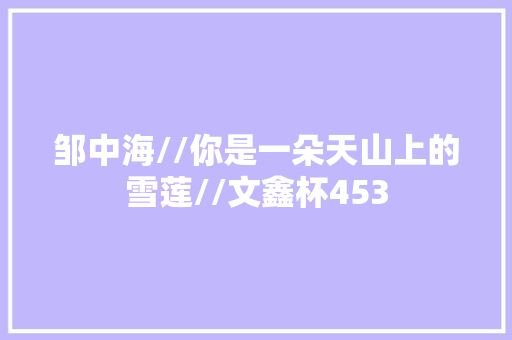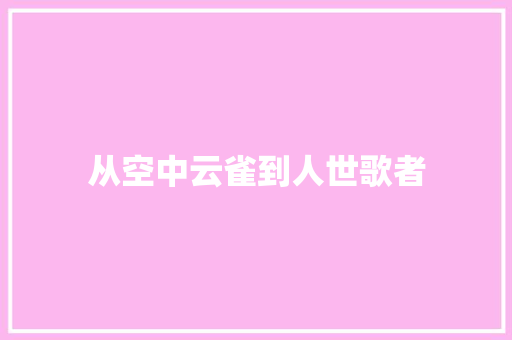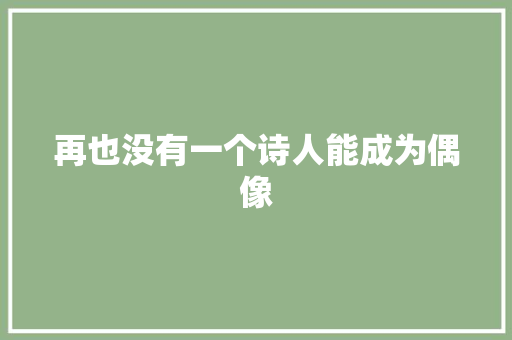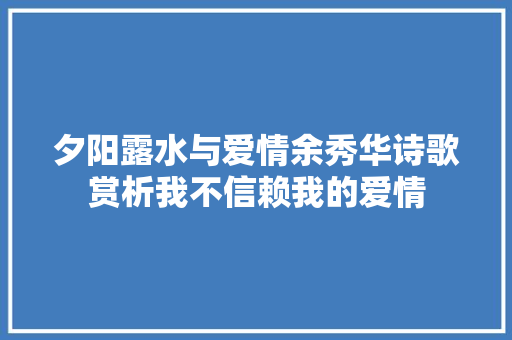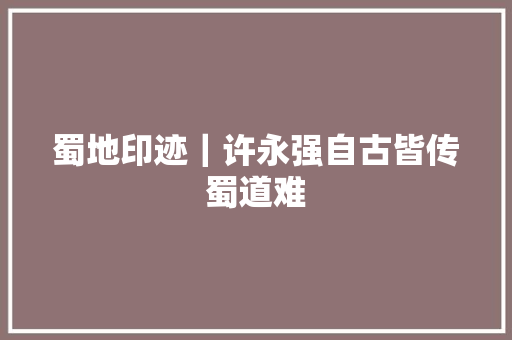我有故事,你要听吗?—— 柚子小姐的列车
比起飞机,一贯以来我更喜好坐“况且况且”的火车,不大不小的空间足以让你有约束的伸展,烦懑不慢的速率刚好可以听完或者发生一段故事,不同的出发点,一样的终点,给你五个小时,到站时记得给对方一个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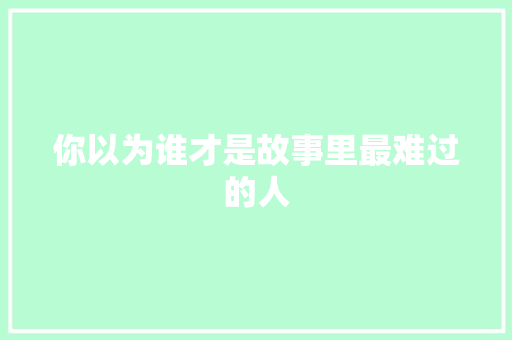
每一次出差或者旅行时,我总会在火车上碰着一些人,听到一些故事。我曾碰着过一个列车墨客,是真是假虽然无法证明,由于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已经醉了。但我以为他是,是墨客,也是醉了。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桌子上一瓶啤酒,一包中南海。他支支吾吾的望着窗外嘴里碎碎念着我听不懂的诗,右手拨动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撸上来,又撸下去,反反复复,动作显得闇练而轻易。
“嘿,你饮酒吗?”
“我饮酒怕醉,吐了麻烦。”
“吐了不麻烦,就怕吐不出,醉不了才麻烦。”
我心想,这丫一定博识,你假如问他去哪儿,一张口估计便是远方、自由之类的词。
柚子:“你去哪啊?”
墨客:“不能说”
柚子:“为什么不能说?”
墨客:“我们不熟,说了不屈安”
他问,“那你去哪儿啊。” 我心想,绝不能输了墨客气质。于是我说,“去远方。”不成想他居然破口而出,“哈哈哈,别逗了,坐火车能远到什么地方去啊!
”
后来他喝醉了,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知青下乡,爱上了一个农场里的姑娘叫官琳。这姑娘有着不错的家境,比起乡里的其他姑娘官琳多少透露着一些灵气,红头绳、马尾辫和水灵的眼睛。在那个禁忌的年代,每到风起日落的夜晚,知青便和官琳偷偷相约在麦田尽头的田埂上,为姑娘作画。
久而久之姑娘和贰心生爱意,但终极还是骗了他。她曾答应他,等着他功成名时回来娶她。知青回城后,不到半年就成了颇有名气的小画家,但再回到农场时官琳却已经嫁人了。
他懊恼不已,以为是自己的离开,让心爱的姑娘受了不安的折磨,让别人有机可乘,于这天夜举杯,不肯醒来。直到农场另一个暗恋他的姑娘见告他原形他才明白,原来官琳早有婚约在身,只是没见告他,他走的第五天,她就结婚了。知道原形后他带着愤怒和悲哀离开。后来由于画山间的野狗而有名于世。
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列车墨客一刻一直地把那在无名指上的戒指,撸上撸下,像是一个孩子正在进行的一场游戏,但更像是一个成人或紧张或悲哀时的惯性举动。“这戒指是我爸留给我的。”他大概是看出来我盯着那枚戒指。
他接着问道,
“你以为这故事里谁是最难过的人?”
“当然是那画家。”
“那是由于你还没听完故事的全部。”
他又接着讲,原来暗恋知青的姑娘,是为了想和知青在一起,就只说了故事的一半。
原形实在是在知青走后官琳就创造自己有了身孕,当然是知青的,但官琳也不知道知青何时才能回来,为了家人的颜面,她只好嫁给了别人。要知道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是要被全村落人指着脊梁骨谩骂,乃至是被浸猪笼……
墨客:“那现在你以为谁才是故事里最难过的人?”
柚子:“这样看来该当是官琳。”
墨客:“实在该当是那个娶官琳的男人。”
柚子:“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墨客:“那是你没明白故事。”
墨客停下拨弄戒指的双手,缓慢的把目光移向我,深吸了一口气后哀叹的说到,
“我们总是以为美好的爱情里,女人为了心爱的男人私奔是天经地义的,而事先定下婚约的男方必定是财大气粗胡作非为的坏人,但这故事里不是这样的。这男人诚笃本分,却被一群风花雪月的男男女女蒙在蛊里。孩子不是自己的,老婆也爱着别人。你说难过不难过。”
他说,人的生平里该当只有两种惦记,对付不在身边的,和永不会再回到身边的。不在身边的该惦记,永不再回到身边的就该永久惦记。可大多数人只对前者辗转反侧,而后者人们把“忘却”当成是唯一的选择。
他溘然又半说半唱的念了那首诗:
山间野狗乱吠,诅咒四季循环
姑娘成了新娘,都是别人的心肺
我和野狗走山路,多般配
但野狗也有贰心爱的狗
而我只有浊酒一杯,多沉醉
我看他的年纪也不像当年下乡的知青,心想这故事一定是听来的,装得深奥深厚。直到临走的时候我瞥见他包里彷佛装了一个骨灰坛子。
他创造我瞥见了那坛子便笑了笑,也没有刻意掩饰笼罩。那一刻我溘然明白,之前那些搭客为什么都甘心去其他车厢也不呆在这儿了。到站后他背着大包小包往北方走了。
我想,大概他是那个被蒙在蛊里的男人的儿子。但这样一来他的亲生父亲便是那个画家了。以是,这个故事里最难过的到底是谁呢?
或许那男人什么都知道只是爱官琳才原谅统统的;
或许那画家是为了功名才离开农场的;
或许暗恋画家的姑娘的遮盖也是为了真爱。
或许当所有人都随着年月释怀了青春里所有的错,难过的只有这个墨客吧。
一场分不清楚是非对错的爱情里,你进我退,错过美好结局的除了韶光的成分之外,还有太多的未知。
我想墨客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惦记。不在身边的,祝福远方的Ta幸福安康;那些永久回不去的,就该永久惦记,怨恨和忘却终归是自欺欺人的选择,那些放不下的才是故事里最难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