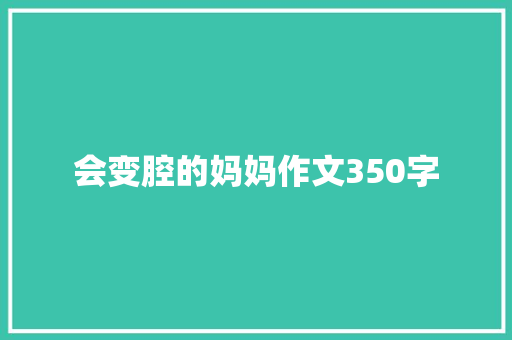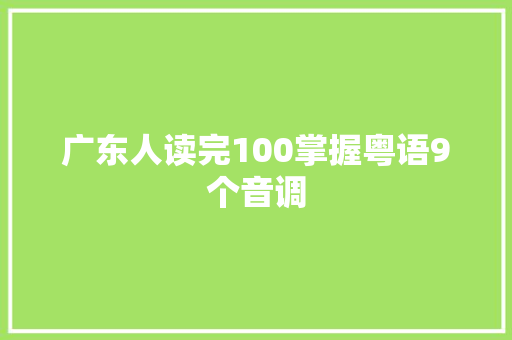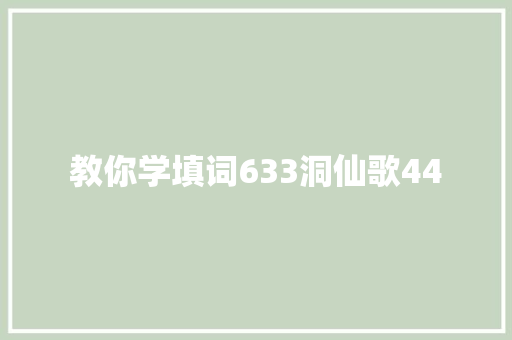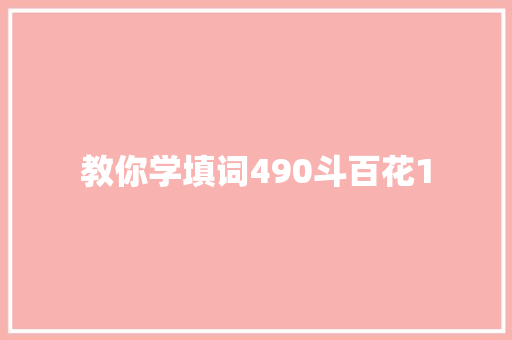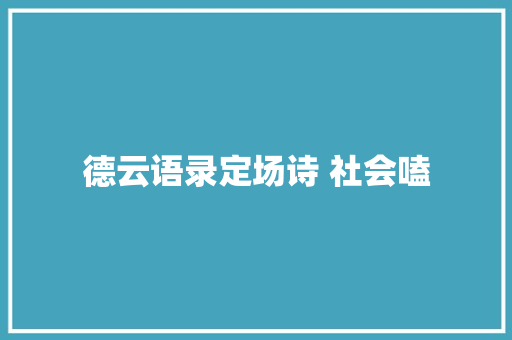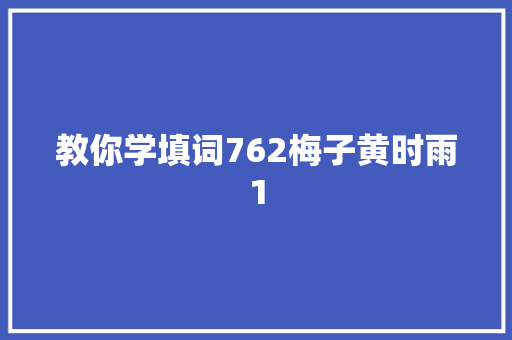2020年第1期 第 104 - 117 页
择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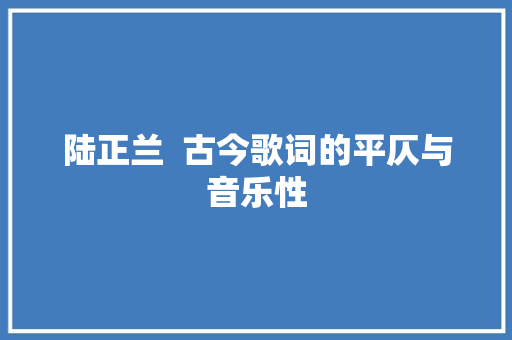
音乐性一贯是古今诗词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今诗词的音乐性至少包括两层,一是歌词声律内在的音乐性,即所说的歌词的平仄韵律。二是诗词(入乐的诗词)的外在的音乐性,紧张是指诗词与音乐的合营关系。很多关于诗词音乐性的谈论将二者殽杂在一起。导致这一局势的部分缘故原由在于中国古代记谱法不发达,歌谱资料缺失落。但是仔细核阅中国当代歌词的音调与音乐相配问题,我们可以创造自古到今,歌词的平仄并不入乐,而是墨客以不入乐诗的格律为模式天生的“自限”。
关键词
音乐性,平仄,节奏,歌词,音调,曲调
1 关于诗词音乐性的谈论
音乐性的谈论一贯是古今诗词谈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今诗词的音乐性至少包括两层,一是诗词声律内在的音乐性,即所说的诗词措辞的节奏,尤其是平仄节奏关系。二是诗词的外在的音乐性,指合乐的诗词与音乐的合营关系。但至今很多关于诗词音乐性的谈论,把二者殽杂在一起。最早的诗歌,即为歌诗,或称歌词。对早期诗歌音乐性的磋商,也就随意马虎稠浊内部音乐性,与外在合乐性。实际上音乐史家谈论的,更多的是合乐性,王守雪称之为“自然格律”:
中国诗从汉到南朝齐梁期间经历了从古诗到近体的衍变,经历了从自然格律到人工格律的衍变,而其核心,则是诗歌音乐美不同内容的衍变。早期古诗中存在的自然格律,是诗乐一体音乐格调的留存,此时人们所认定的诗歌音乐美,是诗乐共同体音乐歌调的美。(2001,p. 87)
刘尧民对诗歌和音乐的关系的意见也基本同等,他的总结是:上古至汉代,依乐从诗;汉至六朝,采诗入乐;隋唐以来,倚声填词。他将依乐从诗期间,即上古至汉代称为“诗歌至上的时期”,将汉之后称为“音乐至上的时期”。这个区分很故意思,由于汉代之前,诗即歌词,汉代之后,诗不一定是歌词。而诗即歌词时“诗歌至上”,音乐单出后“音乐至上”,缘故原由紧张是中国器乐的滞后发展:“器乐在后产生,而古代之器乐也不十分精良,作曲的规律方法都非常大略粗略,以是古代推许诗歌,而以器乐为附属。”他这个剖析有一定道理。
在诗即歌词时,按照杨荫浏的对《诗经》、《楚辞》及汉乐府的剖析,歌曲一定对应了一种曲式,歌词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1981, p.57)但是最耐不起穷究的是唐末出身的“词”,唐圭璋在谈论词的起源,已经指出新曲调是词产生的动力。他的意见是隋唐“燕乐”本不是中原汉人之音乐,五七言歌词难以相配,迫使是非句产生。由于隋唐燕乐乐谱失落落,这个推论已经无法确证,只能想象,“胡部乐”的原歌词没有汉语音节那么整洁。其他文学史家,也赞许这种意见,但谈到词与乐结合,施议对承认,“唐宋时期所传歌词,有词而无谱,又无法入唱,词与音乐的艺术效果,究竟如何体验,确是一大难题”。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磋商,彷佛从一开始就涌现了尴尬。施议对书中举证的《定风波》一词,是从歌词笔墨本身的音乐性,拟猜曲调可能的状态。
问题就出在这里:所有的词学研究者,都承认词的笔墨有平仄规定,然而它究竟是音乐的哀求,还是词人自己打制的桎梏,却难以断言。夏承焘、吴熊和两位前辈说得很清楚:
由于词乐失落传,词的音律、音谱也都随之而亡失落。虽经后人研究,但唐、宋人详细唱奏情形如何,仍难得其原形。清初人万树所编得《词律》,虽名为词律,实际并非词的音律。王奕清等所编的《钦定词谱》,也非词的音谱,他们讲求的都只是词的笔墨格式。不过词的笔墨格式,原为合营音乐而形成的,以是直到本日,笔墨格式也可能作为吟咏及习作的依据。(唐圭璋,2004,p. 211)
的确,近日“仍难得其原形”,但是,不少中国诗词音律的谈论者至今声称,他们在谈论词措辞的音律时,谈论的实际上是音乐的哀求,即曲调哀求平仄安排。这个说法根据何在呢?彷佛殽杂了诗词的内外两种音乐性。
2 “择调”与“依乐用律”
宋人在作词时的确有“择调”的说法,所谓“择调”,夏承焘认为,有三种意义,一为择宫调;二为择腔调;三为“依乐用律”。所谓宫调,便是律调,用来限定乐器音调的高下。宫调是由七音十二律构成,在此根本上形成八十四宫调,它们属于音乐的调性系统。而夏承焘所说的腔调,即为词调,最早为歌谱。夏承焘、吴熊和两位师长西席阐明为,“写作一首词必须先创制或选用一个词调,然后按照它对字句声韵的哀求以词填之。这样写出的歌词方能协音,可以歌唱。以是作词叫填词,又叫做倚声。”(2001,p.20)但问题是“倚声”中“声”是音乐的“声”,还是笔墨格律哀求的“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至今也未明确的难题。两位作者认为,“宋人填词,实不尽依宫调声情。如宋人做小石调的词,大都并不都是‘旖旎妩媚’的,而且每个词调既属于一定的宫调,以是作词时择宫调实际上是与择腔调联系在一起的。”(2001,p. 21)
但这一结论又遭到他们自己的否认:大部分宋词的内部平仄音律哀求,实际上与曲调无关。夏承焘等承认,“宋代一样平常词人填词紧张不是为了应歌,以是填词大都并不顾腔调声情。”他们的情由来自沈括《梦溪笔谈》:
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词,多咏其曲名,以是哀乐语声,尚相协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其矣、哀声而笙歌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冲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沈括,2015,p.45)
沈括是在感叹“今人”所作,曲情和词意的不折衷,并没有指明词的声音和音乐腔调必须合营。实际上沈括因此为,所谓填词的平仄声律,实在与歌谱的“倚声”相去甚远。夏承焘等所说的词的音乐性之三“依乐用律”,虽然在王灼的《碧鸡漫志》、杨瓒的《作词五要》,以及张炎的《词源》中都有记载,但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一种设想和欲望,实际上对填词实践险些没有影响。夏承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宋人之谬:
宋人据以立说,不过附会古乐,并无实际意义。便是大晟乐府诸人及张炎等作词,也并不以此择调。由于词在宋代,虽有不少是按谱协律作为歌词而写的,但一样平常的词人只把它当作一种抒怀的诗的形式,择调时就只考虑词式的是非句格,不再顾及宫调声情与腔调声情,“依乐用律”的更是百无一二。杨瓒、张炎等人论词提倡“依乐用律”。他们只是借古乐来妆点,以此自炫而已。(2001,p. 23)
这可能是当代文学史家对南宋词人的最严重的责怪了,他们的“自我设律”目的只是“自炫”内部节奏。夏承焘的责怪非常有道理,所有在对付中国古代诗歌的“音律”的考证,“倚声”之说,并没有真正依赖乐谱,相反都是从诗词的自身音乐性入手的,很少有真正涉及到音乐研究。浩瀚专家关于词的音乐性的谈论已经表明:许多有关笔墨音律的讲求,实在不是曲调音乐的哀求。
3 古歌词平仄不入乐
问题涌如今何处呢?对这些混乱说法,本文的意见,大略地说,便是平仄等只是词的内部音乐性,由于“平仄不入乐”。平仄节奏的起源,便是从诗不再入乐开始的。魏晋六朝“徒诗”产生,徒诗即不入乐的诗。它们既然不是歌词,写作时就不必考虑曲调。但偏偏是徒诗开始了中国诗歌关于平仄的近两千年的讲究,内部“协律”,是在诗的内部音乐性。这种内部音乐性,已经不再是入乐的哀求(由于徒诗已经不是为配歌而作),只能向内部追求措辞本身的节律。此时涌现沈约的“四声八病”论,是为了拖长音节咏诗时追求的“内在音乐美”。它是在不入乐的五言诗已经立足之后,为所谓“永明体”律诗,而不是为歌词开的药方。
魏晋以降,随着佛经梵语的传入,音韵学兴起,为文作诗讲究音律,也是文人时尚的一种追求。沈约自炫为“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当时钟嵘对这种格律追求,就有所责怪,“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而主见“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峰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1958,p.6557)一旦笔墨讲究落实在平仄,“于是天下相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裴子野,1958,p. 6524)沈约责怪的“八病”,在钟嵘看来,本是正常。一定要算“有病”,只能说是墨客过分的自我设限而已。
到当代,朱光潜的不雅观点就更为明确:
乐府衰亡往后,诗转入有词无调的期间,在词调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往后,诗的音乐性在词的笔墨本身见出。音律的目的便是要在词的笔墨本身见出诗的音乐……诗既离开乐调,不复可歌唱,如果没有新方法来使诗的笔墨本身上见出多少音乐,那就不免失落其为诗了。音乐是诗的生命,从前外在的乐调的音乐既然丢失,墨客不得不在笔墨本身上做音乐的功夫,这是声律运行的主因之一。齐梁是……诗离开外在的音乐,而着重笔墨本身音乐期间。(1998,pp. 219-251)
朱光潜的见地非常确切,正好是由于不再入乐,才不得不用“新方法来使诗的笔墨本身上见出多少音乐”,由于平仄不是音乐对歌词的哀求。章培恒、骆玉明也直截了当地剖断:“声律论的提出,直接的缘故原由,是诗歌大多已分开歌唱,因而须要从措辞本身追求音乐性的美”。(1996a,p.386)诗歌摆脱歌音乐,走向笔墨独立,诗向书面措辞艺术转化, 其变成一种视觉措辞,内向的措辞,更个性化的措辞。从历史上看,在“歌词”期间,反而无平仄哀求。
乃至晚唐北宋,词再度入乐,此时不太看到写此哀求合平仄的议论。直到南宋(12-13世纪)词再次涌现平仄讲究,而这一问题在后来的诗歌文体学史谈论中,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批评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有人认为《后山诗话》是后人托名陈师道的伪作,那么“要非本色”的责怪看来晚于北宋。不管怎么说,“本色”究竟是指什么,是笔墨风格,还是声律入乐与否?至少北宋期间,无人深论。
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晚于苏轼良久,才对此提出较明确的责怪。李清照的《词论》说苏轼词只是“句读不箿之诗尔,又每每不协音律”。他是说苏词既不符合律诗,也不符合词的形式哀求,但是李清照并没有留下笔墨解释词的音律应该遵照何种哀求。
直到周邦彦担当大晟府提举时,“以他的音律知识并接管民间乐工曲师的履历,搜集和审定了前代与当时盛行的八十多种词调,确定了各词调中每个字的四声,乃至同为仄声的上去入都不容相混”。(章培恒、骆玉明,1996a,p.388)对入乐之词平仄,溘然严格哀求。周邦彦当这个朝廷音乐总监倒是挺尽职,反过来证明,在他之前四百年的词创作,无此规定。周邦彦与沈约根本的不同是:沈约的平仄,是为早就不入乐的绝句律诗追加一番平仄讲究,周邦彦是为一开始就入乐的词追加一番平仄讲究。沈约的规定,适宜徒诗的朗读,与歌无关,以是险些一贯延续至今;周邦彦以“入乐”为情由哀求平仄,然而没有阐明曲调有此哀求的缘故原由。周邦彦自称是根据音乐制订平仄四声,由于词牌过多,周邦彦只对应了很少一部分词牌。后世险些每个词牌有平仄规定,是逐代累积,各种人都来制律,他们作为音乐家的资格很可疑,却都被后人仰视为词必须尊重的格律。
我们可以明确说:词的平仄规定,是此作为艺术充分发展往后涌现的额外规定,曲调能否和歌词的这种“平仄的音乐性”应和,至今没有见到确实的研究和实践。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举出周邦彦《饶佛图》一词的“双拽头”部分,指出个中五个字的平仄哀求合理,由于“读来抑扬变革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类而显得拗口的地方。这种词体本身就富于音乐美,同乐曲能完美合营”。(1996a,p. 407)他们明显是从“读来”剖析歌词的平仄哀求,所谓“词体本身富于音乐美”,是把词当诗读。王力指出,宋时入声在许多方言中已经消逝,周邦彦哀求按各词牌填的词符合他定下的四声格律,不知所据是当时“官话”还是何种方言。
南宋的姜夔,同样讲究音律,他却要从周邦彦的平仄规定中脱身。姜夔“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徐献忠,《吴兴掌故》;转引自章培恒、骆玉明,1996b,p.473)有资格寻衅周邦彦。这位学有专长的音律专家,也讲究音律,但却“用各种办法创制新曲来填词,这样就比一样平常词人更多了一层自由,可以在保持音节谐婉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选择句式是非及字的平仄。”(1996b,p.473)既能作词又能作曲,姜夔就可以用曲就词,他的乐谱至今留存七首,但从其词配曲的办法中,我们很能找总结出平仄安排的通则。宋代郑樵的总结很尖锐,他反对专讲究诗词格律,而与音乐无关的诗歌,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二体之作,失落其诗矣——纵者谓之古,拘者谓之律。一言一句,穷极物情,工则工矣,将如乐何?(1995,p.888)
其意大致是说,古代的诗,被称为歌行,后代的诗成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诗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文学,讲究格律的就叫诗,诗配上音乐就叫歌。正由于作诗不是为了歌唱,才开始音律工致。
词的艺术高度发展之后,文人的被虐方向、自囚意识,开始更加发展。此时,北方元曲开始兴盛,摔脱了所有这些额外的对平仄的哀求,乃至韵部都用当时北方实际用的口语发音,韵字可以平仄通押。(1996c,p.71)正是由于是用来唱的,有大量口语和衬字,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一句23字,曲谱只有七字,加了16个衬字。在谈到元曲音韵时,当代学者任二北说,
且所谓曲韵者,既不如诗韵之拘牵,又不如词之泛滥,悉摈古音,较谐俗口,而又无乖废之也。惟北曲中向有入声派作平上去三声用之一法,殊不能遍合于南北人之口,则视其制度惟过去之历史,今日置而不用,仍仿词法,凡入声韵,一首之中,皆单叶之可也。(任二北,2004,p.390)
与此同时,南戏成熟于温州一带,“村落坊小曲而为之”,凑集民间歌曲而造诣中国式歌剧,成为中国地方戏剧的基本模式。北方杂剧有大批文人加入,南戏却被耽于作词的南方文人排斥,一贯保持民间作风,直到元末高明《琵琶记》,才引来明清文人加入,传奇才主流化成为昆曲,末了有汤显祖《牡丹厅》那样文词精细的歌剧涌现。纵然汤显祖这样精工细作的曲词,吴江派的沈憬也认为不合他推崇的昆曲哀求。此后涌现的汤沈两人的辩论,现在读来变得并不主要,由于昆曲究竟有什么语音哀求,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昆曲的念白彷佛殽杂了多种方言,唱词大抵是半官话。到此时,平仄已经不清,曲调如何合营平仄更无从提及,汤沈之争自然没有结果。
明代民歌大兴盛,至今留下许多文人采集的民歌集。例如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这些民歌,哪怕已经经由文人采集、书写、整理,个中也找不出平仄讲究。
王力师长西席《汉语诗律学》有大篇幅列举“词律”,但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八百多首词的“格律”,大半来自清人追溯,方法是找出第一个写此词牌者的原作,依此为平仄哀求范本,同时参照同代较后出作品,看是否有不同,如有不同,即列为“可变通”。这样的平仄“格律”是否真为音乐所哀求的规律,就很难说了。大部分词牌曲调已经不传,传下的也无法看出平仄与曲调相配的规律。因此,大部分平仄格律只是对古人的尊重而已。反讽的是,词的音律最讲究,音律家化工夫最大的平仄安排,在词歌唱时险些完备消逝。古曲保存至今犹存,可以作仔细比拟研究的,范例的例子是《阳关三叠》,其最早的词是王维的七言绝句《渭城曲》(别号《送元二使安西》),作为律诗,它严格遵照了平仄规律。可惜唐代《阳关三叠》的原始曲谱没能流传下来,后人对如何“叠”法,不得而知。今存有30多种《阳关三叠》词,段式互异,况论平仄。目前所见到的《阳关三叠》曲,因此琴歌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据靳学东考证:
现存最早载有《阳关三叠》琴歌的,是明代弘治四年(1491年)刊印的《浙音释字琴谱》,而目前最为人们熟习且盛行的曲谱,原载于明代《新刊发明琴谱》(1530年),后被清代的张鹤编入《琴学入门》之中,这时的《阳关三叠》已经在王维原始的根本上,发展成包括是非句的多段体了。(2001,p.72)
吴丈蜀《词学概说》中引用可能是宋代的《阳关三叠》(此词转引于吴丈蜀,2002,p.9),明显是作歌词用的是非句。王维的《渭城曲》原诗只有二十八字,像一首七言绝句,而此歌词字数增加到一百一十三字。很多赘词是明显根据曲调的须要,在演唱时添加。这种常被称为“散声”、“泛声”和“和声”的各种赘词,才真正是音乐须要,在汉魏乐府中就开始运用。后代越用越多,很不知是否为唐代《阳关三叠》的歌唱形式。如此多叠字之中,王维诗的“内部音律”就不可能显著。方成培《喷鼻香研居词麈》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是非句兴焉。故词者,以是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周颐《蕙风词话》中也说:“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每每声希节匆匆,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
回到本文的基本论证:无论是储备入乐,还是作为“徒诗”而创作,诗词的平仄哀求,更多的是诗词自身笔墨音乐性的须要。曲调并不须要歌词的平仄,实际上也唱不出平仄。既然平仄哀求对曲调中的古典歌词已经不是必须,对当代歌词就更是如此。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歌词讲究平仄,或许能帮助歌曲增强音乐性,但不是配曲之必须。
4 当代歌词音调不入乐
当代歌词和音乐发生最密切联系的是措辞的腔调。这些腔调可分成音调(汉语特有的音节发音差异)、声间调(音节之间的音调比拟)、句调(全体诗句的构造感情造成的腔调变革,以及诗句之间的音调比拟展开)。它们常常笼统地归为歌词的“音调”,实在三者不同,应该仔细区分。
苏珊·朗格认为,“歌词进入音乐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便瓦解了。它的词句、声音、意义、短语、形象统统变成音乐的元素,进入一种全新构造,消逝于歌曲之中,完备被音乐吞没了。”(1983,p.80)苏珊·朗格至少说对了一点:歌词一旦进入音乐曲调,各种音调是被乐音“重修”了。我们须要逐一磋商的是,这些不同的“调”如何被乐曲重修。
旋律与歌词的句调的关系,相对大略。音乐旋律有平行旋律、上行旋律、下行旋律、波折旋律四大类。歌词的句调有平直、昂上、低落、波折四大类;很多音乐家认为,曲调每一个乐句总的进行方向,和句调的提高方向每每相似。这点彷佛成了不言自明之理。比如孙逐明师长西席引用了一下三位作曲家的“体会”,来解释音调、句调和音乐的关系。
作曲家秦西弦认为,乐句与歌词的语句的语调肯定是相配的: “在创作歌曲的音乐主题时,要把稳腔调的进行尽可能与歌词朗诵的语调的起伏达到同等,以便歌词内含有的感情能够自然地表达出来,歌词也让人听得清楚”。(1977,p.12)作曲家余诠也坚持相同的意见: “波折衷语调在表达感情的办法上基本是同等的。实际上,曲调的本身就包含着语调的色彩”。(1980,p.37)李焕之进一步认为歌词语调与曲调必须结合才能成为艺术: “诗词和曲调之以是能相互结合而成为一种艺术——歌曲艺术,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相互结合的成分,这便是音调上的抑、扬、顿、挫”。(1978,p.5)几位作曲家用的术语互异,但仔细阅读,他们说的“语调”、“音调”,实在都是指歌词的句调,而不是字的平仄。
句调与曲调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所谓的“句调”,紧张是由措辞,感情的高昂低沉所决定的。歌曲首先要表达情绪的诸种样式,变革、迁移转变、起伏、至于曲调能否如秦西弦所说的,“让歌词听得清晰”,他没有举证解释。相反,从本文下面的谈论中可以看到,歌词的很多语音要素,入曲之后变得模糊了,乃至消逝了。无论中西歌曲,要听明白歌词,都须要高下语境的帮助。
这里谈论的当代汉语诗歌词中普通话的音调,不是古典汉语诗词的平仄。南宋时,平仄已经与实际发音语调不符,与此后的北方话更不符。当代人谈论平仄,只是一个历史语音学课题,与歌词无关。
音调是指的是音节中具有差异意义浸染的音高变革,当代汉语的音调可以从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剖析。调值指音节高低升降曲直是非的变革形式,也便是音调的实际读法。调值的语音特点有调值和调类决定。调值紧张由音高构成,但决定调值的并不是绝对音高,而是相对音高。一样平常来说,男人比女人声音低,老人比孩子声音低,纵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感情状态下,声音的高低也有差别,绝对音高的对付差异意义没有浸染。
音调是相对音高。同一个音“去”,一个成年人和一个但这种儿童发的音,都是从最高音到最低音,虽然儿童的最低音可能比起成年人的最高音还高,只是变革形式和升降幅度大体相同。在一个音节之内,两个人发音时绝对音高虽然不同,但相对音高类似。以是不会产生互换障碍。
调类是音调的种类,便是把调值相同的字归纳在一起建立的类。当代汉语的音调有四种,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即为“四声”。阴平高而平,即由5度到5度,没有升降变革,又称高平调或55调。阳平由中音声道高音,即由3度到5度,是个高升的调子,调值为35,又称年夜腔调或35调。上声由半低音先降到低音在升到半高音,即2度降到1度在升到4度,是先降后升的调子,市价214,又称降升调或214调。去声由高音降到低音,即由5度降到1度,是个全降的调子,调值为51。又称全降调或51调。在实际语流中,相邻的音节会相互影响,产生语音学中的“语流音变”。例如,一个上声可能从214变为211,由于后面的字音调比较低。这样,音调就部分取决于声间调,但这变革并不是逼迫性的哀求,以是普通话常被大略归结为“一平、二升、三曲、四降”。
在音乐旋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前者指不同的音乐调性,即音乐中的24种大小调。后者指某一种调性中的乐音之间的相对升降幅度,即为音程。这种“相对音高”和普通话的音调的市价并不一致,可以为大三度,小三度,五度,二度,八度等平分歧。
以上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汉语普通话的笔墨的音调一方面是区分语义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给歌词措辞带来了分外的内部音乐性。于是涌现与上面的音律学可以一比的问题:音调这种措辞的内部音乐性是否能进入歌曲?
在歌词和旋律的合营中,一个乐音可以对应一个音节,也可以对应两个或多个,反之亦然,一个汉语音节可以对应几个乐音,但这两种运动形式并没有特定的合营规律。最主要的是,在汉语歌曲中,汉字的音调被曲调中的乐音音高“取消”,不能现出笔墨原有的音调来。除非有分外的安排,像“买卖”这样有主要意义差异浸染的音调,在歌曲中一样平常都消逝。例如《红灯记》中“提篮小卖”,就很难听出是第三声“买”,还是第四声“卖”,听众要靠高下文的语境才能差异。如歌曲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飞吧,飞吧,我的马”,很可能被误听为“你知道我在等你妈?”被误听为“飞吧,飞吧,我的妈”。这是字词在歌曲音调消逝弄出的笑话。
对这种情形,歌曲翻译家薛范师长西席谈得非常详细,他把此称为“倒字”征象,(2002,pp.137-138)即指这种旋律线条(音高和进行)与歌词的音调不匹配。他举的是两句歌词“你是灯塔,你是舵手。” “灯塔”和“舵手”的字调都是由高向低,而曲调6 到3五度上行大跳,正好与字调颠倒,薛范师长西席指出,这两句听起来,就成为“你是等他”,“你是躲寿”。
事实上,这种“倒字”征象,不可避免,相配才是例外。在歌词中音调消逝是普遍的、正常的情形。听者理解歌词,要靠分开音调从语境上才能猜想识别。奇怪的是:只管绝大多数曲并不随着音调走,但很多论者还一贯强调音调与音乐的“匹配”。中国当代音乐史上,赵元任最系统地作过音调与音乐相配实践。赵元任曾批评学堂乐歌期间的作曲家沈心工“由于没有把汉语音调这一音素考虑在内,以是音调的升降和旋律的高低每每不合拍,既难唱又难懂。”(榎本泰子,2003,p.18)这是否重复了李清照批苏轼的旧例?赵元任自己的《新诗歌集》24首歌曲中,据称有22首把稳到音乐与音调相配。(2003,p.13)但实际上,正如赵元任自己所说,24首歌中,“只有第4首是略为模拟普通话的四声,还有第6首中末了的阴上声,听起来彷佛像普通话的上声”。(见赵元任,注释8,1994,p.13)赵元任所说的音调,实在包含两个意思,正如他自己的剖析:
一层由于中国古老的音乐的传统,二层由于方言的音调的关系,作曲家们有一个公认的处理歌词音调的规则便是按照传统的分类法,把音调归纳为平仄两类,这样凡是碰着平声字旋律就用比较长一点的音或是略微低落的几个音。凡是碰着仄声字的时候,旋律上就用比较短也比较高的音,或是变动很快、跳跃很大的音。(1994,p.1)
仔细剖析,赵元任处理的,并不完备是纯挚的音调问题,他看重的,实际上是声间调,即相邻音节之间音调的相对变革。旋律的高低对音调合营的哀求,指的是声间调的哀求。可以取其代表作《叫我如何不想她》剖析一下:
3 ︳5 —35︳5 — 6 ︳5 — — ︳(旋律)
天 上 飘(着)些 微 云 (歌词)
55 51 55(51) 55 55 35 (调值)
看得出来,赵元任的故意处理,并没有做到字字合乐。比如,51调的“上”和旋律中的“5”,只是发音的开始同等,乐音哀求保持“5”的高度,而51调的“上”在音乐中,不可能从5降到1,以是实际发音为,55调的“伤”。歌词中的“云”也是如此,他自己也未完备做到音调的升降与旋律高低的匹配。
真正被赵元任在谱曲时考虑中的,是音调之间的比拟,即所谓的“声间调”。因此,“微”“云”调值分别为55-35,谱曲为6-5 ,“云”相对低一些。但纵然音调间比拟,这句乐曲也只有这二个音节被照顾到了,其他的声间调与音乐无关,例如开头的“天上”二字,音调为55-51,音乐为3-5,旋律既没有合营音调,也没有合营声间调。
总之,纵然自觉如赵元任,在故意为法则作例所做的歌中,音调、声间调与音乐合营的例子,数量也太少,够不成统计学上的意义。自己的例子都不足多,如何成规律?绝大部分当代歌曲的音乐,与字的或字间音调无关。正如赵元任总结的那样,“中国当代的作曲家,多数是不受任何歌词音调的限定的,只是很少成份是受到一点作曲家自己的乡音或是文学上的影响。” (1994,p. 12)
我们可以看到,歌词音调“可以”进入歌曲的音乐,但是在实践中,基本上不与歌曲音乐相配。以是说,在歌中,音调与声间调基本消逝。字的音调,与歌曲无关。从声乐艺术发展来看,比较把稳音调的演唱,大部分涌如今弹词,评书,以及当代的RAP,也有歌剧中几近说话的宣叙调,以及像刘大白的《卖布谣》,民歌《小白菜》这样极少数靠近说话的语调,这些都是半念半唱,念唱并不入曲,以是音调每每念的很准。循推古例,入乐的汉乐府不讲究音调平仄,而后来的诗歌一旦不入乐,就探求自身的平仄格律。这个历史征象背后的缘故原由,便是歌词一旦入乐,字本身的音调消逝了,不必也无从讲究。
当代作曲者,是否依字的音调高低谱曲?当代词作者,有没有特殊把稳字的音调?音调为汉语所特有,将来是否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音调歌曲”涌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本论文至今没有找到足够证据可以作结论,尽为了避免一概否定一些词曲家的空想追求,这里只能说:当代歌诗,一样平常不追求分外的音调安排。
作者简介:
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诗词、艺术符号学。
引用文献从略,请拜会本刊正文
编辑︱李佳效
视觉︱欧阳言多
邱章红 | 电影叙事系统中的层级嵌套模式探析
冯月季 | 反阐述:算法新闻的符号哲学反思
蒋建国 赵艺颖 | “夸夸群”:身份焦虑、夸赞泛滥与群体伪饰
书评 | 马姣姣评赫尔穆特·贝尔金《赠送的社会符号学》
符说 | 为什么我们那么喜好过购物节?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