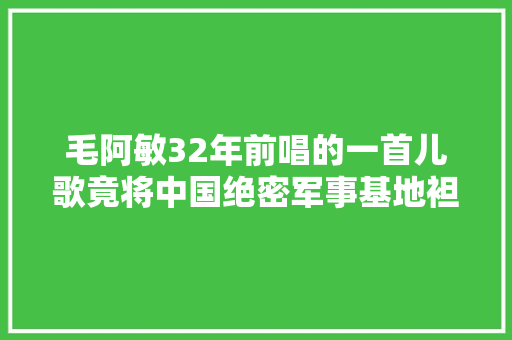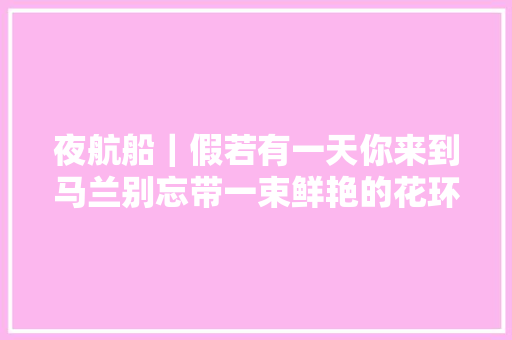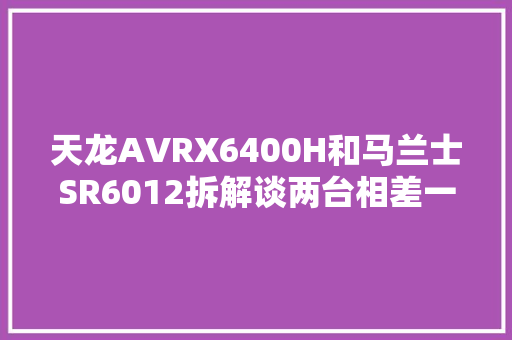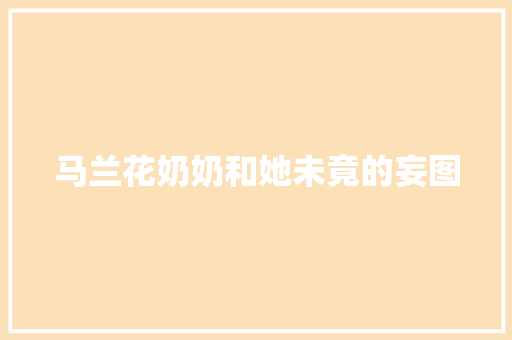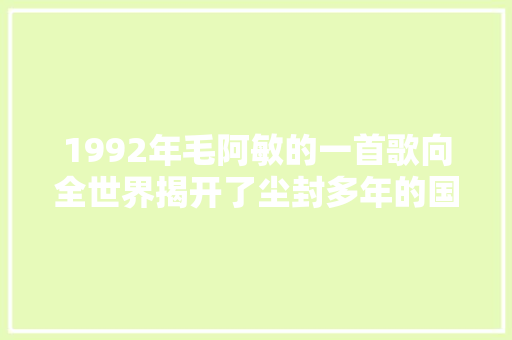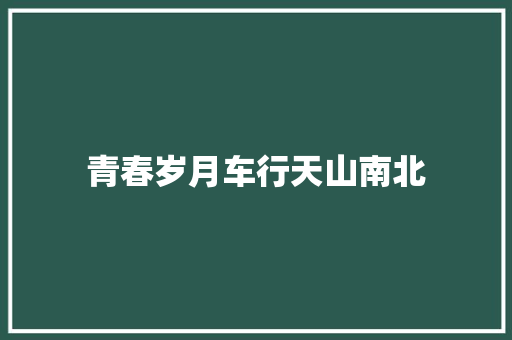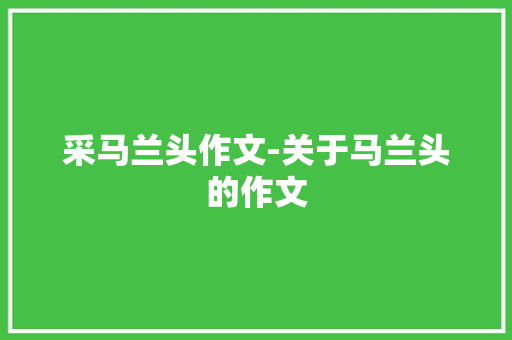光明日报 颜维琦
多年往后,当空中升腾的蘑菇烟云早已散尽,平沙莽莽定格为书架上的照片,张利兴挽着妻子朱凤蓉,回到了上海。17岁离开家乡,归来已是两鬓风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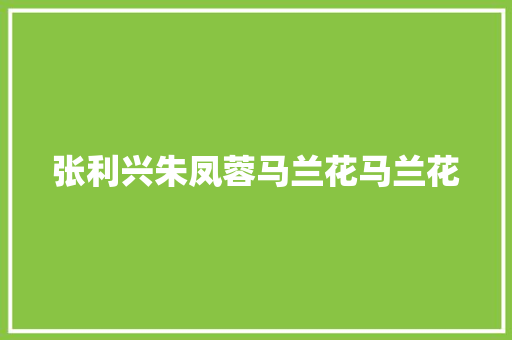
1985年,张利兴、朱凤蓉在研究所办公大楼前。资料照片
1966年10月,一列闷罐车从北京出发,载着清华大学毕业生张利兴和几百位青年,向远方驶去。
终点在哪里?张利兴并不确切知道。只知道,那是天山深处,一个舆图上找寻不到的地方——马兰。
两年后,朱凤蓉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来到这里。从此,他们在戈壁滩扎下根,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奇迹的亲历者,成为大漠里走出来的“将军夫妻”。
今年夏天,来到张利兴和朱凤蓉在上海的家,听他们忆起大漠戈壁的青春和爱情,唱起最动听的少年的歌。
带着一张合影,出发
1965年,毕业分配时,张利兴绝不犹豫地在志愿表里写下两行字:“希望到大西北,到祖国须要的地方去。”
1959年,张利兴参加高考,前几个志愿都与原子能干系。“读高中时就知道,原子能是国家须要,以是下决心要学尖端技能。”
不久,他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关照书。大学第二年,清华筹建工程化学系,以加快核技能研究。包括张利兴在内,工程物理系有3个班的学生整体转入工程化学系。
“我们要研究怎么从铀矿里提炼铀,毕业后去的都是艰巨地区。”张利兴说,至于“艰巨”到什么程度,大家没想,只想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朱凤蓉是张利兴在上海吴淞中学的同班同学。由于高考成绩精良,被录入留苏预备部。一年后,中苏关系分裂,留苏不得不中断,她当选送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就这样,她比张利兴晚一年入学,又成了高下级同学。
朱凤蓉学的专业是同位素分离,那是工程物理系最保密的专业,代号220。
她至今记得系主任何东昌的告诫:“你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都想着成为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但我特殊要见告大家,工程物理系所从事的奇迹,要时候准备着到最艰巨的地方去,乃至捐躯自己的生命。”
提及求学的岁月,张利兴和朱凤蓉不谋而合想起那个深夜,沸腾的清华园。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公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员时,庄严宣告: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当晚,清华大学参加演出的学生就把这个带回了学校。
“当时我已经躺在宿舍床上,就听到楼道里溘然喧哗起来,我也急速跳了下来,那个高兴呀……”夜里,张利兴和朱凤蓉都汇入庆祝的人潮。大礼堂前,欢呼声和歌声冲上云霄,在天空久久回响。
离去的时候到了。张利兴接到关照:新疆,21基地。21基地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马兰。张利兴并不知道21基地有多远,也不知道马兰是不是有马兰花。他唯一心心念念的是:带着一张合影,出发。
他鼓起勇气,找到还在学校做毕业设计的朱凤蓉。终于,一张合影,定格了两个年轻人淳厚的笑颜,也定格了一辈子并肩战斗、携手奉献的人生。
每一天,都身处看不见的“刀山火海”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探求它,请西出阳关,赤心照大漠,血汗写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一首《马兰谣》,诉说着多少奋斗的青春。
“荒凉。”时隔多年,想起初见红山,张利兴脱口而出的还是这两个字。
“除了造好的几排屋子,什么都没有,屋子里也是空的。”张利兴事情的红山,间隔基地生活区马兰还有40公里,车要往山沟里一贯开,开到险些见不到人烟的地方。
1968年秋日,带着两箱书,朱凤蓉也来了。
这个上海姑娘原来可以留在北京事情,学校希望她留校当老师。但朱凤蓉有自己的打算:“学这个专业,便是由于国家须要,我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浸染,到一线做科研更适宜我。”
培植初期的马兰基地,正是用人之时,核试验放射化学诊断急需朱凤蓉这样的专业人才。
起爆后,翱翔员驾着飞机穿进烟云,冒着生命危险也只能取回数量极少的样品。而朱凤蓉和同事们要用这极其宝贵的样品,在当时仅有的商用仪器上进行剖析。为了将诊断精度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必须设计出更好的仪器和方法。大家为此日思夜想。
一次,又是在实验室事情到深夜。独自一人回宿舍的路上,朱凤蓉和一匹独狼迎头撞上。夜色里,狼的眼睛发出两道幽幽的光。
对峙。
不知哪来的勇气,朱凤蓉把大皮帽子摘下,狠狠丢出去,正砸在狼的头上。狼转头跑了。
“那时候,你一定不能怕,要去世去世地盯着它,眼神比它更凶更武断。我已经把腰带抽出来,准备和它搏一搏。”如今回忆起这段“偶遇”,朱凤蓉一脸轻松,将其视为困难生活里的赠送。
她更自满的是,研究碳粒离子源技能,成功地将检测灵敏度提高了几十倍,达到国际前辈水平,使诊断核弹性能有了准确可靠的数据。
“一套诊断方法的形成不是一次实现的,我们要做的,便是不断改进,做出一个个更好的‘秤’。”永劫光近间隔打仗核爆样品,朱凤蓉也为此付出了康健的代价,白细胞一度降至2000,而正凡人的白细胞不低于4000。
张利兴的事情重心则在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3日零时15分,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响后,地爆开释出的巨大能量,让试验区山体剧烈地扭捏起来——新中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
为了这一刻,张利兴所在的“地质水文研究室”默默事情了近5年。
“在马兰,每一天,都身处看不见的‘刀山火海’。”张利兴说,“我们这个奇迹,决定了我们便是在大漠奋力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干的是震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从1958年6月组建中国核试验基地,到1996年9月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成功进行了45次核试验。朱凤蓉完全参与37次,张利兴参与29次。鉴于他们的突出贡献,两人先后被中心军委付与专业技能少将军衔。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在张利兴和朱凤蓉的家中,有一个灰色人造革行李箱,老上海的格局,那是上大学时姐姐送给张利兴的礼物。
2019年,这个盛满青春和乡愁、汗水和欢笑的行李箱,又随主人回到上海。
“将军夫妻”白发归,如同一对平凡的老人。
回到吴淞中学,学生们围着问:为什么要去马兰,马兰有马兰花吗?
是呀,戈壁深处,那紫色的花,小小的,却开得热烈,毫无保留地展现着生命的力量。
1969年12月12日,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张利兴和朱凤蓉结婚了。
同事大姐拿来好看的枕套,借给新人摆一摆。暖壶买不到,战友送来一个。再到基地的军人做事社买些硬糖,战友们分一分,就算是结婚仪式。
在红山,大半年的蔬菜便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1974年,女儿出生,朱凤蓉托人从上海捎些鸡蛋来。
辗转几千公里的鸡蛋到了红山。他们找了个纸盒子,垫上棉花,将皮帽放在盒子中心,蛋放进皮帽,插上温度计监测温度,在皮帽四周布放装热水的玻璃瓶,再用皮大衣包裹纸盒子。没过多久,一窝小鸡出身了!
星期天,骑车到山里挖野菜喂鸡;还要捡牛粪,给地施肥,好让孩子吃上自己种的绿叶菜。“连上海崇明的金瓜都在红山种活结瓜了。”朱凤蓉得意地说。
“红山的日子,也不是只有艰巨,也很美。”朱凤蓉记得,夏天的雨后,远处是洁白的雪山,身边是盛开的野花;还记得忙完任务后,沿着山沟小溪抓鱼的快乐。
实在,他们有太多机会可以离开。1980年,张利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到国外学习。两年后,他绝不犹豫,仍旧回到戈壁。
1990年,浦东开拓开放热火朝天。母校老师力邀二人回上海,到清华在浦东设的点事情。夫妻俩婉言回绝了老师的美意。
“我们只是从清华毕业的普通的学生,仅仅由于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奇迹中,把自己的空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表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代价。”朱凤蓉说。
现在,爱唱歌的她和张利兴一起,加入了均匀年事超过74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韶光只不过是磨练/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唱起《少年》,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光。
他们还爱唱《祖国不会忘却》:“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驰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须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当歌声响起,耳畔吹来戈壁悠长的风,和着吴淞口的滔滔江声。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8日0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