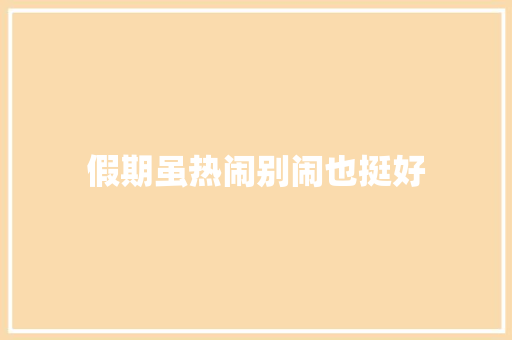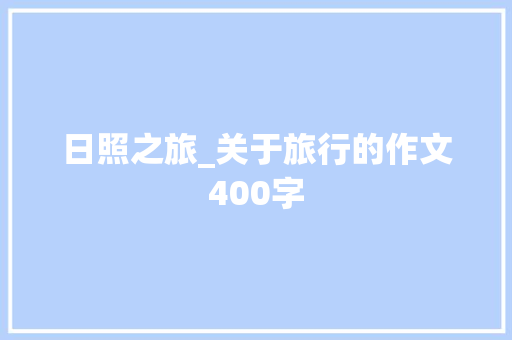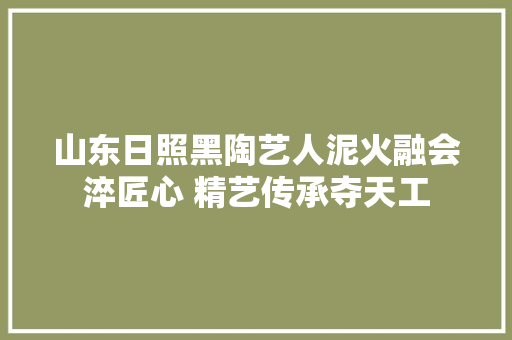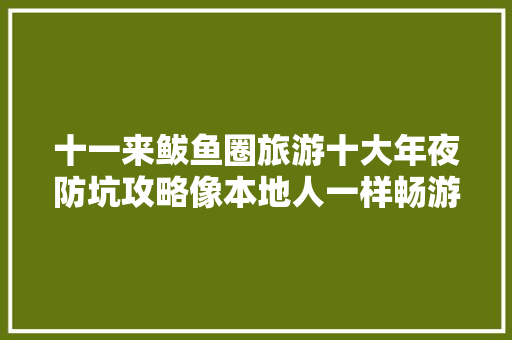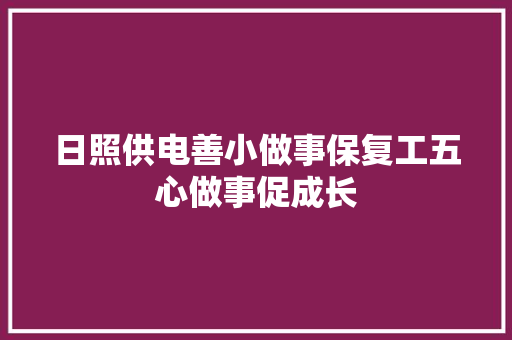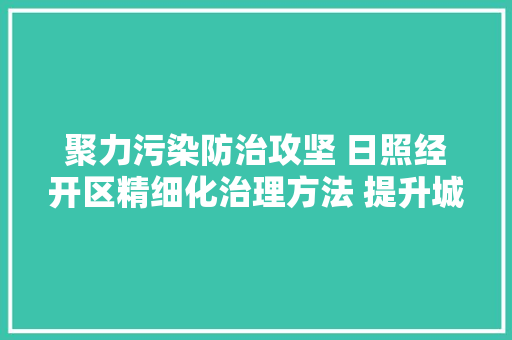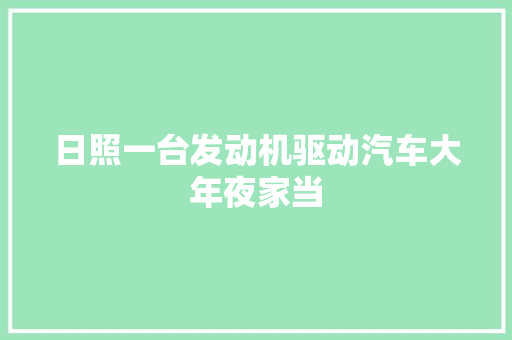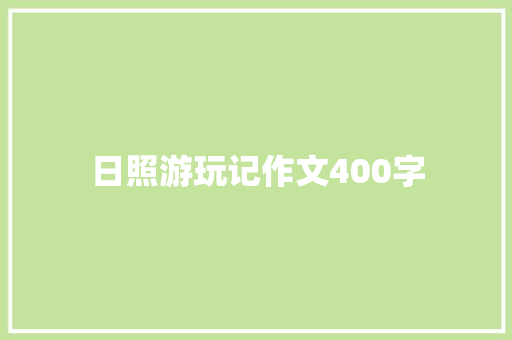赵德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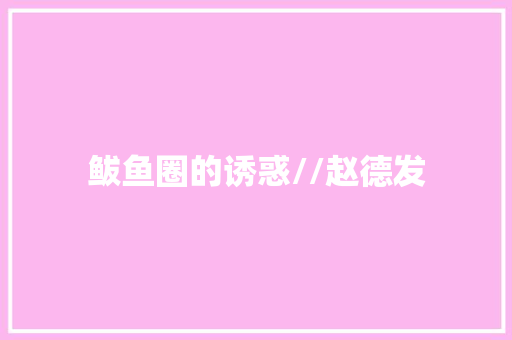
十九世纪中叶,清廷撤消对关东的封禁政策,那些饱受战乱与贫穷折磨的山东人蜂拥北上,或走陆路出山海关,或走海途经渤海海峡,在东北那片肥得流油的黑地皮上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祖宗传给他们的农耕文化,在平原,在山区,开垦地皮,以种粮为生。也有一些人从事渔猎,走向了森林与大海。
说不清是哪个年份,有一帮来自山东日照的流民,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了一片海。故乡的海在东面,这片海却在西边。他们年夜肠告小肠,想到海边捡些蛤蜊生吃,不料走到岸边,却见浪打礁石,浪花中有许多小鱼跃出,又纷纭落入水中。“烂船钉!
这么多烂船钉!
”有认识海鱼的人叫了起来。他们还知道,这种俗称“烂船钉”的小鱼大号为“鳀鱼”,是鲅鱼的主食,有鳀鱼群必有鲅鱼群。他们看看水里,果真有黑压压的鲅鱼群在追捕鳀鱼,吃相凶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鲅鱼!
日照老乡愉快起来,跃跃欲逮,可惜手头没有网具。见阁下有人正用网子往外捞鱼,就过去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人操着另一种方言说:鲅鱼圈。日照老乡问:为什么叫鲅鱼圈?那人说:由于这里鲅鱼多呀。日照人点点头举目打量,创造这是一个月牙形海湾,依傍着一座座小山,就说,鲅鱼圈有鱼吃,有柴烧,咱们就住下吧。于是,他们放下挑来的家当与铺盖,向当地人借来网具捞一些鱼,生火烤熟。还学当地人建窝棚,挖来土垡子垒墙,搭上树枝与芦苇,再覆盖一层一拃多厚的海泥,里面砌上灶台与土炕。他们站在窝棚门口向海南遥望,在心里向家乡的亲人们说:放心吧,俺在北海边上安下家了!
在这里生活,果真比在老家随意马虎。这里有一些来自河北滦县的“老滩人”开着几家网铺,便是合资捕鱼的小团体,日照人可以入伙,凭力气挣钱。日照人将前辈们创造的坛子网技能带到这里,在海里定桩“打户”,拴上大网,拦截随海流游来的鱼虾。每天摇船过去解一次网,将网囊中的鱼虾倒出来,拉回去分捡、加工,等着贩子过来收购。日照人挣了钱,买网,造船,也开起了网铺。他们托贩子捎信给别处亲友,说这里鱼多人少,可以过来,便引来了一些在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日照人。还有些王老五骗子揣上钱,背上腌好晒干的鲅鱼,回老家住一段韶光,娶个媳妇领回来,顺便也鼓吹了鲅鱼圈的富余。于是,更多的日照人和日照以外的山东人就来了。民国初年,来此谋生的日照人越来越多;建国之后,还有日照人陆续过来。北边的海星村落,南边的神仙岛,日照人占半数之多。那时候户口管理不很严格,况且几个村落的干部当中就有日照人,有一位叫戴金生的石臼戴家村落人担当海星村落党支书许多年。他们对老家的人来者不拒,激情亲切有加,海星村落竟然扩展到一千多户,成为公社驻地。
鲅鱼圈,也诱惑了我三十年。我刚到日照时从文史资料上读到,晚清期间就有日照人到鲅鱼圈捕鱼定居,渐成村落。读了之后我浮想联翩,猜度鲅鱼圈的样子。得知鲅鱼圈里鲅鱼多,更是感到好奇。由于我生在离海八十公里的鲁东南山区,小时候只在过年时才能吃到鲅鱼(我们那里叫它“马古鱼”)。要凭票购买,一家只能买一两条。劈成两半腌制的,齁咸。平时挂在墙上,母亲偶尔切下二指宽的一段,用油煎熟,倒进大量萝卜丝,熬出喷鼻香喷喷的一锅,我享用时十分惬意。后来听朋友讲,由于鲅鱼好吃,在青岛有一习俗:用鲅鱼孝敬岳父,并有一句“鲅鱼跳,丈人笑”的谚语。在日照,鲅鱼和刀鱼是收成量大、品质也好的鱼类,1990年代以来每到春节,人们带着成箱的冷冻鲅鱼、刀鱼走亲探友,是最常见的做法。我还理解到,鲅鱼的学名为蓝点马鲛,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鲅鱼有洄游的习气,每年春天等到海水温度上升,便从越冬的东海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而去,四月到达苏北鲁南沿海开始产卵,一边索铒一边连续前行。五月份到达山东半岛东端,一起向北,留在黄海北部;一起向西,进入渤海。莱州湾,渤海湾,辽东湾,到处都有。等到秋风刮起,水温降落,它们记起南方的温暖,便原路返回,再回东海。
我想,鲅鱼圈,中国最北方的鲅鱼驿站之一,到底是什么样子容貌?在那里的日照人,过着若何的生活?我很想过去亲眼看看。前些年我去过几次东北,但机缘不巧,都没能到鲅鱼圈。从去年开始,我大量读书,广泛采访,想写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去鲅鱼圈看看的动机更加强烈,但是由于新冠疫情,一贯没能成行。
今年正月,我偶尔结识了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技能推广站原站长朱志校师长西席,得知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带领日照渔民去鲅鱼圈作业,便请他讲述去那里打鲅鱼的事。他将手一摆:不是去打鲅鱼,是打海蜇。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鲅鱼圈的鲅鱼已经不多,由于四十年前渔民的捕捞能力开始增强,鲅鱼群体在北上途中不断减少,能进渤海的寥寥无几,咱们千里迢迢过去会赔本的。1979年,涛雒公社有人去鲅鱼圈探亲,创造那里海蜇特殊多,回来一说,第二年就有人去了。涛雒公社有十几条渔船过去,生产二十多天,满载而归。从此,日照渔民每年都去鲅鱼圈。
听到这里,我笑着点头:这是鲅鱼圈对日照人的又一轮诱惑。
朱志校,1951年生于日照渔村落石臼,毕业于山东水产学校。由于是科班出身,并且常常出海作业,逐渐成为日照水产行业的技能威信。上世纪九十年代,担当日照水产集团群众渔业部主任的他,曾率领多艘日照渔船远赴赤道附近的帕劳海疆延绳钓金枪鱼,到印尼海疆捕捞杂鱼。提及去鲅鱼圈打海蜇,这位古稀老人斗志昂扬,时时站起身来用手比划,形象生动地向我讲述了一次次去鲅鱼圈的经历。
他第一次去鲅鱼圈,是1983年。由于涛雒公社的渔民连续两年去那里打海蜇,收入丰硕,县水产局决定成立事情组先去调查一番,以便组织更多渔民前去捕捞。朱志校带领事情组,坐汽车到烟台,再坐轮船到大连,然后转乘火车北上,到熊岳城下车,花一块五毛钱坐当地人的毛驴车去鲅鱼圈。老朱说,十八公里路,两边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到了墩台山下,事情组的人下了驴车,从阁下一座海泥屋里走出一位妇女,朱志校创造,竟然是他的堂妹。多年未见的堂兄妹这样巧遇,让他俩十分惊喜。堂妹让他们进屋喝水,说一下子话,然后带他们去见海星村落的干部和老乡。老乡们听说老家的人今年还来打海蜇,纷纭表示支持。事情组住进鲅鱼圈的一家小旅社,集体睡在一盘大炕上,自己用柴油炉子做饭吃。他们在当地做过调查,再租毛驴车去远处的渔村落、渔港理解情形。他们创造,日照人在这里到处都是,不但是出海捕鱼的,就连在街上摆摊卖肉的,路上赶毛驴的、开三轮的,都有好多。老乡们讲述来鲅鱼圈落户的历史,表达对“海南”老家的思念,让他们十分冲动。到了神仙岛,受到该村落党支部布告王建兴的激情亲切接待,原来王布告这天照戴家村落人,60年代到这里落户。他向事情组先容了渔情,还带他们去营口见了市水产局长,取得了当地水产部门的支持。朱志校他们紧张事情一段韶光,到鲅鱼圈村落南的小邮电所发电报,向日照县水产局报告:鲅鱼圈海蜇呈旺发态势,建议在8月20日过来捕捞。水产局接到电报,立即动员沿海各公社做好准备,458只渔船于8月上旬出发。全是机器船,但马力大小不等,小的12马力,要走半个月;大的20马力,只需三个昼夜。他们先是北上,绕过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向西进入渤海,然后拐弯向北,走了一个大大的“S”形。到了鲅鱼圈,停泊在海星村落边。由于船来得太多,过于拥挤,有的连续北上,在二界沟等海湾抛锚。大家到岸上建起一排排大略单纯窝棚,砌起一片片水泥加工池。此时的辽东湾成了海蜇的天下,岸边就有好多,可用网兜直接捞起;有的被海浪冲上沙滩,像一坨一坨凉粉。渔民们开船入海,或用坛子网,或用流网,每网都是满满当当。拉到岸上,用竹刀将海蜇的头与身体切开,分别放进池子,用矾使其脱水。“一矾”脱水百分之五十;“二矾”脱水至百分之七十;“三矾”脱水至百分之九十,成为可进入市场的成品。
海蜇旺季,本地渔民也是忙于“海里捞金”。船多网多,免不了挂蹭牵绊,涌现争执。有一回,日照一艘船与当地一艘船的渔网相互碍事,当地人让他们赔偿。由于数额过高,船上的一个日照人接管不了,只好跪下求饶。一个鲅鱼圈的小伙子这天照人的后代,取出一把刀子大吼:“不准陵暴日照人!
”当地人见状,放弃索赔走开。日照人见这位老乡如此仗义,感激涕泣。他们在鲅鱼圈忙活四、五天,就装上一船加工好的海蜇回来,去青岛或南京卖掉,带着大捆的钞票回家。
此后,日照人去鲅鱼圈打海蜇的一年比一年增多,1984年,610条船;1985年,802条。有人脑洞大开搞技能改造,将20马力的船上加上插篷,机器与风力并用,顺风时50来个小时就到鲅鱼圈。朱志校师长西席讲,这年辽东湾的海蜇特殊多,个头也大。岚山三村落的徐从来开着20马力的渔船过去,带了十条网,只用三条,每天只捕捞一个流(一次潮涨潮落)还加工不完,四天就将带去的150公斤矾全部用光,收成成品海蜇一万多公斤,收入近两万元。1985年,日照人在这里生产成品海蜇2830吨,约占辽东湾当年海蜇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然而在这一年,日照渔民遭受了重大海难。进入8月中旬,第9号台风天生于日本冲绳岛西北方向的洋面上,18日中午在江苏省启东上岸,韶光不长回到海上,向正北方向移动,一起挟带狂风暴雨。经日照,过山东半岛,毁掉无数房屋,摧垮多处海堤。进入辽东湾后,于19日半夜在鲅鱼圈一带上岸。日照渔民虽然收到台风预报,事先靠岸,但由于港湾里船已停满,有一些船只好停在挡浪坝外。这天夜间风狂浪急,船船相碰撞上石坝,很快粉身碎骨。天亮后,日照渔民和当地人涌向海边,只见海湾里到处都是船板与网具。急忙清查,创造有22条船毁掉,有4人着落不明,40多人受了重伤。当地政府、港务局和边防派出所等部门急忙组织施救。港务局长见日照渔民都是赤脚,将自己穿的凉鞋脱下,递给了坐在石坝上哭泣的一位渔民。当地政府将70多名落水渔民安排在村落民家中,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救治。4位失落联者,尸体被陆续创造。朱志校亲眼瞥见,那位已经白了头发的派出所长,让一青年摇橹,坐小舢板去海里探求尸体。寻到一具,他伸手到船外捉住去世者的后衣领往岸边拖,拖上一看,原来这天照岚山镇的一位渔民。传到日照,家乡人含泪北眺,一位副市长和水产局长立即动身,去鲅鱼圈看望。
经此重大挫折,日照人还是抵挡不住鲅鱼圈的诱惑,第二年依然去那里打海蜇,共去了1086艘,而且都是40马力以上的大船,最大的为124马力。但他们去后,海蜇却像集体藏匿一样,不见踪影。辽宁省水产研究所的专家过去研究一番,认定两条缘故原由:一是水温比上年同期偏低,不利于海蜇成长;二是7月20日大水入海,降落了盐度,导致海蜇去世亡。日照渔民只好改变操持,或者南下烟台,改换网具等着捕对虾;或者直接回山东,到家门口的海洲湾张坛子网,从事常规生产。
海蜇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海洋生物,它不能自主运动,只能随波逐流。它没有眼睛,却觉得敏锐,对温度、盐度特殊讲究。有的年份它特殊多,有的年份却特殊少。鲅鱼圈的海蜇从1986年起呈现枯竭态势,此后再没大量涌现。1987年,日照渔民再来这里,创造海里似有海蜇,但近前看看却是沙蜇。这种沙蜇,因伞盖上有沙粒一样突起而得名,长有毒刺。人被它蜇了,皮肤红肿,又痛又痒,有过敏体质的人还可能丧命。渔民们对它很反感,有的长吁短叹一番,掉头回转。但多数渔民依然留下,打起了沙蜇。虽然沙蜇的价格低,但它产量高。加工好了,以一斤一毛多钱的价格在当地直接发卖,收入不菲。有的船一贯干到十月初,才依依不舍开拔,回家过中秋节。这一年,日照渔民在鲅鱼圈共收成沙蜇1225吨,产值1100万元。
此后两年,海蜇时多时少,与沙蜇此长彼消,日照渔民连续前来,但他们船上备有多种网具,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转向别处。进入1990年代,鲅鱼圈的海蜇与沙蜇都不多见,这里很少再有标有“鲁日渔”字样的渔船涌现。
听朱志校师长西席讲完这段历史,我更想去鲅鱼圈走一走,看一看。2021年3月23日,根据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改编的电视剧《经山历海》在央视一套开播,大连海事大学团委约请我31日这天作客他们举办的“有鹏来·读书沙龙”,谈谈《经山海》创作过程。我想,缘分终于到了,决定借机去鲅鱼圈。我通过日照的朋友,找到了几位鲅鱼圈日照老乡的联系办法,与他们约好,4月1日见面。
4月初的辽东半岛,已是花红柳绿。与前辈们不同,他们坐蒸汽火车从大连去熊岳站,我和老伴是坐高铁到鲅鱼圈站,只用40分钟。到预定好的旅社刚办好入住手续,日照老乡戴玉江应约而至。
戴玉江个子不高,头发花白,喝一口给他泡好的日照绿茶,淳厚地笑一笑,开始接管采访。他说,是爷爷那辈人闯东北,才让他成为鲅鱼圈人的。爷爷是石臼镇戴家村落人,从小就给人家补渔网。等到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靠补网不能养家糊口,就带着老婆孩子连同二弟一起坐船到了大连。他们先投奔在敦化的亲戚,在山里开荒种地。但爷爷却怀念大海,以为扔掉补网手艺很可惜,听说鲅鱼圈有日照老乡,就独自来到这里。这里有网铺,也须要人补网,他就在这里飞梭走线,一每天劳碌。等到冬天辽东湾结冰,渔民们把船拉到岸上,将网铺锁上门各自回家,爷爷也回到敦化与亲人团圆。但这样终归未便利,爷爷让百口随着他到了鲅鱼圈。戴玉江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终年夜后一贯在此捕鱼。
他的二爷爷,来这里也是补网。有一天他补着补着,扔下梭子就走,从此失落踪。后来才知道,他去当了兵。这个名叫戴芳忠的日照男人,一天学也没上,从军不久得了个外号,叫“机灵鬼戴快腿”。他参加过解放营口的战斗,参加过抗美援朝,官至团长。戴团长返国后又客岁夜西南剿匪,后来转业到兰州一家大型国营企业,2017年去世,享年九十多岁。
戴玉江1973年出生在鲅鱼圈。他说他十来岁的时候,每年夏天都有日照船来打海蜇,好几百条,港湾里停得满满当当。有一天他下海沐浴,爬到一条船上玩,船上一个日照人问他家里有谁,名字叫啥。听他一说,那人拍着大腿惊喜地说:你是我侄子呀!
原来,戴玉江的母亲嫁到东北之前,在老家认过一个干妈,这人是她的儿子。那人说,要不是遇上你,我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那个姐!
戴玉江领他回家,母亲见了这位弟弟欣喜万分,好好招待了一番。戴玉江说,那几年,每当日照人来打海蜇,鲅鱼圈的日照人险些家家都要招待日照的家人和亲戚,日照话响在大街小巷和许多庭院。
戴玉江说,他17岁那年开始下海,由于读书读烦了,就随着父亲去拉蚬子(蛤蜊)。那时父亲已经置办了一条12马力的船,还雇了两个人。辽东湾是泥沙底,蚬子特殊多,他们用船拉一铁耙,后面拴一网兜,在近海跑十来分钟、两三海里,就把网兜拽上一次,每次都有二、三百斤蚬子。拉满船舱,到岸上卖给收购的人,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只管晕船、劳累,只管有风险,但他从不退缩,以为自己生来便是靠海吃海。过了几年,有了积蓄,他家换了一条80马力的大船,还是拉蚬子,有时一天能拉两万多斤。那时鲅鱼圈没有渔港,大船停在海里,人上人下,卸货,都靠小舢板倒腾。拉一船蚬子回来,要倒腾十几趟,又苦又累,但是卖完蚬子点点钞票,又不以为累了。
戴玉江本来认为,自己会和父亲那样当一辈子渔民,没有料到,他干到34岁就转了行。由于鞍山钢铁厂在鲅鱼圈建新厂,厂址定在海星村落,全村落整体迁居到市区,选了一部分年轻人进厂事情,他2006年景为鞍钢的一名汽车修理工,直到现在。他上班,是干一天一夜,再歇一天一夜,见我的这天恰好歇班。他说,海星村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神仙岛还是个纯粹的渔村落,我带你们去看看。我说好呀,咱们吃过午饭就去。
午后,我们坐出租车上路。如果说,鲅鱼圈这处海湾像个月牙儿,神仙岛就在月牙的最南端。在神仙岛村落头停下,只见沙滩平平展展,海水退去千米之外,有许多人提着桶来此赶海。戴玉江指指岸边停着的大片车辆说,这都是城里来的。有人从海滩上回来,我见他们的桶里有蚬子,有螃蟹,收成多多。转身看看神仙岛村落,楼屋错落,在海边大片排开。由于没有预先联系这里的老乡,我们决定去村落委会探求线索。找到村落委大院,办公室却锁着门。正站在那里商量怎么办,一辆豪华轿车溘然开进院里,下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帅哥。他问清楚我们的来意,说他也这天照人,是老爷爷那一辈来的,但他不清楚当年的事。他有急事要办,就让刚刚进院的一位大嫂领我们去找老乡。这位大嫂说,我带你们找老马,他当过多年司帐,他知道。
我们就随着她,走进阁下一个院子。一个头发乌黑、脸庞清癯的老者迎出来,听说这天照来人,立即让我们进屋,十分激情亲切。经攀谈得知,他叫马祖新,今年69岁。他的祖籍这天照石臼镇马家庄,祖上也当渔民。当年父亲带领百口闯关东,先去敦化林区,听说有个同族爷爷在这里下海,就投奔他来了。那时这里没有多少人,只有几家网铺,有“老滩人”开的,有“旗人”开的。父亲他们到网铺捕鱼,立夏前后打黄花鱼,小满过后打鲅鱼,两个“大海市”过去,就日复一日打毛虾。由于这里有辽河、浮渡河等大河入海,饵料丰富,毛虾旺生。他们在海里选那些有沟有流的地方,立起“衍杆”拴上网,用泥坛做浮子。“小墙子”、“大墙子”、“岗上”、“岗西”等等,都是有名的网地。把小船划出去,使篷借风,辅之以橹,一两个点儿(小时),三四个点儿,才能到达自己的网地,将一张张网拽起“倒户”。拉回来分捡,将毛虾放进大锅加盐煮熟,晒成“虾皮”,装进芦席包。虾皮篷松,装包时要进去用脚踩实。一百斤一包,卖得了分钱,卖不了直接分虾皮。有的人赌博,输者没有现金,就用成包的虾皮抵债。后来山东人到神仙岛落户的越来越多,有三、四百户,多亏海里的毛虾打不尽,能养人。神仙岛地皮有限,各家只能开辟一点用来种菜,粮食要拿钱买,靠毛虾换。粮食不敷,就吃毛虾,掺上一点高粱面、玉米面,烙虾饼,做虾丸子,有人吃伤了,一见毛虾就想吐。但是,他们还是恋着这片海,一贯守在这里繁衍生息,经历了新中国建立,经历了集体化,经历了“大包干”。眼下,神仙岛村落不但靠打毛虾为生了,还从事海参育苗,买大船去远海捕捞,办家庭旅社做旅游业,挣钱的道路多种多样。兔儿岛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你们该当去看看。
兔儿岛?原来这是老地名。村落外有座山,是个半岛,远看像一只兔子趴着。岸边都是礁石,远看像兔子牙齿。潮水拍打礁石,浪花很高,响声很大,过去的“盖县八景”,“兔岛潮吼”便是个中一景。大概是一百年前,有一艘三桅船在辽宁湾夜行,遇上风雨,迷航难行,船老大忽然创造前面有个亮点,就向那边行进。走了一下子,忽然到了一个可以避风的海湾,天亮后看看,山上有个洞。他们认定这个洞里住着神仙,为夜行船指路,从此把这里叫作神仙岛。
我们告别老马,出村落上山。登高远眺,只见碧波万顷,风平浪静,“兔岛潮吼”的景象是领略不到了。了望刚才去过的海滩,此时已经涨满潮水,赶海的人都已撤退。山顶上,有一尊妈祖像,一座龙王庙,都是新建的。岛子下方的石岸边,则有一座小庙。下去看看,小庙建在一个洞口,洞壁已被喷鼻香火熏得乌黑。
手机溘然响了,日照老乡叶庆柱问我在哪里,说他已经回到鲅鱼圈,晚上请我用饭。我们回到村落中,坐公交车回去,老叶很快开车到了我住的宾馆。他59岁,看上去很精明,也很有活力。但他说,五年前得过一次大病,虽然好了,还是要定期到北京复查。他昨天去北京,本日见了约定的年夜夫,一查完就坐高铁赶回来。我听后十分冲动,与他牢牢握手。他与戴玉江相见,二人感慨不已:原来都是海星村落的人,迁居后很少见面,他俩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老叶带我们去一家饭店,点了多种鱼虾,说要让赵老师和嫂子尝尝鲅鱼圈的海鲜。我尝了一样又一样,味道果真不错。我与他边吃边谈,才知道他们家来鲅鱼圈较晚。他老家在日照城南二十五公里的梢公村落,全村落都是渔民。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淮海战役,复员后上船捕鱼。建国初期,日照人听说东北生活好,纷纭闯关东,十九岁的父亲也动了心。他写信与本村落在这里的一个人联系好,然后坐汽车去烟台,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芦屯站,末了步辇儿走到海星村落。那时候这里有了生产队,一来就到队里上船捕鱼。干了一年回去,经人先容在邻村落找了工具。叶庆柱说,他父母成亲时,父亲没说还要去东北,结婚后说了,母亲很不肯意,但经不住父亲的几次再三动员,只好在一年后过来。母亲生前说过,她一来就后悔,以为阔别老家亲人,对这里的生活也不适应。但是等到在这里生下孩子,她只好安心过起了日子,直到二十年后她才第一次回老家。
我考虑到老叶刚从北京回来,不能劳累,建议来日诰日再谈。他答应了,吃完饭开车送我们回宾馆。这时我创造,路边好多地方火焰通亮,仔细看看,原来是一些人在那里烧纸。老叶叹口气说,立时到清明了,他们不能到亲人坟前祭奠,只好这样寄托哀思啦。我看着那些火堆,火堆旁悲哀的脸庞,心想,此时此刻,有多少日照老乡的心飞越大海,回到了老家?
第二天上午,老叶来到宾馆,与我连续交谈。他说他小的时候,父母常常给他讲老家,讲的时候很动感情。母亲由于惦记亲人,常常眼泪汪汪。他九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回老家,住在大爷家上小学,三个月后才回来。大爷是梢公村落的渔业队长,是当地有名的船老大,出海捕鱼很有履历。叶庆柱从老家回来,多年没再回去。想不到,1979年夏天,大爷溘然来了,挑着花生米和白面馒头,给他们百口一个惊喜。大爷是来看弟弟的,在这里住了十来天。他到处转悠,跟老乡们啦呱儿,看这边的渔情。创造这里的海蜇特殊多,回去向公社领导做了申报请示,第二年就有几十条船过来。
我听到这里说:日照人来鲅鱼圈打了十年海蜇,原来是你大爷发起的!
老叶听了连连点头:对,对,是他。那些年,老家每年都来好多船,后来这里没有海蜇了,他们才不来了。我母亲每到夏天就念叨,老家也不来人了,你说那海蜇,怎么就藏起来了呢!
老家不来人,我母亲却一次次回去,由于五个孩子都大了,她有韶光了。母亲回去奉养老爹老娘,看望兄弟姐妹和亲戚,一去就住好永劫光。可惜她走得太早,1993年就去世了,还不到70岁。三年后父亲也走了,活到72岁。但是大爷很龟龄,活到2016年,94岁。大爷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回老家,开车客岁夜连,人车一起上船,到了烟台再开车回日照。在老家住一段韶光,觉得十分亲切。不但是喜好日照,还喜好全体山东,有一回我开着车,看了曲阜、泰山、济南等多个地方。
我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韶光回山东?老叶说,我早早让自己退休了。我下了多年的海,经了那么多风浪,把好多事都看淡了,只想悠清闲闲地过好下半生。
他讲,他从小就随着大人出海,后来正式成为生产队的劳力。集体化的时候,海星村落有三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二十多条风船,每条船卖力二三十块架子网。这里的海,“小雪”结冰,“惊蛰”化冻,海上无冰的大半年里,渔民要每天出海。春夏之交,先打一茬黄花鱼,再打一茬鲅鱼。这两种鱼可多了,渔民们早起出海,下上“流网”,过一下子起一次网,网上都卡住大量的鱼。他们把鱼摘干净,再把网下到海里,每天都是满舱回去。黄花、鲅鱼这两次渔汛过去,就下坛网捕毛虾,一年一年都是这样。但是,海上有风有浪,搞不好就失事,有人在海上罹难,尸体都找不回来。六十年代来过一场台风,海星村落去世了二三十个人。1983年,这里实施“小包干”,分组作业;第二年实施“大包干”,分船到户。开始是至少14户一条船,担保家家有船份,后来有人挣钱多了,就买船单干。过去这里有句老话,“舀不干的海水,捕不尽的鱼”,想不到,船一多鱼就少了。过去每年都大量涌现的黄花鱼险些绝迹,鲅鱼也很少能捕到,有些渔民就买大船,去远海。1985年,他连货加借,筹集17万元,买了一对120马力的大船。他当船长,再雇一个船长开另一条船,每条船上雇八九个人,大副、二副、大车、渔捞长等等,一应俱全。他带船到秦皇岛一带,到莱州湾,到黄海,到东海,哪里有鱼去哪里,哪里打了哪里卖。辽东湾不出海蜇了,江苏射阳那里出,他就去那里打。但是,养船太累,风险也大,他干了七八年就决定不干了,把两条船卖掉,在鲅鱼圈“包滩”。
我不懂什么是包滩,老叶说,便是包下一片海疆养蚬子。2003年他包下五、六亩海疆,办了利用证,买了一条200马力的船,雇了五个人。买来蚬子苗撒进去,两到三年长成,捞出来卖掉。他把那片海分成多少区域,轮流放养,每年都有收入。比起捕鱼,包滩的好处是没多少风险。雇的人在海上值班,他不用每天去,可以在家安歇,可以出门走走。但是到了2008年,他又不干了,由于养蛤蜊的太多,不怎么挣钱了,国家也不让养了。他买了几套门面房,每年有一些租金收入。一对儿女都已经成家,女儿在交警队,儿子在银行,事情都挺好。另日常平常没有多少事情,紧张任务是接送孙子和外孙女上学。
我让老叶先容一下鲅鱼圈的风土人情、风尚习气,他细心心细讲给我听。他说,来鲅鱼圈的山东人把老家的风尚也带到了这里,逢年过节,和老家一样热闹;红白喜事,和老家一样办理。鞍钢建厂,海星村落迁居,海星村落的人也住在一个小区。但是韶光一长,有人换了更大更好的屋子,搬到别的地方,相互之间联系就少了。不过,无论住到哪里,大伙都忘不了海星村落,有时候过去瞅瞅。
我说,你也带我们去瞅瞅呗?
他说,那是必须的,咱们吃过饭就去。
吃过午饭,老叶带我们出了市区,到了墩台山下。只见荒草遍野,道路泥泞。路右边是钢厂的水泥高墙,墙内有两根涂成蓝色的大烟囱直插云天。往左前方瞧,那里也有两根大烟囱,却涂成红白相间的颜色。老叶说,那是华能营口电厂。往里面走一段,见路边有旧船,我让老叶停车。下去看看,创造旧船不但一艘,有的靠在厂外,有的卧在路边,船身已朽,与荒草为伴。高墙边,还有一排圆形水泥池,直径约有两米,深一米多。老叶说,这是当年加工海蜇的池子。老伴向南一指:那里还有船。我举头看看,山坡上果真有一条。我见那船位置高高,船头向着西面的大海,心想,它被摈弃在此近二十年,已成老朽,还在神往着大海?
再往前走,就到了海堤上。前面有一道挡浪坝,坝内尽是淤泥,有一条船烂在里边,只露出半圈船帮。老叶说,过去这里是海星村落的港湾,船那个多呀,真叫一个壮不雅观!
他的话音里,流露出浓重的怀念之意。
我问:村落落迁居之后,海星村落还有没有人捕鱼?老叶说:有,但不多,都是养大船,出远海。政府专门给鲅鱼圈渔民建了渔港,叫珍珠湾码头,但除了休渔期,平时停靠的船很少,船都出去了。
看罢这里,我们去了阁下的墩台山公园。山顶有一座用青砖垒起的烽火台,是明朝初年为防倭寇建的,传说当年由白姓姐妹俩看守,一旦创造敌情,立即举火报警。还有一座上红下白的灯塔,由海事部门管理,为辽东湾的来往船只导航。在烽火台与灯塔之间,则有一座更高的钢构造不雅观景塔,有旋转楼梯可以上去。但入口处挂了牌子,说是正在维修,回绝参不雅观。老叶说,由于去年的一场台风刮坏了玻璃,加上疫情紧张,这塔好永劫光不开放了。阁下的牌子上有笔墨先容,塔高55米,一层是营口开拓区历史博物馆,二层是不雅观光休闲厅,三层是开拓区城市方案沙盘和不雅观光平台。我不能进去看,甚感遗憾。
但是,站在山顶还是可以不雅观光。往北看,钢厂方正广阔,高炉座座,霸占了海边很大一块地盘。老叶说,当年迁居的不但是海星村落,还有其余两个村落,削平好几个山头才垫起了厂址。我知道,鞍钢是受了鲅鱼圈的诱惑,才来此建新厂的,由于通过海运可以大大降落物流本钱,入口铁矿粉能够直接进炉冶炼。鞍钢1916年始建,前身这天伪期间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1948年鞍山解放后由东北公民政府接管,被誉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由于有了鲅鱼圈分公司,鞍钢这家大型国有企业又抖擞了新的活气,2019年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第35位。
往西往南看,营口新港尽收眼底,塔吊密集排列,像一条长长的橘赤色林带。这个大港,也是被鲅鱼圈诱惑来的。营口港原在营口市区,1861年开埠,但由于处在几条大河的河口,淤积严重,发展受限。国家有关部门经由稽核创造,鲅鱼圈湾阔水深,条件优胜,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在这里培植营口新港,现在这个大港的年吞吐量已经超过两亿吨。
我遥遥看见,港区之南,神仙岛之北,有一片银色沙滩。老叶说,那里是山海广场和玉轮湾,很俊秀,我带你们去。他一边开车往市区走,一边向我们先容路边景物。经由一座大楼,门口挂着边防检讨站的牌子,他自满地见告我,他姑爷在这里事情。
沿着辽东湾大街往南走,右边是港区的一个个大门,左边则是高楼林立的市区。我说,鲅鱼圈是个挺大的城市了,老叶说,紧张是有了港口和钢厂才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有许多外地人在这里买房落户,黑龙江、吉林、内蒙,来的很多。听他这么说,我想起昨天从高铁站下车,乘坐的出租车司机便是黑龙江人。他跟我一起唠嗑,说他原在国企,后来企业拍卖,他下岗后拼去世拼活把儿子送进大学,然后就到鲅鱼圈了,由于这里有海,景象宜人。现在儿子在北京上班,他在这里开出租车,日子过得挺好。
来到山海广场入口,我对老叶说,你回去吧,我们逐步逛。他与我握手作别,说放学韶光快到了,他要去接孙子。看着他的车影,我心生冲动。鲅鱼圈现在是营口市的一个区,但过去属于盖平县(后改为盖县,又改为盖州市),我从网上购得1930年出版的《盖平县志》,临来时读了一遍,上边讲:“(盖平)居民除旗族外,大抵由山左关里迁徙而来者为多,习俗每沿用故乡老例,不失落幽冀倔强邹鲁朴厚之风。”九十年过去,我来这里感想熏染到,山东人的后代依然“朴厚”。
山海广场规模伟大,建造精良,我们边走边看,一大会儿才来到海边。近处是大片沙滩,远处是“鲅鱼公主”雕塑,路边则排列了“海上十二生肖”大型钢制雕塑。设计者把鼠、牛、虎、兔等等换成了海牛、海兔、虾虎、海马等十二种海洋生物。我惊叹这个创意,由于这种新颖视角会让人意识到,无论陆上还是海里,都是生生不息;每一种生命,都应得到尊重。
踏上长长的栈桥,我们来到一个巨型贝壳样子容貌的不雅观景平台。在这里往海上看,60米高的“鲅鱼公主”雕像立于碧波之上,很有视觉冲击力。她两手托举一颗白色的大珍珠,下身化成美人鱼的样子在海面上波折,且将尾鳍高高翘起,造型十分幽美。
阁下有一群游客,年轻女导游正向他们讲一个传说:东海龙王派大将鲅鱼王统辖渤海湾,鲅鱼王的小女儿有一天忽然遭到鲨鱼攻击,慌乱中进入一个年轻捕鱼郎撒下的网中。她哭求捕鱼郎放了她,被放走后爱上了捕鱼郎,整天思念。后来,鲅鱼公主用修炼所得宝珠又救过捕鱼郎的命。经由各种磨难,二人终成家眷。
“鲅鱼公主,我也爱你!
”一个胖小伙溘然大喊,引来一片笑声。
“鲅鱼公主”,以及鲅鱼圈的美景,对天南地北的游客也成为诱惑了。
“呜——”,响亮的汽笛声从港口传来。
望着停在一个个码头上的一条条大船,我面前恍惚一下,忽然幻化出百年之前大量鲅鱼在这里聚拢繁盛热闹繁荣的画面。
2021.5.1
原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2期、《极光文艺》2021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