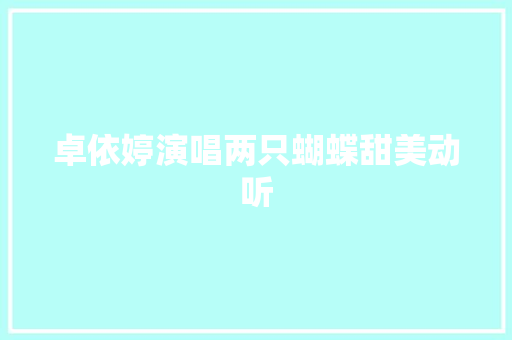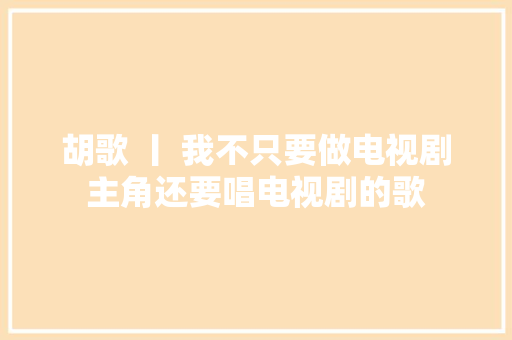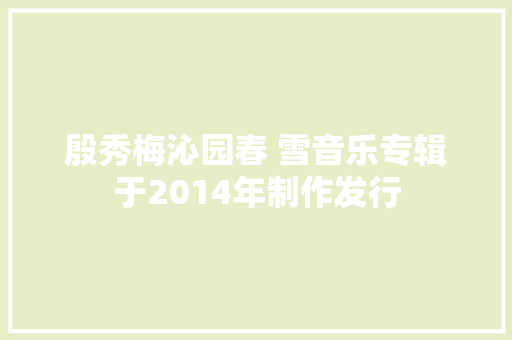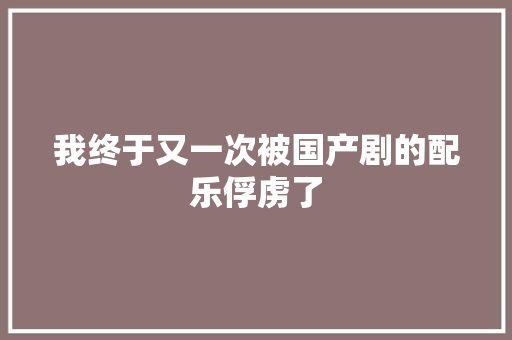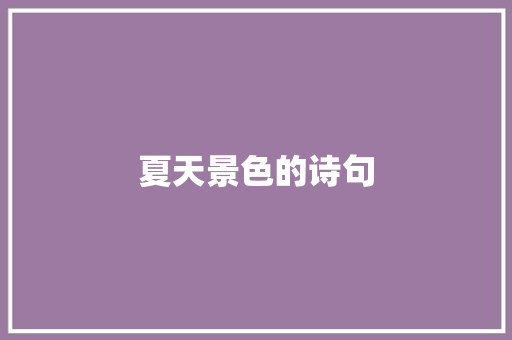作者:艾志杰
继《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洛阳》之后,马伯庸的《风起陇西》又被搬上荧屏。该剧以虚实相生的构造办法,聚焦大历史中陈恭、荀诩等小人物的谍战人生,以繁芜抵牾的情绪关系,串联历史演进中蜀魏博弈的内在逻辑,探寻历史叙事中的生命代价。

《风起陇西》上岸央视八套伊始,剧集开头线索繁杂、调色方向等曾引发部分网友谈论,随着剧集展开后的口碑和热度的持续发酵,该剧在收官之时斩获豆瓣7.9分的好成绩,六次登顶猫眼电视剧热度冠军,微博话题阅读量也步步升温,被许多不雅观众纳入“烧脑剧”必追清单。
《风起陇西》的口碑逆袭,离不开其伟大历史与微不雅观生命,春秋大义与个体情绪,人生信念与人性代价兼容的艺术表达,勾勒出三国谍战在小人物身上映射的历史图鉴。
解史于新,打造虚实相生的古装谍战剧
在解构与重修三国故事的过程中,创作者努力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生活质感与谍战元素、正剧与戏说之间的关系,由此打造了一部虚实相生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的特质紧张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重史尚实与艺术虚构”,在大历史不雅观与小人物的弥合中实现视角创新。从聚焦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权略斗争的《三国演义》(1994),到立足于曹丕兄弟争夺世子之位的《智囊同盟》(2017),关于三国的影像表达每每以伟大叙事展开对历史的理性瞩目与深刻反思。与这种厚重且辩证的大历史不雅观一脉相承,《风起陇西》以诸葛亮北伐为历史背景,以调查“街亭情报案”为叙事出发点,拉开风云诡谲、纵横捭阖的蜀魏之争。不同的是,该剧并未流连于为大众熟知的史上逐鹿三国的英雄豪杰,而是在遵照大历史不雅观的条件下,选取陈恭、荀诩等小人物的故事,并予以合理化虚构。这种务“实”与构“虚”相结合的叙事视角,不仅拓展了电视剧的表达空间,而且也拉近了不雅观众与历史人物的审美间隔。
另一方面,“古装与谍战”,在类型与反类型的平衡中寻求题材创新。伴随主流代价、市场成分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浸染,谍战剧的类型探索也从未停滞。领悟了“古装”与“谍战”的《风起陇西》,无疑在此根本上另辟路子地实现了类型领悟与题材打破。剧中,充满国风采味的配乐、朴实自然的衣饰道具、独具特色的地形风貌以及男性“蓄须”的审美方向,尽显三国期间雄浑、简约的气质。
在此场域中,蜀汉“司闻曹”的陈恭、荀诩等人与曹魏“间军司”渗透到蜀汉的“烛龙”博弈对决,历经潜伏、磨练与捐躯、窥伺三国争战等变幻莫测的谍战风云。因此,古典之“静与简”与谍战之“动与杂”的奥妙领悟,成为《风起陇西》题材独特的关键。
寄史于情,描摹历史演进的情绪逻辑
作为一部“以小人物见大历史”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以蜀汉的“司闻曹”和曹魏的“间军司”两个情报机构来构建错综繁芜的人物关系,塑造了以诸葛亮、李严、杨仪等为代表的“司闻曹”创立者,以陈恭、荀诩、冯膺、阴辑、孙令等为代表的“司闻曹”管理者,以郭淮、郭刚、糜冲等为代表的“间军司”管理者,以翟悦、柳莹等为代表的女性特工。秉承“历史可能性”的创作理念,《风起陇西》实际上描摹了埋没在浩瀚历史中的小人物群像。
面对浩瀚拥有多重身份的人物形象,创作者紧扣充满张力的情绪关系,深入人物的内心逻辑以及历史的某个“横截面”,凸显历史剧“寄史于情”的审美范式。剧集设计了多条羞辱相待的人物关系线索:陈恭和荀诩是至诚至信的兄弟情意,陈恭可以涉险帮助荀诩金蝉脱壳,荀诩可以忍受严刑守住陈恭的操持;陈恭和翟悦是矢志不渝的夫妻情深,翟悦为了不牵连陈恭自行了断,陈恭为了纪念翟悦自断小指;冯膺和孙令是相互扶持的姻亲关系等。
亦敌亦友的情绪纠葛也是《风起陇西》的神来之笔。比如陈恭是郭刚的救命恩人,但又是潜伏在郭刚身边的特工,他们一起经历过死活,却不得不置对方于去世地。再如荀诩和高堂秉,他们在“司闻曹”共事多年,交情颇深,但高堂秉却是魏国特工,一贯向荀诩密查。李严和陈恭暗藏杀机的师徒关系,荀诩和柳莹竹笛传情的暧昧关系,糜冲和陈恭互换身份的敌对关系,创作者都试图以细腻的笔触加以勾勒。正是这些绵长、繁芜乃至抵牾的情绪积蓄,授予《风起陇西》独特的吸引力,让不雅观众感想熏染到历史演进中的情绪逻辑。
演员的素养和演出功底对情绪的呈现和通报也起着不容小觑的浸染。剧中的情绪戏以“翟悦去世于陈恭怀里”的场面为最。黄预看破翟悦的特工身份,并喂以神仙丹,翟悦自知命不久矣,用涂满剧毒的匕首结束生命。陈坤以抽搐的嘴角、沙哑的声音以及脸上暴起的青筋等一系列微表情,诠释出无奈、绝望、不舍的多层次感情,刻画了一个痛失落爱妻却又必须镇静克制的特工形象。
喻史于今,实现三国故事的代价引领
历史剧的实质并非只是为不雅观众建构或耳熟能详、或充满猎奇的历史故事,而更要给予不雅观众思考与回望的空间,在历史叙事中缝合积极的代价不雅观念,升华境界。个体生命以正气为本,与爆款剧《庆余年》聚焦小人物范闲的小儿百姓之心、武断空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风起陇西》同样采取历史阐述捕捉小人物的精神天下,通报人间间的凛然正气。
坚守义务与人间正气,是《风起陇西》彰显的核心意义:无论你身处若何的境遇,要一贯追寻空想、追逐真理。导演试图展现小人物的生命力,哪怕深陷孤独、恐怖与痛楚中,也依然要像英雄一样坚守义务、绽放光芒。剧中,腹背受敌的陈恭保持初心,冒着生命危险自证明净;被施以严刑的荀诩坚守正义,咬紧秘密只为抓捕“烛龙”;遭到疑惑的谷正以去世明志,宁去世也不愿被栽赃侮辱;被魏军围剿的金川大胆殉国,只为保全陈恭身份;落入陷阱的糜冲孤军奋战,以一人之力对抗蜀军;不修边幅的关长老以尸示警,用末了的生命力量向黄预通报信息;生性胆小的孙令守住底线,没有屈打成招拖累冯膺。可以看到,不管是蜀国人还是魏国人,他们始终追随自己的心之所向。这种大历史下的强烈义务感,表示了个体生命的精神风骨。
而“和羮之美在于合异”这样的精神追求,也是《风起陇西》通报的信念。这句话出自曹魏期间夏侯玄与司马懿的对话,意指国家管理需高下、你我之间相互帮助和促进,这也成为了剧中诸葛亮所言“希望天下平定,普通人可以过上安稳日子”的实现路径。剧中陈恭的智谋与理性,荀诩的正派与忠实,翟悦的年夜胆与信念,以及三人之间坚不可摧的情绪关系,是环绕这一层意义的精神纽带,它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与当代不雅观众的对话过程,也是当代电视剧不断提升品质的过程,《风起陇西》不可否认也有值得提升的空间,如剧集的人物对白略有瑕疵,古代书面语和当代口语混用导致的风格割裂感。但瑕不掩瑜,创作者不雅观照三国谍战中小人物的生命正气,凝聚类型领悟与题材打破的勇气,足以让《风起陇西》真正起风。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
来源: 文申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