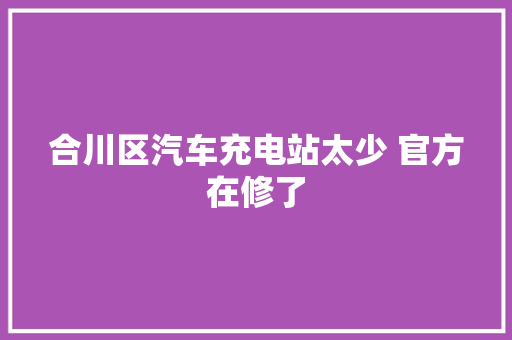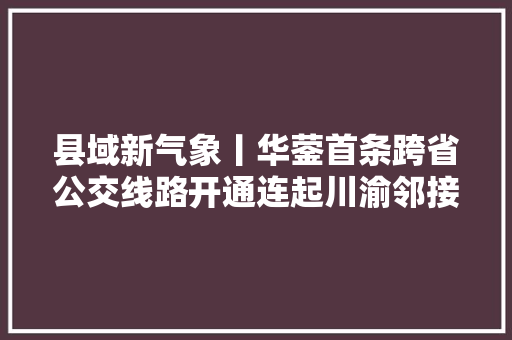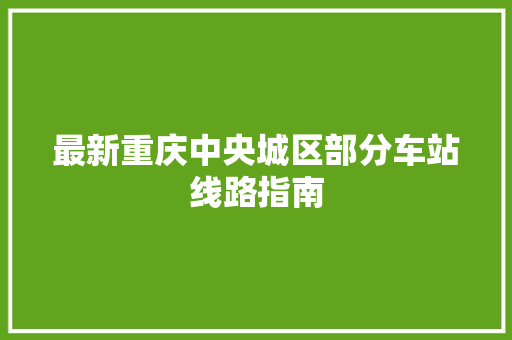安卡
许多年前,我住在渠江边一个州里。夏天涨大水,我随着大人们爬上磨盘山看稀奇。浑浊的江水滚滚而下,像是一场盛大的演出,全然不知大水与粮食的关联。后来顺江而下离开家乡出去念书,依然是在渠江边,却有摆脱了一眼可望穿生活的快感。仿佛下贱和上游已不是同一条河流。江水的影象只剩下一些片段,比如周末的野餐,回家的迢遥。那时父亲在重庆谋生,假期便常常跟随父亲呆在重庆。城市的烟尘与繁华早已盖过野餐的欢快。当公路从城市不断延伸,在我心里,渠江已悄然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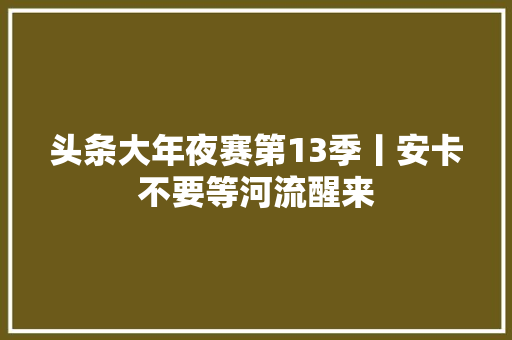
多年后,在看过长江的逶迤婉转,黄河的气吞山河,雅鲁藏布江的声势浩荡······以及无数的河流与湖泊,我落脚在合川北城涪江边,开始关注河流的走向。我喜好在卫星舆图上看合川:嘉陵江,一手挽着左岸最大的支流渠江,一手挽着右岸最大的支流涪江,携手前行汇入长江。我竟然产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之豪情的遐想。
于是和一群驴友操持徒步合川境内三江。每个周末,从合川城区出发沿江而行,豪言要用脚步丈量三江。在一个夏日酷热的清晨,我们从涪江开始徒步。途经了许多村落落,把帐篷搭在村落庄里。村落民同情地看着我们简陋的装备,激情亲切地邀我们进屋用饭,我们委婉地回绝,但喜好和他们谈天。夜晚的村落庄繁星点点,虫鸣蛙叫,寂静又空旷。有一些童年的影象彷佛被唤醒了。
前几年,合川沿渠江建筑绿道,操持从合川主城一贯修到涞滩古镇,全程数十里。作为拍摄事情职员陪同稽核,我们乘船逆江而上。这条我曾肆意离开和忘却的河流,蜿蜒穿行在乡野间,岸边绿植丰满,炊烟环抱,乃至随风飘来果喷鼻香。2016年,首届重庆文学奖在合川举行颁奖仪式,我又一次乘船陪同重游渠江。大家在热烈和愉快中看一江碧水,两岸村落落,拍照记录,回顾着自己的家乡以及笔墨里珍藏的故乡。
曾经跟一个喜好哲学的朋友谈论:渠江汇入嘉陵江,为什么就不能是新的河流而依然叫嘉陵江呢?只是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难道就失落去了被命名的权利?我们是在卢作孚广场谈论这些没有答案的屈曲问题。近六米高的青铜雕卢作孚师长西席的目光远处,是涪江的缓缓流过。那时的作孚师长西席,以“航运是统统奇迹之母”,从上海买来小轮船,开启了川江航运旅途,完成了长江上游航运界的整合。那一段与民生与河流干系的岁月,作孚师长西席不仅在战役年代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也完成了由嘉陵江到长江,由长江到大海的航运发展蓝图。而此刻我与作孚师长西席如此靠近。我居住的小区在涪江二桥下,沿着滨江路步辇儿几分钟即是卢作孚广场。其间的浮雕文化长廊我抚摸过无数次。余复光、于成龙、李实等历史名人,合州川剧文化、历代进士、漕运文化,他们安静地活成浮雕和雕像。也曾步辇儿至文峰街看涪江与嘉陵江汇合处,只水波微澜,远没有渠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泾渭分明,仿佛它们原来便是同一条河流。
人类社会文明源于河流文化。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印度恒河文明、黄河文明,这些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这些只是被书本储存的信息,现在一点点开始溶解。2017年,随我一起生活的父亲因病离世,他唯一的欲望是回到家乡,在渠江边,磨盘山下,老屋门前。我们带着父亲回去,山河静默。我知道,我有了故乡,有了对山河的眷念。
去年,从合川北城搬家到南城,住在嘉陵江边。溘然创造,冥冥中我一贯跟随着三条河流的走向。这种觉得让我莫名欣喜。就像一段剪不断的关系,给予生命原来不可见的形式。
仿佛一种成长,非虚构的生活里,有一些虚构的特性,这种特性来自于不雅观看的办法。常常站在阳台,看附近的窗口,想象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更多的时候,常常沿江步辇儿,看滨江公园溜达或舞剑的人们,看在草地觅食的群鸟,看嘉陵江水的走向。江水原来直行东南下,受东津沱白塔坪的阻击,以撞了南墙须转头的姿态,掉头向北流去。
这个冬天时常暖阳。元旦假期带着家人爬山,爬上白塔坪俯瞰合川,只见一弯碧蓝的嘉陵江水,在冬日暖阳下微微泛波。细窄的脉络被打开,所有的感情都舒放开来,所有的高楼矮了下去,远处的南屏大桥像一条线,牵扯着两岸。嘉陵江水,裹挟着渠江、涪江,也裹挟着我的发展岁月,一贯在平缓流淌。和韶光一样,流淌的形式近乎静止,从来都未曾沉睡。
(作者单位:重庆合川美术馆)
版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