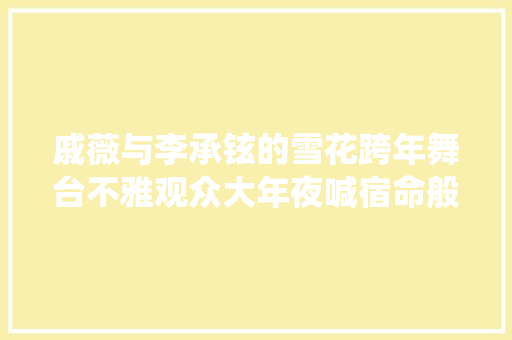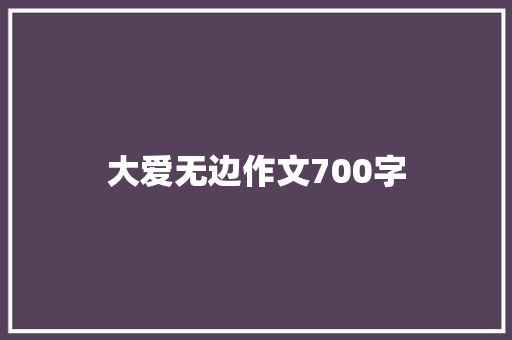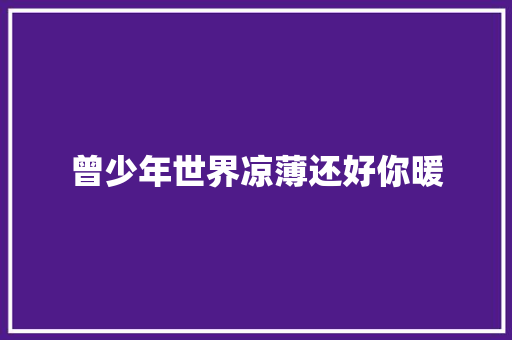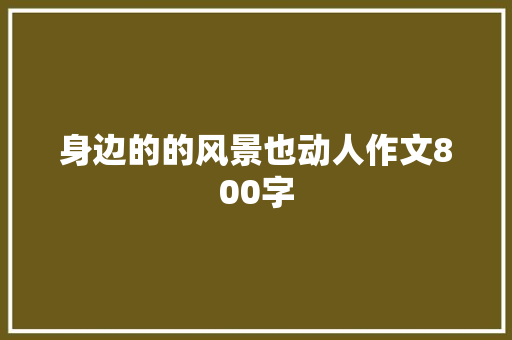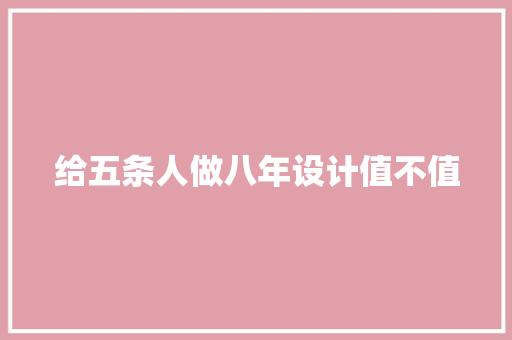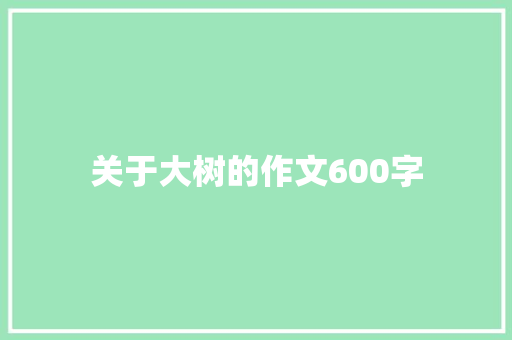皇后乐队的传奇想必不用多说,关注的乐迷自然已经对他们的故事耳熟能详;而纵然是不甚理解或对Rock不感冒的,也很可能在各种场合听过他们的音乐。
这只是皇后乐队大量经典作品中的沧海一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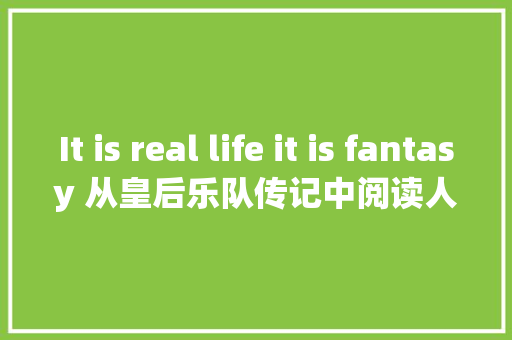
简而言之,Queen是一支成立于1970年的英国,由四位来自不同专业(天才艺术生、天文学家、电子工程研究生和牙科年夜夫)的年轻人组成的摇滚乐队,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创造无数经典、风格多变的歌曲,盘踞了多次榜单顶峰位置,奉献了震荡民气的现场演出,得到了全天下范围内超越一代人的追崇,至今个中两位年逾古稀的紧张成员仍在巡演。这支明年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的传奇摇滚乐队,随着今年以其参加1985年Live Aid 演唱会故事为原型的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喝采叫座,又刮了一阵风。他们的霸气从其队名Queen便可见端倪,要知道目前英国政府有明文规定,是不许可利用King, Queen等皇室头衔专用词注册企业实体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利用了“Queen”,也算是风华绝代了。
在长假读完了他们的传记(读到末了一章节,有点不舍得读完了)。和平日以及今年电影上映前后各个自媒体揭橥的广告文不同,这本2011年出版的题为Is this Real life? (取自歌曲,后半句是or just fantasy) 的传记侧重阐述乐队从开始至今的一个个主要的韶光段、事宜、和一个个细节、生理、生活状态,让读者鲜活地理解舞台之外未曾知道的故事。在那么一支成功了几十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乐队背后,也是真实的生活和各位劳苦大众也一样须要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个非范例乐迷读者,翻阅着书,我体验的是一支70年代英国的四人摇滚乐队,从成立到成名,和成功之后的那些经历,透过这笔墨的阐述,从音乐出发的多个角度体会“什么是摇滚精神”,它并不虞味着颓废和背叛,相反Queen通过他们的音乐、演出,以及这些背后的经历,通过带有冲击力和引领潮流的表现形式,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限可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
We are odds,we orchestrate
我们互异,但我们共处
乐队四人的性情特质和生活态度显然是迥异的。
主唱Freddie Mercury是个华美至去世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艺术和演出天赋惊为天人,有着令人堕泪的嗓音,但也是个绝对的脾气中人,会由于不满某个安排瞬间”龙颜大怒“,也会温顺对待歌迷,是一个外在有多桀骜、内在就有多优柔、须要周围人”呵护“的公主,被外界认为带着“孤芳自赏、自命不凡的气息”,性取向和私生活也是一个众人皆知的谜,他为加入乐队(当时还叫Smile)的执着在电影中已经有所描述,事实上也证明了那是缔造奇迹的开始;
吉他手Brian May是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乐队的”任务担当“,他对皇后乐队的投入和操劳的心血,赛过乐队其他人,理工科出身的他做任何事情都极度追求完美,不许可一丝差错,在其他人不愿意出席发布会的时候,他和Roger总是代劳,作为研究天文学的科学家,在处理人间个人感情时,也陷入过泥潭;
另一创始成员鼓手Roger Taylor,则是“花花公子”,每每有奇思妙想的灵感,搞怪第一,每每成为乐队其他三个硬碰硬男子之间的黏合剂和润滑油,在街头开的铺子曾经为乐队供应了收入来源,特殊“社会”;
低调安静的贝司手John Deacon是最晚加入的成员,电子工程系硕士的他是一个“闷骚”理工男,关系最好的乐队事情职员是司帐,自带打算器干活儿,以汇总乐队在不同国家的版权费,真是对数字感兴趣的哥。他在乐队的表面融入程度可以用“若即若离”,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在皇后乐队待了三年后,终于摆脱了局外人的觉得,才确信乐队会有笃定的未来”, 家庭不雅观念甚重,目前也已经归隐退休,离开大众。但他的内敛并不妨碍他对乐队那种末了一道防线般的浸染。
这几个成员,便组成了杀手级的“皇后乐队”。虽然是遥不可及的明星,从书中点滴细节和事宜的刻画,仿佛也能在周围找到对应每个人物形象的相似代表。有直男、有一根筋的、有“宝宝”、有孤僻不合群的、也有乖张外向的。正是这四个迥异的人,却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想是由于他们有着走到一起并坚持走下去的共同“措辞”——音乐,在不断的磨合中形成了默认的约定和信念,那些冲突和不兼容的个性,却让团体互补,一个都不可少;四个人也相互尊重,他们之间一定有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但却能找到同一种默契,如对付那首著名的《波希米亚狂想曲》,歌词“诡异”,但成员们从来不会去质疑,而是给予了大家空间去想象。其他成员想必理解在Freddie写出这首歌时候个人生活的变革和无意公开的心思。
这种互斥、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相处,其实在我看来,正是 “名流”的深层含义和社会原谅(Tolerant)的表示,也是为何那片在我们眼里”传统守旧“的老牌帝国,却成为迷人音乐文化绽放的土壤。
Survive then surprise
摇滚的天国人间
“摇滚”彷佛不食人间烟火,但摇滚乐队的成功离不开商业化的操作,也面临着各种政策、经济、社会现实状况的制约。在Queen成立早期,几位成员都住在伦敦附近的出租房里,弗雷迪还在用钢琴作床头板,Brian还在靠冷冻鱼条过日子(你我都有吃土的日子)。唱片公司签约、录音室利用、新歌制作、发布宣扬,这统统都须要商业运作的支撑,并无商业履历的他们在一开始也曾由于停约丢失。令人吃惊的是,纵然是在3张专辑发布之后,皇后乐队的成员却仍旧“债台高筑”,据成员们后来承认,“我们的管理公司也是我们的唱片公司,没有真正代表我们去和唱片公司会谈的人”。(Money is money, 劳资抵牾纵然是摇滚乐队也无可避免啊)。
而成功后又有成功的烦恼,英国政府的“重税”达到80%,艺术家也要合理避税,Queen不得不离开英国,每年只能在本土待不超过183天(也便是类似移民监,最长待半年),只能通过不断巡演、在其他国家录音规避;而到了南美,文化不同、政治环境不同,让许多如鱼得水的操作变得不可能,在英国很正常的事情变得困难,在文明社会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如墨西哥的腐败),导致首次南美之行大为烦懑,“连滚带爬逃返国”,还遭受经济丢失;或者要面对如《新音乐速递》这本黑了Queen好多年的杂志,和不断的舆论等,不得不去对付。又如成立了三家Queen命名的公司开展不同业务(如唱片发行、录音、演出等等),则是范例的、成熟的商业化操作“套路”。
从商业运作的细节中,看得到妥协,这彷佛与惯常理解的“摇滚”二字不相匹配,但这便是一支摇滚乐队的真实经历,他们的生活并非天国,相反,作为想要实现音乐梦想的他们,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让步,并与眼里只有钱的“三教九流”贩子互助。也须要在音乐之外,练就一些商业的技能,才得以让他们的音乐之梦和传奇得以延续。这种会谈和选择性“妥协”,并不是耻辱的,“摇滚精神”并不与现实天下扞格难入,而是为了让自己在实现梦想的轨道可持续性地追逐,乐意去改变、提升和调度,保全核心的实力。
Higher and Farther
要的是不同凡响,要的是惊世骇俗
在每一次演出、每一张作品出身中的妥协和抵牾,有激烈的争吵,会相互批评,如Freddie诉说“一山有四虎,画面太美”,特殊是当有重大演出或制作过程中,冲突在所难免,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见地,给人一种这群人一定有强制症的觉得,或者说“孤独的坚韧”,例如Brian 和Roger总能找到暴力撕逼得情由,但绝大部分都因音乐而起,大吵三天,只是为了一个音符;也可能为了某句歌词是否会引起演出当地不适而辩论。弗雷迪也承认自己在音乐上十分“难搞”,认为“想要取获胜利,就不可能太和蔼”。
另一方面,这群摇滚人士的个人生活不同阶段都曾碰着过“狗血”的境遇,殽杂着事情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有面临崩溃的时候。
但既然想的是高远,便不困于面前。无论背后如何争吵,无论各自如何感情低落,在面对大众和音乐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保持着专注,或者说对音乐这个事情是他们排解其他困苦的天国和避难所,并将困苦和感情借歌曲抒发。以是我们也听到了许多隐含了各个成员每个阶段状态和思绪的歌曲,例如当Freddie和德国女模特一段感情溘然走到尽头时,向她献上了一曲《Love me like there is no tomorrow》,如爱车的Roger写了一首《I’m in love my car》,又如在Freddie末了一个生日当天发布的那首悲哀的《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等等。
在星光熠熠的七八十年代(想穿越),同时期的天才何其多,随意列举便是如雷贯耳的大名,摇滚界也不乏让人扼腕的“27岁俱乐部”。皇后能够脱颖而出,并保持青春那么多年,很大程度上,正由于“大多数同时期的乐队展现出来的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皇后乐队却大大方方地表现出了他们聪明的头脑、良好的背景和清晰的思路”。就像Brian曾说:“我们认为机会总会在某个时候涌现,你得等待机遇脱手,成年人和孩子的差异就在于,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机会来临时,我们要把所有事情都排练好,知道舞台演出的每个细节,整件事情都该是专业的。”
专业执着的态度,造诣了惊世骇俗。
Explorers and Voyagers
没有尽头,没有边界
在征服和达到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后,是不是敢于冒着失落败的风险实验性地探索,连续提高的动力又是什么?这是Queen在终于成功征服南美地区、完成巡演后,乐队成员提出的问题,此时已经是20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红了十余年,但这种探索的精神贯穿了他们全体生涯的。
从深度上说,在他们生动的几十年间,产生的作品褒贬不一、或扑街或大卖,但从未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直地做着变革,就像他们打破性地制作了歌剧院之夜这张非范例摇滚专辑,“皇后乐队即便失落败也乐意不断考试测验”,这也是他们长久生命力的来源之一。他们把华美摇滚,前卫摇滚,古典音乐及重金属熔为一体,具有非凡的想象力,风格、主题变革多端。
《The show must go on》这首发布于1991年,也便是皇后出道了21年、弗雷迪去世前夕发布的歌曲,可以认为是弗雷迪在生命后期的心声,也是全体乐队在经历了波澜壮阔后,仍不断提高的决心。
广度而言,几个成员具有完备不同于音乐专业背景的“基因”,什么天文物理、医学、电子工程,主唱还是个机场打杂的,都能够造诣音乐界的传奇,仿佛不可想象,就像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到者,本科学的文学,五十多岁得到物理博士。这种不把人的潜力做边界的框定、具备高度的“容错性”的环境,让人倾慕;现实的土壤可能并不友善,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也有着差别,但若能无论身处何种井隅、到哪个年纪,都不把自己限定在“我只能做这个”之中,也是一种自由。
在互联网尚未如此发达的90年代,Queen具有前瞻性地开通了官方网站。而在弗雷迪去世后,两位紧张成员May和Taylor亦持续在为离开了Freddie的皇后做着诸多努力和探索,并至今在世界各地,和新生代歌手携手巡演,连续着乐队的旅程,这么做是由于“我们还活着”。
Mia San Mia
我还是我
四个成员既是一个整体,但他们各自也是独立的个体。
从乐队的事情机制便可见端倪,他们的模式是每个成员会单独写歌,然后把这些歌曲的想法抛出来给其他几位,由他们建议、改进,乃至谢绝。虽然某种程度上这让“集体感”缺失落,积极的一壁则是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创作,去表达,以是每个人都为Queen带来大量个人创作,如Freddie的波西米亚,Brian的We will Rock you, Roger的Radio Ga ga (目前最爱的魔性之一),和Deaco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在Queen本身之外,四个人还分别在不同阶段持续发展着各自的音乐和其他行业的奇迹,只管彷佛不如Queen那么为人广知。他们每个人都“野插花”,个人或和其他音乐人组成独立于皇后之外的团体,进行歌曲制作和现场演出。跨界更是习以为常,天分过人的Freddie曾专门随着伦敦芭蕾舞团演出,并在后期与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互助,将盛行和歌剧完美结合,只可惜那首互助的《巴塞罗那》在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播出时Freddie已去世;Brian不用多说,在音乐奇迹之外,未曾放弃学术,离开校园三十年后连续科研,得到的帝国理工大学天文博士学位在摇滚界无出其右;Roger这个爱车如命的花少,也终于参加了赛车比赛;Deacon则安静地从事着电子、算着他的数字,投入膝下六个子女的家庭。
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己内心意愿、个人天赋和奇迹忠实的程度,和对皇后乐队本身不相上下。他们都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和内心想追求的奇迹,同时也没有辜负对Queen这个团体的任务。对广大歌迷来说,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皇后乐队,对各个成员自己来说,乐队是他们生命里一个主要的无法割舍的部分,但他们仍保留着属于自己、同样主要的空间。
是他们,也是我们
书中那些去过但未留神、或者耳熟却未曾走过的地方,可能是录音室、学校、街道、运动场、剧院、民宅等等(记得打卡噢),曾经留下过皇后乐队的痕迹,都令人更加确信这既是fantasy,也是real life;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梦幻般的演出背后,也是真实的、百感交集、和自己斗争、向不甘寻衅的人生,It might happen to you, to me as well. 用那位不列颠君主伊丽莎白Queen去年圣诞致辞来说便是“Ordinary people can do exchaodinary things" 平凡人缔造传奇。皇后乐队成员对那首得到最高赞誉的《波希米亚狂想曲》如此诠释“一首伟大歌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会将它与你生命中的亲自经历联系起来”。
一支伟大的乐队给人的鼓舞力量,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