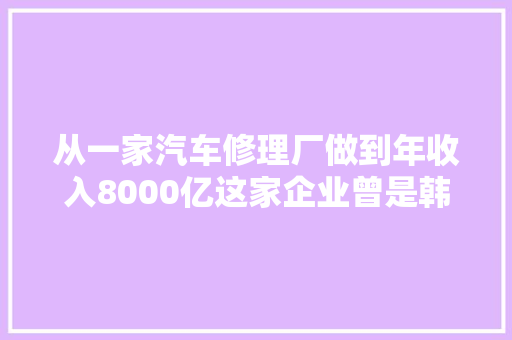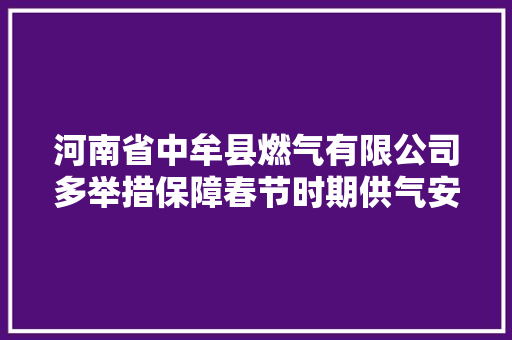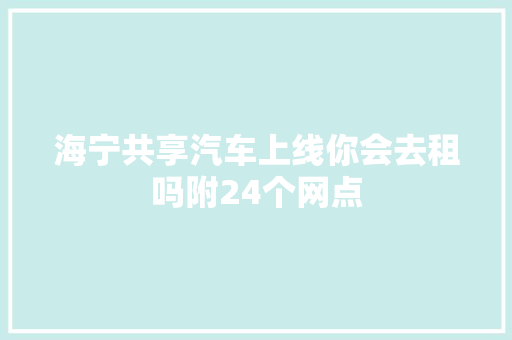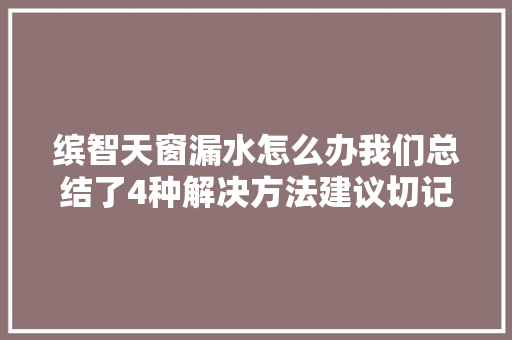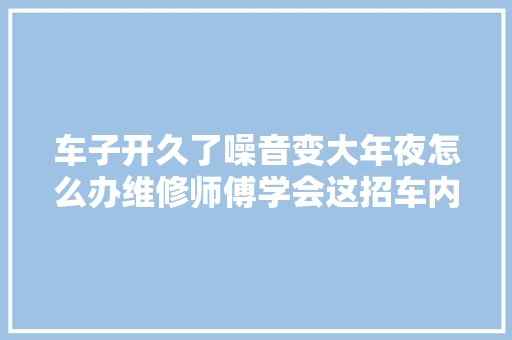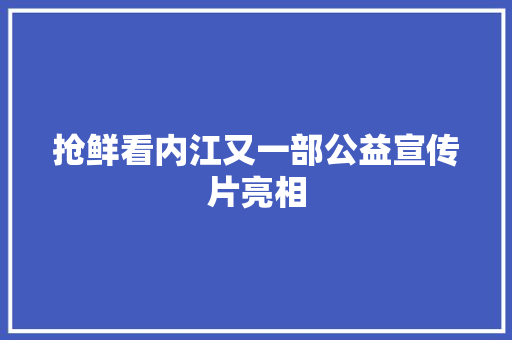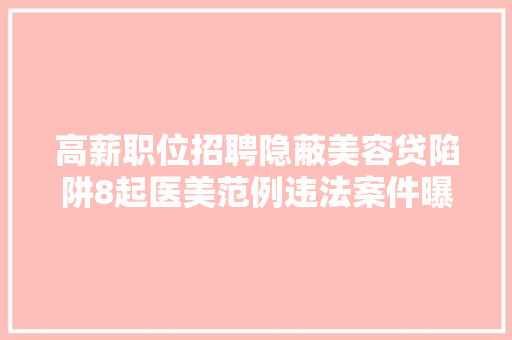“游艺”一词,本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凡各种以消闲遣兴为目的游戏娱乐活动,均可纳入“游艺”之范畴。唐人以辞赋特有之形式书写游艺活动的作品不在少数,紧张保存在《文苑精髓》“杂技”“射”“博弈”类及《历代赋汇》“巧艺”类赋中,依此,可将唐代游艺赋分为百戏类、博弈类、射艺类三种。百戏是杂技艺术的统称,经汉代至隋唐,历演不衰,且种类愈丰富,大致包括绳技、竿技、马技、球技、幻术、角抵、拔河、竞渡等,干系赋作如胡嘉隐《绳伎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李濯《内人马伎赋》、阎宽《温汤御毬赋》、王棨《吞刀吐火赋》、薛胜《拔河赋》、范慥《竞渡赋》等。博弈意指博戏和棋戏,博戏包括六博、双陆、樗蒲等牟利益的游戏,棋戏则包括围棋、象棋、弹棋等怡脾气的棋艺,干系赋作如薛恁《戏樗蒲头赋》、邢绍宗《握槊赋》、卢谕《弹棋赋》、阎伯屿《弹棋局赋》、傅梦求《围棋赋》等。射艺类赋作则如白居易《命中正鹄赋》、元稹《不雅观兵部马射赋》等。这些种类多样的游艺赋,反响了唐人多彩的精神生活与丰富的文化意蕴。
愉悦人们的精神情趣,反响当时的娱乐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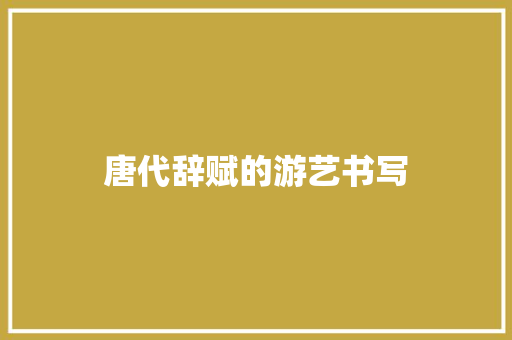
赋本身具有娱乐的浸染,因所施工具不同,可分为娱人、自娱、同娱三种。曹明纲在《赋学概论》中说:“先秦两汉期间的一些文学侍从之臣,以作赋的办法去媚谄于君王,为帝王的巡行宴饮助兴添乐。”如汉代梁孝王好养士,曾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西京杂记》),此可视为君臣宴集以赋同娱的事例。汉武帝身边亦有一批“言语侍从之臣”,个中枚皋最善作赋,“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其目的就在于谐谑媚谄皇上。可见赋的娱人浸染,由来已久。游艺与赋的结合,更匆匆使其娱乐功能的最大化。
唐人花样繁多、博识超绝的游艺活动,不仅表示了唐人富于创造力的大脑、机动的身体,更主要的是反响了全体时期的精神追求与文化氛围。唐人爱玩,爱享受,不但上层统治者如此,平民百姓也不例外,由此形成了一种相称浓郁的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时期氛围。吴玉贵在《中国风尚通史》(唐五代卷)中将游艺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演出性游戏,如打毬、拔河、秋千等;一类是娱乐性游戏,如樗蒲、围棋等。不管是游戏的演出者,还是参与者,都在游戏活动中得到了身心的愉悦、知足与享受。
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不雅观舞马赋》曰:“帝曰司仆,舞我骐马。可以敷张皇乐,可以启迪欢趣。”明确指出不雅观看舞马具有“启迪欢趣”的浸染。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曰:“这天也,悦豫重情,喧阗镐京,角抵惭妙,巴歈寝声,赏舍嘉用,润泽寰瀛。不雅观斯乐之为最,孰不称于隽誉。”金厚载《都卢寻橦赋》曰:“初其委质员来,当场献艺。耀百戏于君所,仰千寻于天涯。干霄迥出,将为悦目之娱;举步俄升,自有翻云之势。孤标上耸,兆庶同嬉。”不仅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给予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也让人们得到了精神上的知足。君王与百姓同看精彩的竿技演出,终极达到同欢共乐的局势。薛恁《樗蒲赋》云:“别有膏粱之子,缙绅之客。时为此物,以代支策。月朔拟而纯卢,忽连呼而成白。相顾则笑,泯然无隙。请倾耳而侧目,看后来之一掷。”借“膏粱之子”“缙绅之客”以樗蒲游戏纾解操心之困,提醒人们应多看重樗蒲的消遣娱乐浸染。难怪唐代郑谷《永日有怀》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两掷未终楗橛内,座中何惜为呼卢。”唐人探求各种名目以娱乐,目的在劳作之余活泼精神,熏陶脾气,张弛有道。
此外,那些描写绳技、蹴鞠、马球、射艺等游艺的赋作,同样具有娱人或自娱的功能,它们是唐人追求娱乐享受的社会风尚的产物。梁启超曾把游戏、学问、艺术、劳作并称为“意见意义主体”,认为“意见意义”在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凡人必常常生活于意见意义之中,生活才有代价。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学问之意见意义》)梁启超从人类生活的长远视角,指出游艺对付人类的不可或缺性,只有投入丰富多彩、活泼有趣的游艺活动中,才能使人们得到愉悦康健的精神享受,并进一步引发人们的创造力、启迪人们的聪慧。这些唐代的游艺赋之以是具有无穷的魅力,其紧张缘故原由就在于它是唐人康健有趣生活的直接反响,表示出唐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娱乐性特色。
颂扬恩德与阵容,寄寓人生情志
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他乡各国有着非常频繁的外交往来。唐朝国力的壮大、经济的繁盛、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使其一度成为当时“中亚朝贡关系”的中央。各国青鸟使因不同目的而不断入唐,或政治寄托、或文化学习、或贸易往来。为显示皇恩,唐统治者少不了设酺宴请各国青鸟使,个中就有百戏杂技节目,它已不仅仅是消遣娱乐,更多含有耀武扬威并使蛮夷臣服、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唐代游艺赋于此有直接反响,如《绳伎赋》曰:“万国会,百工休。俾乐司咸戢,绳伎独留……欢百姓之心,倾四方之国。”《勤政楼花竿赋》曰:“皇上朝万国,宴千官。当献岁之令节,御高楼而赐欢……将煊赫以夸众,候铿锵而取则。”《千秋节勤政楼下不雅观舞马赋》曰:“惟大唐之握乾符,声谐六律,化广三无……则知绝群称德,殊艺逸貌;足之舞之,莫匪贤人之教,则陈力者愿驱策而是效。”《内人马伎赋》曰:“天子顺时不雅观武,乘暇会群。百蛮在庭,如蚁慕于膻附;千官翊圣,类星拱之垂文。……于是羌髳夷羯,毡裘辫发。心目愕眙,形神陨越。屈膝天庭,稽首魏阙。荷臣子之欣戴,咨译人以启示。曰天临有唐,抚绥万方。文德广洽,武义大扬。”张楚金《楼下不雅观绳伎赋》:“方今寰海清,太阶平,兵革不用兮国无征,风雨既洽兮年顺成。上曰可乐,人胥以亨,大则有焘载之义,小则无角抵之名。”阙名《舞马赋》曰:“我开元圣文神武天子陛下懋建皇极,丕承宝命,扬五圣之耿光,安兆民于反侧。功成道备,作乐崇德,上以殷荐祖宗,下以导达情性……野人沐浴圣造,与不雅观年夜德,敢述蹈舞之事而赋之。”赋家不仅以“大唐”“我皇”“我王”“吾君”等直接表达对帝国的赞颂、君王的爱戴,还每每通过夸年夜等手腕描写外邦青鸟使木鸡之呆、形神消殒乃至忘神失落箸的环境,以此达到宣示国朝天威、皇恩浩荡的政治浸染。
在以颂扬为主调的游艺赋中,典范者当属《拔河赋》。《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了唐中宗、唐玄宗期间的两次拔河比赛,尤其是唐玄宗期间,组织了一次千人拔河比赛,且请外邦青鸟使前来不雅观赏,其目的在于炫耀唐帝国的阵容。进士薛胜不雅观后,即写下名盛一时的《拔河赋》。赋作开头即言:“天子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直接点明拔河的意义在于在外邦面前夸耀自己强大的国力。中间一大段极力描摹拔河比赛的激烈场面,末了结以“于是匈奴失落箸,再拜称觞曰:‘君雄若此,臣国其亡’”,借不雅观赛之匈奴青鸟使大惊失落箸的神色呼应开头“耀武于外”的政治目的,赞颂了唐王朝壮大的国力与伟大的气候。
唐代文人还通过赋咏游艺寄寓讽谏之意与人生情志。如胡嘉隐《绳伎赋》结尾曰:“绳有弛张,艺有废兴。用舍靡定,倚伏相仍。如临如履,何兢何喜。犹君之从谏则圣,伎之从绳则正。惟伎可以为制节,绳可以为龟镜。殷鉴不昧,在此而已。岂徒昭玩人丧德,岂徒悦彼殊者子。”作者不仅以绳技之正喻从政、为人之道,劝告君王该当从谏如流、为人正派;而且深知玄宗纵情声色,故以“昭玩人丧德”“悦彼殊者子”劝诫玄宗,讽谏意味光鲜。王邕《内人蹋毬赋》亦云:“方知吾君偃武之日,修神仙之术。但欲扬其善教,岂徒悦其淑质?谓艳色兮可轻,使宫女兮程功而出。”委婉劝诫玄宗勿纵情美色,如此方能发扬善教。尤其值得我们把稳的是,有些游艺赋本身颂扬与讽谕兼具,如敬括《季秋朝宴不雅观内人马伎赋》开头云:“夫何至德之极兮,越五帝而作君。羌柔远以服外,廓寓县而同文。”称颂君王具有一统天地、怀柔外邦的至德之心。而在赋末又云:“斯帝王以是因壮不雅观而戒逸,遂居安而若厉。岂淫乐以惑人,见终朝于郑卫。”劝诫君王不应沉迷内人马伎的游乐活动中而忘却了身居天下之位。博弈本为一项智力游戏,它能熏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但若一味沉溺个中,也随意马虎让人损失心智,故赋家在书写博弈游戏时多含劝诫。如卢谕《弹棋赋》云:“是知冒险者忘于趋进,规利者失落于戒慎……伊众趣之无极,谅所戒以唯贪。苟能知其义者,无弃学而遐耽。”张廷珪《弹棋赋》云:“唯智是役,唯贪是慎。”邢绍宗《握槊赋》云:“足明夫正而不谲,取又非贪……但是终多丧志,吁嗟士兮不耽。”皆借棋道解释戒贪之意。
保存干系文献史料,承载民俗文化意涵
博弈古来即为人们所喜好的一种智力游戏活动。秦汉期间,博弈盛行,樗蒲、弹棋等新棋种随之产生,围棋则连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期间,棋艺类智力活动尤为生动。至唐代,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宽松、文人地位的提高、君臣的爱好等成分的影响,博弈游戏蔚为风尚。
以赋的形式写博弈游戏,其主要代价之一就在于保存了关于棋道、棋艺等文献史料。汉代马融所作《围棋赋》《樗蒲赋》,梁武帝作《围棋赋》,对围棋、樗蒲的行棋方法、理论等皆有论述。魏晋时曹丕、丁廙、夏侯淳三人皆以弹棋为赋,个中对棋盘之布局及棋子之材质等有较为详细的解释,如曹赋曰:“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痹根四颓。平如雕琢,滑若柔荑。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丁赋曰:“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致理肌平。卑高得适,既安且贞。棋则象齿,选乎南藩。”夏侯赋曰:“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唐代卢谕、张廷珪作有《弹棋赋》,对棋局与棋数亦多有解释,如卢谕曰:“不雅观乎局之为状也,下方广以法地,上圆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悬。四隅咸举,四达无偏。居中谓之丰腹,在末谓之缘边。棋之为数也,各一十二汇。”阎伯玙《弹棋局赋》对棋局则有更详细的解释:“西南之美,有西岳之矿石焉;底贡之珍,有荆山之象齿焉。于是工人创器,轨物备叙。丰腹上圆,颓根下矩。”可见由魏至唐,棋局变革不大,大体仍是中间高四周低的场合排场。但弹棋形制略有变革,蔡邕赋曰“放一弊六”,曹丕赋曰“二八次举”,卢谕赋曰“各一十二汇”,可知棋子由汉代的十二颗,增加到魏晋的十六颗,再增加到唐代的二十四颗。据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邢绍宗《握槊赋》也是理解握槊形制和规则的主要史料。赋云:“物以群分,故玄黄而不杂。”表明棋子有黑黄两色。棋子为象牙材质,双方轮流掷骰行马,故“象牙在手,骏骨登盘”。又云:“张四维则地理攸载,背两目则天文可不雅观。不可饰于丹漆,宁假贵于琅玕。”这是对棋盘材质与棋局骰子的描述,不饰丹漆而采取琅玕美石。棋局有两枚骰子,刘禹锡《不雅观博》曰:“有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为骨制,其形状为觚棱形、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字,其规则大约为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字多少行棋,即“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末了以霸占对方棋道分胜负。邢赋中所言“闭六关而不通,因一子而为质”,描述的便是一方棋子被对方围困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不论是棋局还是形制,赋作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为我们理解博弈游戏供应了干系知识。
同样,胡嘉隐《绳伎赋》、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不雅观舞马赋》、李濯《内人马伎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等,个中论及的各类游艺活动,都是为了庆祝唐玄宗千秋诞辰,真实地反响了当时演出之场景,不仅保存了千秋节日民俗文化的宝贵史料,也为杂技史的研究供应了翔实的资料。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1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