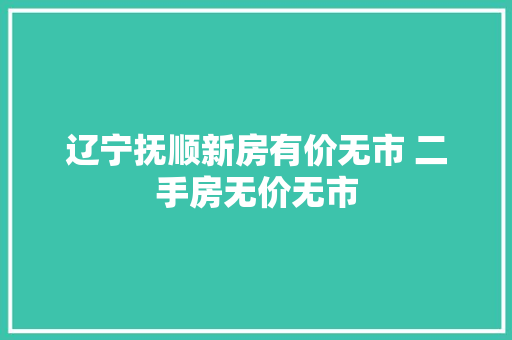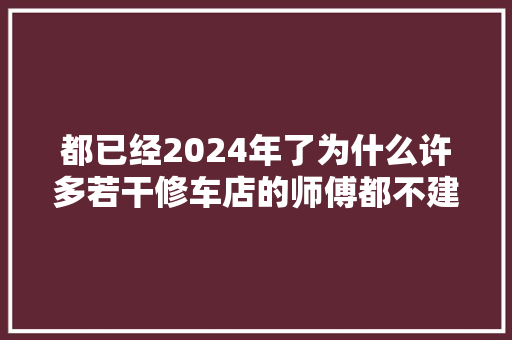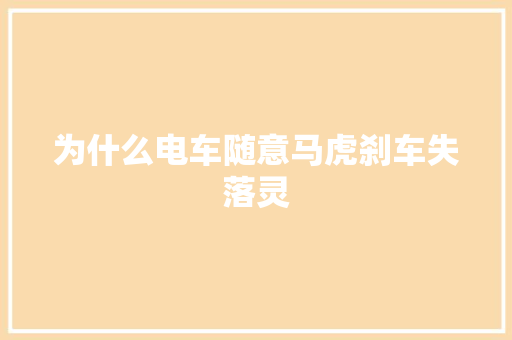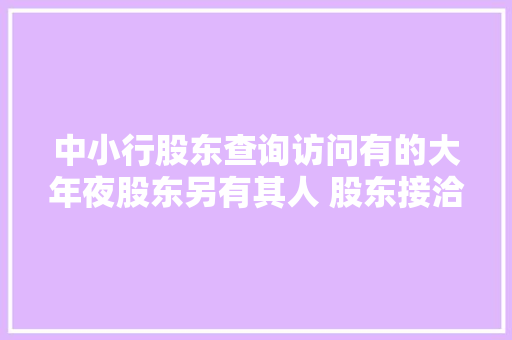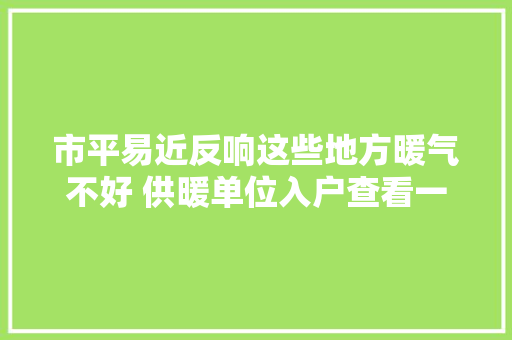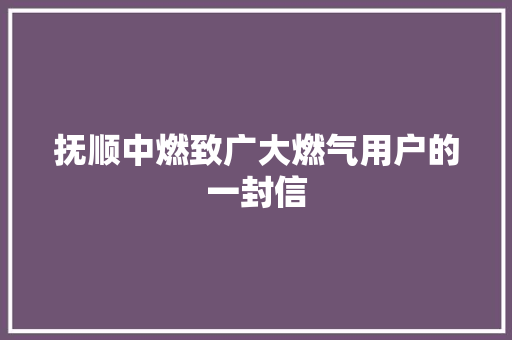我按照舆图上的指引,穿过道口、走过废品回收站转入这条看上去已然许久无人问津的小路。左手边是平行的铁轨,超越铁轨即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矿坑——抚顺西露天矿的南缘;右手边则是废弃已久的厂房,破碎的玻璃窗格下还印着标语,凌乱成长的野草遮住了当年负责涂上去的笔划。单独占了一格、位于正中且漆色依然清晰的赤色正圆形句号看上去与周遭扞格难入,那是这一全体破碎的建筑立面上唯一完全的东西。
我沿着铁轨向舆图上空缺的深处走去,试图弄清楚那上面“机车库”的标注能否给出困惑我多年的问题的答案。阳光直射在脸上烤得发热,仿佛把空气中的烟尘都糊上皮肤,我伸脱手挡在额头前,试图看清楚铁轨延伸的方向是否有我想要的东西,不过却是徒劳。好在在这无人的小路上,我得以透过微风吹过野草扑簌簌的声响,捕捉到一丝微弱而节奏规整的“哐当-哐当-哐当”,那是矿坑深处还在运行的电车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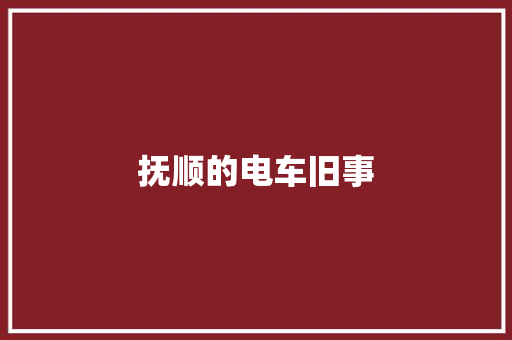
终于,我看到平行的铁轨开始波折,分叉成多条,原来水泥制的枕木也不知道在何时变成了木质。就当我准备迈过铁轨绕过前面的红砖房一探究竟时,溘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喂!
干嘛的?”声音来自视线最远处铁轨旁一个穿着一身蓝色制服的工人。
“我听说抚顺原来那些旧电车都停这边了,想来看看。”我扯着嗓子说,“我在网上瞥见有人来看过。”
听到我是来看电车的,那人并没有要拦住我的意思,而是迈过铁轨向我走来,“嗐,你来晚了,就上个月,都拉走啦!
”
拉走了?我心想,现在才8月,我明明在网络上看到别人2月来的时候,还拍下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制造的满铁101型客运电车,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改造过的“联络号”、“发展号”电车。
“拉哪去了?您知道吗?”我连续追问。
“有几个拉那个博物馆去了,别的就不知道了。”
博物馆站月台
电铁往事
由于各种一定与巧合,当我真正来到那位工人所说的抚顺煤炭博物馆,已经是五年后的另一个8月。由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各类出行限定,我在这个2022年的夏末得到了久违的在家乡“休假”的机会,也终于能够将脑海中关于电车的零零散散的碎片拼凑到一起。
抚顺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最早涌现的电车也是为了做事于煤矿开采。煤炭博物馆位于西露天矿的西南缘,我开着车从市区前往,离开最热闹的市中央,一起便是绕着西露天矿的北缘,与电车铁轨相伴。记得年幼时,每次走过这条路,家人都会提及,曾经我姑姑每天都要在这里坐电车高下班。有一站名叫新生桥,是电车系统中西部客运干线和经济干线的交汇站,连接着曾经的抚顺水泥厂、液化工厂、钢厂、发电厂等等主要工厂,也是家人口中曾经人最多也最热闹的站点,如今只剩下杂草丛生的水泥月台和锈蚀的遮阳篷。
抚顺电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是中国最早涌现的有轨电车系统,在2009年7月客运部分停运前,也是海内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准轨电气化地方铁路系统。虽然抚顺人习气称之为电车,但它更加准确的名字该当是电铁,它不同于长春、大连等地市内的有轨电车,而更靠近于东京、大阪等日本城市如今仍在运行中的市郊通勤铁路系统。纵然不考虑线路的设计,从外不雅观上也能明确察觉到这一点,每次我有不理解抚顺电铁的朋友来到抚顺,他们都会以为那些铁轨是用来跑火车的。
与很多东北城市的交通根本举动步伐一样,抚顺电铁的发展也与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的侵略有关。1904年,日俄战役在中国东北的地皮上爆发,当时的抚顺正处于沙俄军队的掌握之下。为了抢夺抚顺的煤矿资源以供战需,沙俄铁路大队未经清政府容许便匆忙建筑了一条宽轨铁路;一年后,沙俄败北,日本“天经地义”地强占了抚顺的煤矿和矿区的路权,并以这条俄国人建筑的铁路为根本,连续铺设铁道以抢夺抚顺的工业资源。
最初沙俄建筑的铁路是从中东铁路南满支线苏家屯北浑河附近出岔,沿浑河向东至抚顺煤田,穿越千金寨到达老虎台,并引出杨柏堡岔线一条。由于施工匆忙,这条铁路的技能标准很低,线路、桥涵、站舍等大多为临时性建筑,规格利用了俄国海内常见的宽轨标准(1524毫米)。战后沙俄撤出,日本先是将这条宽轨铁路改为窄轨(1067 毫米),随后又增修由杨柏堡至永安台山附近的线路,逐日运行2-4 对列车,那时利用的还是蒸汽机车。
韶光又过了两年,日本为经营中东铁路而设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正式成立,为了连续抢夺抚顺的煤矿资源,并将抚顺的铁路并入南满铁路的系统内,满铁又动手将窄轨改建为标准轨(1435毫米)。1908年7月尾,改轨事情完成,同年11月,大山坑发电厂建成,到1914年,抚顺矿区的铁道系统依托经两次扩建的大山坑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完成了全面的电气化。此时电气铁道总长为40.6公里,共有电机车八台、客车两辆,电铁系统初具雏形。
经由新生桥站再向西行驶一段,很快就到了西部两条线路的分岔,客车干线连续向西前往抚顺的望花区,而经济干线则向南转,通往被称为古城子的片区,行车道也是如此。经由一个旗子暗记灯失落灵的三岔路口,到了古城子附近,路边满是贩卖琥珀和煤精雕刻工艺品的商店。这两样东西算是抚顺煤矿除了煤之外最主要的特产。由于中国产琥珀的地区屈指可数,抚顺琥珀还在2014年被列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不过看得出来,这些店近年的买卖彷佛不怎么样,不少店关着门,还在业务的,也鲜有人像过去那样把自家最引人瞩目的大件煤精雕刻作品摆出来。
随着导航连续向南行驶,转弯上桥超越一段电铁轨,博物馆就在面前了。30元门票,48小时核酸,我顺利进入博物馆内,在可以眺望西露天矿坑的不雅观景平台广场上,曾经的矿用电车和机器设备整洁地停放着。再向深处走,在写着“博物馆站”的仿照月台上,我终于看到了影象中的客运电车,满铁101型客运电车。
机车库附近,后面的工厂是曾经的抚顺石油一厂
满铁101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上大学前在抚顺整整生活了18年的人,我乘坐电车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小学时,父亲带我去拜访住在矿区的亲戚,电车是连通我家所在城区与矿区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而它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在东北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里搭乘,车里真的很冷。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觉得,故乡的事物,身在个中时从不以为它有什么特殊之处,离开那个环境再转头去看,或者借助“外地人”的视角去重新感想熏染,才会发觉其不同的意义。电车对我来说便是这样。2014年,刁亦男导演的电影《白日焰火》上映,它在当年的第64 届柏林电影节得到了金熊奖的最大声誉,同时助男主角廖凡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在看那部电影时,只管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冰城哈尔滨的故事,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抚顺的痕迹,那便是电车。
电影开始,男主角廖凡饰演的警察张独立与前妻离婚,他们末了分别的场景便是电车站,其拍摄地便是抚顺的矿物局车站;随着故事发展,警察张独立须要持续跟踪桂纶镁饰演的女主角吴志贞,以探求凶杀案的线索,个中一个场景便是在电车上。正是由于《白日焰火》,我再次想起身乡熟习又陌生的电车,而当我想要等假期回家再去体验一次时,才创造客运电车已经在五年前停运。
自那之后,险些每一次回到家乡,我都会去矿区转转,偶尔还能看到少量还在利用中的矿用电车拖着装着矸子(采煤的副产品)的运斗缓缓行驶在铁轨上,但曾经的客车都已经消逝不见了。
在博物馆看到这辆被喷上崭新油漆的工业古董,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这辆电车车身遵照着过往的样子被漆成深绿色,而车门处的把杆和车顶部的打仗电线则变成了正赤色。仔细看才会创造,电车所在的这段铁轨并不与表面实际的电车铁轨连通,而是被围墙阻隔,铁轨两端也都是封闭的。透过车头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块金属铭牌,写着“电动客车101”,产地日本,出厂日期为1935年。
经由修复的电动客车101
自1907年满铁成立起,抚顺便是满铁最大的附属地(租借地),其爪牙不仅伸向了抚顺的煤矿,也伸向了抚顺的全体工业体系,日本先后建立了抚顺炭矿发电所、机器制作所、焦炭厂、炸药厂、西制油工厂、石炭液化工厂、水泥厂、电瓷厂、制钢所、制铝工厂等一系列大型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满铁在许多东北城市霸占煤矿,而唯独在抚顺建立了集工业体系、城市体系、电铁交通为一体的轨道交通家当群。根据煤炭博物馆给出的数据,到1940年3月,抚顺电铁总长达到了188.7公里;而借由电铁的上风,自1903年至1944年,日本共从抚顺掠走煤22300万吨,抚顺运昔日本海内的煤占煤矿总输出量的50%,占日本海内煤炭总输入量的60%-70%……这辆“电动客车101”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这辆电动客车101的原名是“満鉄ジテ 1 形特急列车”,由三菱重工和日本车辆会社设计,最初是电传动式柴油机车,在1943年满铁的高速铁路实验中以2小时58分钟的时长跑完了从奉天(沈阳)到新京(长春)304.8 公里的间隔。实验后,满铁将个中一列改装日立直流电机送往抚顺进行电气化运行,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石油资源的匮乏,当年所有的“満鉄ジテ1形”列车都被转交抚顺矿务局,改装成了供工人们高下班利用的通勤电机车。
走近电车,我无意间创造一道未关紧的车门,我握住已经被焊去世而无法迁徙改变的把手向左用力一推,才创造这一道门并没有上锁——是新装上的门链松掉了。但毕竟它的“年事”摆在那里,车门的滑道不再顺畅,我耐着性子一点点拉开门,走进车内,除了新涂的红棕色油漆,车里的内饰还保留着我影象中的样子。
我上来的这一节车厢是正反背靠背的木质座椅,座椅上方则是木条与金属组合成的行李架;上车就有拱形的金属扶手,在车厢中门处也有同样的设置;穿过连接处来到另一节车厢,则是与之完备不同的侧面座椅设计,就像现在的地铁,只不过这样的车厢并没有中间车门,座椅也是贯穿始终的。只管被刷上了油漆,但还是能看出它曾经的样子,那些已经微微翘起的地板、不再润滑的窗框都给人一种韶光倒退的错觉;唯一冲破这种错觉的是进门处已经不那么清晰了的“儿童购票线”,显然它已经从我的头顶退到了我的胸前。
“捷克儿”电机车,阁下地上是电阻
机车厂里正在检修打仗网的工人
末了的电车厂
从煤炭博物馆离开后,我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沿着曾经的南干线绕了一圈。不同于已于2019年闭矿的西露天矿,位于东边的老虎台矿与东露天矿如今依然有少量煤矿作业,因而还会有电车通畅。就在曾经的老虎台矿俱乐部附近的一处道口,我再次与一台事情中的电车相遇,纵然机车车头已经从我面前走过,但道口的栏杆却依然老实地展现着它的古老,苗条的木杆已经从中间断裂、被迫用铁丝缠绕上新的一节,而另一侧作为平衡的压秤物,并非规则的铁块,而是几块普通的石头。
只在煤炭博物馆见到了一辆曾经的客运电车,我多少心有不甘。彷佛便是这几年我才意识到,家乡工业遗产的宝贵,它们实在是地理与历史共同创造出的礼物,而我却是在缺点的韶光打开了它们。看着面前缓缓行驶的电车,我忽然想到2019年抚顺市政府曾试图规复一条客运电铁线路,作为老工业区的旅游项目吸引游客,但很快不明晰之。不过现在间隔2019仅仅过去三年,或许我能够找到那一辆被重新修缮过的电车?
过了一周,通过家人和在矿务系统事情的邻居的帮助,我幸运地来到了抚顺矿业集团的电车维修中央。这里的前身是1914年满铁在抚顺成立的中国最早的电机车厂,原来这处厂房只卖力制造,位于东露天矿青年路附近的厂房卖力维修,但由于矿区的沉陷问题,另一处厂房早已荒废,而如今也鲜有电车生产,于是两边就合二为一了。除此之外,在抚顺市西部紧挨着沈阳的望花区,还有一处厂房,被工人们称为西厂。
卖力接待我的师傅姓王,他上世纪80年代从煤炭学校毕业后就在这里事情,卖力电机车的维修。在煤炭博物馆时,我把稳到了这些看起来极其相似的矿用电车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产地来源。师傅指着入口处正在由年轻工人拆卸打仗网的电车向我先容,这台由湘潭电车厂制造的电车他们习气称之为韶峰,而最早日本1940年代生产的车被他们称为黑车,东德产的叫大德,捷克斯洛伐克的则简称捷克(儿),特点是操作室位于车辆中段,以是在矿上非常好辨认。师傅讲起“捷克(儿)”时带着清晰的儿化音,一瞬间让我以为面前已经生锈的电车仿佛活了过来。
“以前,全国的电车都得拉我们这来修。”王师傅提起过去,语气中不乏骄傲,我问到2019年作为旅游项目而规复运行的电车是否也是在这里修缮的,师傅说那台车便是他修的,可惜只运行了半年不到,在那之后,他乃至也不知道这辆由自己亲自复活的电车去哪了。
王师傅提到,在过去,险些是“有矿就有电车”,以六盘水、湘潭和抚顺为核心的电车制造及修理工厂支撑起了全国的需求;而现在,一方面由于煤炭行业本身的萎缩,另一方面也是更大略实用的传动式履带替代了还须要轨道才能运转的电车,“以前一个月我们要修将近20 台车,现在也就3到4台。都淘汰啦,现在的矿都不用这东西了。”
上世纪90年代,还有来自北京首钢、黑龙江七台河、双鸭山、鹤岗等地的电机车须要在这里维修,近些年来,就只剩下还留在抚顺的这些老古董了。在这些还能够运行且须要维修的矿用电机车中,纵然是最年轻的“韶峰”,也产于上世纪60年代,自1972年引进抚顺煤矿,已经由去了半个世纪。看着面前正在电车上忙上忙下的年轻工人,我感到一阵唏嘘。
我问起师傅如今新入行工人的状况,师傅依然不乐不雅观,“现在年轻人哪还想干这些。化工大学(辽宁省石油化工大学)有定向培养专业,但是大家都甘心去矿务局坐坐办公室;下来修车的基本都是专科的小孩,干一阵就走。”现在无论任何行业,年轻一代换事情的频率都会被拿来谈论,而据王师傅讲,修电车是个履历活,聪明的可能要 三到四年才能上手,假如笨一点,修个八年十年都搞不明白。“以前我们厂有五千 多人,光修车就一千多人,现在算上办公室的,统共加起来也就一千来号人。我也就再干几年,退休了,也就完了(结束了)。”
离开机车厂,我又回到矿物局的办公室。恰好之前托邻居联系的一位卖力对外宣扬的事情职员有空,说可以和我聊聊。在这之前,由于没有办法查阅矿物系统的档案,邻居曾发给我一份从她那里得来的夹杂部分抚顺电铁历史的演讲报告。刚一见面,她就说道,“现在系统记录的历史,也便是新闻里报告里讲的那一些,但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帮你回顾回顾。”
“我在煤炭博物馆看到了那辆日本产的老电车,那批客运电车都去哪了啊?”我直接抛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没想到她的回答瞬间让我抱负破灭:那些电车都报废了,不是按照工业古董的逻辑保存,而是直接作为废品报废了,就和淘汰的二手汽车一样。我又问起,当年刁亦男导演拍摄《白日焰火》的时候,情形是若何的,毕竟在电影里还有着电车行驶的画面;不过可惜,她并不知道这部电影,更对那时候的事情没有印象。
107号车正面
“不过,前几年还有人来拍电影呢。就在矿务局站那的电铁桥,我们还去当群众演员来着。”说到这,我溘然想起在网上看到曾经与101 同款的满铁电车被剧组借去拍电影,于是连续追问。她想了想说道:“拍电影那辆便是博物馆停着的那辆,这个车还有一台被拉去沈阳的博物馆(沈阳铁道博物馆)了,然后可能机车库那还有一台。别的就都没有了,就这仨了。”
听到机车库,我再次抱着末了试一试的心情,从矿务局开车驶向了那里。开着车走在五年前我步辇儿走过的路上,我尽可能地放慢速率,想要看看这里是否有什么变革,可除了道口的废品回收站看上去买卖更好了——废弃的沙发和柜子乃至堆到了路上,其他险些没有变革。
我停下车,穿过铁轨沿着矿坑边往深处走,又是一个阳光毒辣的8月午后,但矿坑看上去却不似过去迷蒙。或许是近些年持续进行的防沉陷和绿化工程起了浸染,也或许是这里彻底歇工了的缘故,空气质量彷佛好了一点,可周遭依然不是什么令民气旷神怡的景致。绕过那个也和五年前没什么差异的红砖房,我终于看到了一辆漆皮爆裂、门窗破碎的浅蓝色101型客运电车,车头的编号是107。
我走到近前看着这辆废弃已久的电车,只管它残留的漆色蓝得犹如晴朗的天空,但破碎的漆皮背后露出的赤色铜锈却沉默地记录着它经历的每一场风雨。我本想看看自己是否还有在博物馆时的运气,找一扇还打得开的门进去看看,但看到它已经七零八碎的门板和看上去立时就要掉下来的脚蹬,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把手机透过掉落的门板伸进车内,用摄像头代替眼睛,看到的依然是脱落的灯罩、满是灰尘碎屑的地板和同样起了漆皮的座椅。
没有人知道,这一辆末了还停在抚顺电气铁路系统上的客运电车,末了是会被拉到博物馆、变成拍摄道具,还是被扔进城郊的废车厂作为垃圾报废。或许已经没有人想再管它,它会一贯停在这里。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嘉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