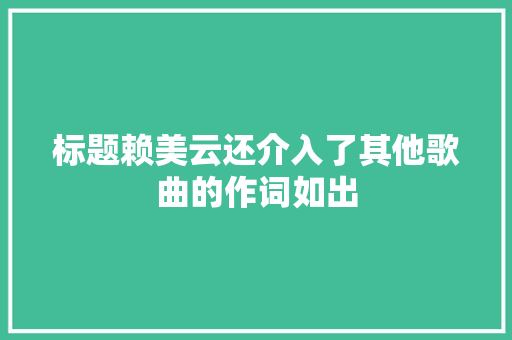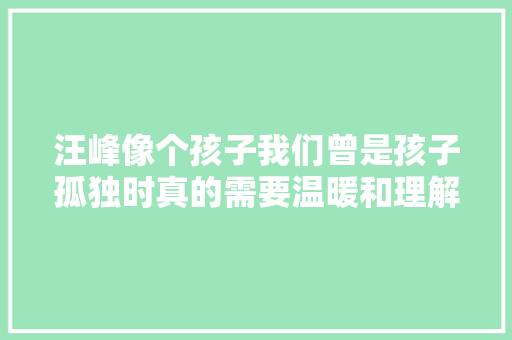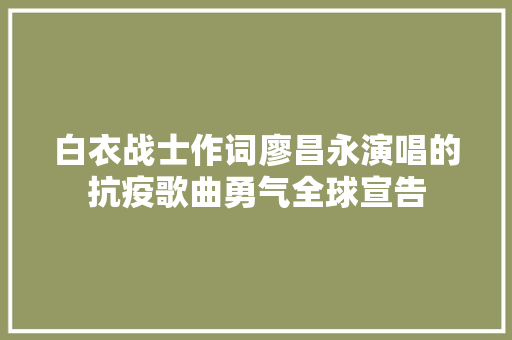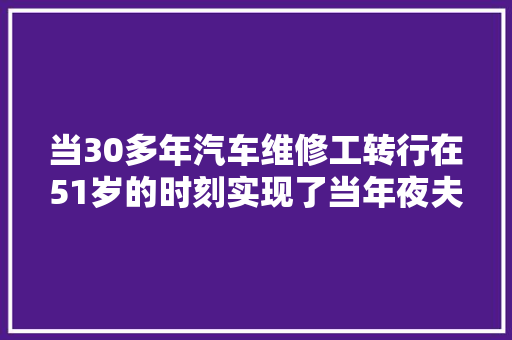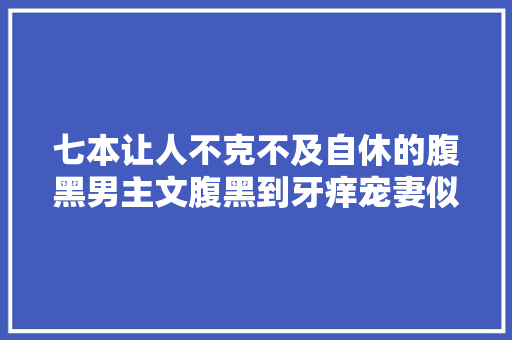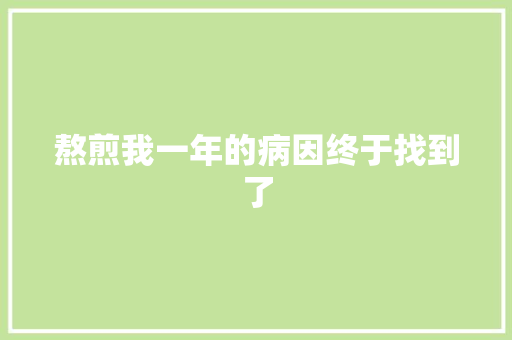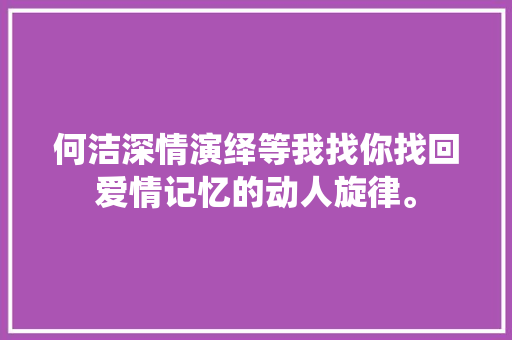人们在感情聚拢的时候最惦记的还是家乡,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候都会想起身乡。最惦记的是冬天麦地里的冰凌花,让清晨的太阳反射出亮眼的光芒。虽然野草野麦不多,但是不上学在家便是这个活。冬天里的风把光洁的路面吹得真干净,能更清晰的分辨出远方的路面与路旁桐树颜色。愿望着终年夜,也不知道终年夜能否顺着这条路走向远方。
晚上透过微开的门,电灯泡下粉条的人手里晃动的漏瓢,顺溜的流下粉浆和出出进进向外架子上架粉条杆的年轻人。清晨架在空地里拿起棒槌碰碰啪啪的锤击冻,结实的象铁板一样的冻粉条。一趟趟绳子扯到树上,与人一样高挂上一杆杆锤散的粉条。日光下一直的滴水,到了中午粉条蓬松开来,白白悄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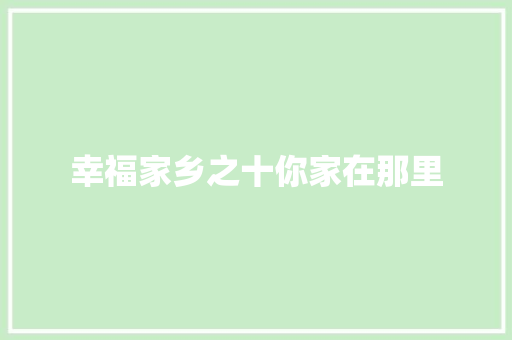
傍晚塑料布或布单子铺在架子车上,兜了粉条拉回家去。背起锄头锄地岭麦,背揽化肥种豆种玉米。烈日当空还是微雨蒙蒙,狂风吹还是头顶乌云飞。掂起铁锨浇地拉土拉粪撒粪。寒风里还是夜漫漫,秋雨绵绵泥泞地,还是口感舌燥年夜肠告小肠,晒黑了的肩膀被喇伤的口子火辣辣疼。
都过去了,早都过去了,没有这个日子了。但是我还会想起明月、寒冬的冷月、秋夜的亮月、满天的星星。你是哪里的?我是王楼的。你们庄不大?不大。你们庄可偏是吧?不偏,有点偏。愿望着终年夜,终年夜了可以挣钱,有钱花。要多少钱?五块钱。人家都缴了吗?都缴了。
瞥见那双结满茧子的粗糙的手,逐步的打开快折叠成一条线的五元钱。我一贯以为天下的手都是这样的粗壮结满茧,这双手与粗糙不挨边,这双手拧过我的脸,这双手拉过我的手,这双手每年去割麦、去锄地、去拉楼、去拉车、去采摘菜、去烙馍、去煮饭,这双手抹过我的眼泪也抹过她的眼泪,扶着我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农活。
你是哪庄哩?我是王楼哩。您庄收鸡子多吧?多哩没活干。您家在哪里?我家在王楼。小时候想终年夜,终年夜怕长老。东地的谷子沉甸甸的,东沟的高粱红了,叶子红了,穗长得与沟沿齐了。70多的老汉肩上搭个毛巾,拎着锄头,不才午的骄阳下锄芝麻地。
王楼的历史50年前也就100多口人,100年前估计也就几十人,200年前估计也不多,300年前也可能没有这个村落。王楼是个家,由于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光阴。由于偏僻经济弗成,富余程度就弗成。由于是个家拴住了奋斗的腿,由于把它当成了家拴住了奋斗的翅膀,出不去就象在大山里两条腿迈不出去这个大山。
家乡就像鹞子线又把远方的游子拉回来,愿望着疫情过去早日回到家乡。老了去世了长眠在麦地里,人总要去世的,关键是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值得回顾的。青青的麦子露出新苗,麦苗暗绿在寒风里簇拥着。春天里翠绿的麦苗在东风里摇荡,逐步的抽出靓丽的麦穗。夏天里桐花一落,麦穗充浆逐渐麦苗变黄,麦穗逐渐沉甸甸起来。
你家是哪里的?我家是。未语泪先流是吗?那个远方的家家里还有谁?那个远方的家槐花树还在吧?那个远方的家是谁的家?门口的杏花树春天来了还是第一个着花,夏天里结了黄色的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