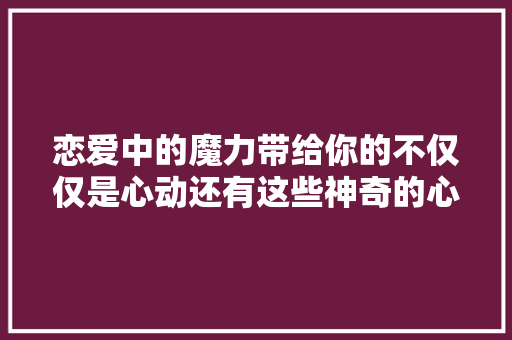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场盛行病已经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无论是好是坏。他错过了在Chapultepec公园闲步的机会,就像他为自己取消的课程感到高兴一样(他一点也不喜好自己刚开始的学校生活)。不管若何,躲避病毒总比躲在天花板或冰箱里更合理,就像他和捉迷藏时常常向我建议的那样。或者是像我向他建议的那样,躲进圣经或莎士比亚全集里去。以是我们挤在桌子底下,假装发出恐怖的恐怖尖叫——但理论上,那一刻我也确实感到恐怖。
自重新冠爆发以来,我们成年人对此已经说过、抱怨过太多,然而对付刚认识这个天下不久的小孩来说,这场Pandemic(盛行病)对他们而言,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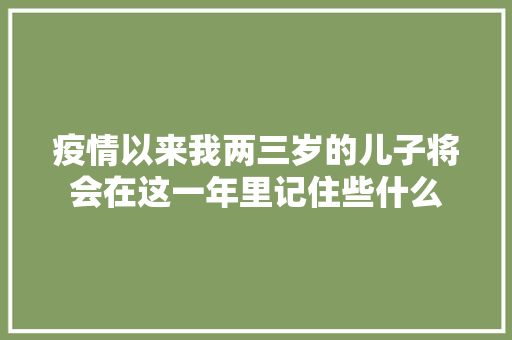
我儿子会记得这恐怖的一年吗?我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虽然有时我会乐不雅观地见告自己,他还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但更多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到十分不安的。当我想象或以某种办法知道,这样一个才仅仅拥有三年经历、29磅重40英寸高的、彷佛活得比我们更负责更有代价的、我们看着他终年夜的小生命,在不远的将来会忘却险些所有他在过去所经历的统统,这我们固执地坚持称之为现在的统统,是多么奇怪和悲哀。
可能从某一个成年过渡期开始,我们很随意马虎假定自己的影象开始于3或4岁旁边——换句话说便是,我们根本记不起任何在这个年事之前的事情。但是任何抚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当他们3岁乃至2岁时,他们会记得上周或去年夏天所做的事情,而这些影象是非常纯粹的,不是之后我们说给他听而被植入的影象,而且这常常让人惊异——至少当我儿子回顾起最初对我来说彷佛不值得影象的事宜或事宜细节时,我会感到十分惊异。
当我们想到那些我们抹去、忽略、失落去的岁月时,我们都会产生一些感情或不安。当我们才5天、10个月或2岁的时候,那时一整天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我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会常常听到父母说:“我教你怎么走路、我喂养你终年夜,你拥有的统统都要感谢我。” 我们可以凭直觉或想象父母画中所提到的那些年我们极度依赖他们时的样子,但实在只有等我们自己也做了父母,被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折磨得没法好好睡觉时,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我们从未感谢过,也无法感激的关怀是什么样子,由于我们根本就不记得它。
如果我们像Jorge Luis Borges笔下著名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的人物角色Funes那样拥有可以记住统统事物且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们的生平就会被无尽的怨恨和自发逼迫性的感激之情所麻痹。这种神秘的童年失落忆症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忘却了所有我们可以评判父母的主要成分。当然,如果我们忘却了从粗心大意和轻忽中学习到的教训,情形则会更糟。影象被摧毁或净化,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塑自己,重新开始,惩罚,体谅,发展。
“多年来,我一贯声称我能记得自己出生时看到的事情。”我在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开头读到,从某种程度上说,整部小说都是从那句绝妙的话中流出的。三岛的角色选择相信或发明一种独创的、绝对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完美地浮夸了这种想法,这种我们创造自己影象的想法对精神剖析来说是如此宝贵。我乃至认为三岛在这里建议我们须要自己去创造影象,而创造影象又适值是文学写作的基本组成部分。
墨客 Robert Lowell 出生于1917年,但他通过母亲的影象和条记本,开始详细地展开关于他所说的“美国参战,我母亲结婚”这段他还没出生时的韶光段里所发生事情的想象。然后,他又加上了一句温顺而恰到好处的讽刺:“我常常很高兴,在我逐渐成型的那几个月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怪我。”当我20岁旁边的时候,我翻看那些相册,觉得到的不是高兴,而是耻辱——为自己或他人感到耻辱,但最主要的是,它很令人崩溃——不是由于照片显示了什么,而是由于我总以为他们向我隐蔽了些什么。
我不记得过去有没有想过相册里的照片揭示得太少了——我乃至以为它们彷佛太多了。我想象着我的父母在智利独裁统治最残酷的岁月里摆着拍照姿势,或者在相册里排列照片。我以为统统都太薄弱了,我也太屈曲了——什么都不记得,也不认识家庭故事所植入的场景,这些场景在任何情形下对我来说都是模糊的,总是那么无法触及,这彷佛很恐怖。
“你还记得你出生的那天吗?”我问儿子。
“我记得,”他撒谎说“你抱起我哭了,由于感到太幸福。”
贰心知肚明他根本不记得,我也清楚明白他不可能记得,但偶尔我们会玩这个游戏,我们会重复一段关于哭泣的对话。大概两年前我们就有过这样的对话——我试图向他阐明,眼泪不仅仅来自悲哀,由于有时我们会由于快乐而哭泣。我回忆起他出生那天,当我第一次看到他刚从他母亲的子宫里出来。我向他阐明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溘然哭了起来,但是由于幸福而堕泪。
那时,他乃至没法说一个完全的句子,但他非常喜好模拟声音。我们有时会用尽我们的储备,然后连续发明动物的欢笑和哭泣。我们会花几个小时来模拟一条狗的笑声,一匹马的哭声,游戏无限期地进行着,直到我们兴趣勃勃地迷失落在胡言乱语中:一只口吃的鳄鱼,一只打哈欠的喜鹊,一只打喷嚏的负鼠。
我手机里有1422张照片,我儿子险些涌如今每一张照片里。他出生于1266天前,这意味着我均匀每天为他拍1.12张照片。除此之外,还有他母亲、外祖母和他叔叔(他是拍照师)给他拍的照片,还有……溘然间,我想到他能得以见到这些照片,那些他母亲写的书和我写的书(他涌现得越来越频繁的书)。纵然他不涌现,他也仍旧潜伏在书中故事的背景中,这彷佛是不公正乃至很过分的。
我以为我们该当销毁这些记录,为新的遗忘腾出一点空间。还有其余一个抵牾却又明确的想法:最近我以为我彷佛在为他写作。我就像我儿子的通讯员,我假装在事情,而实际上我所做的只是在为我儿子写短讯。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道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写他将要失落去的影象,就彷佛我是托儿所的老师或是一些名叫Joe Brainard, Georges Perec或者 Margo Glantz的幼儿的秘书,帮助他们将来写“I Remembers(我记得)”。
1978、79年,我3或4岁时,我坐在沙发上,我父亲在阁下看电视上的足球赛,这时我母亲进来给我们倒适口可乐。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影象。当时不仅我的母亲,险些所有的女人都会照顾男人,在放着电视的客厅里,电视机永久开着,孩子们险些总是可以一窥电视里的天下,就像他们总是喝适口可乐一样。
“爸爸,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有电视吗?”我儿子问我。
“我不记得了,”我见告他“我想该当有吧。”
我和妻子同等决定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下才让他看电视,以是到目前为止他认为我们寝室的电视坏了。我和我妻子都不反对看电视,但我们不愿定我们能把握好这个度。我们偶尔会给他看音乐视频和照片,因此他有了他曾经是一个婴儿的想法。这彷佛让他领悟了他脑海中迢遥的过去和他所记得的过去之间的差异。更主要的是,每次他碰着一个新生儿,他都要我们给他看一下他自己的那些老照片,他会盯着它们严明地沉默着沉思。我提到他的沉默是由于他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一点也不沉默,而是一个说话极快的人,一个预言家,一个健谈的人。
我儿子最常常的毁坏行为是玩卫生纸,玩一长串神秘的游戏。这些游戏有时深不可测,相称抽象,充满舞蹈色彩。我知道天下上大多数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嗜好——如果他们出版自己的杂志,肯定满是对不舒畅的尿布的激烈评论和对断奶的谩骂,我相信他们也会用几页版面来写厕纸游戏,就像他们的体育课一样。
“这不是厕纸,爸爸,”一天早上,他在我的责骂面前含羞地说,“这是Confort.”(这是我们智利人所说的卫生纸,以Confort品牌命名,一个所谓的“通用牌号”。当一个智利人说出来时,有着非常精确和急迫的意义。)
我儿子是说墨西哥语,非常墨西哥化的那种,但那一次他用了我的母语智利语,意图吸引或谄媚我。
“我知道我要从Viejito Pascuero那里要什么礼物了。”他对我说,又用了一个智利人的名字,Viejito Pascuero是智利人对圣诞老人的称呼。
“什么?”
“一卷Confort”他回答。
那时才八月或玄月,离圣诞节还有很长一段韶光,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他的官方哀求,他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这个欲望。这是他唯一想要的东西,属于他自己的一卷卫生纸,这样他就可以在宁静中,在完美和自主的孤独中玩耍。然而,到了12月尾,他对厕纸的激情亲切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Ivan Turgenev的一个角色说过:“这便是孩子存在的意义——让他们的父母以为不那么无聊。” 如果这个笑话见效,那是由于我们方向于把和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看作是每天不断地自我捐躯。然而,在全体新冠疫情期间,我常常通过与儿子玩耍光降时缓解我的焦虑、愤怒或忧郁,彷佛他的存在不仅起到了消遣的浸染,而且还起到了抗烦闷或抗焦虑的浸染。
在所有涉及到父亲照料的事情中——用餐韶光当他的啦啦队队长、楼梯间的搬运工、衣柜助理、袜子匹配工、玩具垃圾网络者和浴缸救生员等等——个中我演出得最愉快,我相信也是最拿手的,便是小物件配音演员。个中有些很范例——可爱的长颈鹿,或者说各种口音西班牙语的手指木偶——还有一些很难拟人化,比如咖啡机、窗户、吉他盒、无处不在的温度计,乃至一些我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的东西,比如天平或者——哦,我最讨厌的高压锅。因此,病毒不仅是我们捉迷藏游戏中的分外客人,而且它也成为这一系列故事中的人物,由于没有更好的形容词,我只能把它归类为寓言。
我很喜好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里的场景,个中一个角色和一个巨大的加菲猫毛绒玩具说话时。我很喜好这一幕,由于它既风趣又严明。由于它是媚俗的(就像生活),也由于它是悲剧性的(就像生活)。
一天早上,我问儿子:“你梦到什么了?”。
“你梦到什么了?”几秒钟后他回答。
“一只会飞的长颈鹿,”我即兴编了一个。
“我也是,”他说“它很大,对吧?”
他回答得非常严明,彷佛梦的巧合是很自然的事情。
几周过去了,我们一起完善了长颈鹿翱翔的梦想,但它成为了一个相称现实的故事:她不再有翅膀,而只是乘坐热气球旅行。哦,天呐!
这对长颈鹿来说肯定是一个相称不舒畅的交通工具。
“你梦到会飞的长颈鹿了吗?”我儿子昨天又问我。
“是的,”我说“你也是?”
“没有。”
“那你梦到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我做了些梦,但我不记得了。”
“影象不是从过去组织起来的,而是从未来组织起来的”阿根廷精神剖析学家Néstor Braunstein补充道,“一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结果,相反,是影象的缘故原由。”
每天我都觉得到我儿子的变革。最近一个月来,他和其余五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师呆在一个小屋里,每天早上他都说他不想去,但他去了后又实在很享受;他须要那些不按他的节奏玩耍或舞蹈但能教他点东西的孩子,他们相互帮助,而且他们都以乌龟的步子离父母越来越远。大概是受这些孩子的影响,我儿子开始迷上毁坏遥控器了。我和妻子以为我们得在他会用苹果电视之前,就把电池给取下来。
但我太夸年夜了。他没怎么变,真的没变。大概我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父亲,偶尔也包含着夸年夜。在书桌旁的一张小桌子上,我和妻子把我们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的草稿堆在了一起,我儿子就把这些草稿纸重新拿来画他的披萨和各种星球。本日早上,他给我展示了一个绿色和粉色的星球,画得很不屈均,背面便是你正在读的这篇文章的一部分。
我认为屠格涅夫是对的,这没有抵牾:父母的存在是为了娱乐他们的孩子,而孩子是为了让他们的父母不感到无聊(或焦虑)。这些是互补的想法,也容许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幸福,或爱,或身体怠倦,或所有这些事情同时进行。
现在,当我听着痛楚的晨报时,我以为我得去叫醒我儿子了——他常日在6点乃至更早的时候醒来,叫醒我们。但现在已经快7点了,他还在床上,我想立马去叫醒他,由于我很无聊,由于我很焦虑。
Alejandro Zambra是小说“Ways of Going Home” 和“The Private Life of Trees”的作者, 他最近的一部小说“Chilean Poet”将于2022年初出版。英文原文由Megan McDowell翻译自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