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校长将其在北平结识的几名“月牙派”故友聘为教员。按以往记述,“月牙派”教员是校内学阀,平日干涉校务,致使学生在1932年夏发起抗议,而杨振声则被指为“滥用私人”,并在校内“大同盟派”及“何思源派”的排挤下与数名“月牙派”背景的教员相继离职。
但实际上1930年代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内教员关系亲睦,杨振声离职的缘故原由紧张在于学生涯动及政府方面的压力,并无来自教员的“排挤”,而所谓“大同盟派”亦属子虚乌有,这种派系之争的传言紧张出于学生反抗策略的须要以及学运领袖晚年的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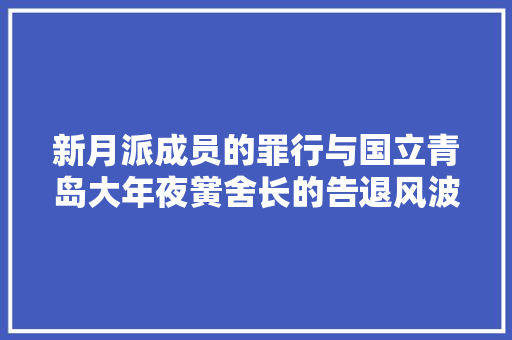
本文出处:《近代史学刊·第21辑》,马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近代山东高档教诲发展缓慢,省内第一所国立大学——国立青岛大学直至1930年秋方才成立。学校规模有限,然而“科研勤奋,校风朴质,温古崇新,无学术门户之见”,各教职员一贯关系融洽。不过1932年6月,部分学生因不满校方修正学则而发动罢课罢考,这次抗议持续两个月,导致杨振声校长辞职,多名教员离校,青岛大学(以下简称“青大”)遭遇不小打击。
根据部分当事人的回顾,“六月风波”紧张针对“月牙派”西席对校务事情的干涉,同时涉及校内“大同盟派的赵太侔”、“山东教诲厅长何思源派的杜光埙”与“月牙派”的内;“赵太侔跟何思源一起把杨振声挤走,赵太侔就当了校长。那种社会,你不挤掉他,你也呆不下去。”
不过,学生与“月牙派”教员以及杨振声本人的争执起因为何?所谓“大同盟派”、“何思源派”与杨振声的内又是否存在?这些是否为杨振声离职的缘故原由?以往学人在谈论杨振声以及青大“月牙派”时重在阐述其办学实践和日常活动,涉及杨振声辞职的缘故原由以及学校内部的派系问题时每每语焉不详,或直接引用上述当事人的说法后大略带过。本文将对青大内部派系的缘起、互动以及杨振声离职的详细缘故原由进行详细梳理和稽核。
“月牙派”进入青大
自1920年代以来,媒体对学界拉帮结派的官僚化方向不无讥评,尤其对付长期把持北大的“太炎弟子”颇多诟病。因而某位学人一旦被论敌冠以某派系的“走狗去世党”,切实其实趋附者众,避之唯恐不及。于是,鲁迅不得不一再澄清自己绝非“某籍某系”,顾颉刚宁肯就职于教会大学,也只管即便避免与同学故人故友共事,以免招尤纳侮。但一样平常而言,当时文艺界及教诲界为便利起见,常习气于将某些社团或报刊同人统归为“某某派”,纵然社团内部年夜家见地态度不尽相同。
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方令孺、费鉴照等学者先后来校任教,他们即所谓的“月牙派”教员。当时学生中间还流传着“月牙派经办青大”之类说辞,王林即王弢,李林即李仲翔,两人是1930年代青岛大学的学运领袖。可见其地位之高。那么青大校内的“月牙派”之名从何而来?这与他们此前的经历有关。
“月牙派”最早得名于徐志摩、胡适、丁西林等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成立艺术团体“月牙社”(社名源自泰戈尔的《月牙集》),社员以《当代评论》及《晨报》各种副刊为辞吐舞台,揭橥新诗、政论、散文或译作,倡导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闻一多留美期间,在纽约与赵畸(字太侔,北京大学毕业生,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后任青大教务长)相识,两人1925年6月结伴返国后,一同参与创立北京国立艺专。
恰在此时,闻一多因向《当代评论》投稿而结识该杂志编辑杨振声,两人成为好友,随后闻一多又加入月牙社。1926年1月,闻一多在致梁实秋信中称“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蛰、赵太侔、杨振声等。国家主义的同道中有一样平常人也常到我家里开会,月牙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四子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
同年4月,闻一多、杨振声、徐志摩创办《晨报·诗镌》,《诗镌》停刊后,闻一多与赵畸续办《晨报·剧刊》,杨振声、梁实秋均曾为《剧刊》供稿。不久,北京教诲界爆发“八校欠薪”风波,各校学潮不断,政治形势日趋紧张,闻、梁、赵、杨四人先后离京。1928年3月10日,《月牙》杂志在上海首刊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先后担当主编,闻一多还将其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心大学)的学生费鉴照和陈梦家的文章推举给《月牙》揭橥。
闻、梁二人的政治及学术态度,充分反响了月牙社成员的普遍取向。闻一多从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留学美国期间,他与好友梁实秋及部分中国留学生曾在芝加哥聚会谈论,“认为现在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聊天下一家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空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厉行自由民主之系统编制,推戴人权,主见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之共产主义”,末了与会诸君成立一个疏松的团体“大江会”,“崇奉大江的国家主义”。“大江”即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返国后,闻一多依然坚持此态度,并与中国青年党人来往频繁。在写给梁实秋的信里,他称中共党人为“赤魔”。梁实秋晚年曾回顾,“一多对付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冲突与斗争,虽非积极领导的分子,但是确曾躬与其役”。闻一多对阶级斗争不雅观念和共产主义者的排斥一贯持续到抗战后期。
1927年1月,梁实秋在《复旦旬刊》创刊号揭橥《卢梭论女子教诲》,梁认为男女在“自然”上便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以是当代人纵然主见女子经济独立、可以做“时髦女子”、可以做生意从政,纵然女子在这方面比男子做得还好,“她已失落去了她的女子特性”。该辞吐在上海文坛激起轩然大波,鲁迅1928年1月起接连在《语丝》揭橥《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拟豫言》等文章指斥梁实秋,鲁迅好友郁达夫也在《北新》半月刊揭橥《卢骚传》、《翻译解释就算答辩》等文章,暗示梁“多读几年卢骚的书再来批评他罢”。此后直到1930年代中期鲁、梁及双方支持者又为“文学的阶级性”、“硬译”等问题论战不断,由学术辩论发展到意气之争,相互攻击对方“拿苏俄卢布”、“成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的“论敌”,并不但鲁迅一人。梁氏留美归国后,致力于宣扬其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倡导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对时下部分文人颓废腐败的生活办法颇为不屑(紧张指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他认为:“在我们中国‘文人无行’已成为一句针言,假道学的口吻固然令人讨厌,真荒诞的行为岂是应得鼓励的?”缘此,1927年春梁实秋在上海编《时势新报·青光》,以漫画形式攻击张竞生的《性史》,梁实秋认为此事并非针对张本人,而是“当时冒张师长西席之名而印行的《性史》有十几册之多”,而且上海不幼年报,“不是鸳鸯蝴蝶,便是低级意见意义”,亦是《青光》的批评工具。但张竞生对此大为不满,遂在自己主编的《新文化》月刊上以极下流之辞攻击梁氏。
此外,梁实秋的论争文章大多揭橥于《月牙》,而胡适、罗隆基也在该刊揭橥鞭笞一党专政、倡导自由民主的文章(后收入《人权论集》),招致国民党当局不满,不久《月牙》便被迫停刊。虽然梁实秋对自己被归为“月牙派”感到啼笑皆非,梁实秋后来在台湾回顾,“月牙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他们不过是一起办杂志的一伙人,并非一个有组织有共同主见的团体。但在1920—1930年代,《月牙》杂志同人与创造社、左联及国民党当局都“结下梁子”,备受攻击。直到抗战期间,梁实秋与左翼文人(他称之为“左翼仁兄”)仍不断发生辩论。
1928年,闻一多经王世杰之邀来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长,不过武大在1930年夏爆发学潮,闻一多成为被攻击的工具,无奈辞职赴沪;正在上海任教并主编《月牙》的梁实秋,亦陷入沪上文坛的笔战,不堪其扰。此时,两人的故友杨振声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正在沪为学校物色教员,在杨氏力邀下,闻、梁携手来青,分别主持青大中文系与外文系的教研事务。两人与随后到校的方令孺、陈梦家、费鉴照等教员,之前均与月牙杂志社有或多或少的交往,被学生称为“月牙派”教员。
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在京沪各地的经历,多少影响到三人对青大教员的甄选及治校风格。杨振声虽非月牙社同人,但一向与“月牙派”及“当代评论派”诸君交好;另一方面,杨振声与鲁迅素无交情,与左翼文学家群体保持一定间隔。杨振声的成名作——小说《玉君》得到“当代评论派”成员陈源的高度赞誉,后者称之为“中国新出的最有代价的书11种”之一;而鲁迅并不认同《玉君》“撒谎话才是小说家”的叙事办法(但对杨氏其他作品如《渔家》则予以嘉赏)。
1930年冬,废名想在青大谋一教职,托恩师周作人致信杨振声求情,此前周作人曾向杨振声推举杨晦被婉拒,便不想再碰壁,又写信给俞平伯请其帮忙。1931年1月,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也收到废名的乞助信,但他直接劝其打消去青执教的想法。学人多以此事证明杨振声聘西席“不徇私情”,但废名素与“语丝派”人士过从甚密,加之脾气古怪,难免不为杨振声所喜。与此同时,赵少侯、沈从文等曾经《语丝》的“论战工具”——《当代评论》撰稿的学者却陆续被杨氏延聘,闻一多也将自己的好友及学生招徕至校。
“月牙派”教员在青大校园声誉甚高,不仅校长杨振声、教务长赵畸与他们关系密切,全校教职员亦大多方向“月牙派”。他们秉承之前月牙社倡导的治学理念,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主见学生应埋首书桌、潜心学业,不应过多涉足政治、参与社会事务或党派活动。1931年7月,青大召开第23次校务会议,针对“每学年必修学科有三门不及格,或全学年所修学科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如何处理一事展开谈论,教职员中梁实秋等三人主见开除之,但经举腕表决后,终极颠末议定“每学年必修学科有三门不及格,或全学年所修学科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留级一年,四年中留级两次者,即令其退学”。
此规定施行不到一年,1932年4月学校第43次校务会议,又将该条学则改为“学生整年学程所修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此外,1931年底青大学生赴南京请愿归来后,闻一多曾主见开除请愿学生首领,虽然末了并未落实,但“月牙派”教员严厉的治学态度亦可得窥一斑。
国立青岛大学
杨振声受累“月牙派”
杨振声长校期间,青大曾经爆发三次风潮。第一次是1930年底反对甄别证书事宜,由于教务长张道藩找来军警干预,很快平息下去;不过,据次年青大参与反对“学分淘汰制”罢课活动的学生印发的《驱闻宣言》所讲,张道藩离校后曾表示关照军警者为闻一多,这成为学生责怪闻一多的另一项“罪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深感不满,相继赴京请愿抗议,青大全校学生当年底亦冲破各方阻挡奔赴南京请愿。梁实秋回顾道:
北方学生一批一批涌向南京,在南京也造成了纷乱的气氛,我们镇静不雅观察认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无法说服学生不这样做。学生团体中显然有所谓左倾分子在把持操纵,同时学校里新添了几个学系,个中教员也颇有几位思想不很平正的人物在从中煽惑。在校务会议中,我们决议开除为首的学生多少名,一多年夜方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
杨振声同情学生的爱国激情亲切,但又感难以向政府交代,便主动呈请辞职,后在教诲部挽留下连续长校。他并未狠心开除请愿学生,只是将几逻辑学生领袖以布告的形式记过了事。但闻一多和梁实秋在校务会议上处理罢课的严厉态度招致部分学生不满,成为1932年6月学运中二人的“罪状”之一。
1932年4月,校方修正学则,对学年课程不及格者予以重罚。此项决策招致学生抗议。在部分左翼学生看来,校方是“阴谋开除大批进步学生,并且逼着一样平常学死活读书而无暇关心国家大事”。此时,学运领袖将斗争矛头指向“月牙派”教员,指出“月牙派”曾经对学生借阅书本严加限定:
(“月牙派”)除了在讲堂上倾销反动透顶的英美资产阶级毒品以外,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撤消图书馆里极有限的几本马列主义的英文著作和中文的左翼文艺书刊。图书阅览室里原来有一部左翼刊物《新文艺》,这一期上有马雅可夫斯基《谈诗》一文的译文,支部用它作为培养赤色群众的武器,忽然有一天不见了,党团员以为收藏起来了,就问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说是被馆长梁实秋检讨出来禁止出借了。她并且指着堆在屋角的其它被禁止借阅的革命书本叫党团员看。
1932年5月,学运领袖在上海左翼文学刊物《文艺新闻》发文,称青大现在完备被“月牙派、民生派等国家主义者所统治”,学生在校园贴出壁报,抗议“月牙派”在图书馆内“清书”,将鲁迅、蒋光慈等人的著译作品“不下二百余种完备清出”,但“月牙派小说家沈从文和墨客陈梦家冒雨来看了之后,不到一个钟头,壁报就被撕去,代替的是吓的‘训令’,学校当局调遣一批走狗同学暗中调查办报的人,月牙派所施行的自由主义德谟克拉西,原来如此!
”
杨振声受到来自政府和学生的双重压力,5月初赴南京辞职,之后回北沉着养。闻一多受校务会议委托,来北平奉劝杨氏回校,杨、闻回青后,校中谣言四起,称闻一多北上是“逃走的”。学生在罢课示威之余,还印发《驱闻宣言》,声称闻一多“援引了好多私人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旁边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梁实秋曾回顾,罢课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写“闻一多与梁实秋”,还题了一首抗议闻一多的“新诗”:
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闻一多上课有“呵呵……”的口头禅。闻一多深感无奈,在给饶孟侃的信中抱怨:
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月牙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手,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险些不能安身……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月牙派……在这里我两人险些是自身难保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月牙派致之害人一至于此!
……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哀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个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月牙派而发的,由于从前已有过月牙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6月尾,因未得到满意答复,大部分学生在王弢等人率领下宣告罢考。而此时学潮针对目标已不仅是闻、梁,杨振声与教务长赵畸在部分学生眼中也已成为包庇“月牙派”的帮凶,必欲逐之而后快。罢课学生揭橥《全体学生否认杨振声校长并驱逐赵畸、梁实秋宣言》,称杨振声“职长青大,于兹二年,善政不闻,过失落彰著,耗费公款,滥用私人”,赵畸则“平居无建树之功,遇事起摧残之念”,梁实秋“与闻一多朋比为奸,操纵校务,欲以月牙派一手包办青大,对职务不谋效忠,对学生唯取压迫”,尤其痛斥赵、梁在上年底处理赴南京请愿学潮时的严厉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风潮,事先有中共青岛市委和青大地下党学生俞启威、王弢、李仲翔等人的精密策划,从偶尔抗议发展到集体罢考,均在学生领袖的操持中。俞启威1931年秋考入青大后,与中共党员王弢成为好友,两人互助发起海鸥剧社从事文艺活动。从《全体学生否认杨振声校长并驱逐赵畸、梁实秋宣言》的主题和文风以及当事人事后回顾看,其虽声称代表“我青大全体同学”,但该当出自李仲翔或王弢手笔。
闻一多、梁实秋之以是被罢课学生针对,连累杨振声一并受到鞭笞,关键在于“月牙派”教员严厉的治校风格以及对左翼文化的排斥态度,同关心国运的学生产生极大冲突。实在,“月牙派”教员平日在学校里与同事及大部分学生相处无碍。杨振声期间的三次学潮,教员中基本无同情罢课学生者,而学生中亦不乏“月牙派”的拥趸。梁实秋在青大授课极受学生欢迎,以至于学生联名劝挽其赴北大任教;闻一多被迫离校前,也有不少学生如冉昭德、臧克家、王前辈、许星园、李桂生等为其送行。实在,当年青大校内有《月牙》背景的人,亦非铁板一块。沈从文经月牙派骨干徐志摩推举至青大任讲师,但其在教员中较为边缘化,而沈氏创作的小说《八骏图》因有讽刺闻一多和梁实秋之嫌,导致几名同仁对沈不满,此种环境在当年青大西席群体中极为少见。
关于图书馆“清书”问题,最早传播此事的,便是青大学生投在《文艺新闻》里的那篇文章,连鲁迅也有所耳闻,但梁实秋晚年否认了“封杀鲁迅著作”的传闻,只承认将书架上的“低级黄色书刊”取去注销。当然梁实秋出于个人偏好,确曾采购大批莎士比亚著作及干系研究书本,因而有学者认为梁有无清空鲁迅作品及左翼书本之行动,直到现在都是一桩“迷案”。不过外文系学生郭良才当年可从图书馆借到柔石的《旧时期之去世》、阐述日本社会主义者生活的小说《恋爱与监牢》以及鞭笞成本主义制度的小说《密探》等书,或可间接证明梁实秋并未打消左翼书本。
因而“月牙派包办青大”之辞,紧张反响了“月牙派”与青大部分激进学生关于“革命救国”抑或“安心学业”两种取向的不合。当时的激进学生多奉鲁迅为精神导师,鲁迅对“月牙派”人士的鞭笞自然会对青大学运领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俞启威考入青大前曾是前上海南国社成员(南国社终结后,其成员多加入左翼戏剧家同盟),他来青后与“剧联”领导人之一的赵铭彝(也是前南国社领袖)取得联系,秘密成立“剧联”青岛小组。而海鸥剧社所演剧目多为“剧联”成员作品,可见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对青大学运的影响。
学潮平息后,闻一多、费鉴照、陈梦家陆续离校,梁实秋则在杨振声奉劝下留在外文系连续任教,但为“避嫌”起见,辞去了图书馆馆长职务。数十逻辑学生被“甄别”后开除(包括李仲翔及王弢)。而杨振声在被学生指为“滥用私人”,受到攻击后,连续三次向教诲部递交辞呈,终得批准,赴北平编纂教科书。
月牙派部分成员
所谓“大同盟派”排挤杨振声
前文提及的“大同盟派”,又称“孙文主义大同盟”或“中山主义大同盟”,是北伐前国民党中心党部北京政治分会成立的一个疏松组织。1920年代北京政局动荡、经济困窘,校内学术与辞吐环境日趋恶劣,不少学生同情革命,加入国民党。国共互助往后,在北京的不少国民党青年党员(多为学生)标榜彻底贯彻三民主义的政治主见,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成立“孙文主义大同盟”。
“大同盟”以郭春涛、王振钧等北大学生为代表,推戴丁惟汾、王乐平(国民党北京实行部委员)、路友于、顾孟余(北大教务长)等党内大员。该社团成员遍布各省(以山东和湖南人最多),一度多达数百人,紧张生动于华北和长江流域。1926年后,大同盟成员逐渐分解,路友于等人虽与共产党为敌,却也同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和“CC系”方枘圆凿,反对蒋介石的“清党”和“取消农工运动”,因而被“CC系”分子指为“准共产党”。1928年后,随着丁惟汾在南京政府逐渐失落势,“大同盟”成员星散,大部分加入改组派。
赵畸(1889—1968),字太侔(一字海秋),山东益都(今潍坊青州)人,1907年进入烟台实艺学馆专习英文,在此期间经丁惟汾、王乐平先容加入同盟会山东分会。民国成立后,赵畸加入国民党,1914年考入北大英文系,在校期间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黄凌霜、袁振英等人发起成立实社。大学毕业后回山东省立一中任英文教员,不久与杨振声等考取山东官费赴美留学。1925年返国后,赵畸在闻一多当校长的北京国立艺专任教并在北大兼课,其间与杨振声、闻一多等青大创办人过从甚密。
1925年后,在京大学西席纷纭南下,赵畸则远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心青年部秘书,参与预备广州中心美术学院。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赵畸在陈友仁部下任外交部秘书(此时闻一多在武汉政府下的总政治部短期事情),一年后转赴南京。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三天,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辅导委员会在泰安成立,赵畸任省党部常委。此后赵畸曾受何思源之邀入职省教诲厅,并短期兼任过省立一中校长及省立实验剧院院长。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赵畸担当教务长。
赵畸为“大同盟派”成员的说法,出自当年学运人物以及教员家属的回顾,难免夹杂一些意识形态和个人感情色彩。虽然丁惟汾与赵太侔同为山东籍国民党员,丁又是赵的“伯乐”,但目前尚无史料证明赵畸加入过“孙文主义大同盟”。若回到当年语境,实在不少史料反而证明,不仅青大教员中间并无“大同盟派”,纵然杨振声与赵畸二人亦无私怨。他们皆有山东—北大—留美的经历,返国后在北京共同为《晨报》编辑副刊并撰稿,又同时参与筹办青大。
杨振声长校的两年间,与赵畸、邓初(校医)住同一阁楼。杨、赵不仅事情上互助无间,私下亦时常与教职员酒聚。青大同人大多好文且嗜酒,“健饮之名几闻全国”,黄境遇时任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查《黄境遇日记》,青大教员有时乃至一周七天均有酒会。杜光埙(总务长)也是酒桌常客,省教诲厅厅长何思源亦时常自济南来青赴会。
1932年“六月风波”后,青大被教诲部终结整顿,罢课学生大部分在“甄别”后被开除。杨振声辞职得到教诲部批准,随后杨氏致信梁实秋,建议赵畸继任校长一职:
目前有两种主要问题,一为省府难堪,一为教员问题,关于省方,太侔若肯担当,协款及其他,皆可作为担当时先决条件,较弟为易(弟不能再有条件也)。省方若不肯除销大学,其条件必易办理;若志在除销,弟归亦为无益,徒自取辱。……弟在平与青一样,同时可稍不雅观望省府对此发展如何。
在写该信之时,杨振声已“同时有致太侔、之椿一信,劝太侔为校长,之椿为教务长”,他私下曾对梁实秋说:“校长一职一定要让太侔,由于对付他正在进行中的婚事将有决定性的助益。”所谓“婚事”指赵畸当时正在追求戏班后辈俞珊(时任青大图书管理员),“之椿”即吴之椿。按《黄境遇日记》所记,赵畸接替杨振声长校后,各教员依然酒会不断,杨振声还曾多次返青与赵畸及其他教员痛饮畅谈;此外,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即国立青岛大学)复校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振声还曾受邀担当山大北平校友分会会长。由于“孙文主义大同盟”成员在1930年旁边已星散各地,在青大校内并未结合为所谓“大同盟派”,纵然将赵畸勉强归为之前北平“大同盟派”之列,他与杨振声之间亦无内,学校面临的困难紧张在于省政府方面的压力。
从左至右,分别为闻一多、王统照、杨振声、梁实秋、苏雪林、萧红、萧军、沈从文、老舍、赵太侔、洪深。
杨振声的辞职原形
由上述剖析可知,杨振声不太可能是被子虚乌有的“大同盟派”挤走,而是另有缘由:
一是杨振声与省政府之间的抵牾。本文开始交代的所谓“何思源派”即是省政府方面的势力。虽然目前尚无史料证明杜光埙与杨振声“争权”以及杜氏是否属于“何思源派”,但青大校方与省政府确实在经费及学校方针方面存在较大不合。青大在法理上属国立大学,校长任免权归教诲部,后者却一向对其疏于关照;青大大部分经费由省政府包袱,而省方却无法问鼎学校管理,校内人事变动及发展方案基本由校务会议及教授会卖力;再加上省主席韩复榘非蒋介石嫡系官员,与南京政府同床异梦,这种局势导致中心政府、山东省政府及青大校方之间形成多重张力,也使青大历任校长(尤其杨振声与赵畸)在筹集财源方面面临诸多阻难。
虽然在杨振声任职的两年间,省政府一贯如数供给青大经费,但双方的争执始终存在。归根结底在于韩、何关注“本省教诲”(包括中小学、师范、职业教诲等)而杨关注“大学教诲”,尤其杨振声与何思源关系奇妙。杨振声长校的两年,“大学设在青岛,而省教诲之重心在济南,虽中间交通尚便,而声息不免隔阂,减少彼此间切磋之益”,何思源认为青大既然紧张由省政府供资坚持,则须回馈本省教诲。杨、何二人职务、态度、不雅观点不同,多次因经费与学校发展方案产生龃龉,杨振声逐渐萌生去意。
16年后,杨振声承认“我就为这名称的地方性太大(虽然我是山东人)而辞职了”。这一说法得到梁实秋文章的印证。梁实秋晚年回顾,杨振声曾对其透露“辞职的紧张缘故原由是与省方不恰”,“今甫曾很奇妙的夸奖何思源,说他长于做官。做官就不能不坚持官的态度,私人间友情所能发生的浸染自然就有其限度了,今甫属绅士类型,与官场中人不可能沆瀣一气”。
二是频繁爆发的学潮使中心、省政府对青大学生行为极为恼火,乃至打算停发经费;而学生更是寸步不让。在规模最大的“六月风波”中,学生最初将矛头指向闻一多、梁实秋等“月牙派”教员,不久又指向杨振声本人,并以罢课罢考相威逼,哀求杨振声辞职。于是形成政府责怪杨振声管理不力,学生认为杨振声“包庇”月牙派的局势。杨振声夹在中间十分难堪,且不被双方理解。在此双重压力下,杨振声索性辞去行政职务而回到北平教书。因此,杨振声在校内所面临的压力紧张来自学生一方,而非赵畸、杜光埙等教职员的排挤。
总之,青大的派系之争并非在教职员内部,校内虽有“月牙派”教员的存在,但他们与其他教员并无抵牾和内,其紧张反对者为左翼学生,由此连累杨振声辞职;而校内更无“大同盟派”一系。杨振声离职的真正造因,其实在于学生攻击“月牙派”时夹杂着对杨振声“滥用私人”的不满,以及无可避免的来自省方的压力。所谓“月牙派”与“大同盟派”之争导致杨振声离职的传言,是罢课学生出于斗争策略的考量所作的宣扬笔墨,不无浮夸色彩。
本文原载于《近代史学刊·第21辑》,原标题为“青岛大学‘月牙派’、‘大同盟派’与杨振声校长的辞职风波”,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张家豪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张进
校正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