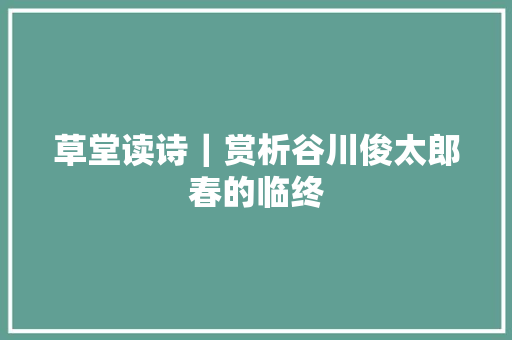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单读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这些天我们编辑部都在反复思虑的问题。我们不愿置身事外,但又不愿保持沉默。而在那么多实际的痛楚面前,任何的表达都显得太甚剩,任何的宣布都显得可疑。
而在过去的几天,单读编辑部受邀参加了“2017年喷鼻香港诗歌之夜”。在这里,我们仿佛找到了答案。这些来自天下各地的墨客,他们的国家和个人生活都从大大小小的危难中走来。

被封锁的,被遗忘的感情,被消解的权利,终极都会在文学、在诗歌中留下其印记,绽放出时期无法阻挡的创造力。
我们采访了经历过二战的日本著名墨客谷川俊太郎和流亡巴黎的叙利亚墨客阿多尼斯,并且在喷鼻香港大学美术馆谛听了他们的一场对谈。
谷川俊太郎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开口说话,由于他说“沉默是一种美德”。上前给他别麦克风时,他主动伸直手臂、抬高到与地面平行、坚持这个动作直到走开,仿佛习气性地为他人供应方便。身着朴素蓝布西装的他,符合人们对日本人的全部想象:礼貌、谦逊、充满秩序。
而年纪相仿的阿多尼斯却完备不同。他始终戴着礼帽和一条橘红针织围巾。他打量着房间里的每个人,目光偶尔落在俊秀女性身上。对每一位女性表现出欣赏,是阿多尼斯式的礼貌。
他们实在太不相同了。谷川俊太郎说他喜好统统飞在天上的东西。但阿多尼斯却在说:“所有批驳天空、守卫大地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谷川俊太郎说他从小物质优胜,生平都饱尝了自由。而阿多尼斯却说:“你所霸占的统统都在霸占你”。谷川俊太郎提问阿多尼斯的“私人生活”,阿多尼斯直接理解为“性生活”,在对谈中坦白了自己的初夜……
但正是由于这些不同,让他们的对话变得万众期待。他们的对谈被称作“世纪对谈”——媒体在形容任何主要的发言时,都喜好利用“世纪”这样的词汇。仿佛唯有漫长的韶光才能彰显其主要。但真正主要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作为墨客,如何处理那些细微的韶光点,这个中包含了历史节点,更包含了日常生活。无论他们的国家在每一场战役中处于哪个阵营,在经济发展中遵照哪一种模式,在精神上受到哪一种宗教的“统治”,在那样一个安谧的午后,在象征着原谅也同样象征着抗争的喷鼻香港,他们评论辩论着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都关心的话题:孤独、禁忌、和性。他们用诗歌去接管人类全部的行为,在这样一个时候,他们的诗歌大概能为我们供应一种处理现实的迂回路径。
2017年喷鼻香港诗歌之夜:阿多尼斯对话谷川俊太郎
主持:李欧梵
翻译:田原(日语)薛庆国(阿拉伯语)
李欧梵:这一次的诗歌节,主题叫做古老的敌意。这句话十分值得重新思考。这句话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句,那首诗是这么说的:“由于诗歌和生活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敌意”。尤其在一个环球化的时期,充满了战役和反面。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诗歌是否还存在某种古老的法则?在生活和诗歌之间总存在着古老的敌意,生活充满了苦难。诗歌的源泉是苦难,但是诗歌可以超越苦难,生活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中间存在着非常吊诡的暧昧,和谐或者纷争。
阿多尼斯师长西席和谷川俊太郎师长西席两位的诗,无论在自己国家还是天下诗坛,都已经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从自己的生活履历,诗歌写作的履历,来反省我们所处的时期。两位墨客都经历过战役,阿多尼斯师长西席经历过流亡。他们一直地写诗,希望能得到生命的灵感或者超越苦难的方法。这个世纪对话,把时期的范围拉长,讲的是二十一世纪,也会横跨到二十世纪。
请两位墨客各自先容自己的履历。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墨客生来便是宗教的反对者
阿多尼斯:首先感谢北岛师长西席和他的朋友,让我们在这里相聚。今天主题是古老的敌意,这个话题本身就很古老,但是又有现实的意义。我们作为墨客,有必要重新核阅一下词语的意义。比如当我们谈到诗歌和现实的敌意的时候,这个现实到底是指什么?是政治现实,经济现实,还是我们存在的现实?只有确定了词语的意义之后才能对这个话题进行深的入谈论。有人说现实不仅仅是我们见到的有形的现实,也是无形的事物,也是一种现实。
第二个,诗歌到底是什么?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诗歌或者创作诗歌,是再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另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在诗歌的层面上,我们见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以是通过写诗能够使我们看到我们所看不见的事物,认识到我们如果不写作就看不见的事物。比如说超现实主义墨客认为看不见的现实才是现实,他们认为诗歌该当写作现实之外的更高的现实。对付我来说,阿拉伯的现实,伊斯兰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或者美国的现实是完备不同的。纵然在同一个时期,也有多个层面的现实,或者不止一种现实。我本日要谈的是我本人在这个时期我所生活的现实,以是我更多谈谈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现实。
每个文化都有一些核心,或者是核心的身分,阿拉伯文化的核心是诗歌和宗教,这两者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宗教是阿拉伯主流文化或者系统编制文化赖以存在的根本。宗教代表可见的现实,代表权力,代表对其他事物的排斥,它淹没了阿拉伯文化里具有创造力的事物。历史上一贯存在伟大的思想家、墨客和作家,反对这样的现实。在全体阿拉伯文化或者诗歌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一位伟大的墨客,同时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教徒,所有伟大的墨客都对宗教持批驳质疑的态度,同时宗教也是反对墨客的,因此可以说阿拉伯墨客生来便是反对宗教的现实。
刚才讲的是历史上的情形。从理论或者现实来说,对我来说,写作的宗旨便是改变而非沿袭,写作是创造,是变革。诗歌只能是站在现实的反面,无论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墨客通过自己的写作想象可能的事物,或者更好的事物,而非现成的事物。诗歌犹如爱一样,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最深刻的表现,一种更伟大的表达。人从实质上来说便是墨客,由于人生来便是改变者,而非守成者。人的更有代价的事情必定是改变生活的,是改变性的事情。
故意义的诗歌一定是不断创造跟现实的不一致,超越现实。诗歌的时期不是历史,跟历史时期不一样,跟数字时期也不同。本日我们读罗马史诗,读古巴比伦史诗的时候,这些诗歌作品既是几千年前的作品,它表达的意义仍旧具有当代性。以是统统有益的创作必定是超越时期的,因而也是也是超越现实的。
本日创作的问题,或者文学的问题,我认为紧张表示在有一种盛行的不雅观点,把文学或把诗歌当作对现实的再现。如果你追求诗歌对现实的再现,犹如把一壁镜子贴在脸上,你实际上看不见自己的脸。统统旨在再实际际的努力,本身就在抹杀或者遮蔽现实。
谷川俊太郎:古老的敌意该当超越措辞
李欧梵:刚刚阿多尼斯的发言充满了诗意和吊诡,已经让我们开始寻思了。下面请谷川师长西席发言。
谷川俊太郎:本日的主题叫古老的敌意。我听到这个题目后首先想到的是跟我离婚的太太的面孔。我的第三个太太,她已经去世,她是个散文作家同时也画画。中国读者可能知道,佐野洋子。由于她常常说,在阅读我的作品的时候,会感想熏染到敌意。这可能是散文和诗歌的差异,但是她的画里面充满了散文的精神,大概我的诗歌里充满了诗歌的精神,这种精神该当也有共通的地方。
在我跟我太太离婚后,我写了几篇散文反省我自己,命名为《现实措辞和作品措辞》,这两种措辞有天地之间的差别。比如我们在创作作品时利用的措辞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利用的措辞,只管都这天语,但是有根本的差异。跟第三个太太恋爱的时候,我写过一首情诗给她。他后来拿到刊物公开拓表,但是她知道后大发雷霆,说我们的隐私不应该拿去公共空间揭橥。以是隐私跟公共之间的冲突抵牾是存在的。
我以为古老的敌意,该当超越措辞,从古代到本日,一贯是存在这种日常和作品之间的冲突和抵牾的。阿多尼斯师长西席至今还没有日文版的诗集出版,以是我没有机会读到他的日文版诗集。但有一本书,是跟一位法国学者的对话,里面写的对付古兰经的批驳,我很受启示。对更多日本人来说有佛教、神道,但对伊斯兰教还是比较陌生,以是这本书对我的启示很大。对日本人来说不论是哪种宗教的信徒,都没有人禁止你写作的措辞。但我读他的对话集的时候,强烈地觉得到了非常明显和严厉禁忌。我想问阿多尼斯师长西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这种被禁忌的宗教环境中终年夜,这对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非常好奇。
阿多尼斯:在伊斯兰宗教里,统统创造都意味着异端
李欧梵:刚才谷川师长西席关于宗教的问题,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发挥一下。刚刚阿多尼斯特殊提到伊斯兰传统里,墨客或者创作性墨客永久是不满于宗教乃至对抗宗教的。这个传统彷佛在日本文化里是不太明显的。可是阿多尼斯师长西席面临很严厉的伊斯兰宗教上的压力,使得他的诗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我想问,从日本的美学态度来问的话,在阿拉伯宗教传统之下,是不是也有很多俏丽的诗篇,这些俏丽的诗篇是不是也能化解一部分宗教上的狂热?而墨客创作伟大的作品,这种艺术上的努力是不是在阿拉伯文化的历史上,有时候也受到宗教家的尊敬?
阿多尼斯:我们评论辩论伊斯兰话题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繁芜的话题。我们为了简便起见,每每把伊斯兰简称为伊斯兰,但伊斯兰不是一个单数,它实际上是复数,有多种多样的伊斯兰,有宗教意义上的伊斯兰,还有苏非神秘主义理解的伊斯兰,还有仅仅将伊斯兰作为一个文化框架理解的伊斯兰。而且我们还该当把伊斯兰和信奉伊斯兰宗教的人穆斯林区分开来。
我谈伊斯兰的时候,更多指的是权力、政治、制度性这个层面上的伊斯兰。纵然在这个最大略的层面上也包含两层,一个是伊朗层面的,一个是沙特所代表的伊斯兰,他们是完备不一样的。适用于个中一方的说法,对其余一方就完备不适用。
纵然在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意义深远的两场革命,一个是诗歌革命,一个是苏非主义和哲学的革命。诗歌革命最具有代表的是阿巴斯期间最有名的墨客麦阿里,他的一句诗是,天下上的人无非两类,一种是有头脑的人不信宗教,一种是虔信宗教但是没有头脑。
第二场革命是苏非主义和哲学层面的,这是更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传统宗教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对真主,对神的观点。对传统的正统派来说,神超脱于天下之外。但是苏非主义认为,神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内部。
苏非主义的其余一个意义便是对身份话题的哲学思考。按照正统伊斯兰教的说法,身份是继续的,你的父亲是什么,你的身份就必定继续父亲的,以是穆斯林生来便是穆斯林。而且天下是一分为二的,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或者是穆斯林和异教徒。但是对苏非主义来说,人的身份,是人在创造作品和思想的时候,他创造了自己的身份,身份意味着一直的创造,而且一贯处于变革之中,或者说身份来自前方,而非身后。跟这个有关系的是如何看待他者。
对付苏非主义来说,他者不是异教徒,而是构成自我的存在之一。由于如果没有他者,连自我也不存在了。苏非主义有一位墨客说过:纵然当我在梦中想象自己在旅行的时候,这个旅行也要经由他者才能实现。正统伊斯兰反对这种理解。因此在阿拉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诗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人被杀去世,还有更多人作品被点火。
刚才李老师问在阿拉伯历史上有没有有代价的作品,当然有,一贯有反对现实的作品,但是一贯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了,由于主流历史一贯是被政权书写的,而不是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日阿拉伯的现实,跟十四世纪以来的现实没有什么差别。对文学的审查,对创作的审查,不仅仅是当权者审查,而且审查变成了阿拉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身分。
我认为一神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建立在以下几个根本之上:
第一、先知,穆罕穆德是唯一先知,在他之后再无先知。
第二,先知所传达的真理是终极真理,先知之后再无真理。
第三,如果你是宗教信徒,你不能背离宗教,命运便是被处去世。
第四,连神灵都已经无话可说了,由于他把终极的话语对末了的先知说出来了。
以是按照这种理念,这个天下必定是完备封闭的天下,也必定是反对统统创造的天下。由于在阿拉伯语里,“创造”跟“异端”两个词拥有同一个词根,统统创造都意味着异端。以是你们可以理解我,为什么我说统统伟大的创作者必定是反对现实的。
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关于伊斯兰教的几种理解,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持有同样的不雅观点。作为穆斯林个体,在伊斯兰天下也呈现了非常多伟大的创造者,他们的造诣跟其他天下的创造者比较也绝不逊色。本日在坐有很多女性,我乐意提及一位精彩的女性,她是天下级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她已经去世,她便是一位阿拉伯妇女。另一位伟大的创造者,苹果手机的发明者乔布斯,他也是来自叙利亚背景。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伟大的创造者都不是生活在伊斯兰天下,而是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并不是从宗教文化中脱颖而出,而是从广阔天下中接管了文化,而成为伟大的创造者。
谷川俊太郎:神弥漫在宇宙之中,超越人的统统力量
李欧梵:刚刚阿多尼斯给我们上了非常宝贵的关于伊斯兰文化史。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华人间界里面,对伊斯兰天下的繁芜性和文化传统理解得太少,我们须要连续补课。特殊在环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背景我们都该当理解,不能再唯我独尊了。
我还是要说,在我有限的知识里,像阿多尼斯师长西席这样寻衅宗教威信的人不多。我非常赞许薛庆国师长西席提到的,他引用了一段阿多尼斯的诗句,大意是: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妖怪,两者都是墙,将我的双眼蒙上。这是非常故意思的寻衅,我对此感到崇敬。刚刚阿多尼斯师长西席提到,在阿拉伯文化历史传统中,神灵,君主,国家,部落,集体,乃至于父亲,都是高高地悬置在个体之上的,但是刚刚提到的我和他者的关系,没有他者就没有我,他者和我共同构成人的定义,这个非常靠近西方几位人文主义理论家的说法,我也很赞许。
下面我还想问谷川师长西席几个问题。谷川一开始就说想到已经故去的离婚的妻子。我立时想到最近读到的他的几首诗。各位如果看北岛安排之下出版的这套诗歌节的诗集中,有好几首谷川师长西席的诗都是爱情诗。我感到谷川师长西席诗非常有感情的墨客,一个有感情的墨客会重写抒怀的传统。
谷川的情诗给人一种非常温暖,当代人的觉得。每每使我想到里尔克和拉丁美洲几位墨客的作品。譬如说有一首诗叫《接吻》,我看到就觉得一阵暖意升上心头。我吟两句:
“一闭上眼天下便远阔别去/只有你的温顺之重永久在试探着我/沉默化作静夜/如约降临于我们/它此刻不是障碍/而是萦绕我们温顺的迢遥/为此,我们意想不到地融为一体……”
我以为非常温顺。只有谷川这样的日本墨客在日本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我们不妨把他的情诗和徐志摩的比较一下,差别很大。
以是我想就求教于谷川师长西席,想请您多讲一点关于抒怀传统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的诗歌传统从诗经到当代诗,根据王德威教授的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抒怀的传统,当然对付抒怀有各种不同的阐明。而在日本传统中,诗歌、小说、散文之间,是否有各有不同的意象,像中国古体诗一样,彷佛抒怀的时候只能写诗,不能长篇大论地写文章。散文的抒怀传统是从五四之后才有,我非常希望谷川师长西席能够跟我们阐明一下他自己的作品里面的这个抒怀传统。
我从谷川师长西席的先容里面理解到,最近在北大的一个活动上,提到谷川师长西席有一个“三不主义”,一是没有名片,二是不打领带,三是不接管任何政治家或有政治意味的大奖。我非常佩服。以是末了我想问的是,怎么样处理你抒怀的创作传统,跟日本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敌意或者紧张的关系?
谷川俊太郎:第一次天下大战后,很多日本墨客终于觉醒到,必须通过诗歌来表达思想。日本是一个高龄社会,我曾经给我的女性朋友讲,你们不要结婚,一个人很好,如果嫁给我们这种高龄的人,你们永久就要奉养我们,要付出很多。昨天有人问墨客在过着若何的生活,怎么个活法。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吃,洗衣服,整顿屋子,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阿多尼斯只管年事相仿,但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思考天下的办法也都不一样。我非常好奇,也非常想知道阿多尼斯师长西席的私生活。
阿多尼斯:让墨客评论辩论自己的私生活,这个实际上是对现实保持同等的做法。而我作为一个墨客,我是反对跟现实保持同等的。
李欧梵:谷川师长西席附和跟现实保持同等吧?
谷川俊太郎:当然不反对。在日本有私小说,完备写个人的私生活。日本有这个文学传统。如果这个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比较悲惨,这个小说的读者就会更多。当然所有的墨客都是贫穷的,贫穷的墨客中,确实也有写得非常棒的贫穷的诗。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贫穷的诗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有些墨客,通过买股票发财之后,那种好诗也不存在了。对不起,我彷佛跑题了。
我个人与阿多尼斯师长西席比较,宗教之间的间隔很大。但是这种间隔也影响了我们进入诗歌写作的抒怀性。我们小的时候,日同族里一样平常都有佛坛。我父亲是大学老师,他没有固定的宗教崇奉。我母亲毕业于基督教大学,我母亲在基督教大学上学的时候,偷过红葡萄酒,以是我母亲该当也不是一个正宗的基督徒。
我上幼儿园进的是基督教幼儿园,那时第一次知道了有天国和地狱。但是去我姥姥家,创造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佛坛,祖祖辈辈牌位都摆在佛坛阁下。在战役期间,每个家庭都要信奉神教,不信奉神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国民。我从小学读到的书中,最亲近的是希腊和基督的神,由于他们都保护人,他们都活得很自由。我该当是对禁忌很多的宗教没有任何履历。在终年夜之后,也读到了古兰经,还有圣经,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包括我,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上小学的时候,常常向神祈祷,我的父亲母亲不要去世掉。但这个神是什么神?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无神论者,总以为神有超越的力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现在我认为,神便是弥漫在宇宙之中,超越人的统统力量的存在。无论人类发明再多便利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自然。我的宗教不雅观大略地说,并不是详细的某个宗教,而是超越这些存在于宇宙当中的一种未知的超越性的存在。
我父亲曾写过一本书,他信奉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的不雅观点,是用科学的力量无法阐明和抵达的。我很好奇阿多尼斯现在有着什么样的宗教感情?
阿多尼斯:我是一个天然的叛逆者
阿多尼斯:首先,我个人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尊重统统崇奉各种宗教的人,对很多人来说,他都须要思考超自然,形而上等等这些关系。但对付我来说,我不是。
其次,在伊斯兰教里,统统在现世里被禁止的东西,在天国是被容许的。包括同性恋,在天国里就被容许。一个男人,进了天国还是一个男人,但女人在天国,就不是女人了,而是仙女,仙女紧张的浸染便是供男人取乐。以是按照伊斯兰教的不雅观念,穆斯林男人在天国里可以永生不老,可以永久享受性生活,由于总是有仙女陪伴。我建议你不妨试一试伊斯兰这种崇奉,到了来世永久有仙女陪伴。当然,我反对这种不雅观点。(笑)
你刚问我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宗教禁忌多的环境下,变成一个叛逆者。我也不知道,大概我天生具有叛逆性。你还问我私生活问题,我现在就跟你坦白吧。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次性履历。当时是我们村落里的一个女孩她迫使我在野外(发生了关系)。我也好奇,你的第一次性履历是什么时候?(笑)
谷川俊太郎:实在我问的私生活并不是性方面的,而这天常的个人生活。跟阿多尼斯比较,我的第一次远远迟到了。在伊斯兰宗教里,女人在天国变成仙女,奉养男人,太恐怖了。我原以为阿多尼斯跟我一样,都热爱女性,但我听了阿多尼斯的话之后,以为阿多尼斯不那么热爱女性了。(笑)